- +1
洞鉴|《地方与无地方》:一次对现代无根性的全面剖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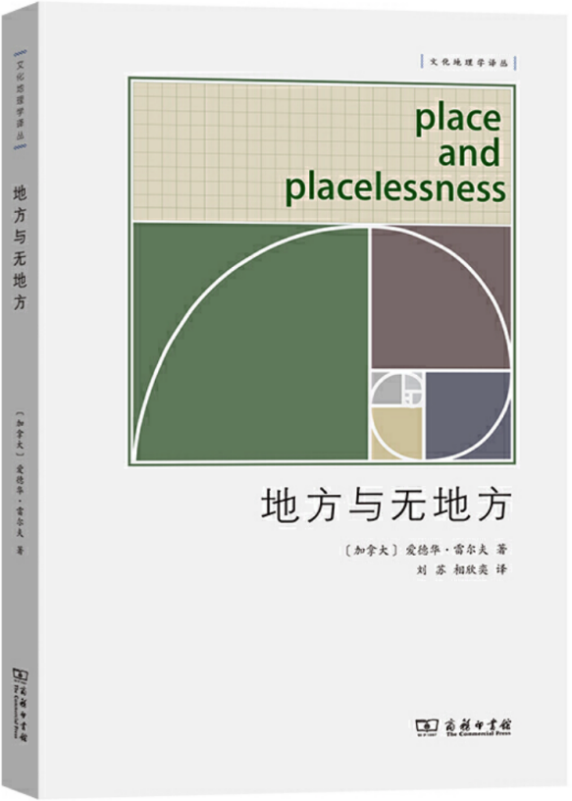
《地方与无地方》,[加拿大]爱德华·雷尔夫著, 刘苏 相欣奕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2月版
20世纪70年代,英美地理学界掀起了一股影响深远的人文主义思潮,即“人文主义地理学”或“人本主义地理学”。该思潮吸取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想,以日常生活为根基,着力探讨人的经验与地方的意义,涌现出不少以此为旨趣的人文地理学家,如段义孚、安·布蒂默、赛明思(Marwyn S. Samuels),等等。
其中,爱德华·雷尔夫在1976年出版的《地方与无地方》(Place and Placelessness)是该时期的一部代表作。地理学家大卫·西蒙认为,这部著作是人文主义地理学鼎盛时期(1970-1978年)最重要的十部文献之一。20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中文版。或因引介较晚,个中思想在中国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2021年2月,曹杨公园。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由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而在欧美,自M.M. 韦伯1964年在《都市场所与非地方的都市领域》(The Urban Place and the Nonplace Urban Realm)一文里提出“非地方”(Nonplace)概念以来,围绕无地方与非地方现象,学者已展开诸多研究,形成了较醒目的领域。其中突出的文献著作,还包括莎伦·佐金的《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权力景观:从底特律到迪士尼乐园》,马克·欧杰的《非地方:现代性人类学导论》,詹姆斯·昆斯特勒的《无名之地的地理学:美国人造景观的兴衰》以及段义孚的《宗教:从地方到无地方》等。此外,如J.N. 恩特里金、H. 科克斯、大卫·哈维等学者,也以论文形式,对无地方现象进行大量讨论。
正如城市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所言,当今“绝大部分的现代建筑都已失去了外观上的美感;呆板、单调,整个城市环境让人了无生趣。”上世纪中叶起,无地方现象已演变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其原因多在于现代性带来的同质化不断破坏地方的差异,使地方的意义逐渐丧失。这亟需城市规划、建筑学、地理学等领域去面对和解释。
雷尔夫创作《地方与无地方》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正值欧美的地方独特性被城市急剧发展所吞没,城市发展完全采用现代的模式与风格,被效率至上的价值理念引导。值此,雷尔夫说:“我创作《地方与无地方》这本书的目的,旨在描绘当现代性所具有的无地方把根植在地方之中的历史与意义连根拔起来的时候,我们所失去的一切。”

2019年11月,上海老西门即将拆迁的一片弄堂。
在《地方与无地方》中,雷尔夫采用了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哲学进路,来探讨地方本质,进而析解出无地方性。所以,本书不仅是着眼于人地关系(亲密/疏离)的地理学著作,还可以归入现象学与建筑学相结合的领域。
类似著作还包括诺伯·舒茨的《场所精神》,国内学者编著的《建筑现象学》与《现象学与建筑的对话》等。这些著作的共通点,在于沿循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进路,诠释地方(或场所)的本质,直指人的基本生存论问题,包括“无根性”问题。所以,这类研究对理解地方意义,以及如何维护且营造一个有意义的地方给予了重要启发。后文,我将围绕“无地方”概念做一浅释。

爱德华·雷尔夫

《地方与无地方》英文版封面
无地方
“无地方”是这本书的核心概念。什么是无地方?“无地方”是相对“地方”概念而言的。“地方”本质在于其本真性。雷尔夫写道:“本真作为一种存在的形式,其含义在于人对自身的存在所承担的责任具有完全的接纳与认同。”具有本真性的地方,是同人自身有着真真切切和紧密联系的地方。比如:“出生与成长的地方,目前居住的地方,有过独特搬迁经历的地方,我们也都深深关切着这些地方。”

2021年2月,上海长风大悦城。
换言之,这些地方都充满了意义(sense),而地方的意义“构建起了个人与文化的认同,也是人类安全感的来源,是我们由此出发的坐标,能让我们在世界当中找到自身的定位。”相反,无地方则是地方意义的消亡。
《地方与无地方》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对无地方的景观特征和背后原因展开了系统性分析,且诠释出其中的生存论原理。
雷尔夫指出,无地方的原因在于非本真性:“非本真的态度,是以封闭的心灵去面对世界,以及对人类身上多种可能性的不闻不问。”在非本真的地方态度中,一方面是个体在不自觉的主观状态下被“匿名的他者”所左右;另一方面是更加自觉与刻意的状态,关联着大众化且客观的人工世界——人们依据公共利益与决策来掌控一切事物,而大众的利益与决策又取决于人为设定的世界与同质化的空间与时间。前一方面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状态。“常人”总是沉沦于预先设定好的规则,并被其所左右;后一方面则指向实证主义的环境设计与场所规划。

2020年3月,上海人民广场。
在萨特看来,非本真的态度就像一名服务员,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拥有较高的天赋与才能,但其工作对他本人而言缺乏真实的意义,也很难感受到对工作的真实委身。所以,在工业化社会,大众价值观与缺乏情感的实证主义式的规划是造成无地方的原因。它使得“人对地方的深度象征意义缺乏关注,也对地方的认同缺乏体会。这种态度只是为了实现社会的便捷,对各种陈词滥调缺乏反思,也对知识与审美的流行方式不具有真正的委身。”
这样的态度在景观中有怎样的体现呢?
首先,雷尔夫指出了两种非本真的态度:“媚俗”与“技术化”。
所谓“媚俗”的景观,是指那些平庸、艳俗、能唤起甜美感受的事物,它们混杂在出售的纪念品和礼品中,还包括相关的家用品、音乐、建筑与文学,等等。“在那里,琐碎的东西被视作重要的,而重要的东西反而成了琐碎的,幻想变为了现实;本真性被贬值,而真实的价值却通过肤浅的价格、颜色与形状来衡量。”比方说,今天的旅游业让大多数游客的地方体验设定在规划的景点和酒店里,裹挟在批量配备的纪念品商店里,但游客本人却对踏足的地方缺乏真实的体会。

2021年2月,上海一处工地。
雷尔夫说:游客们“望着城市与荒野里的景色;他们置身于人来人往的集市与南方的诸海岛;他们凝视着庞贝古城的残垣断壁与巍峨的安第斯山脉;然而对于他们来讲,这一切都仿佛是过眼云烟,他们望不见这些事物的过去与未来,也体会不到它们的伟大理念。在这里,没有什么事物与他们相关,既无历史,也无应许。每件事物都只是单纯地杵在那里而已,一件一件地从眼前依次刷过去,就像移步换景似的演出,最后将观众留在原地。”
所谓技术化态度下的景观,隐含一个前设,即:空间是连续一致的、客观的,人在其中的行动是可被操控的。地方的差异和意义显得不再重要,地方也因其巨大的开放潜力被化约为单纯的地点,目的是实现秩序和高效率。这样的景观乃是借助大众化的方式被设计出来,像一套套崭新的高速公路网、贫民窟重建计划等,而这些事物与设计师本人之间是超然冷静的疏离关系。
同时,雷尔夫还指出,无地方的蔓延乃借助一系列媒介得以实现。这些媒介包括: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大型企业,以及涵盖一切的经济制度。
首先,大众传媒借助标准化的品味与时尚的蔓延,导致景观均质化。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媒体,减少了面对面交往的方式,将人们从地域限制中解放出来,由此导致共同体基于地方重要性的降低。所以,从事规划设计时,不会以具体地方的原则为基础,而是以大众的时尚品味为基础。可以是大同小异的郊区别墅群,也可以是市区里鳞次栉比的国际风格建筑,它们借助混凝土与玻璃架构,实现特定的功能与效率。

2021年2月,上海苏州河畔。
其次,由于政府与专业规划设计师依据大众文化批量生产出时尚品味的景观,地方被千篇一律打造出来,因此这些地方多具备“指向外部”的特征。换言之,“它们都是刻意用来针对外来者、参观者、过路人以及所有的消费群体。”
其中较典型的,是旅游业发展造成的大量外生型场所。雷尔夫说,这类场所包括:“从弹球廊道的魅惑,到拉斯维加斯式的博彩业,再加上艺术历史博物馆与休闲度假胜地;以及五花八门的休闲地;从国家的露营,到坐落在山间、湖岸或海边风景迷人处的奢华酒店”,其相似处在于“异国情调的装饰、艳俗的色调、怪诞的饰品、不加甄别的舶来风,再冠以世界上最流行的地名。”这类景观的突出悖论在于:尽管区域性的景观恰好是旅游业发展的动力之所在,但它们又被大同小异、随处可见的旅游建筑物、人造景观与虚假的地方所取代。
在大众文化浸淫下,还有几个更突出的景观特征。雷尔夫称之为:“迪士尼化”、“博物馆化”、“未来化”和“乡村都市化”。
其中,“迪士尼化”是指“将历史、神话、现实与想象的元素以超现实的方式糅合在一起,创造出怪诞且虚假的地方,这些元素都与特定的地理环境没有任何关系。”在雷尔夫看来,迪士尼乐园不仅是人们逃避枯燥乏味、腐化堕落的现实世界的避难所,也在一定程度上“以流行与媚俗的方式表达出了现代信仰,这种信仰相信人们能客观地操控自然与历史。怪兽、野生动物和历史在人们的操控下变得毫无威胁可言。在更深的层次上,迪士尼化似乎也是对技术成就背后人们态度的无意识表达。”

2020年3月,上海地铁口。
在技术支持下,这类无地方可以在全世界到处复制、蔓延,并与周围环境割裂。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体验不到追逐梦想的艰辛与实现梦想的成就,相反,梦想只是以一种直接刺激的方式提供的享乐品,因此这样的地方同样是非本真的。
而“博物馆化”是“迪士尼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对历史进行保存、重构并理想化地建构。”比如,对历史上的村落、古镇、城堡实施改造和重建。因为博物馆化的地方,乃是为迎合过去岁月的完美意象,制造出舒适感,不可避免地对历史进行篡改。在加拿大,人们恢复的圣劳伦斯河谷的史前村落,是按照过去岁月的浪漫想象打造出来的,采用了最完美的建筑形式呈现。但这样的完美与舒适又是失真的。
“未来化”与“博物馆化”类同,前者是眺望未来,后者则是回首过去。雷尔夫认为,第67届世博会的建筑,正是典型的“未来化”建筑。由于不断追求先锋派和新技术,破坏了地方内生的机理,并将传统赋予地方的本真性拒之门外。

2021年1月,上海高架桥上。
最后是“乡村都市化”。它呈现为大同小异的房屋在大地上漫无边际蔓延开去。这是欧美大城市郊区化后典型的无地方景观,如美国著名的莱维顿式住宅。雷尔夫认为,乡村都市化的发展并非以人们对某个地方的直接经验为基础,而是以造园工程师般超越与冷静的视角和技术化的手段为出发点。因此,“乡村都市化展现出一套随机布局的点和面,每一个个体都只具有单独的目的,而且与所在的背景相疏离。它们只是被公路连接了起来,除了那些指向外部的房屋以外,这些公路与周围的城镇景观都是相互疏离的。”
雷尔夫举了一个生动例子,来说明乡村都市化的无地方性。一位住在郊区的家庭主妇的生活状况是,如果要从家出发去另一栋房子,她一英里借着一英里地步行,在购物中心后方的第四个路口向右转,然后在第三个路口向左转,接着又在第二个路口向右拐,然后在第一个路口向左拐,数一数右手边的第五栋房子,就是它了。“我必须时刻集中注意力”,这名家庭主妇说道,“如果我拐错了一个地方,就会迷路。这些房子全都是同一家公司建造出来的。”
另外,大型企业的景观,像炼钢厂、炼油厂、照明工程厂等,都与其所在环境疏离。矿场、采石场等制造业还会造成某个地方的毁灭。“不论是大坝建设带来的洪水淹没、矿石开采造成的挖掘开垦、矿渣堆的掩埋,还是直接在地表上实施新的建筑工程,皆会如此。”雷尔夫认为,这种毁灭的景观不仅是无地方性,更是一种“反地方性”。

2021年2月,上海一处工地。
此外,由于大型企业都服从于同一套经济体系的价值与目标——追逐更高的空间效率,因此,其途径必然是在地表打造出逼近空间理论的景观。雷尔夫说:“经济发展的浪潮将会从增长极扩散到腹地,进而将领土范围内的地域都整合进统一的经济之中。这种有序的发展将会导致人口、生产和收入的进一步扩散,或许也会带来理想化的理论景观的真正实现,就像很多发达国家目前呈现出来的样子。”进而,地方的本真意义荡然无存。
“你感受到了一片广袤而孤独的大地,大地上只耸立着那些丑陋不堪的事物,你摧毁了在我周围能让我变得清晰而明智的事物,将它们变成了粗陋的、毫无价值的、可怕的,甚至是不知羞耻的东西。你运用自己的积习与法则去繁殖和开发那些邪恶的事物,你竟然还能称它们为‘地方’。”
超越无地方
“保持并复苏人的地方感并不在于保存那些陈旧的、古老的地方——这会造成博物馆化;也不在于人们自觉地去恢复传统地方营造的那些方法,因为这要求人们重新具备失落了的单纯。相反,人们必须去超越无地方。”雷尔夫认为的“超越无地方”,是指重新整合淹没在同质空间(无地方)里的人文要素。
事实上,无地方与地方之间,可以是一种辩证的共生关系,此消彼长,因为“当人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候,也可以因为一些不重要的甚至冷冰冰的大一统景观而生发出些许的本真性。”19世纪英国的工业城镇景观,外人看来深感压抑,而对当地住户而言,里面却充满一个个本真的小世界,类似一座座村庄。那么,如何激发出被无地方淹没的地方性要素,进而超越无地方呢?雷尔夫认为,一种有效的途径在于,努力推进“世俗化”。

2020年7月,上海虹口待拆片区。
所谓“世俗化”,就是去挖掘一个特定的地方里人们日常生活的丰富经验,以此为基础,开展地方的设计与营造。雷尔夫说:“地方自身所拥有的秩序都应当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重要经验,而不是从武断的抽象概念中得来,比如规划图纸。”而在一个特定地方,人类的生活世界具有怎样的丰富模式?这正是现象学的地方研究(place study)要回答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在这方面已做了大量研究,值得参考。
2009年,雷尔夫进一步将该思想提升为“实用主义的地方意义”(A Pragmatic Sense of Place)概念。此概念认为,在后现代的社会状况下,我们必须承认地方性与全球性的共在。地方既是全球网络中的节点,也有它自身的独特性。换言之:“‘实用主义的地方意义’总是以对比性的语境为基础,像世界遗产保护地的设计同地方艺术与节庆维续之间的对比,连锁超市售卖的地方产品同慢食运动和地域特色的烹饪之间的对比。”进而,以认识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共在、杂糅和此消彼长为基础,努力挖掘地方经验的丰富性意义与模式,才能实现超越无地方的场所设计与建造。
无地方与非地方
与无地方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里,还存在“非地方”的概念,其内涵类似“无地方”。但马克·欧杰理解的“非地方”更倾向于从人类学视角出发,探讨后现代状况下的空间实践。其内涵基本可概括为:传统社会中的“契约义务”(contractual obligation)和“时序联系”(chronological connectivity)在后现代社会的消亡,进而带来人的原子化。

2020年7月,上海街头。
传统社会都拥有基于共同价值与信仰的集体契约义务,进而指导成员的社会行动;而在后现代社会,以机场、高速公路、超市等场所构成的非地方则直接通过指示、代码、数字来指导个体行动。由此,个体相互间不再产生契约关系,个体只需直接通过上述指令就可实现合乎规则的行动。其次,传统社会的物质与文化都与历史相连,具有时序性,进而产生出地方归属感;但后现代将人与历史切断,时序性消亡,地方归属感不复存在。进一步地,“契约义务”和“时序联系”的消亡,最终结果便是人的原子化。
正如欧杰在《非地方:现代性人类学导论》里所说:“超现代性将古老(将历史)变成一场特殊表演——仿佛包含一切异国风情与所有地方本位主义……超现代性的非地方当中,始终有个特殊的位置(橱窗、海报、在机器右边、在高速公路左边)是留给这类‘珍品名胜’的:象牙海岸的凤梨、威尼斯——总督之城、丹吉尔城堡、阿莱西亚遗址……假如非地方是超现代性的空间,超现代性无法声称与现代性有同样的野心,一旦个体聚集,他们便会组织社会并规划地方。超现代性的空间则被逆向操作:它只与个体(顾客、旅客、使用者、阅听者)打交道,而他们只需在入口或出口确认身份、社会化与定位(名字、职业、出生地、地址)。”

2020年7月,上海待拆二手市场。
笔者认为,尽管“非地方”概念倾向于从当代空间实践的人类学视角诠释原子化的个体,而“无地方”倾向于从现象学的生存论视角去剖析人地关系的疏离,但二者恰恰构成一组相辅相成的批判性概念,从日常生活世界出发,有效地诠释出个体在(后)现代社会里无根的困境与迷思。
(作者刘苏系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