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算法周刊·深析|成瘾?焦虑?学界对网络游戏有哪些研究
网络游戏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发展壮大成一个巨大的产业。2020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786.87亿元。
那么网络游戏对玩家的影响到底有哪些?游戏产业的发展存在怎样的特征?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简要梳理了近年来关于网络游戏/电子游戏的研究与回顾。
通过浙江大学的求是学术搜索(该搜索支持海内外近400家出版社的文章直接链接),澎湃新闻记者以video game为搜索关键词,以2016年-2021年的相关研究为对象,将引用量、期刊质量、发表时间作为考量标准,选取了以下33篇研究与回顾文章。此外,所摘录文章也包含时间较早但引用量较高的研究。
对于网络游戏对玩家造成的影响,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关于游戏的心理病理学研究,二是游戏与玩家身心健康研究,三是游戏与玩家暴力倾向的关联进行研究。
在游戏的心理病理学研究方面,学术界主要围绕着网络游戏障碍(internet game disorder)展开,部分学者对电子游戏与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相关性进行研究,也有学者着重对电子游戏成瘾的定义、分类、人口学特征、影响等维度进行探讨。在游戏与玩家身心健康方面研究,研究者对游戏带来的潜在身心风险与红利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游戏与玩家暴力倾向关联研究中,与以往发表的研究相比,近年来许多研究者从游戏对玩家长期和短期暴力行为和态度等方面的研究似乎表明,暴力游戏与玩家暴力倾向不具有显著关联性。
据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在最新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网络游戏障碍 (IGD)是一种暂时性障碍。
根据 DSM-5,在超过 12 个月的时间里,至少有五个核心症状(共九个)出现即表明网络游戏障碍的出现。网络游戏障碍诊断标准包括以下九个临床症状: (1) 专注于电子游戏(专注);(2) 玩电子游戏时出现不愉快的症状(戒断);(3) 需要在电子游戏中花费更多的时间(容忍);(4) 控制参与电子游戏的尝试失败(失去控制);(5) 因玩电子游戏而对过去的爱好和娱乐失去兴趣(放弃其他活动);(6) 尽管知道心理社会问题,但仍继续使用电子游戏(继续);(7)在电子游戏数量上欺骗家庭成员、治疗师或其他人(欺骗);(8)使用电子游戏来逃避或消除负面情绪(逃避);(9)因参与电子游戏而伤害或失去关系、工作或教育或重要的职业机会(负面后果)。
对于这一分类的代表性,在研究者中存在着争议。如2015年Griffiths, van Rooij等学者在Addiction期刊上对于Petry等人此前撰写的网络游戏障碍的真实性和代表性提出质疑,并对每一条IGD标准提出了讨论和建议。 https://doi.org/10.1111/add.13057

哪些人更可能成为游戏成瘾玩家? 2015年Wittek等人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期刊发表的研究具有参考意义。基于全美游戏玩家的代表性样本,研究者从性别、年龄、人格类型、身心健康等维度对游戏玩家进行了画像。
研究结果显示,在调查的3389个样本中,有1.4%的游戏成瘾者,7.3%的问题游戏者,3.9%的沉迷游戏者(engaged),以及87.4%的正常游戏者。(编注:对游戏玩家的分类标准见原文)
性别(男性)和年龄组(年轻)与成为游戏成瘾者、问题游戏者、沉迷游戏者的概率成正相关。
出生地(非洲、亚洲、南美洲和中美洲)与成瘾游戏者和问题游戏者呈正相关。
在电子游戏成瘾与五大人格(编注:五大人格是经验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神经质)之间的关系上,电子游戏成瘾与尽责性人格呈负相关,与神经质人格呈正相关。身心状况不佳与问题游戏者和沉迷游戏者呈正相关。研究者认为,这些变量之间的关联有助于为如何识别潜在游戏成瘾者。https://doi.org/10.1007/s11469-015-9592-8

目前,已有许多研究者对网络游戏障碍与焦虑、抑郁、注意力缺陷等症状的相关性进行研究。2018年González, Santamaría等人在Public Health期刊发布的文章则系统地回顾了目前文献。研究者使用PubMed、PsychINFO、ScienceDirect、Web of Science和Google Scholar(r.n. CRD42018082398)数据库进行电子文献检索,获得24篇符合相关性效果标准的文章,其中包括21个横断面研究和3个前瞻性研究,大多数研究在欧洲进行。
研究发现几个显著相关性的变量:92%的网络游戏障碍(IGD)与焦虑相关,89%的IGD与抑郁相关,85%的IGD与注意缺陷障碍(ADHD)症状相关,75%与社交恐惧症/焦虑和强迫症状相关。此外,大多数研究表明男性的IGD发病率较高。然而,文章也表示,由于缺少纵向研究、缺少与既有结论矛盾的研究发表,研究者无法检测变量之间关联的方向性。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5040668

2018年Stockadale与Coyne在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期刊发表文章,对18-25岁年轻人的电子游戏成瘾情况进行研究,通过自我报告与调查的方法,将互联网游戏障碍量表(IGDS)定义下的网络游戏成瘾者与非成瘾者在精神状况、身体状况、社会情感健康等方面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网络游戏成瘾者与非成瘾者相比,表现出更多的情绪障碍,如抑郁、焦虑、社会孤立感;更可能病态地接触网络色情内容。
https://doi.org/10.1016/j.jad.2017.08.045

网络游戏障碍(IGD)并非是“绝对”的概念。有学者对“游戏成瘾”归为精神病理学表示质疑。2017年Bean, Nielsen等人在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期刊发表研究,对DSM提出对IGD概念的三点质疑。首先,“游戏成瘾”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物质滥用(substance abuse)领域,该领域的研究方法无法较好地理解媒介消费(如电子游戏)上瘾问题。其二,一些研究表明电子游戏上瘾并不是稳定建构的概念,上瘾带来的临床损伤可能很低。其三,游戏行为的病理化已经超出了治疗议程(therapeutic setting)。
https://doi.org/10.1037/pro0000150

在游戏与玩家身心健康方面研究上,Kyriakou与 Glentis于2019年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diatrics and Adolescent Medicine期刊发表了电子游戏与青少年皮肤病的关联的研究。
研究者系统性地对涉及到电子游戏导致皮肤病的文献进行了回顾,文章中涉及了病例的临床特征、病因、诊断和治疗的报告案例。
研究者使用PubMed、SCOPUS、Ovid MEDLINE和EMBASE数据库进行了文献回顾。报道案例中涉及的引起青少年皮肤病的硬件包括电子游戏机、个人电脑、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和平板电脑。
这些皮肤病主要集中在四肢,特别是手掌和手指。大多数与重复性摩擦和创伤以及过敏性接触敏感有关。对于所有由电子游戏诱发的皮肤病症状,早期识别和清除不合适的硬件是最经常使用的解决方式。由此,研究者建议,当皮肤科医生遇到有持续游戏行为的未成年患者的皮肤病时,应该对电子游戏造成的影响予以考虑。
https://doi.org/10.1016/j.ijpam.2019.09.002

Siervo, Sabatini, Fewtrell和Wells则在2013年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期刊发表文章,探究了玩暴力电子游戏与玩非暴力电子游戏对玩家的血压(BP)、食欲感知和食物偏好的短期影响。48位年轻(年龄范围:23.1±1.9岁)且体重正常(身体质量指数BMI:22.5±1.9 kg/m2)的男性参加了一项三手(three-arm)随机试验。被试分为三组,分别玩1小时暴力游戏,1小时竞争性非暴力游戏或者看1小时电视。对于被试的血压以及食欲感知在标准一餐(300大卡)前、干预中每隔1小时进行记录。实验结果显示,与其他两组相比,玩暴力游戏与舒张压显著增加有关(Δ±s.d.=+7.5±5.8 mm Hg;P=0.04)。此外,与玩非暴力游戏或看电视相比,玩暴力电子游戏似乎与血压增加和食欲感知增加具有相关性。
https://doi.org/10.1038/ejcn.2013.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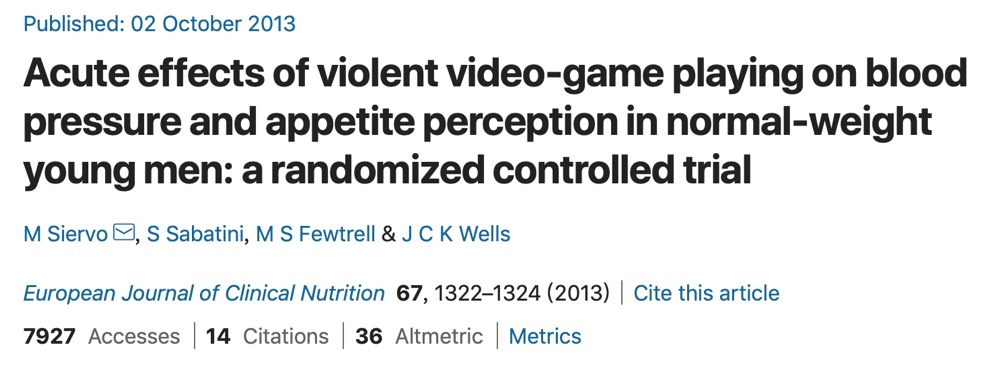
Janssen则在2016年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表明积极电子游戏(active video games AVGs)比久坐电子游戏(sedentary video games AVGs)更利于玩家心理健康,积极户外活动(active outdoor play AOP)比积极电子游戏更利于活动者健康。该研究以20122名6-10年级的加拿大青少年的代表性样本。暴露变量为每天花在AVGs, SVGs, AOP上的时间(小时/天)。心理健康程度则根据情绪问题、生活满意度、亲社会行为三个指标衡量。此外,同时间替代模型(Isotemporal substitution models)估计了用同等数量的AVGs时间代替花在SVG和AOP上的时间对心理健康指标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用1小时/天的AVG取代1小时/天的SVG,与6% 的高情绪问题减少有关,与4% 的高生活满意度增加有关,以及与13% 的高亲社会行为增加有关。用1小时/天的AVG代替1小时/天的AOP与7% 的高情绪问题概率增加有关,与 3% 的高生活满意度概率减少有关,与6%的高亲社会行为概率减少有关。
https://doi.org/10.1016/j.jadohealth.2016.07.007

在网络游戏与暴力的关联上,澎湃新闻记者在对文献简要梳理时发现,研究者对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存在一致的看法。
Hilgard, Engelhardt等人在2017年Psychological Bulletin期刊发表的研究中指出,暴力电子游戏被认为是“导致游戏玩家产生攻击性思想、情感和行为的重要原因”这一观点,主要来自于2010年Anderson等人进行的一项大型的元分析。 然而,Hilgard, Engelhardt等在研究中指出暴力电子游戏对情感的短期影响在上述研究中被高估。
研究者使用了更广泛的检验偏差与调整效果(adjusted effect)(编注:在消除一个或多个其他预测因素的影响后,一个预测因素或自变量对反应或因变量的影响) 的技术重新审视此前研究的分析,从三方面得出与2010年研究不同的结论。首先,研究者在关于暴力游戏对攻击性情绪和行为的影响的实验中发现了大量的发表偏差(publication bias)(编注:发表偏差指结果为统计显著的论文相比于统计不显著的论文更容易发表)。第二,在调整偏差后,实验中暴力游戏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非常小,对攻击性情绪的影响也大大降低。与此相反,横断面文献(cross-sectional literature)发现的相关性似乎基本没有偏差。第三,符合原作者的研究方法论质量标准的实验并没有产生比其他实验更大的调整效果,而是产生了更大的偏差迹象,这表明也许它们是由于原作者为提高显著性而被选择。
https://doi.org/10.1037/bul0000074

一些学者也指出暴力游戏对游戏玩家情绪处理不具有长期效应。早在2012年,Willoughby, Adachi和 Good在Developmental Psychology期刊发布的调查即表明,非暴力的电子游戏不能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攻击性行为水平的提高,调查结果也并未支持对社会化假说(编注:社会化假说意味着暴力视频游戏预测长期的攻击性)和选择假说(编注:选择假说意味着攻击性预测长期的暴力视频游戏)。研究者通过对1492名学生(女性占50.8%)在9年级-12年级四年中的调查得出该结论的。
https://doi.org/10.1037/a0026046

与其类似,Szycik, Mohammadi等人在2017年发表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期刊的研究中认为,暴力游戏对游戏玩家情绪处理的影响或许是短暂精准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暴力游戏玩家与非玩家在情感处理上没有差异。研究者通过将暴力性电子游戏的15名过度玩家与控制了年龄和教育变量的非玩家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两组实验对象的大脑反应并没有显示出显著差异。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7.00174

2019年Kühn等人在Molecular Psychiatry volume期刊发表的研究也表明,暴力电子游戏从长期来看不会增加成年人的暴力程度。在两个月的实验中,研究的三组被试每天玩暴力电子游戏《侠盗猎车手5》、非暴力电子游戏《模拟人生3》或根本不玩游戏。在实验干预前后,研究者对参与者的攻击性行为、性别歧视态度、移情和人际关系能力、冲动相关要素(寻求感觉、厌倦感、风险承担、延迟补偿)、心理健康(抑郁、焦虑以及执行控制功能)进行测量。研究结果表明,玩暴力电子游戏的组别与玩非暴力游戏组别或不玩游戏组别相比,没有明显的差异。
https://doi.org/10.1038/s41380-018-00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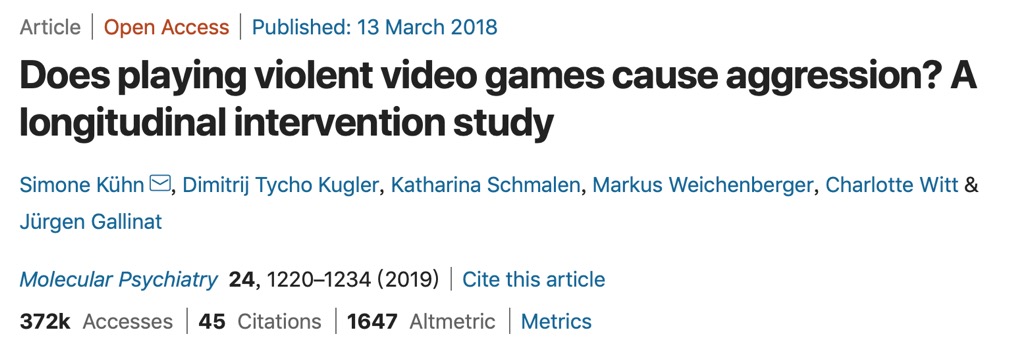
2016年Velez, Greitemeyer等人在Communication Research期刊上发表对于暴力电子游戏不同类型进行探究。通过实验表明,合作性的暴力游戏可以抵消暴力电子游戏的攻击性增加效应。
研究探讨了合作游戏对玩家随后对电子游戏伙伴(实验1)和非电子游戏伙伴(实验2)的攻击性行为的影响,同时对适用于社交电子游戏的可能理论进行了讨论。与竞技游戏或单人游戏相比,合作性电子游戏导致电子游戏伙伴之间(实验1)和非电子游戏伙伴之间(实验2)的攻击性更少。有趣的是,合作性游戏和不玩游戏产生的攻击性水平相似(实验1),而竞争性游戏和单人游戏产生的攻击性水平相似(实验2)。这些发现与有界广义互惠理论(Theory of Bounded Generalized Reciprocity)(编注:BGR理论认为合作游戏应该通过积极的互惠行为增加玩家的期望, 以抵消游戏的负面影响)相一致。合作性地玩暴力游戏可以抵消暴力电子游戏的攻击性增加效应。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214552519

也有研究指出了游戏输赢而非游戏暴力程度对玩家行为的潜在影响。与以往大多研究暴力电子游戏学者将研究主要集中在玩家的攻击性行为上不同,Hemovich 在2021年
于Games and Culture期刊发表的文章则研究了游戏障碍大小与暴力视频游戏玩家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在研究实验中,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玩暴力电子游戏与玩非暴力电子游戏组别中,每个组别中部分人在玩游戏时观看屏幕被大纸片遮挡以增加玩游戏难度,部分人的屏幕则没有被遮挡。亲社会行为则通过参与者帮助捡回笔这一行为测量。
研究结果显示,屏幕遮挡条件占帮助捡回笔这一亲社会行为的34.5%的差异。在有障碍观看条件下,玩家在游戏中输比赛次数更多,并参与了明显较少的帮助行为。无论是玩暴力游戏还是非暴力游戏,在观看障碍条件下,参与者捡回笔的行为的比例都较小。在这一研究中,研究者强调了游戏输赢作为暴力电子游戏玩家行为的影响因素之一。
https://doi.org/10.1177/15554120209137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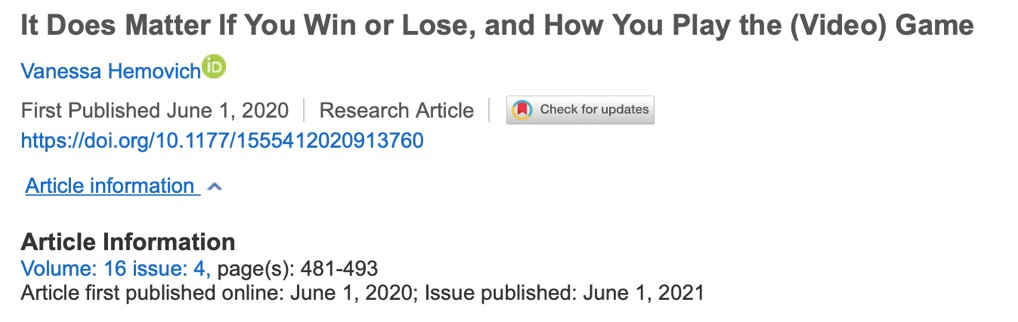
总结来看,暴力电子游戏与暴力关联的学界研究表明,对于暴力电子游戏是否能导致玩家的暴力情绪和暴力行为,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近年的一些研究表明,暴力电子游戏在短期和长期似乎并不会导致暴力行为。不同学者也研究了暴力性游戏的类型(合作型/竞争型)、玩家既有攻击性倾向、游戏障碍大小等因素对玩家暴力倾向的影响。
与此同时,有许多学者的研究揭示电子游戏在某些情形下对人的积极作用。研究在医学领域和教育领域均有涉及,在医学领域如电子游戏能够发挥对于老年人、残疾者等人群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作用,在教育领域如电子游戏对激发青少年学习兴趣、提高“问题”学生的课堂融入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些学者对玩电子游戏与提高认知能力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探讨。Stanmore, Stubbs 等学者在2017年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期刊发表的研究中表示使用电子游戏将身体活动和认知任务结合起来,可能提供一种新的改善认知功能的策略。研究者确定了17个符合条件的随机对照实验,其中包含926名参与者的认知结果数据。随机效应荟萃分析发现,电子游戏明显改善了整体认知(g = 0.436,95% CI = 0.18-0.69,p = 0.001)。此外,研究在健康的老年人和患有神经认知障碍的临床人群中都观察到了电子游戏的好处(所有p<0.05)。
https://doi.org/10.1016/j.neubiorev.2017.04.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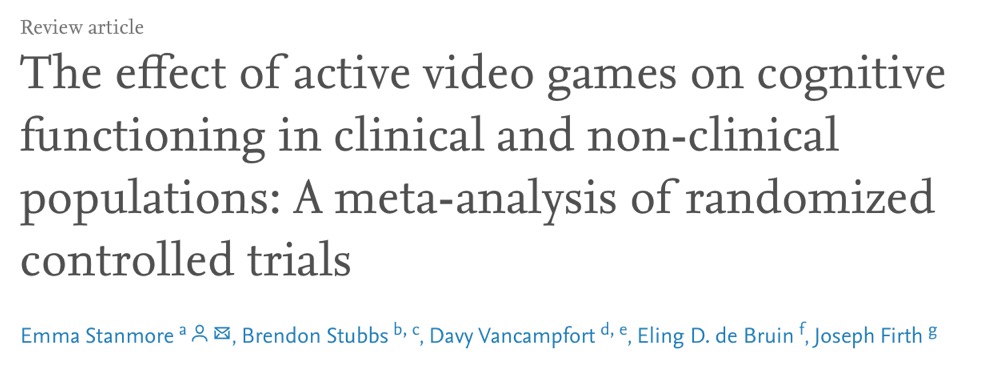
据Sala, Tatlidil和Gobet 2018年在Psychological Bulletin期刊发表的研究,通过训练提高认知能力的可能性成为过去20年认知心理学中最具影响力的话题之一。然而,对专业知识心理学的大量研究和最近的一系列元分析评论表明,各种类型的认知训练(如工作记忆训练)只对受训任务的表现有利。
在该研究中,Sala, Tatlidil和Gobet通过三个随机效应元分析模型测试以往研究显示认知能力(包括视觉处理、注意力、空间能力、认知控制)与电子游戏训练之间的关联性。
第一个荟萃分析(k=310)考察了视频游戏技能和认知能力之间的相关性。
第二个荟萃分析(k=315)研究了电子游戏玩家和非玩家之间的认知差异。
第三个荟萃分析(k=359)研究了电子游戏训练对参与者认知能力的影响。在所有三个模型中都发现效应值很小或为零。这些结果表明,整体认知能力和电子游戏技能只有微弱的关系,且研究并未发现玩电子游戏和增强认知能力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https://doi.org/10.1037/bul0000139

2018年Wong和Chang 在Nature发表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全局与局部构成的分层刺激物。在两个实验中,研究对象被要求将注意力集中在全局的或局部的对象上。在每个RSVP试验中,研究对象被要求辨认初始物,并探察第二个目标物的是否出现。电子游戏能手显示出了明显较少的注意瞬断(attentional blink)(编注:注意瞬断指在快速连续地呈现两个目标刺激的情况下,第一个目标出现后的几百毫秒的时间内,人无法准确的辨别(甚至检测)出第二个目标刺激),这一结论通过其在全局注意还是局部注意中相比于非电子游戏能手展现出的更高的T2感知敏感性得出。研究者观测,观察到的视觉-注意力优势不大可能与单纯的感知倾向(即更大的全局有限性)差异相关。这一感知倾向被认为与注意瞬断减少相关。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18-23819-z

有学者对残疾人的游戏研究表明,玩电子游戏能够让残疾人感到自己有能力。2021年,Cairns等学者在Games and Culture期刊发表的研究通过对一个普通游戏社区的71名非残疾玩家与123名残疾玩家进行调查,询问受访是什么使游戏对其很重要。研究发现的既定游戏动机包括建立社会联系和逃避社会现实。但除此之外,也有玩家认为游戏对其而言是有益的且能够提供艺术体验。值得注意的是,残疾玩家明确提到游戏能帮助他们感到自己有能力,与非残疾玩家处于平等地位。研究者认为,这意味着构建对残疾者无障碍的游戏是提供残疾人与非残疾人有价值的联结的重要方式。
https://doi.org/10.1177/1555412019893877

2017年,Mack等学者在European Eating Disorders Review期刊发表一篇文献回顾。为了评估视频游戏对抗和预防儿童肥胖症的可能与局限,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文献搜索,对针对7至15岁儿童的营养、身体活动和肥胖的视频和电子游戏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文献梳理。该研究区分了1)增长关于营养、饮食习惯和运动的知识的游戏;2)促进体育运动的游戏;3)结合上述两种方法的游戏。研究发现,这些电子游戏和视频总体而言被广泛接受并具有对缓解肥胖的积极影响。然而,研究指出,观察到的效果是很小的,因此电子游戏作为体重管理的方式无法带来满意的结果。电子游戏作为预防和治疗的手段,只能是辅助性的组成成分。
https://doi.org/10.1002/erv.25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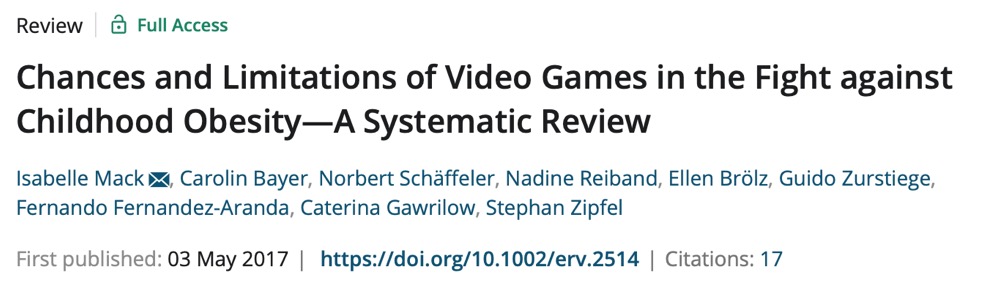
电子游戏作为一种干预手段也可以在教育上应用。2018年Hanghøj, Lieberoth和 Misfeldt在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期刊的研究表明,合作性游戏(cooperative video games)可以从多维度对“问题”学生的课堂融入产生积极影响。
该研究在八个初中班级(共190人)中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游戏学习活动干预。实验干预包括合作行动角色扮演游戏(co-op action role-playing game)《火炬之光II》,以及旨在纳入32名具有社会困难和缺乏动力挑战学生的类似的游戏化行动(analogue gamification)。电子游戏在实验中被用来创造更具包容性的课堂,团队协作则用以增加学生的参与机会。学生们同时也参加了游戏化的丹麦语与数学的学习活动。电子游戏对社会幸福感(social well-being)、学习和激励模式(learning and motivational patterns)的影响通过老师评估与儿童感知因果关系量表进行测量。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电子游戏的课堂参与对学生带来了多维度的积极效果,包括对高危学生(at-risk student)的幸福感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减少了学生参与数学和丹麦语学习所需的外部监管力量。由此,研究者表明,游戏化课堂的影响不在于其趣味性,而在于如何使社会参与以及学生的课堂参与得到重塑。
https://doi.org/10.1111/bjet.12642

2016年Sun 和 Gao发表在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期刊的研究表明,积极的教育电子游戏(AVGs)对小学生的学习动机有积极的影响,从而有利于提高其学习效果。在随机对照实验中,53名小学生被分配至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提供了AVG的学习环境,对照组则是基于久坐教育电子游戏(AVGs)。对学生们知识测试结果的反复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两组学生在后测中表现都好于前测(P<0.001,η2=0.486),在后测分数上两者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实验组的学生新绿明显高于对照组的平均心率;同时实验组学生比对照组学生感受到更高的情境兴趣(p < 0.01,η2 = 0.301)。研究者由此认为,AVG通过提供愉快的学习经验和充足的PA(身体活动)使学生受益。然而在学习成绩方面,AVG没有显著效果。
https://doi.org/10.1016/j.jshs.2014.12.004

2021年Li在The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期刊发表的文章探究了历史电子游戏的情感性、想象性和游戏性。研究表明历史题材电子游戏在中国的流行有利于玩家的历史意识培育以及反事实(counterfactual thinking)方法论培养。研究者认为,当媒体生态改变,新的进取和创造精神也彻底改变了历史信息流动方式。中国新一代具有战略眼光的公共历史学家的介入,将促进这一趋势进一步的发展。
https://doi.org/10.1177/1354856520967606

在探寻游戏产业机制与社会环境发展中,学者们不断呼吁游戏产业承担起社会责任,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社会治理的建议。在电子游戏产业机制方面,一些学者探究了游戏货币化(video game monetization)的手段与影响。也有学者从更宏观的层面着手,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等视角对游戏产业发展进行研究。
战利品盒(loot box)是电子游戏中可以用金钱支付的物品,其中的内容具有随机性。这些奖励能够使玩家在游戏中提高自身表现以保持自身竞争力,因而对玩家具有吸引力。2018年Zendle和Cairns在PloS One发表研究对7422名游戏玩家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表明,战利品盒花销与赌博问题严重程度之间存在联系([eta].sup.2 = 0.054)。相比于问题性赌博与购买其他游戏物品之间的联系([etc.].sup.2 = 0.004),购买战利品盒与赌博的联系更强。研究者表示,该研究尚不清楚购买战利品盒是否为促进问题赌博的因素,以及问题赌博者是否更倾向于购买战利品盒。然而,研究者表示,无论是哪种情况,相关机构对游戏中的战利品盒机制都应予以监管。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67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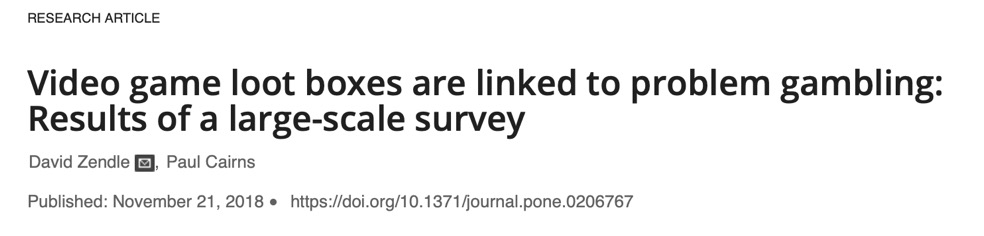
2018年Aaron和James在Nature期刊上评论道,电子游戏战利品盒与赌博行为具有心理接近性。作者通过赌博与战利品盒的定义梳理得出,在鼓励和维持用户参与的方式上,战利品盒与赌博具有重要的结构和心理相似性。作者提出了三项建议:1)ESRB(编注:ESRB为美国游戏分级制度)等其他评级机构和赌博监管机构应考虑将涉及战利品盒的电子游戏限制在合法赌博年龄阶段的人访问;2)相关机构应对涉及战利品盒的游戏加强审查,并适当提高游戏的推荐最低年龄;3)相关机构应详细说明关于战利品盒的运作机制以帮助游戏消费者与家长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2-018-036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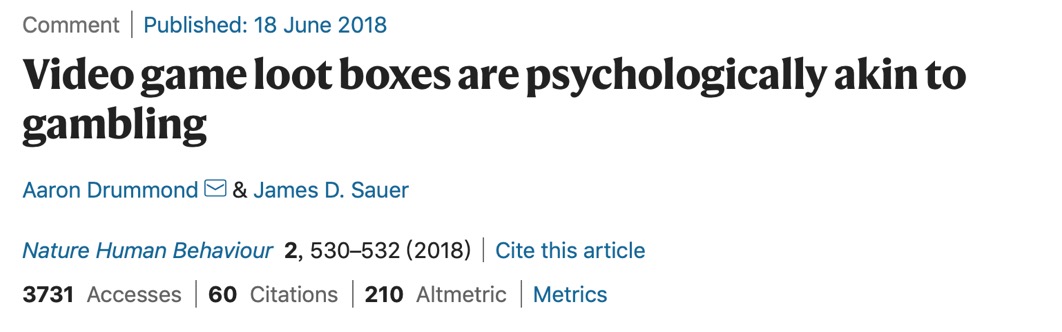
2021年Macey等在New Media & Society期刊发布了一项关于电子游戏消费、电子竞技、赌博和人口学因素研究。研究者对1368个样本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观看电竞和参与一般形式的赌博都与电竞投注有直接联系。然而,研究者并没有观察到电子游戏消费和电竞赌注的直接联系。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游戏能够作为赌博内容的载体,但没有直接鼓励赌博行为的内在因素。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20908510

以战利品盒为代表的电子游戏货币化机制,本质上是玩家与游戏公司的不平等关系的体现。这一体现在游戏设计中即已凸显。2019年King等人在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期刊上发表研究,对谷歌专利(Google Patents)上13项游戏内购买系统(in-game purchasing systems)专利的分析。分析内容涉及与消费者权利和保障相联系的专利受让人使用协议条款。研究认为,一些游戏内购买系统是不公平的甚至对玩家具有剥削性的。这些协议描述了系统通过信息优势(如行为跟踪)和数据操纵(如价格操纵)等方式激励玩家持续消费以促进游戏变现。与此同时,协议也表明游戏设置中为玩家提供了十分有限的或没有保护(如退款权利),并且其对弱势玩家(如问题玩家、青少年)具有更强的剥削性。研究者呼吁,为了保护游戏消费者的利益,需要适当的政策和消费者保护措施、心理学干预措施和游戏设计道德性准则的颁布。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9.07.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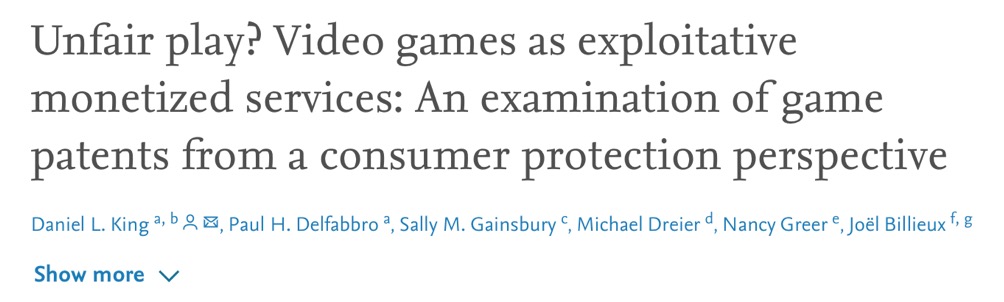
蔡润芳在2018年发表于《新闻界》的研究中则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聚焦电子游戏产业“平台化”与游戏玩工(playbour)在平台经济中“劳动化”过程,由此揭示以平台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流通形式的平台资本主义垄断和剥削特征。一方面,研究认为游戏产业逐渐显现出具有社交属性的“平台化”特征。凭借起对信息数据、社交关系等新兴资源的垄断,得以形成以“数字劳动”为生产力,以互联网“价值网”为结构的新利益循环网络模式。另一方面,普通游戏玩家显现出“劳动化”趋向。在游戏中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玩游戏同时也为游戏公司和平台公司创造巨额利润,一方面作为产消玩工参与游戏内容生产,另一方面作为“你媒体(you media)”参与游戏营销。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18&filename=NEWS201802010&v=SrSclR6RIuU2b83vlKW%25mmd2FxqRjKig8ZmcamIjHrZ%25mmd2FUaKdXhMqa%25mmd2F5n8TdlZx0qM5YR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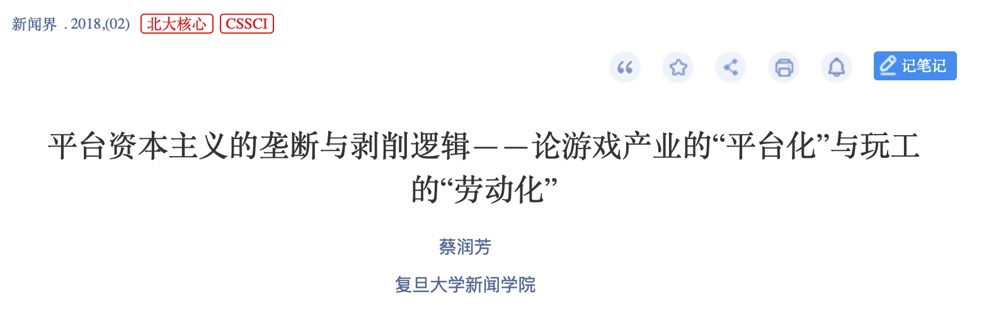
从社会结构角度来看,电子游戏的内在机制设置也是社会结构的镜像。一些学者从性别、种族等视角出发,反映了电子游戏中反映的社会不平等的结构。
2017年Fox和 Tang在New Media & Society期刊发表的研究根据293位女性样本调查了在线电子游戏中女性遭受性骚扰的经历,包括骚扰的频率、对骚扰的思考(rumination)、对游戏公司做出解决骚扰问题努力的看法、退出游戏的比例。调查结果表明,女性报告的减轻骚扰的策略包括避免与其他玩家交流、通过网名或头像选择进行性别扭曲(gender bending)或者性别中立化(gender neutralization)、在游戏内外寻求帮助或社会支持。性骚扰以及其他形式的骚扰都具备女性从网络游戏退出的预测力。性骚扰将造成反思(rumination)以及随后的退出游戏。然而,从性骚扰到退出游戏的关联,也受到游戏组织解决是否有力的影响。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6635778

Ruvalcaba等人2018年在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期刊的研究重点关注了女性玩家在男性主导的电竞空间中的反馈以及遭遇性骚扰的经历。在研究1中,研究者分析了在线游戏玩家对不同性别玩家和观众所呈现的反馈态度的差异。在研究2中,研究者在游戏观察中分析了玩家的性别差异,这些观察集中在Twitch(一个流行的视频游戏流媒体网站)上观众对女性和男性游戏者的评论。 研究结果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玩家在网络游戏中的体验是混合的,且包含了更多的性骚扰。https://doi.org/10.1177/0193723518773287

2017年Paaßen, Morgenroth 和Stratemeyer在Sex Roles发表的文章中,探究了电子游戏文化中男性玩家的刻板印象与女性玩家在其中的边缘化角色。研究者认为,女性玩家与男性玩人数大致相同,但是电子游戏仍然被认为与男性有更加密切的关系。这一刻板印象的常见理由是,尽管女性也许会玩游戏,但她们不应该被认为“真正”的游戏玩家,因为与男性玩家相比,她们玩得更随意、更不熟练。在研究中,研究者回顾了现有的关于性别和游戏的文献,从系列论文的准确性、持久性、影响、未来展望的角度来研究男性游戏玩家的刻板印象。研究结果表明,刻板印象所描述内容的准确性取决于对“游戏玩家”的定义。研究者认为,由于几乎所有游戏文化中的专业者及高度可见的人物都是男性,且达到中等水平的女性玩家则容易被忽视或由于各种因素选择主动边缘化,由此造成了对游戏玩家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研究者进一步提出,男性玩家刻板印象会对女性造成伤害,使她们无法享受到电子游戏带来的积极成果,如进入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的机会。
https://doi.org/10.1007/s11199-016-0678-y

2016年Lynch, Tompkins等人在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期刊发表的研究对31年间(1983-2014)电子游戏中女性角色变迁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观察到性化女性角色的高峰以来,女性角色被性化的情况在电子游戏中有所好转。传统意义中以男性为导向的游戏类型(如格斗)比角色扮演型电子游戏有更多远的角色。青少年级游戏与成人级游戏在女性性化程度上没有显著区别,并且相比于每人游戏(everyone game)有更多的女性性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游戏中出现了更多女性角色,但这些角色在游戏中常被描述为次要角色,并且相比主要角色有更多的性化(sexualization)特征。女性角色的性化程度与这些角色的身体能力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研究者在文章中用社会认同理论与物化理论对此进行阐释。
https://doi.org/10.1111/jcom.12237

2021年Jenson和 Castell在Explorations in Media Ecology期刊的研究借鉴女性主义观点,试图理解电子游戏是如何成为一个性别化场域的。该文章通过媒介生态学理论研究性别,以洞察女性不友好的媒介生态是如何在性别化敌对行为的重复中被合法化的。研究者希望超越对于性别歧视现象的“天真的惊讶与义愤的表达”(naïve expressions of surprise and righteous indignation),转而阐明厌女症和骚扰如何深深嵌入于电子游戏的性别生态之中的。
https://doi.org/10.1386/eme_00084_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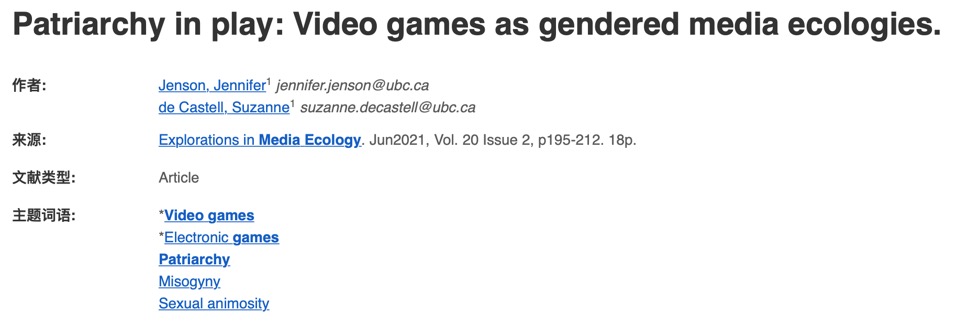
除了对电子游戏中性别因素的讨论,学者也对根植于种族意识、国别意识中的电子游戏生态进行讨论。2021年Bulut发表在Games and Culture期刊的研究对电子游戏发展中的白人男子气概、创作欲望(creative desire)、生产性(production)意识形态作出讨论。在其专著《帝国游戏》(Games of Empire)中,Bulut提出了“可笑的宗教性”(ludic religiosity)的概念,以揭示白人男子气概如何影响游戏工作者的专业化与、技术实践以及“可笑的欲望”(ludic desire)和想象的。经过三年的民族志研究,Bulut一方面试图证明游戏开发者是如何渴望生产“逃避现实者”(escapist)这一认知资本主义商品的,另一方面也试图在白人男性生产文化中重新思考意识形态背后的种族化和性别化的话语和实践。研究者认为,意识到种族化和性别化的实践和想象如何为全球游戏产业背后的欲望提供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https://doi.org/10.1177/1555412020939873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