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以虚构为荣的纪录片:赫尔佐格不要会计的真实,要狂喜的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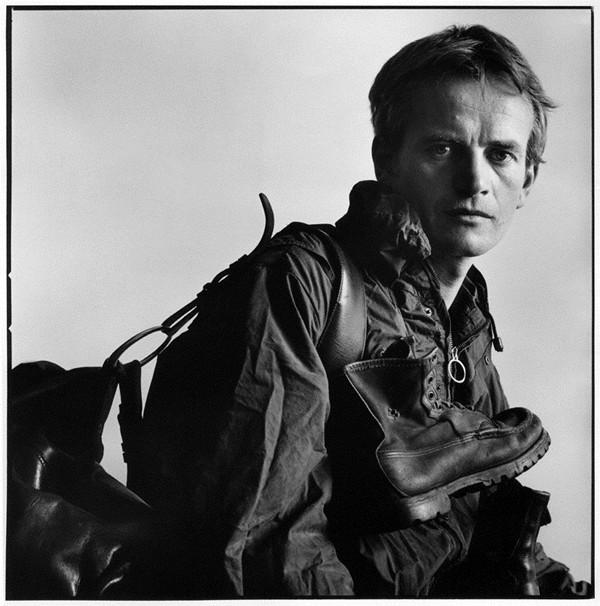
苏珊娜·克拉普(Susannah Clapp)在写布鲁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的回忆录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查特文去世前病得很重,他住在伦敦利兹酒店的房间里接待客人。许多前来探望的人都会得到一份礼物。其中一位得到了一个锯齿状的小物件,查特文说这是澳洲土著成年礼时用来割开尿道的割礼小刀。查特文在澳大利亚的灌木丛里捡到这东西,身为鉴赏家的他一眼就看出其价值:“它明显是用某种欧泊宝石做的。色泽美丽,几乎是查特酒的淡黄绿色。”不久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馆长在满怀感激得到这礼物的人家里看到了这个小物件,他拿起来对着光看了看,喃喃自语:“嗯……土著能把一个旧啤酒瓶碎片做成这么个东西,可真了不起。”
查特文有种粉饰现实的天才,如阿拉丁的神灯般,能够讲出极其魅惑神秘的故事。他是神话制造者,也是能将平庸事实变成诗的寓言家。若去质疑他故事的真实性,那是不得要领。他既非记者也非学者,而是最高级别的讲故事大师。这种写作的美妙之处在于完美的隐喻,能够启示现实表象之下的东西。该类型的另一位大师是波兰人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他记录了第三世界的暴君和政变。他的《皇帝》一书诗意地描述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的宫廷生活,时常被解读为隐喻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波兰——但作者一直否认这种说法。

德国电影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是查特文和卡普钦斯基的朋友。他把查特文的一本书拍成了电影《眼镜蛇》(Cobra Verde,肯定不是他最好的作品),讲述一个半疯的巴西奴隶贩子在西非的故事,由半疯的克劳斯·金斯基扮演。这样的搭配是自然而然的,因为赫尔佐格也是一位伟大的寓言家、虚构者。在他接受的无数次采访中(对于一个号称自己宁愿像中世纪工匠那样默默无闻工作的人来说,数量未免太多),他时常将自己与摩洛哥马拉喀什市集中讲故事的说书人比较。与查特文和卡普钦斯基一样,赫尔佐格也极受“热带巴洛克”(遥远、荒芜的国度或是茂密的亚马逊丛林)的吸引。像他们一样,赫尔佐格也爱说可怕的困境、与大难擦肩而过的故事:肮脏的非洲监狱、秘鲁的洪灾、墨西哥横冲直撞的野牛(当然赫尔佐格很谦虚,好像自己的故事其实没什么要紧似的)。赫尔佐格在洛杉矶的一次BBC电视采访中,正用他那低沉、魅惑的嗓音说德国已经没人要看他的电影,这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赫尔佐格弯下了腰,他被一支气枪击中,留下了一个可怕的伤口。“这根本不重要”,他面无表情,嗓音低沉依旧,“我被打死也不奇怪。”这一时刻是如此的赫尔佐格,简直叫人怀疑是不是他自己策划了这一切。
这种怀疑并非捕风捉影,因为赫尔佐格对字面上的真相不仅毫无兴趣,甚至鄙视之。“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强调捕捉真实,时常用手提摄影机跟踪拍摄,赫尔佐格斥之为“会计的真实”。雷沙德·卡普钦斯基总说自己是记者,否认为了诗意或隐喻效果去编造故事,而赫尔佐格毫不讳言自己在拍纪录片时虚构场景,甚至以此为招牌。事实上,他并不认为自己拍的纪录片和虚构影片有什么区别。在精彩好书《赫尔佐格谈赫尔佐格》中,他对保罗·克罗宁说:“虽然《来自深处的钟声》和《五种死亡的声音》通常被归入‘纪录片’,但我觉得这是误导人的。它们只是伪装成纪录片而已。”至于剧情片《陆上行舟》,讲的是十九世纪末的橡胶男爵菲茨卡拉多(克劳斯·金斯基饰)梦想在秘鲁丛林中建造一座歌剧院,还把一艘大船拖过一座山的故事,赫尔佐格认为这是他最成功的纪录片。
在赫尔佐格看来,“会计的真实”的对立面是“狂喜的真实”。他在纽约公立图书馆参加活动时说:“我追求的东西更接近狂喜的真实,那种我们超越了自身的东西,那种有时会在宗教中出现的东西,比如中世纪的奥秘派。”《来自深处的钟声》达到了这种奇妙的效果,该片讲述俄罗斯的信仰和迷信——西伯利亚的耶稣形象等等,查特文对此也相当着迷。影片开头的场景极其迷幻,一群人在冰湖表面匍匐爬行,透过冰层张望,好像祈祷者在寻找看不见的上帝。赫尔佐格在旁白中说,实际上他们在寻找伟大的失落之城基德希(Kitezh),传说这城就埋在无底的湖冰之下。鞑靼侵略者洗劫该城时,上帝曾派大天使救赎居民,赐他们安居在深深的海底,唱唱赞美诗、敲敲钟。
的确有这传说,画面也美轮美奂让人过目不忘。但影片完全是摆拍的。赫尔佐格从当地村庄的酒馆里找了几个醉鬼,付钱让他们躺在冰上。他在旁白中说:“其中一个脸贴着冰,看起来陷入深度冥想中。用‘会计的真实’描述是:他烂醉如泥,我们得在拍完后叫醒他。”这是骗人吗?赫尔佐格说不是,因为“只有通过创作、编造和戏剧表演,你才能达到一种更为剧烈的真实,别无他法”。
查特文的崇拜者会说一模一样的话。我得承认我也是其中一员,但并非完全没有矛盾之感。影像的力量肯定会被放大——如果你相信那些人是真正的朝圣者而非拿了钱假装朝圣者的醉汉。如果一部电影或一本书是被当作准确事实而推出的,观众或读者肯定对之有相当程度的信任,这与暂且搁置怀疑还不太一样。一旦你知道了未经修饰的真实故事,魔力就会部分消散,至少我是这样。不过赫尔佐格作为影像演说家的天才在于,他的纪录片即便当成虚构作品看也一样动人。若要为他的独特风格辩护,我们可以说他用虚构不是为了伪造真实,而是为了加剧、提升真实,使之更生动。他最爱用的手法之一是为人物编造梦境或幻觉,虽然这些都不是真的,但却显得十分真实,因为都与人物内在贴合。他选择拍摄的对象都是一些他个人感到亲近的怪人。某种意义上说,赫尔佐格电影里的主人公,都是他自己的各种变体。

赫尔佐格出生于战时的慕尼黑,在巴伐利亚州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遥远小村庄里长大,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影院。他小时候梦想成为一个跳台滑雪运动员,挑战地心引力、想飞翔成为他电影中不断出现的主题,不管是滑雪板、热气球,还是喷气战斗机。1974年他拍了一部纪录片《木雕家斯坦纳的狂喜》,就是讲一个奥地利跳台滑雪运动员。斯坦纳是典型的赫尔佐格式人物,一个独来独往的偏执狂,将自己推到极限,以驾驭对死亡和隔绝的恐惧。用赫尔佐格的话来说,斯坦纳和“菲茨卡拉多形同手足,菲茨卡拉多把一艘大船拖过大山也是挑战引力之举”。
1971年赫尔佐格拍了他最惊人的纪录片之一,讲述另一种最极端形式的隔绝——眼盲耳聋之人。《沉默与黑暗的世界》中的主人公芬妮·斯特劳宾格是一位极有勇气的德国中年妇女,她只能通过在别人的手心里敲一种盲文来交流。她在少女时代遭遇事故后双目失明,所以依然有视觉记忆,她记忆中最鲜活的形象就是跳台滑雪运动员在空中翱翔时脸上的迷醉表情。实际上斯特劳宾格从没见过跳台滑雪运动员。赫尔佐格为她写了这些台词,因为他觉得“这是能够代表芬妮内心和孤独的伟大形象”。
这样会消解影片,或歪曲芬妮·斯特劳宾格的真实吗(哪怕她同意读那些台词)?我们很难给出明确的答案。是,这是一种歪曲,因为它是虚构的。但它并不会消解影片,因为赫尔佐格令它看上去很可信。而且,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得知芬妮·斯特劳宾格或任何其他人的内心。赫尔佐格做的是去想象她的内心。跳台滑雪运动员的故事是他如何看待芬妮的一部分。在他看来,这个故事能照亮她的性格。这是另外一种真实,是肖像画家的真实。
赫尔佐格喜欢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艺术的槛外人,在危险的边缘上独自飞翔。不过从许多方面来说,他在挖掘的是一种丰裕的传统。渴望狂喜、在荒野上独自一人、更深层的真实、中世纪神秘主义者,所有这些都带着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腔调。赫尔佐格频繁使用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比如讲述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科威特燃烧油井的《黑暗之课》),时常表达对荷尔德林诗歌的喜爱,这些都说明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浪漫主义趣味。他厌恶“技术文明”,美化游牧生活以及一切尚未被现代文明摧残的生活方式,也与浪漫主义同调。他有时道德感十足,甚至达到清教徒的刻板程度。“旅游是罪”,1999年他在《明尼苏达宣言》中宣布,“徒步是美德”。消费文化至上的二十世纪是“巨大的灾难性错误”。他在歌德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冥想的西藏僧侣是好的,但冥想的加利福尼亚主妇则“令人作呕”。为什么?他没说。我猜是因为他觉得加州主妇都是为了赶生活方式的时髦,不是真的信徒。
和许多浪漫主义艺术家一样,赫尔佐格很看重风景,这是他努力获得视觉本真性的一部分。很少有导演能够达到他的高度,去描绘丛林的可怕繁殖力、沙漠的骇人荒凉,或是高山的庄严巍峨。他从不把风景当成布景,风景是有性格的。他评价丛林“真正关乎我们的理想、我们最深的情感、我们的梦魇。它不是一个处所,而是我们心灵的状态。它拥有几乎全部人类特质。它是人物内心风景中的关键部分”。赫尔佐格崇拜的艺术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从来没画过丛林,但把这描述放在他的其他画作上也毫无违和感,比如孤独的人凝视着狂风暴雨中的波罗的海,或是站在雪峰顶端凝望脚下的云层。弗里德里希将风景视为上帝的显现。赫尔佐格经历过一段“戏剧性的宗教阶段”,少年时改信天主教,“在我的一些作品中看到了宗教的回声”。
战后的德国人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有时会对这种浪漫主义的神圣观感到不适。它太容易让人联想到第三帝国吹嘘宣扬的伪德国精神。也许这解释了为何赫尔佐格的影片往往在国外更容易被接受(现在他住在洛杉矶,他喜欢这城市因为它有“集体梦想”)。事实上,赫尔佐格对祖国曾经释放出的野蛮主义有极端敏感的体察。他说过:“我甚至看杀虫剂广告都会忧虑,知道从杀虫到种族灭绝仅一步之遥。”赫尔佐格从未把玩过纳粹美学。他做的要有趣得多:他虚构出一种被纳粹给滥用并粗俗化了的传统。比如莱尼·里芬斯塔尔自导自演的那种登山片,充满了狂喜和死亡,在战后很快不再流行,正如赫尔佐格所言,它们“与纳粹意识形态步调一致”。于是赫尔佐格着手创作“一种全新的、当代形式的登山片”。
对我而言,看赫尔佐格的影片带来一种全然不同的、在希特勒之前已经长久存在的、更受欢迎的浪漫主义:好像卡尔·麦的小说描写无畏的德国猎人去美国西部探险。麦笔下最受欢迎的主人公是老沙特汉德,和印第安土著阿帕切族的“结拜兄弟”威尼图(典型的十九世纪高贵野蛮人形象)一起漫游在西部大草原上。除了来复枪,老沙特汉德与一切技术文明划清界限。他全靠机智在危险的自然中生存。卡尔·麦于1890年代写下这些西部小说时从未去过美国,他的描写全凭虚构,小说中充盈的真实细节都来自地图、旅行记录和人类学研究。

在所有赫尔佐格的主人公中(无论虚构与否),与老沙特汉德最接近的不是一般人以为的那些执迷不悔的幻想家(通常由克劳斯·金斯基扮演)——寻找黄金国的西班牙人阿吉雷,或是菲茨卡拉多;也不是《灰熊人》中的蒂莫西·特莱德威尔,这位钟情灰熊的美国人以为自己能在阿拉斯加的寒冷野外活下来,只要灰熊对他的爱有所回应就成,结果灰熊把他给吃了。老沙特汉德不会对自然如此多愁善感,他懂得其中的凶险。
不,更像卡尔·麦笔下人物的是战斗机飞行员迪特尔·登格勒(Dieter Dengler)。登格勒出生于德国的黑森林区,后来入美国籍,因为二战结束时每当美国战斗机飞过他家屋顶,他就渴望飞上蓝天。由于战后德国无法满足他的心愿,他先当了钟表匠学徒,然后揣着三十美分登上了一艘开往纽约的船。他加入美国空军后有好几年都在厨房里削土豆,然后才意识到得有大学文凭,于是他住在加州的一辆大巴士里艰苦生活,同时考出了文凭。终于他如愿以偿开始接受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很快被送去越南参战。在一次老挝的秘密任务中,他的战斗机被击中了。他被巴特寮俘虏,送去丛林深处的俘虏营,经常被拷打折磨。这些牢头喜欢把他倒吊起来,让他的脸埋在蚂蚁穴里,或是让公牛拖他,要么就是用竹签刺他的皮肤。
和他一同关在俘虏营的还有别的美国人、泰国人,牢饭是生蛆的米粥,他不得不从茅坑里抓些老鼠和蛇生吃以补充营养。靠着技术达人的机智以及超乎人类的生存技能,登格勒和同伴杜恩·马丁越狱了。他们赤脚穿过雨季的丛林,朝泰国边境的湄公河前进。在碰到一群敌方村民后,杜恩被村民用大砍刀斩首。不久后,已经瘦成骷髅的登格勒被一个美国飞行员发现,救了回来,这全是运气。如果有人问他怎么能忍受这么多苦难,他会说:“这是我生命中的有趣部分。”
赫尔佐格容易受强壮之人的吸引,但他很快会加一句,说那不等于健美先生。在他看来,健美先生浅薄之至,像那些冥想的加州主妇一样假惺惺,“令人作呕”。赫尔佐格二十岁时拍了电影处女作《赫拉克勒斯》(1962),将车祸、轰炸和健美先生的形象拼接在一起,批评无意义的男性气概。一个赫尔佐格式的强人也可以是女强人,比如芬妮·斯特劳宾格或尤莉娅妮·薛普克,后者是一次智利空难的唯一幸存者,1999年赫尔佐格拍摄《希望之翼》讲述了她的故事。赫尔佐格式的强人不光要体魄健壮,还要有坚强的意志,知道如何险中求胜。
如果迪特尔·登格勒没有活下来,赫尔佐格也会编造故事。登格勒是完美的赫尔佐格式强人,也是赫氏最佳纪录片之一《小迪特尔想要飞》(1997)的主人公。其中第一个镜头已是创作:我们看到迪特尔走进旧金山的一家纹身馆,假意要在背上纹上野马驾着死神的形象。但他决定反对这想法,他说绝不会要这样一个纹身,因为濒死时他觉得“天堂之门开启”,他看到的不是野马而是天使:“死神不想要我。”
事实上迪特尔根本就没想过要纹身。赫尔佐格拍这个场景是为了表现迪特尔的九死一生。下一个场景是拍迪特尔开着敞篷车回旧金山北部的家。沿途风景怪异地让人想起战前德国的登山片:雾蒙蒙,高远,似乎远离人类文明。迪特尔开关车门好几次,有点儿强迫症,然后又开关了好几次前门,其实根本没锁。他说有人会觉得这习惯有点儿怪,但这是被俘时养成的。开关门会给他一种自由感。
在现实中,迪特尔并没有把门开开关关的怪习惯,就像他没想过要纹身一样,虽然他墙上挂着一套油画,主题是各种开着的门。他只是按照赫尔佐格设计的场景去表演。影片后面我们还会听到迪特尔不断重现的梦境:在战俘营里,美国海军派船来救他,但与他擦肩而过,他只能拼命向船挥手。这也是虚构。不过在看完《小迪特尔想要飞》之后,我们会强烈感受到一个像老沙特汉德般的德国英雄的内心肖像被转接到了迪特尔身上,他以高效、有纪律、技术高超之类的“典型德国精神”超越了美国同胞。迪特尔本人也是高明的叙述者,他的德国口音和赫尔佐格的旁白有趣地融为一体,几乎无法区分。这个例子不单单是导演认同他的拍摄对象,他几乎变成了迪特尔。

赫尔佐格拍电影的许多天赋中,还有一样是对音乐的惊人运用。科威特油井燃烧时配上瓦格纳的《众神的黄昏》可能太明显了,不过战斗机从航母上起飞时配上卡洛斯·加德尔的探戈音乐也十分有效果。轰炸越南村庄时配的是一个蒙古呼麦歌手,产生的混合效果既可怕又美丽。迪特尔讲述濒死经历时,瓦格纳又出现了。迪特尔站在一个巨大的水族馆前,蓝色水母在他身后怪怪地漂着,好像无数降落伞。迪特尔说,这就是死亡的样子,背景音乐是瓦格纳的《爱之死》。当然,水母又是赫尔佐格的主意,不是迪特尔想出来的,但无可置疑这形象十分有力。
事实上只要你问赫尔佐格,他从不讳言这些虚构,但并不能完全驱散人们对这类影片的疑问。如果这么多东西是虚构的,到头来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才是真的?说不定迪特尔·登格勒的飞机从来没在老挝被击落过。说不定他根本不存在。说不定这,说不定那。我能说的是,作为赫尔佐格作品的仰慕者,我相信他对拍摄对象的诚意。所有那些虚构——门、水母、梦境——都不会改变迪特尔叙述的亲身经历。它们只是隐喻,不是事实。而且迪特尔本人也明白这些虚构的作用。
最好的例子出现在电影结尾处。后半部分迪特尔和赫尔佐格及拍摄组回到了东南亚丛林,他再次赤脚走过灌木,又被村民绑了起来(当然是赫尔佐格雇来的),他回忆了如何逃脱以及朋友杜恩被杀的具体细节。我们还看到了他在黑森林的老家,他讲述了祖父是村中唯一拒绝追随纳粹的人。我们还看到了他回到美国,和救了他的美国飞行员吉恩·迪特里克一起吃一只巨大的感恩节火鸡。所有这些镜头过后,在收场白(迪特尔在阿灵顿公墓的葬礼——他死于渐冻症)之前,我们看到他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军用机场的空旷休息区荡来荡去。摄像机扫过一排又一排报废的战斗机、直升机、轰炸机,迪特尔说他来到了飞行员的天堂。
这个场景也是赫尔佐格的发明。迪特尔没想过去亚利桑那的图森。不过他在片中的徜徉看上去很真实。开飞机是他毕生的迷恋,他需要飞翔,所以不管是谁安排他去瞻仰飞机的坟墓,小迪特尔看上去真的像在天堂一样。

鉴于这部纪录片取得的巨大成功,再拍一部同题材剧情片的想法可能听上去很怪。迪特尔喜欢这主意,也可能只是想从中赚大钱而已(可惜他在影片完成之前就去世了)。赫尔佐格明显被这个人和他的故事迷住了,无法放弃。于是他又拍了一部好莱坞小片《拯救黎明》(Rescue Dawn),把摄制组和演员送去泰国,其中包括两个年轻男明星: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迪特尔,斯蒂夫·赞恩饰演杜恩。此片遭受了司空见惯的赫尔佐格式困扰:无休止的争吵、愤怒的制片人、不上心的摄制组、和当地官员的矛盾。对演员来说还有不寻常的困难:克里斯蒂安·贝尔为了演迪特尔掉了一身肉,看上去真的像是丛林炼狱里逃出来一样。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他还被迫吃了看上去极恶心的昆虫和蛇。
演员都相当不错,特别是配角。杰瑞米·戴维斯饰演的吉恩尤其棒,他是抵制迪特尔逃跑计划的一个美国俘虏。赫尔佐格捕捉大自然之美丽恐怖的眼光也从不失色。然而使得《小迪特尔想要飞》成为杰作的东西在剧情片里丢失了。首先是登格勒本人。剧情片里重演他的故事,不知怎地就没有纪录片里的那些火花。剧情片看上去很俗套,甚至扁平。迪特尔完全成了一个美国人(现实中并非如此),即便他比影片中的其他人都要坚强、机智。剧情片的结尾处倒是与事实更接近,登格勒被救回海军战舰,战友迎接,但比起纪录片里图森的飞机坟墓那萦绕不去的形象,剧情片只是好莱坞式感伤催泪而已。
我觉得这其中的区别,关乎赫尔佐格对幻想的运用。在纪录片里,他的方法更接近小说家。《拯救黎明》则紧紧跟随登格勒的故事,没有太多背景铺垫,更别说他的内心世界了。它看上去就像制作精良的文献片。然而在纪录片中,正是那些家庭历史、梦境形象、个人怪癖的拼接,加上真实的信息,使得迪特尔·登格勒成为一个丰满的人物。这不是说剧情片里没法达到同样的效果,而是表示赫尔佐格愿意在突破体裁的路上走多远,将常识中的纪录片看成“影片而已”(“just films”)。因为没有更好的词,只能将就用这个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