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蒋斐然:时间.zi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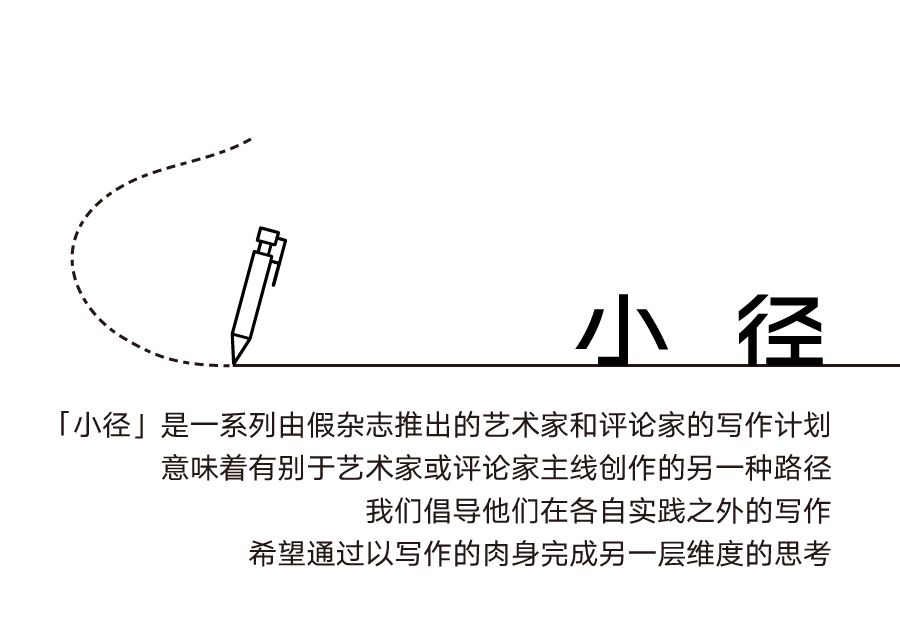
时间.zip:现在
作者|蒋斐然
名为“时间.zip”的压缩文件始终隐藏着它的扩展名。
因此,多数人并不知道它是一份压缩文件。时间只是一个箭头形状的图标,似乎不需要点击便已自动运行。聪明的人投靠度量衡,随身携带钟表与地图,在一秒钟之内走更多的路。
少数技术专家知道时间是一份压缩文件,但不去点击。有什么用呢?解压不过是解开历史长长的裹脚布,摊开铺往火星的蓝图。时间的长河可能已涨满洪水,陈词滥调矣;也可能已经风化成枯石,盖棺定论矣。46亿年前这里都是岩浆,如今你看那山山水水,时间也。
少数自称无畏的冒险者点击了这份文件。没有密码,解压快速。这个潘多拉的盒子里,没有历史,没有未来,没有时间线,仅有一个名为“现在”的文件,同样隐藏了扩展名。“所以,时间就是现在。对,就是现在,此刻。”就在那一刻,保守者退出了时间的窗口。如果他多停留一会儿,或许就能感受到窗外吹过的时间之风。
到处都是窗户:并列的窗户,层叠的窗户,移动的窗户,嵌套的窗户,变形的窗户,闪烁的窗户。年轻的人热爱瞭望窗外,如果关掉一扇窗户,一定会同时再开几扇窗户。重点不在于观看,而在于开关窗户的乐趣;重点也不在于窗外的风景,因为窗与景都切换得太快。年老的人行动缓慢,只热衷于开阖同一扇朝向过去的窗户,风景从未改变。两种速度通向了两种“现在”:一种轻盈得像流云,一种沉重得像枕木;一种斗转星移,一种亘古不异。“时间”就在两种“现在”中发生了撕裂,又在开关窗户的动作中维持着表面的统一。
很多年过去,时间的秘密一直封存在这个压缩包之中。如何对待守在“时间”门口的这个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却永恒如一日的“现在”?
在一个不见天日的无夏之年,火山喷发,气候异变,瘟疫肆虐。斯芬克斯复活,从悬崖上升起,守在时间之城的门前,向每一个过路的人发问:现在,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过路的人抬头望望这不辨晨昏的天色一脸茫然,清晨,正午,黄昏竟连成一片没有边界。一个叫玛丽·雪莱的女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用电光石火将死去之人复活,打通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也穿透了“暂时性”的谜题。斯芬克斯自尽而死。
在一个气温44摄氏度的夏日午后,一位土地测量员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推动着融化中的立方体冰块,惊讶地发现“未来”正像是安装在这块名叫“现在”的立方体中的冻结的时间。因此,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可以互相丈量,而“现在”,是一个换算器或中转站。这个在全球变暖时代发明的土地测量员专用消暑新工具,让他意识到冰川融化的速度也可以取代钟表和气温表的刻度,用来丈量他汗水滴下或头发变白的速度。就像没有钱也能以物易物,从此,他废弃了虚构的尺度。
这两个夏天之后,科幻文学与相对论获得了大发展。人们打通了一条条时空隧道,建造了无数个天空之城。啊,时间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只是关联与关联。于是,人们向蜘蛛学习,没日没夜地织网;又向渔民学习,以网渔和冲浪为生。
城市无边无际,望不到头。你住在城东或城西都一样,房屋和街道可以瞬时移动、自由组合,建筑的基本单位是连接符、放射线、点阵与网格。住在任何一处都不会有邻居,但这不妨碍你随时随地与人相遇。如果在城中住得够久,你或许会在某个黄昏的狗狼时分,看到城市的另一个模样: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或穿入云霄的巴比伦塔,或残垣断壁的荒原,或言语不通的人群。事实上,这一切都同时存在于这座城市,相遇问题取决于足底踏中的时间频率。
不必抬头就能看到城门上方那只明亮的眼睛。在其他城市,这个位置常用来悬挂领袖的肖像,但在这里,就连钱币上印的也是这只古怪的眼睛:没有瞳仁,自体发光。目光来自眼睛正中的机械装置——一只通电的灯泡。这是《格尔尼卡》画中的眼睛。本地人不喜欢画中的混乱气氛,只将这永不瞑目的眼睛加以供奉。从此,这是一座没有睡眠的城市。久而久之,一些人死于劳累,更多人因为失明而从空中坠落。盲症成了最新的大规模流行病。在那些目光消失的临终时刻,人们会在闭眼的刹那,脑中又浮现《格尔尼卡》。
大半个世纪过去,没有人再打开那个时间的压缩包。“现在”这份文件备受冷落,无人问津。这是一个过时的课题,世界正成为全速奔向未来的运动图像。“现在”慢得不合时宜。
直到零年的降临,世界突然关上了灯,像拉动了百叶窗那样,从运动-影像翻到了时间-影像。惯性变得不再可靠,人们甚至无法对写字或张口吃饭这样的身体肌肉记忆作出自动化反应。街道不像街道,楼房不像楼房,线条和砖块倾泻而下,成为波洛克的滴画。现实主义与抽象派合而为一,艺术家不再制作那些令人看不懂的小装置,而是整日枯坐在街头,像一尊尊雕像,琢磨着世界这个看不懂的大装置。出发点和目的地都消失了,只剩下中途和中途。人们又开始传阅《在路上》,醒着的时候,觉得自己在做梦;睡着的时候,又觉得自己还醒着。在零年,人们永远地滞留于绵延的现在,闭口不谈未来,因为所及之处,满眼都是历史的幽灵。
在无边无际弥散开来的时间之中,人们又想起那个古老的压缩包,重新思考起现在之谜。在零年,“现在”变得像一团形状未定的云。
游荡的人们渐渐聚集在那个废弃已久的中空之地,那个跟时间一样苍老的圆形广场上,讨论起“现在”的话题。这片残垣断壁,杂草丛生的环形废墟,看上去却是世上唯一坚定的地方,唯一不像中途的地方。历经沧桑的老人们会对儿孙说,这里就是时间的入口。
一位挥舞着假肢的生物学家上场,说:“现在”持续约0.3秒,这是大脑各区块对正在经验之物建立同步节奏的时间。然而在零年以前,“现在”沦为了生产着机器时间的永续机器,越来越多的事物被挤压进这0.3秒之中,不断剥削着越来越短的“现在”,直至大脑无法拥有足够的时间去感知它。因此人类早已失去了“现在”,沦为机器时间的一颗螺钉。如今该庆幸,零年停摆了机器,“现在”回归,人可以复苏了。
一位从中世纪来的神学家上场,说:时间就是“现在”:历史是过去的现在,未来是将来的现在,而现在是现在的现在。如果用心念,一瞬可以像永恒那么长。他盘坐于广场正中,闭上双目,只一刹那,就进入了穿越几世纪的冥想。
一位研究两栖动物的哲学家上场,说:时间不是一瞬取代另一瞬,而是一条衔尾蛇,过去伸长自己的脖子,一口咬住了将来。蛇身就是现在,可以伸缩绵延,钟表和冥想都不能完全抓住它变化的节奏和长度。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在不断蜕变的鳞片与千变万化的纹路中在场。
一位研究摄影的量子力学家上场,说:“现在”是一簇相关但不相同的可能性,一些可能性被显影和定影,另一些仍保留着虚拟现实的潜影状态。多个“现实”共同存在,但这些“现实”的潜影,要在对历史的再显影之中才能复现。如果回到历史的潜影中,重新显影一个新的“现在”,就有可能定影一个不同的“未来”。
一位研究烂铜废铁与旧报纸的环卫工人上场,说:“现在”是一个以旧换新的回收装置,可以不断地被重新启动,像呼吸一样清理被污染的肺叶和心脏,以安装新鲜的“时间”。
他顿了顿,继续说:
尽管如此,时间却剩下不多了,就像世界快要变成一整个垃圾填埋场了。所以我现在就要启动这个装置。就是现在。
后记
青洲是多年以后的新巴比伦。如果你还没有亲自访问过时间的压缩包,就不太容易找到这个地方。这里已经没有了城市的迹象,但沙漠之中遗留着从前城市的水泥。其中一个水泥包装袋上印有“青洲水泥”的字样,故得名“青洲”。一些考古学家或科幻作家曾到过此地,但下落不明。据说,在另一个未来中,这地方是完全不同的模样,且有个对应的名字叫“绿岛”。也有人说,青洲和绿岛是同一个地方,只是不同的译名。而那些参透时间的人,因为不小心说出了同一地点同一名字下的不同城市,而被人认为是胡言乱语的疯子。

作者|蒋斐然,创作者。
编辑|杨怡莹
假杂志欢迎艺术和文字创作者的艺术批评及文学写作,投稿请发至邮箱yangyiying@jiazazhi.com,一经录用发表,即予稿酬。
原标题:《蒋斐然:时间.zip/小径》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