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周濂张汝伦止庵等五人谈:什么才是我们时代的良好生活
【编者按】
这是刚刚落幕的2015文景艺文季的一场论坛,学者张汝伦、干春松、周濂与作家止庵、王小峰畅谈他们各自心目中“我们时代的良好生活”。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编几位嘉宾的发言。

张汝伦:良好的生活(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不仅仅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地沟油、雾霾等许多事情,让你对这良好生活轻易能够说什么真的很难;更重要的是——当然是我的职业——这个问题在哲学当中,它本身就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和困难的问题。
最近上海书店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最美的哲学史》,这是法国前教育部部长写的,是一本非常有个性的书。这本书的确像法国散文家写的,没有丝毫法国人的理论风格,写得非常流畅。他说哲学就是追求好生活,这个话讲得没有错,虽然好生活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是人生的目的,可是什么是好生活?
其实中国哲学到最后,你也可以说,根本的关怀点就在追求什么是一种好的生活。我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对这个问题讨论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和幸福联系在一起。什么是幸福?我们知道有很多讨论,但是至今哲学家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定论。为什么?因为好生活的问题,实际上至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看来,不能够非常肤浅地用外在的指标,比如一年挣多少万或者说拥有什么东西。好生活实际上是你对幸福的理解,而对幸福的理解在我看来大概是一个人对自己人生的理解。苏格拉底讲过一句话,未经反思过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因此对古希腊哲学家来说,人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件严肃的事情当然牵扯到你对自己的生活要有深层次的思考。
好生活——如果我们一定要说——我个人认为包括这几个方面:第一,它包括我们对自己、对人是怎么回事的看法;第二,天人关系,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按照中国哲学讲是天人关系,按照西方讲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第三,当然还有我们人是社会当中的人,所以什么样的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因为人是一个社会的动物,所以好生活跟好制度一定联系在一起。加尔布雷斯写过一本回忆录,叫《我们时代的生活》,他把这些东西统一起来考虑,可能才会考虑什么叫“良好生活”。
当然论坛的题目还加了一个“我们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问题,所以每个时代对美好生活的思考恐怕也是对这个时代的思考。我们这个时代是怎么样的?我们每天打开电视机、打开各种各样资讯的媒体,会发现并不可以让我们内心很宁静。所以这还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周濂:张老师刚才引入了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生活和良好形成的理解。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德性在他那个时代起着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说到德性生活、良好生活,我想起前些天读止庵老师的一个访谈,您在里面谈到,说您的母亲在去世前两年,找了174个小说,把它读完了。您又说日本著名的作家尾崎红叶在临终前去买《大英百科全书》,用三个月时间读完了。我读到的时候特别感动,觉得这是所谓良好生活的一个典范。但是看这段话的时候我的余光扫到页面的一个广告栏,就是“苹果ISO9:你必须了解到的10亮点”。然后我就觉得良好生活真的非常之难。

止庵:我先讲一下“我们”前面的“时代”,就是“文革”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很难想到良好生活,但并不是一分钟都没有良好生活。我讲我们家来一个客人,这个客人是我爸爸的一位朋友,一位演员,很能喝酒,之后就喝醉了。他要吐,就拉我们家大衣柜,说他是爱干净的人,不能吐在我们家里。我说这不是大门的门,这是大衣柜。但他不听劝,后来就吐在了大衣柜里。这个在别人看来真的不是良好生活,但是这个对于他自己来讲,在那一刻来讲是不是就是他的良好生活?
我们这个题目叫“我们时代的良好生活”,“我们”搁在这个时代前面,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儿。如果这个标题改成“这个时代的我们的良好生活”,这样的话“良好生活”就有一个主语,可是现在这样的写法,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是“我们”的良好生活,还是“我”的良好生活。我们的良好生活和我的良好生活可能不是一回事,别人的生活不一定能照搬到我的良好生活,我的良好生活也不一定纳入到我们的良好生活。以我活了五十多岁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凡是把良好生活弄得不是一个人的,而弄成一帮人的或者一个群体的、一个民族的,背后就是一个坑。如果大家都过良好生活的话,这种生活恐怕就是最不良好的生活。假如说有一个人带着我们共同过良好生活的话,我觉得赶紧把这个人诛灭,根本不能留这个人在世界上存在,因为根本就是一个大祸。
所以从我个人来讲,我对一种集体的良好生活,慢慢地就不信,就信我的良好生活。我能做到的,就是做到不妨碍别人的良好生活。当然别人最好也别妨碍我的良好生活,大家相安无事,和平共处。
一九二几年的时候,钱玄同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说如果人人各扫门前雪,莫管人前瓦上霜的话,这是多么好的生活。但现实往往不是这样,大家往往都不扫自己门前的雪,只想管他人瓦上的霜,这样好不了。
我小时候读的一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就是《庄子》。这里讲了很多今天这个话题的事情,比如他讲到北海有一个皇帝,叫倏,南海有一个皇帝叫忽,中央的皇帝叫混沌。倏和忽都有一个七窍,混沌是没有七窍的,他没有,多苦,咱们给他凿一个,可这样就把人凿死了。就是把我的范式加给你,你可能活都活不了。这是对我们的劝解。
《庄子》还有一个故事对我影响很大,就是有一个国王派一个使臣找庄子,说给他钱,让他来做官,就是礼聘他。庄子说,你听说国王那儿有一个神龟,这个龟死了三千年了,还被装在匣子里,人人对它非常敬重。他说死了三千年的龟好,还是在泥土里爬的龟好?那个人说当然是在泥土里爬的好。庄子说,那你还是让我在泥土里爬吧。其实就是说,我想把这些都撇开,你说的那些良好生活我不想过。
周濂:谢谢止庵老师,他对我们的主题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分析,就是:我们是谁?什么时代?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发问。其实联系之前张汝伦老师说的好生活和好制度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呼应的。其实止庵老师想说的是好生活可能只是关乎一个人的,而好制度可能是关乎更多人。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正义追问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一起。比如说我虽然非常讨厌某些人,像司马南,但是某种意义上我还是要跟他生活在一起。但是你要揪着我的脖子上,你必须跟司马南过同样的良好生活,我觉得我只好用脚投票了。所以政治哲学追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而伦理学追问的是我如何能够过上一个良好的生活。我觉得止庵老师用非常生动有趣的例子给我们阐释了这个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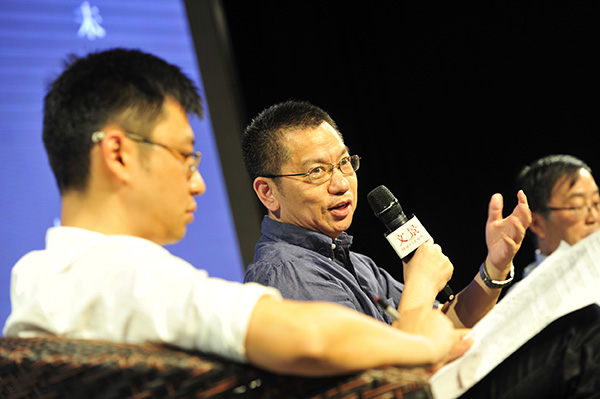
干春松:我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吃了一惊,三个是哲学的背景,另外两位作家。作家是有另外一个称号,叫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哲学家似乎是告诉人家生活的道理,因为我曾经的同事周国平就是专门告诉人家该怎么活的。但是如果你在大学待过,就知道哲学家活的是不太良好的生活。理由有几个,一个是哲学家善于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刚才张老师和止庵先生的发言,大概也能体现这样的特点,就是哲学家呢,就是没事找抽的那种。再者做哲学的跟作家比的话都是收入比较低,生活也不太良好的,周濂老师除外,因为他兼有哲学家和作家两种身份。
我觉得哲学家跟作家谈良好生活是找虐。为什么呢?我会问:我凭什么告诉人家,我都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美好的生活?就是说我凭什么从我的经验里,一直活得不算太好,怎么就突然有了资格去告诉人家该怎么良好生活?无非我是教哲学的。大学里疯子最多的可能就是哲学系,很多人家好好的孩子进来,被我们教了之后想死的人不少。不是考虑怎样好好活着,是考虑怎么好好死。我始终怀疑我自己,有没有能力告诉别人怎样好地生活。
所以我觉得一个良好的生活可能还离不开一个良好的社会。这就是我们该怎么弄在一起,刚才周濂老师说不想跟司马南生活在一起,止庵老师说不能强迫他过什么样的生活,小时候我妈教育我,好好学习,才能过好生活,但我能像止庵老师刚刚说的“诛灭”了我妈吗?
我在大学里是教儒学的,我自己一定要说儒学的好处,因为儒学就是在探讨大家怎么集体生活在一起的。当然很多人会说,你这样当然不太考虑个人的问题,但是我的确觉得,儒学它好的地方在于说,它是提倡一种好的生活,它会有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现在大家都不信了,但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我经常说它有一种劝诱性的,就是你跟我这样过,会过得不错;你不过的话,你爱进山隐居隐居,它没有任何强迫的意思。它通过自己活出美好生活来影响别人,这也是它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儒家活在这个世上很累,历史上,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王阳明,不是被人打成政治上的反对派,就是被宦官迫害,没有几个过得好的。我要说的是,我不能做到比别人生活过得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历史上存在着这样一群人,他不像庄子那样说,我在山里待着,他是要告诉你: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首先要在一起生活。第二,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自己先做成什么样的人,才能让别人做成什么样的人,你不听我的我没有办法。这样的理论,我觉得费孝通先生有一个比较好的概念,我自己认为是比较贴近经典意义上的或者先秦的思想,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问题。就是自己独好不是好,大家好才是好。
周濂:我纠正一下,我说的是如果不得不跟司马南生活在一起,但是我坚决不会跟司马南一起过良好生活,这还是有差别的。儒家还是希望让大家都过上良好生活,当然我们现在都不太信了。
你们不要听干教授说他的生活多么悲催,他的生活好着呢。刚才问他,他说刚刚打完羽毛球,还有刚换了一台轿车。我说你为什么换这台车呢?他说我女儿想让我换。在儒家,不可想象父亲要听女儿的话,所以我想他是受到了自由主义污染的儒家。

王小峰:其实良好生活分两个层面: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坐在这儿讨论的,肯定不是在讨论物质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百万元户了,只要有一套房子,所以物质上不用讨论,我觉得还是精神上的。就是说从我个人的这些年的生活经历,我觉得止庵老师刚才说的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就是我过我的良好生活,别人不要来干涉我;或者说我不愿意接受你的那些价值观,我跟你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周濂:他发言的主题意思是,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越少就越能过上良好生活。其实我觉得止庵先生和王小峰先生的观点比较类似,就是与这个时代没有联系的生活可能就是良好生活。张汝伦教授主张是有德行的生活就是良好生活,并且是要建立在好的制度基础之上的生活,才是良好生活。干春松教授他的观点可以用“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来概括。其实从上述四位嘉宾的观点可以看出来,关于良好生活是什么,其实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我想请问张老师,您对刚才三位嘉宾有什么补充意见吗?
张汝伦:其实事情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自己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你想过你自己的生活,比方“文革”当中,千辛万苦,我的一个亲戚从他的朋友那儿借来两张唱片,是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和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听了五分钟,就有人上门敲门来了,说你们跟我到派出所走一趟。因为上海的住宅条件很差,邻居告密了,说你们在听资产阶级音乐。封套上写着,革命导师列宁曾经说过,“我难以想象人类能创造出这么美好的音乐”,说这是列宁讲的,但还是不行,一起带走。我问你贝多芬是哪国人?德国人。德国人不就是资产阶级?儒家这点上是很清楚的。你想独善其身,别人可能认为我有一个权利我就可以把你弄到派出所去,那个东西就没收了。万幸的是没有让你在里面坐着,只是把东西没收。这不是我讲的,其实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最美的哲学史》,那个人写到十七世纪的时候,文艺复兴时期的开始,写皮埃尔·培尔,写培尔为什么对人这么认识,然后写到整个的启蒙时的思想。当然很奇怪,可能自由主义者不太高兴,为什么不写洛克?因为作者是法国人,所以不提洛克,纯粹从法国写过来。所以可以看到很多考虑,有作者认为说,我们西方之所以有这个制度的话,是因为其实是围绕,他当然没这么说,是我读出来的,是围绕着好生活,我们才说好生活应该这样。比方说人的权利优先,比方说人有自由,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天赋的权利,等等。这背后的动机实际上是好生活。因为你说人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这只不过就是一个认定。没有说逻辑上的理由,都是一个认定,其实都是一个断定,后边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语言。所以这个就是恐怕我们没办法现在到岛上去过像鲁宾逊那样的生活,像动物那样的生活。班固讲过,人从天赋上来讲不如很多畜生,爪不如畜生利,力气不如畜生大等等,但人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就是因为人能“群”。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今天不能很简单地回答。
刚才干春松讲了,儒家大概没几个混得好的,如果讲好生活的话,孔夫子2岁死了爹,17岁死的妈,老婆和孩子都走在他前面,最后他是孤家寡人老头一个。从他个人生活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可是我们现在骂孔子的,捧孔子的,从来没有考虑过他曾经作为一个人承受的煎熬,以及个人的生活对他考虑问题的影响。其实你想想,他绝对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当然《论语》不是他写的,是学生给他记录下来的,学生跟他在一起觉得老师有魅力,把他的言和行编下来。他可能还写了其他东西,他肯定跟维特根斯坦一样,临死的时候,他说你告诉别人,我是过了多么美好的生活。维特根斯坦是得恶疾死的,但他觉得自己过了美好的一生。这个问题我想人会一直想下去的,为什么会想下去?因为我们过得不太好。

周濂:刚才止庵和王小峰老师谈的更多的是倾向于消极自由的理念,就是不受干涉的自由。像张老师说的,很多时候我们自由是会受到干涉。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什么样的干涉是正当的干涉?比如说我如果不受干涉的自由,伤害到了别人不受干涉的自由,我这个自由是要被干涉的。如果这样干涉的自由没有伤害到你的基本自由,但是你却用良好生活这样的价值来试图干涉我的生活是否成立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儒家代表干春松教授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干春松:我这么说,因为刚才周濂老师采取了一些措施,说我到底是怎么样的,把我生活降低成开什么车的状态,所以我还是挺考虑精神上的享受。
我要说的问题是什么呢,周濂老师说了一句话,好在我现在不太信,或者说我们不太信儒家。但是我觉得周老师说这个话可能有点说过了,他微信聊的最多的就是他的父母,我觉得周老师是特别关注家庭幸福的一个人。所以说家庭的幸福或者对孩子的教育,这些可能比他哲学的视角更重要。
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个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就是他可能不是有意这样,而是自己流露,这样对家、对于父母和孩子这样的一些情感,其实恰好是儒家特别看重的情感。周濂说我是被自由主义污染的儒家,其实他是一个被儒家滋养的自由主义者。
刚才张老师说的,其实我觉得在生活中都会遇到这样的,打比方说在座的诸位可能单身,也很享受单身的生活,但是总会有人问,有朋友没有,我给你介绍一个。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习惯的想法,觉得这样的生活是一个好的生活,你应该是这样。这可能是你生活中的一个小事。刚才止庵老师说了一个大事,有些人不是关心你个人的事,甚至关心你所有的事。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刚才周濂说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我当然很尊重止庵老师和王小峰老师,就是不受别人打扰的生活。当然我也尊重像张老师说的,孔子忙忙忉忉,他总是想让别人过得好点。就是世上有两类人:我自己过得挺好,你别烦我;但是有一类人,总是琢磨别人,像周濂老师总是琢磨怎么让我们这个社会好,就是像刚才说的制定什么样的规则,这些规则是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制定,总是有人琢磨这些事,这个背后的精神就是我们说的兼济天下的精神。
刚才听王小峰老师说,他很不满意我们现在的状况,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抗议现在社会贫乏的,他这个就是兼济天下的胸怀,他是用独善其身的方式表现出兼济天下的胸怀。我自己认为,现在很多的人,说不信儒家的那些,他可能自己也不太信,但是在他的生活中,我越看周濂越像儒家,是热爱家庭、孝心父母、热心公益事业这样的大丈夫和君子,这样的东西他说不信,我都不信。
周濂:我都不好意思反驳你。
干春松:所以我是特别同情他。他一天到晚希望别人过得好,尽管他可能起反作用,但是我们不能怀疑那些希望大家过得好的那样些人的做法,包括王小峰老师,包括周濂老师,当然也包括在座的另外三个人。
周濂:我的确受到儒家思想的滋养。我说儒家对我来说是生活,但是对干春松来说是生命。生命的意思就是说,会把儒家一些有益、重要的信条放在我非常私人化的伦理当中去贯彻它,但是我会很警惕是不是把这些价值信条推而广之到陌生人的身上,甚至把它作为一个政治的基本原则。我觉得这是要做一个区分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当然会承认儒家对我的私人生活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滋养,没有问题。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