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亨利·基辛格:武器装备一直在变,但政治家的任务不会变
【编者按】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应邀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方面高度重视此次访问。基辛格本人著作也在近期密集出版,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作《世界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则即将出版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第一本书《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
《重建的世界》回顾了拿破仑战争后期以及欧洲政治家们为取得长期和平作出的种种努力。在一个大多数政治学家备受热核战争威胁困扰的时期,讨论十九世纪早期欧洲的宫廷外交看上去缺乏时代性。但是基辛格暗示,即使战争的装备改变了,政治家的任务也不会变。本文选自该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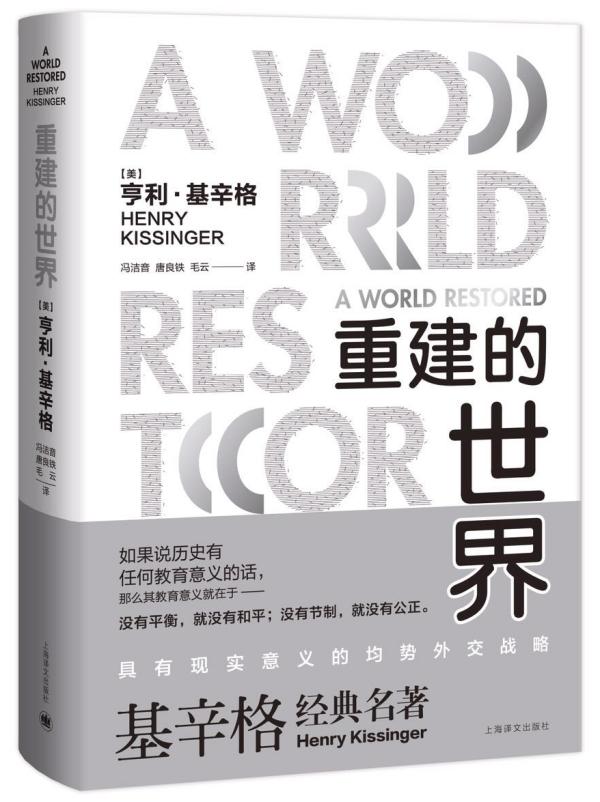
身处热核毁灭威胁的时代,不免让人怀念那些较少采取严厉制裁措施的外交的时光,那时战争的危害是有限的,大灾难几乎无法想象。如此形势之下,也难怪实现和平成为关注焦点,对和平的需求被认为是实现和平的推动力。
但实现和平不像渴望和平那样简单。因为历史离不开复仇女神涅墨西斯的身影,她以另一种形式满足人类的愿望或过分实现人类的祈祷,从而将其击垮。回顾以往,那些看似最和平的日子却是最少寻求和平的时候,而人们似乎无休止地寻求和平的时候,反而始终无法获得安宁。每当和平——即避免战争——成为一个或数个大国的首要目标,国际体系就处在了国际社会中最霸道成员的摆布之下。当国际秩序认识到即使为了和平某些原则也不可让步时,至少还可能在实力均衡的基础上建立稳定局面。
因此稳定往往不是追求和平的结果,而是产生于一种普遍接受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不应与正义的概念混淆,它只是有关可行性安排的本质及外交政策上所容许的方法与目标的国际协定。它意味着该国际秩序框架被所有主要大国接受,至少一定程度上没有国家过于不满,没有像《凡尔赛和约》后的德国那样以激烈革命的外交政策来表示强烈不满。合法化的秩序并不能完全阻止冲突发生,但它限制了冲突的规模。战争仍会发生,但将以现行格局的名义展开,战后的和平会被认为是更好地体现了“合法化的”普遍共识。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即通过谈判协调分歧,只能在“合法化的”国际秩序下进行。

外交是一门控制权力使用的艺术,无法在如此的环境下施展。认为只要有“诚信”和“达成共识的意愿”,外交手段总能够解决国际纠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处于变革的国际秩序中的每个大国都会被其他强国看做是恰恰缺乏这些品质。外交官仍会会面,却无法说服彼此,因为他们不再有共同语言。由于缺乏对什么是合理需求的共识,外交会议充斥着对基本立场枯燥乏味的重申、对背信弃义的谴责或“缺乏理智”和“颠覆破坏”的指控言辞,变成了一场场煞费苦心的舞台剧,意图将尚未表态的国家贴上某个对立体系的标签。
对于长期习惯于和平安宁又毫无灾难经历的国家来说,这将是艰难的一课。经过一段看似永久的稳定时期,它们几乎不可能相信革命的国家声称要摧毁现行的体系架构是认真的。因此现行体系的维护方一开始往往如此对待革命的国家,好像它的抗议只是策略层面上的,好像它实际上接受了现行的合法体系,而只是为了讨价还价才夸大了它的情况,好像只是因为心怀怨恨,想得到一些有限的安抚而已。那些及时对危险做出警告的人被认为是杞人忧天;建议随机应变的则被认为是稳妥理智的,因为他们占尽了所有充分的“理由”:他们的论据在现行框架下被视为有效。“绥靖主义”如果不是作为争取时间的手段,那就是因为无力对付无限制目的的政策。
但革命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它拥有坚持自己信念的勇气,愿意甚至迫切渴望将它的信念贯彻到底。因此,无论一个革命国家能取得其他怎样的成就,它也将产生侵蚀作用,即使不能改变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至少会影响该秩序运行中的制约力量。稳定的秩序具有自发性的特征,革命局势的本质则是具备自我意识。在合法时期,责任原则是再理所应当不过的而从不被提及,因此该时期在后来者眼里似乎肤浅和自以为是;而在革命的局势下,原则却成为关注焦点,一直是人们的话题。成效甚微的努力很快就耗尽了其全部的意义,双方以同样的词语来援引各自有关合法性“真正”本质的版本也就很平常了。由于在革命的局势下,比起调解差异,竞争体系更在意破坏忠诚的行为,所以战争或军备竞赛就代替了外交手段。

政治家的作用是什么?
那么政治家发挥的作用是什么?有种社会决定论研究将政治家贬损为被称为“历史”的机器上的控制杆,是命运的代理人,他或许能够对此命运有所察觉,但是却不顾自己的意愿继续成就此命运。这种相信环境的普遍存在和个人的无能为力最后扩展为相信决策的观念。人们总是听说计划的偶然性,因为无法了解事实,听说行动的难处,因为知识有限。
当然,不能否认政策可能会产生于虚空,也不能否认政治家会遭遇他必须作为既定的存在来对待的材料。不但资源的地理位置和可获取性能够显示政治家才能的有限性,而且人民的性格及其历史经验的性质也能同样显示出这一点。但是我们说政策不能创造出自己的实质,这并不等于说实质可以自我实现。意识到拿破仑帝国摇摇欲坠,这是1813年政策的条件,但是它本身并非政策。是否必须以均势秩序来取代革命的时期,是否行使意志将让位于坚持合法性,这可能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事情。但是只需研究一下大部分国家采取的摇摆不定的措施,就能理解,无论是这种均势的性质还是实现均势的措施都还不是一目了然。
无论国家利益现在看来如何貌似“不言自明”,当时的人们却被迫面临政策的多种选择,要考虑互相矛盾的行动方针:大部分不提倡无条件中立的奥地利政治家或者认为必须继续与法国结盟,巩固奥地利与无往不胜的征服者的关系,或者认为必须立刻改变立场,考虑到横扫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热忱。

梅特涅(先后担任奥地利外交大臣和首相)几乎是独自一人坚定不移,因为他坚信拿破仑的帝国与均势体系不相容,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多语言的帝国要与民族主义的时代相容。与此同时,当英国内阁催促推翻拿破仑,后来又要求条件苛刻的和平时,那只是反映了内阁的意见。是卡斯尔雷(英国外交大臣,1812—1822)造就了均势的和平,而非报复的和平,造就了一个和解的法国,而非完全丧失能力的法国。对这些政策的选择并不在于“事实”,而在于如何诠释事实。它涉及的事情就根本而言是一种道义行为:是一种判断,其有效性既有赖于目标的构想,也有赖于了解可用之材,后者基于知识,但并不等同于知识。
因此,衡量一个政治家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有能力识别力量之间真正的关系,并且使这种知识为他的目的服务。奥地利必须寻求稳定,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国内体制所决定的,但是它能够成功地将其国内合法化原则与国际秩序的合法化原则等同起来,即使是短暂的,而且无论如何不明智,那也是它的外交大臣的功劳。英国也尝试在实力平衡中寻求安全,这是二十三来间歇性战争的结果,但是它居然能成为欧洲协同的一部分,那要归因于一个人的努力。因此,没有什么政策比它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更好。
卡斯尔雷作为政治家的衡量标准是,他意识到在建设合法秩序时,保持欧洲团结比实施报复更重要,而梅特涅的衡量标准是他从来没有混淆他所取得成就的形式与实质,他理解奥地利帝国能够生存下去,不在于取得胜利,而只能在于和解。这两人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超出了手中可用之材的能力:卡斯尔雷的设想超过了他本国社会的构想,而梅特涅努力的目标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是无法企及的。
但是仅仅根据政治家的观念来判断他/一位政治家是不够的,与哲学家不同,政治家必须实现自己的构想。政治家最终总是要遭遇他手中可用之材的惯性力量,会遭遇这样的事实:其他的国家不是可以操纵的因素,而是必须与之和解的力量;安全的需求因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内体制不同而有差异。他的工具是外交,是一门艺术,通过达成一致意见而非动用武力,通过展示一种将特定企望与普遍共识协调起来的行动的理由,来将国家联系在一起。
外交活动有赖于说服而非强迫,因此 前提是有明确的框架,或者通过对合法性原则达成一致意见;或者,理论上说,通过拥有对国家之间关系的相同诠释,尽管后者在实践中最难做到。卡斯尔雷与梅特涅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他们非凡的外交才能,两人都能主导自己参加的每一次谈判:卡斯尔雷是因为有能力调解相冲突的观点,以及具有得之于实证政策的一心一意;梅特涅则是因为具有掌控对手的异乎寻常的个人禀赋,
他有能力定义一种道义框架,使得当对手作出让步时,看上去不像是屈服,而像是自愿为共同事业作出牺牲。
然而,对一种政策的严峻考验在于是否能获得国内的支持。这有两个方面:在政权机构之内使一种政策合法化,这是一个涉及官僚理性的问题;是使其与民族经验相和谐的问题,而后者又是一个涉及历史发展的问题。
政策的精神与官僚的精神是根本对立的。政策的本质是它的偶然性;它的成功取决于判断的正确,而这种判断部分是出自推测。官僚主义的本质是追求安全,其成功在于可靠性。深刻的政策得以成功,在于持久的创造性,在于对目标的不断重新定义。良好的执政管理有赖于常规,也即对可以应付平庸的关系的定义。政策涉及风险的调整;而行政则涉及避免偏差。政策的合理性在于其措施与平衡感之间的关系;而行政的合理性则在于根据既定目标所采取的行动。试图以官僚方式来实行政策,将导致追求可靠性,结果往往为事件所困。努力在政治上进行管理则导致完全不负责任,因为官僚机构的设计本意在执行,而非构想。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