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东吴法学”一百年:中国法学教育的光荣与梦想

上海市昆山路146号,一栋4层小白楼,方方正正,隐匿于市井街巷当中。除了附着于正面墙体上挑高三层的拱门立柱上还能捕捉到一些建筑当年受过西方风潮影响的痕迹,整栋小楼再无特别之处。
普通的小楼,有着不普通的过往。63年前甚至更早,进出这里的是一批中国最精通英美法、最擅长比较法研究的人物。小楼正是被称为“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最著名的法学院”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当年的所在地。
今年,东吴大学法学院建院整百年。消失多年后,再被重新提起,人们对它的兴趣丝毫未减,它的身上有太多东西值得探究,而最为人关注的要数它饮誉海内外的法学教育——从这里走出去的毕业生曾与中国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在区域和全国范围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出生地:上海
9月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生日月,而上海是它的诞生地。
1915年9月3日,在上海负责东吴大学(开办于1901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以西式办学体制兴办的近代高等学校)附属中学的兰金(Charles W. Rankin)借中学的校舍创立了“东吴法律专科”,以夜校的形式招生,传授法律知识。兰金是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位律师和传教士,他有着极敏锐的触角,创办东吴法科是为了“法律职业对人类过去的意义”以及“中国对律师和领导者的迫切需要”。确切地说,在上海这个工商业中心,兰金看到一所法学院的成功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东吴法学院是嗅着市场机遇的气息而生。
“诞生在上海是因为这个城市的秉性。”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说,“中国本土律师到民国后才有了职业资格。民国成立前四十几年的时间里,上海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诉讼,那时无论是什么样的诉讼,哪怕原被告双方都是中国人,也是请的外国律师。在法租界的法庭上用的是法文,在公共租界法庭用的是英文,简单来说,就是‘全球化’的时代需要诞生全球化视野的法学院,中国不能没有法学人才,这时东吴法学院应运而生。”
借着熊月之的话,来看看当时的上海。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租界林立、华洋杂处,对外贸易相当繁盛。东吴法学院章程里曾提过“上海工商繁盛,狱讼滋多”。那时,中国尚未形成自己的商事法律,上海的商业完全受控于英美商业界,依托的最重要的商法就是“英美”的。
凭借治外法权(又称领事裁判权),英美等13个国家先后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领事法庭,英美两国还分别设立了驻华法院。在上海这样一个混合的司法领域,通晓外国法和中国法的外国律师非常吃香,甚至供不应求。
身处特殊历史环境的上海为东吴法学院提供了潜在的师资,兰金通过“刷脸”请来了一批驻上海的外籍律师与法官为学生兼职教课。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夜校的教学工作便开启,这批兼职老师低偿甚至免费授课,为学校带来的是最系统的美式法学教育。兰金的想法得到了时任美国驻华法院法官罗炳吉(Charles S. Lobingier)的响应,罗炳吉是比较法和罗马法的专家,曾在菲律宾开设比较法学校。作为在中国建立法学院的积极推动者,他认为:“应当首先将外国法律制度教授给中国年轻人,让他们将来从中选取素材建立他们新的法律体系。”The 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中国比较法学院)这个名称也是他的提议,后来东吴大学法学院的中文名称有过变化,但是这个英文名称贯穿始终,并为海外熟知。
将视野放得更广一点。东吴法学院的建立契合了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20世纪初年,中国政府已经着手法律改革和现代化的重要规划,致力于建立一个既能与中国社会相契合,又可为西方列强所接受的现代法律体系,以取代其传统的司法制度。在中国建立现代法律制度和颁布新法典无疑需要对法官和律师的培训,然而中国从未有过正规法律教育的传统(康雅信《中国比较法学院》,张岚译,载《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兰金相信,法学院会为中国建立新的法律体系做出贡献。
正如兰金之后的教务长刘伯穆(W. W. Blume)所说:“中国法学院面临的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为学生提供‘适应这个国家需要的法学教育’。”东吴法学院的对策是讲授比较法。“只有在对中国本土法律与那些现代国家法律的比较研究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法律制度,中国才能够在良好地管理自己的同时,使其法律制度与现代工商业世界相协调。”
在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健看来,上述的地理文化因素、美国化的办学特色,对造就东吴法学的影响和地位至关重要。“东吴法学院创办于上海,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祥地,城市化建设起步早,国际化程度高,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各方面都处在关注域中,在这样一个掌握着中国近现代文化话语霸权的城市创办法学院,是容易获得全国的影响和声誉的。但仅在上海,还不足以造就东吴名声。”
当时的上海拥有众多法科机构,如复旦、震旦、大夏、中国公学等。东吴法科能从中脱颖而出,靠的是其美国化的办学背景及其办学特色。“美国在华法律家群体,包括在沪执业的罗炳吉、费信惇、佑尼干、刘伯穆等皆为有培养法律人才兴趣的美国职业法律人,不仅为‘东吴法科’注入了英美法教学模式的先天基因,同时又为适应在华办学的实际条件,发展了比较法教学这个重要的办学特色。美国化的办学背景这个因素随着美国在二战后取得世界法律智识的领导地位而被放大,进而促进了东吴法学的地位和影响。”王健说。

一个个写入历史的名字与故事
“学校外貌几乎没有怎么变,只是进来的地方本来有个篮球场。”顾念祖曾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高院院长,在东吴法学院读过两个学期。坐在当年的教室里,86岁的顾念祖一点点还原着上学时的情景:“课桌椅换了,我们那时就是每人一张椅子,椅子扶手处固定着一块小桌板;19岁读大学,进来感到压力很大,其他课目都可以应付,就是英美法大纲不行。上课的老师是教务长鄂森,他曾在东京审判做检察官顾问,上课从点名开始就是英文,讲课也是英文,听得有些吃力。”
有人问顾念祖,为什么今天,在这座学院消失了这么久之后,还要纪念它的诞生?顾念祖的回答不假思索:“因为这所学校走出了许多人,做过许多事,而现在却很少有人记得。”
在教育界负有盛名的东吴大学法学院,除了研究相关领域的人及其学生后人,现在恐怕在很多人的耳朵里都是陌生的。
列举一下印上“东吴法学院”标签的人物及历史事件。著名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八大律师”中,七人为东吴法学院毕业生。吴经熊与盛振为同为东吴学子,后成为学校管理人员,他们一同参与起草构成民国“六法全书”主体的民、刑、商法典,吴经熊更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其发表的《吴经熊氏宪法草案初稿》曾一度引起争论,成为1936年《五五宪章》的蓝本。有学者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吴法学院的毕业生“在法律职业和在民众生活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而且上海法律界几乎任何一个有影响的人物都一度与法学院有关”。
20世纪40年代中期,海牙国际法学曾评选全球50位杰出法学家,中国有王宠惠、杨兆龙两人入选,皆是东吴法学院教授。
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而与东吴法学院有关的事件中,最为国人念怀的是他们在东京审判中做出的贡献。1946年至1948年间,盟国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共有17人参加,其中10人来自东吴法学院,包括首席检察官向哲濬,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助理检察官裘劭恒,检察官顾问鄂森、桂裕,法官秘书方福枢、杨寿林,检察官翻译高文彬、刘继盛、郑鲁达等。
今年93岁的高文彬是目前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健在的亲历者,曾做过向哲濬的秘书。说起往事,高老充满自豪:“为什么找我们去,因为只有东吴法学院是教授英美法的,学生英语都很好。我们念英美法,课程完全是英文讲授,老师也请外国老师,英美法是请美国总领馆的法律顾问给我们上课,德国法则请徳领馆的法律顾问上课。那时到远东国际法庭工作的人很多都与我们东吴法学院有关系,我到今天也觉得荣幸。”
远东军事法庭是由美英主导的国际审判,主要采取英美诉讼程序,有无有力的证据,对于判定战犯罪名至关重要。但是,由于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注重搜集保留证据,日本方面投降后又销毁了大量犯罪证据,摆在中方检察官面前的是艰难的搜集战争罪证的过程。最终,在中方检察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堆起来有一尺多高的证人证词和其他证据材料呈上法庭,最终致日本战犯伏法。
东吴法学院秉承了东吴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寓意学校教育与报效国家之间的逻辑关系。首任华人教务长盛振为曾言:“良以法律教育之目的,不在培植专为个人求功利之普通人才,当为国家社会培植知行合一、品学兼优之法律人才。”东吴法学院走出来的学生,恐怕最能证明这座学校的能量。这种能量在30多年间的迸发,曾引得无数人探究原因——1989年美国法律史学会年会、1990年美国亚洲研究年会上,相继出现了《民国时期的法律教育》《东吴法学院与上海律师界》等多篇学术论文(盛芸《盛振为先生之办学理念》)。美国夏威夷大学法学教授康雅信(Alison W. Conner)更是多次往返海峡两岸,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并走访多位东吴老人,以探究这所学院的历史以及其毕业生在现代中国法律职业发展中的作用。

“东吴法学”的秘诀
熊月之说,在东京审判的时候,东吴法律人之所以能涌现出来,不外乎学生的全球视野、比较法学的知识储备两个原因。这正是东吴法学院的两大“招牌”——英美法和比较法学教学,赋予其学生的特色。盛振为曾将东吴法学院的教育方针概括为:“原以英美法与中国法为依据,而旁参以大陆法,继应时势之需求,改以中国法为主体,以英美与大陆法为比较之研究。俾学生对于世界各大法系之要理,皆有相当认识。”
学院创建初期,可以说是完全照搬了美国法学院的模式,最初10年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美国专家以英文教授普通法,其课程也得到美国法学院的承认,许多学生毕业后赴美留学,其中不少人后来重返母校走上讲堂。
东吴法学院的英美法因素在学校的教学方式上得到了体现。例如在外语教学、型式法庭、案例教学法等多方面都反映了当时东吴大学法学院参照美国法学院的教学方式,按照英美法的体系培养学生(何勤华、高童非、袁也《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英美法学教育》)。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学院的新教师往往是刚获得美国学位的东吴毕业生,课程用的是最新的案例教材。在给时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的信中,当时还是教师(后任首任院长)的吴经熊这样写道:“我已经教了一个学期的法律了。我教的是财产法[用沃伦(Warren)的案例作为课本]、罗马法 [梭伦的书(Sohm's Institutes)]、国际法[用伊文(Evan)的个例],以及司法学[用萨尔蒙(Salmond)]。我敢保证,教学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常常,整个班都因一个问题而争论得冒火。学生们自然而然地按着他们的哲学倾向而分为两组,有时候是更多派别。……我相信,我的法律知识由于教学而变得较为巩固了。”(吴经熊《超越东西方》)
即便后来中国法的授课内容增加,这种英美法学的授课方式依然得以延续。高文彬还记得上学时的一段插曲:“我们学的都是英文原版教材,而当时外面是封锁的,英美书没法进来。我们就弄来本旧的,跑到上海四川路五马路,那里以前有个龙门书店,他们来帮我们做翻版书,实际上这是违法的。”王成培1945年入学,在他的回忆中也能看到东吴法学院的英美法授课方式:“英美法教学以案例教学为主,但教授上课的风格各不相同。我印象最深的是法律系主任姚启胤教授的《英美契约法》。他先在几天前公布下次讲哪几个案例,要求学生预习并写好案例摘要(包括案情事实、争议焦点、判决、理由四个部分)。在学生充分预习的基础上,上课用启发式教学,通过提问与讲解、讨论,引导同学们逐层深入地理解英美合同法的规则及其原理。每次提问都要记分,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40多年后,我离休到企业集团从事法务工作,在研究《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时,沉睡多年的英美合同法知识有些居然苏醒过来,帮助我消化新的知识,可见当年受益之深。当时教英美刑法的是刚从设在东京的远东军事法庭工作归来的鄂森教授,讲课时穿插不少审判日本战犯的案例……教我们《比较司法制度》的是法学家倪征燠教授,当年他刚从欧美考察司法制度回国……教我们本国法律课程的老师既有权威学者,也有在当时颇有声望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其中物权法权威曹杰教授教大部分民法课程,他是专注于民法教学和研究的著名法学家。”这种教学方式顺着“老东吴”的学脉一路流传下来,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朱应平犹记得,出身东吴法学院的浦增元先生本世纪给上海社科院的研究生上课时依然选用了他当时上学时接受过的教学方式——全程英文,用案例教学,要求学生看外文资料,熟悉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宪法案例:“老人家的英文非常好,是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后来中国宪法学会要派员参加国际宪法协会的学术活动,就让他去,他还担任国际宪法会议执行委员;我国每年出台的法律都会集成一到两本有着中英文记录的年刊,老先生生活条件不好,但这本四五百元的书,他一定要买。”
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范忠信感喟:“当年东吴法学院的这种‘与国际接轨’的办学标准,半个多世纪后才作为新中国法学教育的‘提倡标准’被正式提出来,尤其是‘国际类法学课程以外语进行教学’、使用国外原版法学教材的要求直到2000年前后才列上日程。”(《东吴法学传奇的史鳞片拾与沧桑浩叹》)
东吴法学院奉行的是职业化的精英教育,认为法学教育应当基本上是职业化的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严进严出”是其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比如入学学生必须完成初步的大学学习之后才能学习法律。上世纪20年代早期,在教务长刘伯穆主张下,入学要求提高到至少修满两年大学。法学院后来开设了自己的预科课程以保证学生受到高水准的法学预科教育。
不过,在国民政府的干预下,东吴法学院的法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为本科教育,而不再是研究生阶段的职业教育,培养职业法律家的教育模式被削弱,降低了其法学教育的水准。即便如此,东吴法学院的教学依然重质且严苛。王成培说,有相当部分同学无法跟上学院教学的步伐,一年级时班级约有80位同学,到四年级只剩40余人,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是功课负担重、要求严,跟不上就只好转学。与著名比较法学家潘汉典同一届入东吴法学院的有71名同学,1944年毕业时获得学士学位的为25人,即使将内迁重庆的部分学生计算在内,1944届毕业时获得学位的学生人数与入学时的人数之比,也不会超过50%。
比较法教学和研究是东吴法学院的另一特色。康雅信称,东吴法学院的办学宗旨、目标和教学方法都有其比较法的性质。2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法课程的引入,法学院的教学变得职业化,也在实际上更像比较法了。1927年改名为“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后,学院的管理层开始“本地化”,教务长和同年新设的院长一职均由华人担任——美国留学归来的吴经熊被任命为首任院长。吴经熊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曾在巴黎大学、柏林大学、哈佛大学等知名学府从事哲学和法学研究。1924年,他到东吴大学任教,之后又先后担任上海特区法院法官、立法委员、司法院法官、上海特区法院院长及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等。丰富的欧美留学经历使得吴经熊可以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之间转换自如,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哈德逊(Manly O. Hudson)认为吴经熊是“熟练掌握各个法律体系的大师”,“从未见过比他更适合做比较法学院院长的人”。
吴经熊、盛振为等一批参与过起草中国刑法和民法典的专家,都不赞成将他国法律简单地移植到这个急需建立新法律体系的国家,比较法正是在这个时机显示出其价值。随着中国主要法律的颁行,东吴法学院开设了广泛的中国法课,形成中国法和普通法的双轨制教学,学生可以受到英美法和中国法两个领域的训练,1927年至1939年间,东吴法学院的比较法教学达到其顶峰。
推动东吴法学院比较法课程在这一时期发展的关键人物是盛振为。他“以一种开阔的观点看待比较法学习,并明确地把它视为东吴法学院的宗旨,而不仅仅是一种传统”(康雅信《中国比较法学院》)。盛振为坚持东吴法学院应当自由讲授所有法律,人们并不是一定要同意所有讲授的内容:“只是了解它是什么,并且如果你愿意,尽管去批评它。”盛振为还致力于建设东吴法学院的比较法图书馆。1935年,图书馆已经拥有20000册法学书籍,被称为“远东最好的法律图书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20年代,东吴法学院还开设了硕士班,研究生部规章指导学生“以比较的方法研习法律”。这是中国现代最早开办法学研究生教育的范例。至1951年,东吴法学院断续进行了20多年的研究生教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东吴法学院迁至上海公共租界避难,其后8年法学院就在一个又一个临时落脚点继续开办。1941年12月,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法学院随后分成两支继续发展:1943年到1945年间,正规的法学院在盛振为的组织下于重庆重新开办;留沪师生暂避租界以东吴法学院的谐音“董法记”名义恢复上课,“董法记”貌似商号名,以此避开了日伪的注意和迫害。高文彬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法学院,他依然记得上学时的情景:“学校多次迁址,后来借用了爱国女校的校舍,那时上学是很难过的,我上学的路上会经过一个日军的岗亭,要停下来向他们敬礼,不敬就要吃耳光。为了避开这件事,我宁肯每天绕弯路到达课堂。”
直到1946年,两个分支终于合并,并搬回了昆山路14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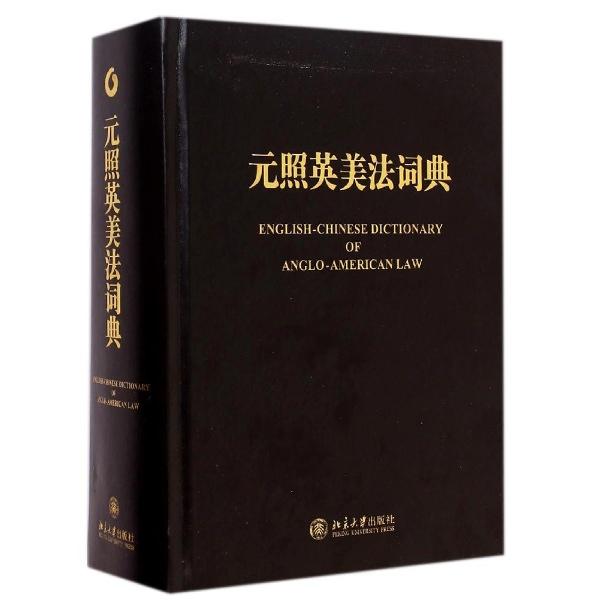
“东吴法学”的微光
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对英美等国的政治态度支配着教育和学术,由于强调建立社会主义的崭新法制而对资产阶级法律不屑一顾,更由于法律虚无主义观念长期占主导地位而使中国法制受到严酷的摧残,曾经辉煌的“东吴法学”长期没有受到正确的对待和应有的重视(艾永明《东吴法学先贤文丛》总序)。
尤其是1952年,教授“旧法”的大学法律系全部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新成立的政法学院。在这个过程中,东吴大学与其他院校合并成立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东吴法学院的法律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会计系并入上海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东吴法学院末任院长杨兆龙的女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陆锦璧评价那段时期称:“当时一直强调要用蔑视和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国民党《六法》及英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中外法律文化遗产统统被当作反面教材来批判。”
与此同时,东吴人几乎都被打为“右派”。盛振为以反革命罪获刑12年,尔后发往苏北农场劳改,劳改6年后被遣往苏州教英语。鄂森曾参与东京审判、“七君子”营救等,却以与上海帮会有关联被捕。教授“旧法”的教师失去了教授法律的资格,等待他们的工作是教授外语或在图书馆、资料室任职。
“东吴法学”,甚至是中国法学教育的学脉就此断裂。1957年,杨兆龙公开发表文章声讨这种“一刀切”的行为,认为其“过分强调法律的政治性而忽视了它的专门性和科学性;将党外的‘旧法出身’的人士估计得很低,认为他们不可能或者很难改造为对新社会有用的法学人才;不信任党外的法学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们”。而他未能自保,之后的人生饱受摧残。
即便如此,即便生活从此潦倒,“老东吴”们依旧在上海各处发着荧荧微光。
1958年,华东政法学院整体并入上海社科院,社科院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法学所。法学所在1978年恢复重建后,吸收了一批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新工作的东吴法学院老教授,尤其是法学所的编译室,成员全部是东吴法学院的毕业生。在那里,“老东吴”们组织编写了一套12本的《国外法律学知识丛书》,当时大学刚刚恢复,缺少教材,这套丛书起到了一个支撑全国法学资料的作用;他们编的另一套书是《各国宪政制度和民商法要览》,共5本,全靠老教授们自行翻译。香港回归前,有26大卷的香港法律大全要翻译成中文,因为知识断层,法律空白很多,这项工作无人胜任,编译室和他们散落在全市范围内的东吴校友再次担起重任。上世纪90年代,法学所的老师跟东吴老先生们互相支援,在社科院研究生部还办起了东吴比较法进修学院,虽无文凭,却十分被看好,有不少社科院甚至华政的学生来旁听。
2003年,《元照英美法词典》(主编薛波、总审订潘汉典)出版。这部词典的编纂历时近10年,由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牵头,联合了包括潘汉典在内的众多法学学人、东吴学子共同参与。潘汉典1940年考入东吴法学院,在东吴法学院取得学士与硕士学位,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成为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一直致力于翻译国外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文献,立志把国外最好的法律制度和先进的法学思想介绍进中国,发表出版了大量法律法学译著和多部外国宪法的中译本,被称为“外国法律法学翻译界第一人”。
一部词典的编纂,让藏身民间的英美法“大牛”们以东吴法律人的身份,重新走到一起。审稿老人的平均年龄为84岁,有人称《元照英美法词典》是东吴法律人的一份集体作业,而完成这份作业的每位老人都严谨相待。对这件事,高文彬的感受是:“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英美法,解放以后英美法被打倒了。现在我们有机会把我们过去所学的东西贡献出来,编这样一个词典,它将来肯定对后辈有很大用处的,说明我们过去学的英美法没有白学。”
《元照英美法词典》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460多万字,收入词条4.5万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这本词典为何如此必要?高文彬说:“文学英语跟法律英语不同,法律的言语严谨,有专用的词。比如说,国际法庭开庭时,法官要喊:‘All personnel beseated!’而不是有些影视节目里的‘Sit down!’后者是普通话,而不是法庭用语。”上海社科院教授、哈佛法学博士、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卢峻在词典的序中有着更系统的解释:清末修律以来,中国以日本为跳板与榜样,在法律制度方面借鉴与学习西洋的基本上是欧陆罗马法系的概念与学理。现代汉语中许多法律用语,在早期曾直接借用日本人的汉字译文,历经百年的沉淀,这套法律词汇已成为我们分析法律概念,进行学理探讨的基本语言工具,我们对它的历史源头已淡忘而浑然不觉。而当我们用这一套法律词汇来翻译英美普通法系的东西时,它的历史源头就鲜明地显现出来。欧陆罗马法系与英美普通法系在概念和学理上迥然不同,两者之间在很多方面找不到精确的对应译法。比如,英美地产法,尤其是英格兰地产法中的许多内容,无法用欧陆罗马法系里的“物权法”的概念阐释,如“freehold estate”、“copyhold estate”、“fee simple absolute”等。
令人欣慰的是,东吴法学的学脉也在重续。在台湾,1954年,东吴大学法学院重建,继续突出英美法教学,也为学生提供上大陆法或比较法专业的选择机会;在大陆,与东吴法学院有着渊源的三所学校——苏州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一起努力实现着对东吴法学传统的继承,比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比较法人才、训练学生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和案件的能力。如朱应平所说:“东吴法学院在历史上的办学方针、采用的教学、研究方法不仅在当时先进,在今天看来,也仍然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代表了中国法学院校的发展方向。”
(本文原载于《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9月18日刊,原题《“东吴法学”一百年》。《文汇学人》微信公号:wenhui_hr。)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