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访丨阎云翔:从新家庭主义到中国个体化的2.0版本
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前后,关于中国人口增长放缓、少子化、生育意愿等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最受瞩目的问题之一是中国人口增长放缓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潜在的影响。但除了人口与经济的宏观角度,反观家庭本身,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正在经历何种变化? 在新的人口转型中,我们又是如何言说家庭?
自新世纪初开始,一种新的家庭主义开始在中国兴起。这是一种家庭利益大于个体利益的价值观。但与传统家庭主义不同,新家庭主义已不再围绕祖宗崇拜,家庭利益也不再是光宗耀祖、传宗接代,有了一种全新的成功标准。这种新家庭主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更延伸影响到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道德取向,且越来越与国家发展紧密关联在一起。

今年3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教授阎云翔编辑出版的Chinese Families Upside Down: 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Neo-Famil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倒立的中国家庭:21世纪早期的代际互动和新家庭主义》),辑录了多位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并从“新家庭主义”的角度重新探索中国家庭变迁。此次访谈,阎云翔谈及为何近20年来,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急速上升,以及为何在当下的国家话语中,家庭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同时,透过“新家庭主义”的框架,阎云翔分析了中国近年来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化,并探讨了“鸡娃”等围绕家庭问题的社会现象的成因。最后,他谈及新家庭主义与民族主义和物质主义一同构成个体化的2.0版本。
一、 “亲子一体”的“新家庭主义”,个体成功不够,一定要家庭成功
澎湃新闻:你在2003年出版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谈的主要是个体的崛起、重视个人幸福、实用性的个人主义等。而今年你编著出版的《倒立的中国家庭》一书中,主要观察到的是一种新的家庭主义,也即家庭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的现象。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种变化?
阎云翔:2003年那本书出版后,我更多开始关注社会转型和道德变迁的问题,并发现了个体化这个更重要的趋势。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中,我主要谈了两方面:一是延续之前的脉络谈个体的崛起;二是谈社会结构的个体化,也即90年代制度性变革后,国家从社会福利的承担中撤出,要求个体承担更多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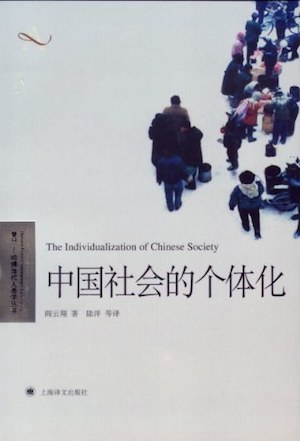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明显出现了风险社会的特征,现代化自身产生的种种问题和风险正在改变政府和社会的行为方式。社会结构的个体化将这些风险转嫁到个体头上,既不公平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例如,食品安全问题事关整个生产运输营销诸多系统,但我们最终的解决方式是非常个体化的,比如,大家开始分享如何自行辨别造假或有毒的食品,比较有条件的人开始到有机农场购买食品。个体只能凭借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来规避这些系统性的风险。但这个过程中,少数人的优势加剧了在获得安全食品上的不平等性。
个体怎么应对系统性风险一直是我很关心的问题。无论是欧洲的福利国家,还是改革后的中国,个体化之所以受到国家的制度性支持,就是因为很多风险被转嫁到了个体身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处在风险社会中的个体,被要求自己面对、解决这些系统性的风险,但又找不到能帮他们克服这些问题的资源,最后只能找到自己的父母和家人。这使家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从2015年左右,我开始研究家庭在社会生活中重要性的上升,而且观察到很多新现象,例如“孝顺”的重新定义:老年人放弃了对子女 “顺”的权威性要求,而年轻人会提供更多情感上的支持和关心,就是“孝而不顺”。
所以我一直紧密跟踪的其实是中国的个体化进程。中国个体化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我称之为个体化的2.0版本。
澎湃新闻:你近年提到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下行式家庭主义”(Descending Familism),也即将全家的资源集中在子辈、孙辈身上,例如现在夫妻双方倾全家之力来照料孩子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也是中国家庭一个重要的变化。如果我们与其他国家做横向对比,什么样的社会更容易出现“下行式家庭主义”?
阎云翔:简单说来,曾经有过传统家庭主义的社会容易这样,例如意大利、墨西哥等。另一种可能性是古典个人主义的缺席使得自我的界定是深陷在关系之中,尤其是家庭关系中的。这里有必要指出,我们对个人主义的理解有偏差,只强调自我中心和自私自利,完全忽视了个体的自主、自立、尊严和与他人的平等关系等等。所以,我认为古典个人主义从来没有在中国社会得到正确理解和传播。
近几十年来,虽然很多国家也出现了代际关系的加强,有祖辈照料孙辈的现象,但跟我们的情况有很大区别。例如在美国,祖辈的支持和阶层、种族有密切关系,背后是教育资源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祖辈支持在非裔群体中一直存在,因为父亲缺席的家庭很普遍。再如,单亲白人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需要祖辈的支持。
在美国这种个人主义占主导的社会,隔代抚育绝不是普遍的情况更不是道德化的常态。祖辈的帮助是雪中送炭式的救急措施,在有需要时提供,一旦困难解决就会停止。但在中国,祖辈照料是普遍现象,甚至变成了一种道德义务,如果有祖父母拒绝这样做,舆论会认为他们没有尽到责任。
有必要说明,我仅在2015年左右使用过“下行式家庭主义”来概括当时的研究结果,但是很快我就改用“新家庭主义”的概念。后者包括前者的内容但同时又涵盖若干新的发现。有别于祖先中心的传统家庭主义,新家庭主义下的家庭生活中心和各种资源从祖先向后代转移,特别是流向孙辈。要强调的是,资源下行不仅指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包括情感和生活意义两方面,都转移到子代、孙代身上。
这一方面导致“父系”的弱化,例如孩子可以选择跟母亲姓。另一方面,代际之间的亲密关系大大增强,出现了“亲子一体”的认同。近20年来的中国,代际、亲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超过了横向的夫妻亲密关系。例如,父母包办离婚的现象;子女闹离婚,最后和好了,父母反而坚持让他们离。这是因为子女在身份认同上离不开父母,而父母反过来也认为子女就是他们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新家庭主义语境下的子代反哺和青年困境也值得我们重视。80后一代的许多个体在过去的十年中陆续承担起养老育幼的双重责任,成为“三明治”中的夹层,至关重要但也几乎不堪重负。除了熟知的尽孝之外,子代反哺还包括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方面帮助老年父母适应不断加速变化的当代世界。2020年疫情爆发将老年人的新困境和子代的新责任都凸显出来。另据媒体报道,不少90后青年也开始居安思危,既考虑如何照护终将老去的父母又担忧自己未来的养老困境。他们看到自己的父母为照顾祖父祖母而不得不作出许多自我牺牲,在开始理解体谅父母的同时,也对自己的人生未来多了些前人未有过的焦虑。当看到豆瓣网上居然有多个年轻人建立的“养老互助”小组并讨论他们如何颐养天年的策略时,我顿时感到心中一沉。养老这些事情本不应该这么早就进入年轻人的视野。显然,新家庭主义绝不是单行道,而是十字路口,对许多人而言甚至是迷宫深处。所以,下行式家庭主义的概念早已过时,必须放弃。
在新家庭主义下,个体的成功还不够,一定要有家庭的成功。而且一个家庭是否幸福、成功,衡量标准是非常物质主义的。就连我们刚刚提到的年轻人担忧养老的问题,大家说来说去,最终的结论还是要挣钱,拼命多挣钱!微信朋友圈等新媒体的发展,也使这一点不断强化。大家一个普遍的焦虑是,总在看自己的家庭生活是否达标。所以要晒出漂亮的妻子、成功的老公、优秀的孩子。孩子的成功之所以越来越重要,也因为这是家庭成功的标志。而家庭的成功变成了你个人成功的重要标准。换句话说,新家庭主义下,个体的身份认同越来越融于家庭团体中。
澎湃新闻:今天的中国,一方面,代际间的亲密关系越来越强,但另一方面,当父母开始更多介入儿女的婚姻、甚至恋爱和离婚,育儿,把本来很私人的亲密关系、情感关系,转化成了可以精密计算的家庭项目。你如何看待中国家庭亲密关系中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
阎云翔:这个矛盾在传统家庭主义里基本不存在。传统的家庭是纯粹的功能性团体,亲密关系要尽量被压抑,不能高于家庭中的等级和纪律。新家庭主义中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上升了;但同时,家庭的功能性又没有消失,而且因为社会结构个体化的挑战,家庭的功能性甚至更重要了。
所以家庭就变成一个必须要理性经营的项目,需要有经营策略,齐心协力达到目标。其实不光是父母介入子女的人身大事,反过来也一样。比方说黄昏恋,基本就是父母受到子女的牵制和干涉。子女干涉的理由其实就是财产,担心父母的财产(其实也是整个家庭的财产)被骗走。这时父母又变成了子女要经营的项目。
新家庭主义下,理性经营家庭项目和家庭内的亲密关系是有矛盾的,家庭幸福和个人幸福之间也是存在张力的。处理这些矛盾要求人要有技巧。所以我们现在的心理咨询越来越盛行,而且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家庭关系。这些家庭关系的技术性指导也让家庭显得更像一个精心经营的项目。
澎湃新闻:在当下中国,很多引发人们焦虑的问题都跟家庭有关,例如最近被频繁谈论的 “鸡娃”。你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社会对于家庭问题越来越强烈的焦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阎云翔:我记得十年前,我一个美国学生的中国朋友,留学一年后回国探亲,他父母对他很失望,因为他没有变得像他们认为的美国孩子那样有主见。当时我的学生说:孩子又不是项目产品,你怎么可能想让他变成什么样就变成什么样呢?从他的角度看,无论变与不变,我就是我,不可能永远按照父母期待的方向变化。
父母的这种想法发展到今天“鸡娃”这样的焦虑程度,国内的讨论认为原因主要是阶层下滑的担忧。但阶层下滑在美国也是一个被频繁谈论的话题,只是他们谈论的焦点跟我们不一样,大多是讲自己工作机会的减少,但很少为自己孩子将来如此焦虑。
我记得在电视剧《小舍得》里,有天晚上,南俪和她老公在散步,说,我们女儿是不是上不了我们这样的大学,那是不是就找不了我们这样的工作,是不是就不可能买到我们这样的房子,过上我们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担忧不是多数美国人经历的,这是新家庭主义价值观框架下的阶层下滑恐惧,不但要担忧自己,还要担忧孩子20年后的未来,很大程度扩大了需要焦虑的范围。实际上父母现在为孩子20年后做的准备不一定有效,但在单一的赛道上只能无休止的竞争,结果就是成功标准不断提高。十年前兴趣班是弹钢琴,现在变成马术和冰球,兴趣班之间还产生了鄙视链。而且这不是让孩子纯粹出于兴趣选择,学得怎么样没关系,而是一定要有一个成功的结果。

《小舍得》剧照
另一个原因是,很多父母在利用孩子的成就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小舍得》里的田雨岚有一句话:“只有子悠出人头地,我才能扬眉吐气”。作为妈妈,她一直在为儿子而活,为老公而活,最终只有孩子出人头地,她才可以扬眉吐气。
还有一个居功甚伟的因素是新家庭主义环境中的物质主义标准的攀比。更糟糕的是大家都用单一化的生活理想来界定成功标准,只有一个赛道,也因此加剧了竞争。这背后的原因还是回到了个人主义缺席的问题。
澎湃新闻:家庭资源从祖辈向子孙辈转移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套以孩子为中心的“正确”的家庭范式。这种范式不但影响了家庭,也影响了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在这种范式下,女性的地位和角色有何变化?女性如何被这种范式规训?
阎云翔:我们可能还是要区分女性群体中代际的差别。例如,这种范式总体上是增强了年轻女性的话语权,在育儿方面做得好的女性,话语权比她们的丈夫要更强一些。所以从这些方面看, 这似乎把年轻女性放在比较有利的位置上。但仔细分析,这更多的是传统“母以子贵”的现代延伸。如果一个妈妈在育儿上达不到家人的期待,她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强的话语权。
我们可以预见,育龄女性所承受的道德压力会有所增加。最有可能的就是动用一元化的观念,从家庭、国家的角度,强调妇女生育的道德性。这样会对女性有很大的压力,来自男性中心主义的敌视或不友好态度也有可能会得到额外的道义支持而加强。值得整个社会反思的是,为什么有些年轻人会做出不婚、不育或少育的选择?除了生活方式转变之外,现实生活中那些已经超出个体应对能力之外的系统性问题,例如歧视育龄女性的就业市场、家庭福利政策的短板等等,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人口转型下,家庭更多元还是更保守?
澎湃新闻: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已从2010年的3.10下降到2.62,且是在中国2015年开放二孩生育后。这意味着中国家庭规模缩小,家庭结构也在变化,例如单人户和夫妻户增加。这会冲击“新家庭主义”吗?中国社会有无可能发展出对多元家庭的想象和包容?或是会被维护传统家庭范式的话语反噬,走向更保守的方向?
阎云翔:从逻辑上讲,导致新家庭主义兴起的原因不是家庭规模缩小或者第二次人口转型的其它因素,而是个体化、社会风险等社会结构因素。如果这些结构性因素不会发生逆转,新家庭主义的趋势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家庭结构简单一般会增强家庭内的亲密关系。儿女与父母之间物理距离的扩大,甚至可能导致情感依附的增强。如果我们在一个风险社会不能独立自主,有自己的活法,如果绝大多人都只有一种活法,这种活法又只能通过亲友的支持才能实现,那新家庭主义就不会减弱。从现在看来,新家庭主义还是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起作用,不会受人口政策和家庭规模变化的影响。
中国目前家庭结构的变化,会否走向对多元家庭的包容,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对于多元化的容忍程度。如果没有对不同的活法的接受和包容,那么在家庭规模缩小、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原来主流的家庭模式就会越来越变成刚性的要求,就会走向保守的一面。而新家庭主义自身的逻辑,是倾向于有一个正确的家庭范式的。说到底这是一个集体主义或者群体主义的价值观体系,它要求个体隶属于家庭;而不是那种认为家庭是个体选择如何实现自我的方式之一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另外从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来讲,社会主流价值观有一种对多元化的恐惧。这其实就是对于秩序变动的恐惧,因为多元意味着有可能失去既定的单一评判标准和等级安排,对于那种安于现状的人而言就是乱,所以害怕。
澎湃新闻:新家庭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被视为个体的庇护所。但实际上我们看到,随着家庭规模缩小、人口老龄化,独生子女一代已面临养老、育儿的双重压力,如果是单身或丁克家庭等,甚至无法指望家庭作为最后的保护网,家庭作为庇护所的作用是否在减弱?
阎云翔:这个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一个趋势。所以现在国家的家庭福利政策至关重要。如果要维持健康的人口规模,保持人口活力,就要减少大家对于家庭负担各方面的担忧,这些担忧又是系统问题,不是个体能解决的,只能由国家层面通过政策、社会制度,还有健康有力的社会来解决。
过去十年里,国家其实出台了很多政策,也提供了很多的支持,比方说新农保,在农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问题国家确实有效解决了。但总体来看,强政府弱社会的模式依然如旧,资源过分集中,政府承担的义务过多。在现代化风险面前,社会和政府应该是维持国家这个大房子稳定的两条腿,如果压力全在政府这条腿上,政府的负担就会不断增加。但如果社会更多元化,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帮助处理不同的问题,而且这些组织可能是跟市场结合在一起,甚至带动市场,这样又增加了市场这第三条腿。真正遇到风险,三条腿的结构肯定比一条腿好。
三、中国个体化的2.0版本:新家庭主义,民族主义和物质主义
澎湃新闻:你提到,近几年“家庭”频繁出现在官方话语,并且与国家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家庭和国家的联系会被反复强调?
阎云翔:让我从个体化角度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认为,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制度变迁,中国的个体化现已进入新的阶段,我权且称之为2.0版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中,个体化2.0的版本包括三个核心组成部分:新家庭主义,民族主义和物质主义。
个体化1.0版本的主要特征是国家通过制度性的改革,推动个体承担更多的责任,增强个体的竞争力,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欲望和追求被正当化。这是个体从传统家庭、集体主义脱嵌,进入市场的过程。正在浮现的个体化2.0版本中,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已经建成,亟待化解的主要矛盾变成个体再入嵌的问题;目前,再入嵌是通过新家庭主义和民族主义解决的。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由于个体化要求个体承担更多责任,以个体奋斗的方式解决系统性问题,也由于社会机制的持续弱化,个体在寻求再入嵌资源时发现只有家庭才是不离不弃的保护伞,于是才有新家庭主义的兴起。但是,新家庭主义无法为个体提供私人生活领域之外的庇护更不能产生社会意义。民族主义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民族主义虽然不能解决个体的衣食住行问题,但可以使得个体与他人建立一种公共性纽带,大家共同再入嵌到现代民族-国家这个超大共同体之中,获得精神上的安全感和满足感。
如此再入嵌的结果导致一种悖论式的个体生活体验。许多人对个人发展前途不乐观,觉得工作、生活压力很大,而且无论如何奋斗,实现自己愿景的可能性都不大。于是,坊间才有关于“内卷”“躺平”的讨论。但另一方面,人们对国家、民族的大前景充满希望,强烈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兴奋和荣誉,并因此而进一步增强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个体越是感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孤立无助就越是要强化新家庭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求自保,至少获得心理情感方面的满足。这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在个体化2.0版本中,新家庭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应对个体化挑战的同一回应方式的两个方面。这种回应方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国天下的文化传统,也是路径依赖的结果。
现在的社会更像一个“家国的社会”。传统文化中,皇权和宗族社会是有张力的。现代社会也一样,如果每个人都太看重家庭利益,就会忽略他作为公民的义务。强调家庭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统一,家庭梦想和国家梦想的统一性,实际上是借力于传统儒家的家国同构的话语来加强国家在个体化2.0中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是个体再入嵌到家庭中,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家庭之上不会再有其他的社会组织形式横亘于个体和国家之间。通过家庭,个体被嵌入国家这个超大共同体内。
连接家和国的是物质主义。私领域中,通过消费主义实现家庭的梦想和幸福感很重要。同时,物质主义把个体重新划入不同的阶层,人们以物质主义的标准为自己界定在社会中的位置,例如拥有多少财富、住在什么地方、能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等,通过这些标准来找到跟自己身份相似的人群,以此界定自己的身份认同。公领域中,扩大内需、发展消费经济,是国家富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方式。国家的发展也是靠物质主义的标准衡量,例如GDP。从物质主义的角度,在很多年轻人看来,整个国家前途充满希望,特别是近些年跟西方国家做比较的时候,在很多方面显示出中国特有的优势。依据传统文化中小我服从大我的逻辑,个体很容易接受只有作为国家民族的大我充分发展之后,小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的话语,并通过物质主义理想的实现将家与国同构化,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如果对比欧洲,西欧、北欧已进入了后物质主义阶段,人们并不通过追求生活中的奢侈性界定自己的身份,反而开始追求简朴的生活方式,同时在反物质主义的方向展示自己的个性。这就是生活方式的政治。这些方面,我们的2.0版本还没有显示出任何新的征兆,绝大多数人仍觉得财富积累远远不够。但随着通货膨胀、社会攀比标杆的上升,你永远达不到“财富自由”。而每当有零星反物质主义的迹象出现,如“躺平”的话语,主流话语总是担忧,担忧中国会变成日本那样的低欲望社会。这意味着我们从整个社会的层面上,也觉得财富还不够,还要努力拼搏,因而很难反思现有的被物质主义所绑架的生活方式。
物质主义与新家庭主义、民族主义似乎正在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个体生命体验闭环,自下而上地共同支撑着个体化的2.0版本。
(本文英文版首发于Sixth Tone,原标题为:The New-Style Family Values Underpinning the ‘China Dream’,中文版内容有调整增减。)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