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姚大力:朱维铮为什么越到晚年越反对“以史为镜”
姚大力认为,朱维铮越到晚年越是坚定地反对“以史为镜”,尽管他在生前仍在时刻关注着政治,但“历史研究从业者从他的特定知识结构出发,也可能为国家当前建设贡献某种独到的见解,但这只能是历史从业者履行他作为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历史学本身的目标或任务。”他从朱维铮那里,强烈地感受到也认同着“史学本身并没有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功能或属性”。

朱维铮对政治:尝试过、痛恨着、仍关注
朱维铮在“文革”期间曾作为上海写作组中的一员,以历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自觉成为意识形态的排头兵。这段经历,让他付出了代价,也成为笼罩他日后史学思考的幽灵。
对此朱维铮从未讳言,但姚大力认为,“在长安追日的迷信和革命狂热破灭之后,朱先生越到晚年就越是坚定地反对‘以史为鉴’。”
作为一个活在当下的历史学家,朱维铮的全部史学研究活动无不与他所经历过的那些时代的现实政治发生密切关系。在这一方面,姚大力觉得用“曾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仍时刻关注政治”来描述朱维铮正合适。这句话前半句是徐复观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后半句是姚大力的评价。
在奉贤的滨海墓园,朱维铮墓石上的一段话,反映了印刻在学生和友朋心目中的朱维铮形象。从中,姚大力既看到了对朱维铮的治学一面的评价,也看到了对其“论事”、“致用”一面的描述,由此不难看到,朱维铮的治学与现实政治存在着密切交织。如此说来,朱维铮“反对‘以史为镜’、反对把历史当做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到底还对吗?历史学的研究与现实政治到底还有没有关系?如果有,二者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姚大力设问道。
朱维铮善于还原学术被政治化的过程
姚大力认为,传统中国的历史学,可以用两个“司马”来代表,即司马迁和司马光。但是两人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取向:司马迁的“原始察终”取向体现了对比较纯粹的意欲认识和理解过去的追求,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取向则把历史学当做辅助甚至指导政治统治的工具来看待。“在中国历史学领域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几乎一直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取向。”
正因为如此,面对这种带有明显价值判断和个人立场的历史文献,就必须结合形成这些文献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以及作者的政治立场去予以解读和分析处理。余英时曾引述金岳霖的话说,研究宋代理学的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道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去阐述,姚大力认为,这种做法可能产生的最大问题在于,道学家与他们实际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从一开始便没有进入哲学家的视野。
但是,朱维铮研究中国思想史,“最拿手也是最打动读者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把思想家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方式,包括他们正在从事的政治斗争之间的关联,自始纳入到自己视野之中。”
当一个思想家的观念和立场转变,明显与他所思成的那套学说以及学术内在理路的走向不相符合时,朱维铮总是转而从当时政治斗争去求得这个思想家的观点和立场之所以发生如此转变的原因。在姚大力看来,这绝不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而恰恰是在还原历史上学术问题被政治化的那个过程,那段历史实相本身。
史学没有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功能
对于史学研究,在姚大力看来,有两种相当普遍的误解需要进行澄清。一个是认为历史研究者应该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保持客观的价值中立,“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观察者,都做不到也不必要求自己隐藏乃至完全泯灭对它如实加以叙述的情节中所含有的美丑善恶,以及被这种美丑善恶所激发出来的爱憎。”所以姚大力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研究者在自己书写的叙事中,不需要规避自己针对叙事对象的是非观念和政治立场。
另一种误解,姚大力解释说,是以为所有的历史现象,都可以被简单地划分为推动或者阻碍历史进步这两大范畴之中,并且据以裁定一切历史上的大是大非。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春秋中叶后,“礼崩乐坏”的局面也因此被我们的标准历史叙事当做排除腐朽势力、实现历史进步的大好事来称颂。
但是顾炎武却把春秋到战国时代精神的转变看做是从讲理讲信到讲求利害的堕落。姚大力认为,正因为此,在“礼崩乐坏”形势下强调军国主义耕战政策的法家,才得以在过去受到全国范围内的敬仰追捧,并且至今瘤毒未清。与讲求厉害的法家十分相似的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受到现代政治学的严厉批判,姚大力觉得应该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
进步就是善的历史观念来源于何处?姚大力援引以赛亚·柏林的说法认为,把进步等同于善的错误历史观,是黑格尔体系的真正标志。
黑格尔认为老式的历史学是讲求道德的,回顾过去时为了了解事物的缺点,所以里面充满了责备或者赞扬的评价,黑格尔对这种历史学予以了谴责,他呼吁有理性的人们主动与伟大的运动力量自身相认同。但是以赛亚·柏林对黑格尔的看法无法认同,认为这是一种源于线性进化的历史目的论,而且很可能导致人们崇拜权力,导致一种尤为残酷的政治现实主义。
“从前,首先从线性进化的历史目的论推演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运动,然后仅仅从顺从和抗拒这个历史方向的角度来看来解释人类行为,完全排除了理应对支配这种行为的理智的目的和道德法则进行具体评判的思考,成功就意味着善,成功就意味着道德和政治上的正当性。”柏林写道。姚大力显然是站在柏林一边。
那么什么是对上述两种认识论的解药呢?姚大力认为,就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和弘扬价值理性。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是历史的代理人,我们应该做这做那,这是历史的要求,阶级的要求,民族的要求,我们所走的是向前进的高速公路,这是历史本身决定的,凡是阻碍我们前进的一切坏东西都要扫除干净。”在姚大力看来,处在这种精神状态的人往往会践踏人的权利和价值,因此有必要维护人的根本尊严,反对这种强烈并且往往是狂热的信念。
姚大力相信,这种根本的价值关怀是可以融贯古今西东的,所以尽管朱维铮力图呈现的只是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而绝不是借古讽今或者以今训古,“但是他在指向过去时期事件的那些笔端总会传达出鲜活的现代脉动。”
如此说来,历史学究竟有没有古为今用、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功能呢?“朱先生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姚大力认为,我们不得不同意这个看法。但问题是在过去,史学曾不只一次的和现实政治斗争发生纠葛,又应该如何看待呢?
“这是政治绑架了学术,史学本身并没有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功能或属性。历史研究从业者从他的特定知识结构出发,也可能为国家当前建设贡献某种独到的见解,但这只能是历史从业者履行他作为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历史学本身的目标或任务。”姚大力分析道。
朱维铮质疑史学政治化的现实意义
朱维铮对史学政治化(以史为镜)的质疑,至今仍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在姚大力看来,这种政治大批判有沉渣泛起之势,其中一个表现形式就是诛心论。
所谓诛心论,姚大力解释说,就是用诸如“别有用心”“亡我之心不死”等等针对动机的指责,来替代和回避对于辩论主题摆事实、讲道理的基本论证环节,“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批评者的内心意图。我们曾经用这样的方法伤害过许多人,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
他以拉铁摩尔的例子,来警示我们必须检讨这种教训。拉铁摩尔是没有读过大学的大学教授,他平生以不带翻译而能广泛游历中国边疆地区最感自豪。他被冷战的双方同时指控为对方的特务,但是却受到蒙古人民的高度尊敬。
姚大力认为,贯穿在所有这些形形色色褒贬之中的,只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拉铁摩尔是一个同情弱者的人。“他在中国和当年欺负中国的西方列强之间,站在中国一边;在力行大汉族主义的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少数民族之间,站在中国少数民族这边;在蒙古上层和饱受他们掠夺的蒙古民众之间,他站在蒙古民众这边。”姚大力说,拉铁摩尔更有资格被看做中国人民的朋友,而不是国家敌人,“我们如果还有良知就不能再像这样伤害无辜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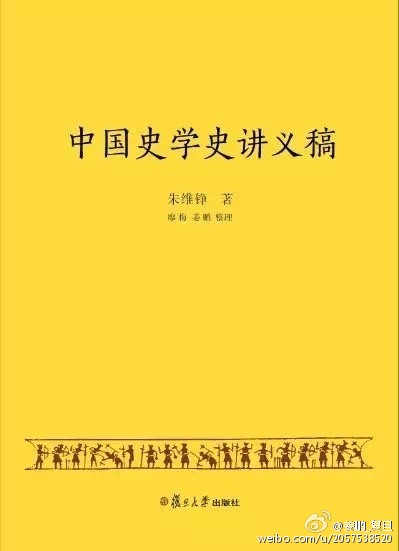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