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重走二战滇缅公路的美国人:将壮丽故事重新注入血肉与灵魂
【编者按】
滇缅公路曾经书写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缅、印、英、美等国人民共同付出鲜血与泪水的悲壮故事。2002年11月,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委托,资深撰稿人多诺万·韦伯斯特从印度加尔各答启程,穿越缅甸境内的热带丛林,再度踏上这条早已荒芜的公路。通过沿途极为艰苦的实地考察,多方探访当年的老兵以及修路者,韦伯斯特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完成了《滇缅公路:二战“中缅印”战场的壮丽史诗》(九州出版社,2015年9月版)。
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该书的“序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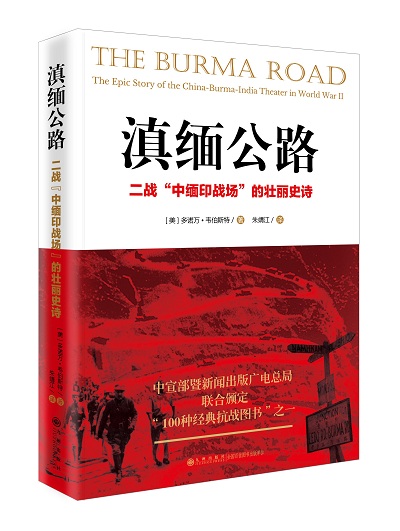
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坚信:那条在等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指引他们跋涉过陡绝的印度喜马拉雅山垭口、深入闷热蒸腾的缅甸丛林直至进入中国的道路,在时光的涤荡下早已经湮灭无痕。他们毋宁说那条路本身仅仅以一场陈年的旧梦而存在着,并断言道路如弦索般纤细的两条轨迹——如今已有六十年的历史——怕早就被山崩、雨浸以及沼泽般蔓延的热带丛林所吞噬了。
但现在,一步紧随着一步——在一月中旬某个沁凉的早晨——我的双脚正踏在老战士们曾反复警告过我的同一条砾石路上。在道路两旁丛林的墙隙之间,我仿佛穿行于上百英尺高的绿色帷幔,出发去找寻那些老战士的战友们阵亡的沙场,那些他们曾亲身付出了血汗——或许最为重要的——那些如此深刻地烙印在生命里,以至于当他们被从午夜的噩梦中撼醒,仍可以品咂到酸涩的枪弹烟尘、仍可以感觉到丛林蚂蟥在潮湿的棉布军服下蠕动的地方。
在晨曦中,这条向前伸展的道路逶迤右转,往复曲折地消失在另一座丛林覆盖的山巅。而在我眼前,这一行程初始的开端——就在嘈杂的印度人聚居区利多镇东北方几英里开外,最早铺成道路的砾石与柏油已然坑洼破烂。路肩风化散乱于森林的边际,在一些路段,斑驳的孔穴横亘于整块路面,将一条条断裂的伤痕留在它残缺的身躯之上。
刚好与老战士们所确信的相反——那条道路依然存在着。三十英尺的宽幅,它蜿蜒蛇行于藤蔓悬垂的古木林翳之下,复又仰身折向浓绿欲滴的莽莽群山。它悄然滑过印度边防军的哨所营房与土著部落的丛林茅舍;从它的辙印上经行的,不单有摩托以及满载着煤炭工人的巴士,更有满载盗伐得来的柚木的卡车——虽然这样的砍伐在多年以前就被宣布为非法。这片文明世界的边地是如此之遥远,看起来没有人会在乎这里究竟发生着什么。
周五的早晨,十点钟光景。在我头顶上方万里无云的天空里,太阳正透过树梢,将金晃晃的圆斑投映在路面上。空气潮湿,气温约在65华氏度。几缕晨雾从森林中飘溢而出,淡然的雾色将我周遭的日光柔和了下来。道路两旁的丛树梢头,灰色的长尾小鹦鹉在腾挪跳跃。一辆吱嘎作响的牛车从我身边经过,车身上紧捆着几截柚木的树干。一头印度神牛就在前面不远处的道路上游荡:白色的毛皮,一支牛角被涂成光洁的绿色,另一支则是黄颜色的——它看上去根本无视那些拐来绕去想要躲开它的车子们。我抻了抻腰杆。喧闹的利多镇上,卵石铺就的市集外边,在“拉吉旅舍”一间带马桶与冷水淋浴喷头的小房间里,我躺在胶合板床上渡过了上一个长夜。整个夜晚,当地人都出来站在旅馆门外的空场上,瞪着二楼的阳台,向我——这个陌生的到访者——扯开嗓子问候。
“你好,美国人!”他们喊叫着。然后他们就站在碎石地面向上张望,期待我走上狭窄的阳台,向他们挥手致意。而在小巷的另一头,一家寒碜昏暗的餐馆里,火苗在泥炉中跳跃闪烁,煨热了咖喱,并且映照着餐馆油黑烟墨的四壁。一群孩子在巷子里玩板球,也时不时地朝我喊上几声。在起先的半个小时里,我对楼下的欢迎人群所做出的唯一回应,仅仅是房间里那盘蚊香的一缕青烟,顺着通风口散逸出去,随它飘入茫茫的夜空。
最终,当意识到我不可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并奢望一份耳根清净时,我走下楼梯,和一个名叫德杰拉的12岁小女孩打羽毛球。她身高大约四英尺,骨瘦如柴,乌黑发亮的头发齐腮修剪,肤色黝黑并有一双深深的黑眼睛,德杰拉满面笑容地问我道:“你从哪里来?”德杰拉说,她和家里人也是才到这镇子上不久。六个月前,他们全家刚从孟加拉搬到本地街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她的父亲之所以迁居到利多,是为了在当地煤矿找一份矿工的活计。然后,德杰拉递给我一把弦索断裂的球拍,我们就在小巷里一张假想的球网两边,上下翻飞地抽打起一枚小小的塑料羽毛球。
几分钟之后,我对和德杰拉一起打球表示了谢意,随即穿过香料店的门面——也就是“拉吉旅舍”的一楼,像一只动物园里的野兽那样被从头到尾地打量着,返回了我那间位于二层楼上的客房。
“你好,美国人!”在我锁紧门闩、钻进蚊帐,并且吹灭了屋里唯一的光亮——一支蜡烛之后的好几个小时里,那召唤我的声音还在小巷深处回响不绝。
现在,又一个早晨,我注视着这条道路,拎起行囊继续我的旅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架设的木头电线与电话线杆勾勒出道路的轮廓——玻璃绝缘器依然还在原位,曾经密织的线网却早已难觅踪迹。回首1942年末,就在这条道路开始被美国工兵营破土修造时,没有一位盟军的指挥官或士兵会相信,未来的27个月里,当他们在崇山峻岭中开岩凿壁,抑或在沼泽湿地上夯土搭桥,以每天一英里的速度延伸这条路线的时候,日本人会寸步不舍地向他们发动致命的攻击。还在道路完全竣工之前,日本的狙击手与炮弹(再加上疾病和事故),就让这条全长1100英里的道路途经的每一英里土地上,永远倒下一名盟军士兵。
在这条道路刚刚动工的1942–1943年,盟军的官兵同样也不会相信,在这场战争的中国–缅甸–印度战场上,每每因战斗而阵亡一人,就会另有十四人由于罹患(甚至死于)疟疾、痢疾、霍乱等传染时疫,丛林湿疹以及此前无人所知的一种名为“灌丛斑疹伤寒”的传染病而减员。他们也决不会相信,就在这条道路完工之前,“中–缅–印战区”最受人爱戴却又暴躁易怒的指挥长官——美国将军“醋乔”史迪威——将被迫离职;他们的性情乖僻却让部下誓死效忠的特种部队领导人——英军少将沃德•温盖特——将会在一场令人震惊的意外事件中阵亡;再有,或许也是最让人无法接受的:他们曾浴血奋战、拼死修筑的这条公路,甚至在它刚刚完工之际,就将被视为过时的废物而遭到无情地丢弃。在精疲力竭地离去之前,史迪威除了靠一句蹩脚的拉丁语格言作为其最后的支撑之外,几乎已无力回天。这句“Illegitimati non Carborundum”,被他译作“别让那帮混蛋把你压垮”,成了史迪威最为著名的一句座右铭。
我跨过一条流水淙淙的阴沟,它用水泥砌成的槽床因为常年潮湿而呈棕红的水锈色;沟底的水流绞缠如辫,淌过藤蔓悬垂的地下。这条道路曾被冠以诸多名称——譬如利多公路、史迪威公路、匹克大道、“每英里亡一人”之路、山姆大叔高速路——但它最通行的名字却是颇为简单的几个字:缅甸公路(中国一般称之为“滇缅公路”——译注)。尽管历史学家们或许将其礼赞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为伟大的工程壮举之一,但那些老兵们却一次又一次地断言:它只可跻身于现代历史上最被人遗忘的道路之列。而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他们宁愿相信:它仍应保持着那份孤绝的姿态。
就在前方,这条道路穿过印度阿萨姆邦,在一个名为斋兰普尔的边界小镇进入阿伦纳查尔•普拉代什地区。此后,它逶迤而上,盘旋在帕特凯山脉两列海拔4000英尺的山麓之间,在班哨关翻越帕特凯山的第二高峰,最终深入缅甸境内。
我登上阿萨姆邦的最后一座山丘向下俯望,斋兰普尔镇低矮的棚屋散布在丛林蓊郁的山谷里。山羊与野猫四处乱窜,居民从一间茅舍游荡到另一间茅舍——在这里大约有20来座建筑物。就在小镇的中心,一座二战时期留下的活动钢便桥横跨过泥泞的纳姆齐克河,斋兰普尔的检查站就设置于此地。桥的跟前,道路右侧,一座带有环形走廊的黑柚木屋显得饱经风霜,这便是哨所的安全检查办公室。身着咔叽布制服、头戴蓝色贝雷帽的哨兵们坐在椅子上打盹,他们的机关枪斜倚在回廊的栏杆上。
看到我向他们走来,士兵中一个身高六英尺、鼻梁上架着一副航空太阳眼镜的壮汉挺身站起。一群白色羽毛的小鸡乱哄哄地穿过了街道。在路的左侧稍稍靠后几英尺,正对着检查站的方向,是一座墙壁洞开的警备室,沙包堆成的防护墙后面,一挺架在底盘上的机关枪更具威严。一条子弹带从摆在地上的铁皮箱中伸出头来,填进机枪的后膛里。随着我步步逼近,一名原本趴在警备室阴影里的木桌上打瞌睡的机枪手,悄然转移到他的武器身后。他伸手抓住机枪右侧的枪栓,“咔咔”两声拉动手柄,将手指扣在了扳机上。
在这两座房子的中间就是关卡的闸门:一根交替染成红白两色的长竹竿。它像一条杠杆那样被压低下来阻住通路;一块大石头被缠入绳网,绑在靠近警备室的竹竿一端,充作保持平衡的配重。
“你好!”我朝那个戴太阳镜的哨兵打了个招呼,展颜一笑。他回报以一张冷脸。“你好。”他说,“请出示你的证件。”我将护照和签证递给了他。这下他笑了笑,然后就闪身消失在房间里。我可以听到他正通过电台向什么人呼叫。电波的频率嘈杂混乱,在一片噪音之中,他的声音依稀可辨:“是的,”他报告说,“没错,他是个美国人。”
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迄今依然是外国人的禁足之地。其中一些地方甚至从19世纪早期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开始,就严禁外人到访。如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第56年,也是印度挣脱英国控制独立以来的第54年,印度东北部终于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缓缓地向外界开启了门户。与印度主体社会不同,部族体制仍然在东北部地区占有主要地位。在这一区域彼此隔绝的山谷中,至少并存着105种以上的地方语言,几十年以来,一些势力较大的部落为争取他们自己的自由而与印度中央政府长期作战。正因如此——并且以我个人的人身安全为根本理由——我未能获得考察滇缅公路在印度境内最后十八英里所必需的“限制性区域许可证”。
我注视着在眼前奔走的鸡群,用手掌摩挲着拦路门杆上的油彩。我指了指桥下二十英尺宽的混浊河流,向另一个哨兵询问:“水里有鱼吗?”那是个小伙子,依然半躺在他的椅子里,把穿着黑皮靴的双脚搭在门廊的栏杆上,斜挎的来复枪紧贴着他的小腹。他比那个戴墨镜的士兵要瘦小一些,大约25岁年纪,咔叽布军服下面是条瘦骨嶙峋的身子。
“当然有!”他回答道,“有一次我们还见过一条大鱼。”他举起双手,空出十八英寸左右的间隙,思忖两手之间的距离是否恰当。
“太阳镜”再度出现在我面前,面带微笑:“生日快乐,韦伯斯特先生!”他说。我早就把今天是我的生日忘得一干二净,太阳镜一定是从我的护照上记下了这个日期。“韦伯斯特先生……”他停顿了很久,“您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我向“太阳镜”解释了我沿着全长1100英里的利多公路–缅甸公路旅行的计划。在印度,我希望能再沿这条路上行18英里,至名为“班哨关”的山顶上抵达印度与缅甸的边界。在那以后,我将飞去仰光,从缅甸境内再度启程至班哨边界。我很清楚,因为印–缅边境恐怕是世界上把守得最为严密的边界线之一,所以我不可能今天直接从印度入境缅甸。但我前往“班哨关”的目的之一,就是想通知双方的哨兵:我将会从边境的另一侧再度出现,这样当他们在下个月又一次见到我时,就不会感到紧张慌乱。
一言以蔽之,我告诉“太阳镜”说,我的滇缅公路之行将穿过印度的雨林与喜马拉雅山麓的丘陵,下经缅甸低地蒸笼一样闷热的丛林地带,最终攀上中国西南地区的西藏高原,在云南省昆明市结束我的旅行。我会在沿途必要的情况下徒步、搭车,或租用交通工具,但最重要地,我将寻找那些在战争中幸存的人们,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条最为漫长的战线上所发生的壮丽故事——如今已为大多数人所淡忘——重新被注入血肉与灵魂。这段旅程将会持续三个月的时间。
“太阳镜”又笑了笑,他以一种戏剧式的迟缓动作摘掉了脸上的墨镜。尽管他的头发乌黑,皮肤是印度人最为典型的深棕颜色,他的眼睛却是令人吃惊的浅灰色——它们让我有些心神不宁。
“我只想看一眼‘班哨关’,”我对他说,“这样我就可以说我曾经到过那里。”我提起背包,将它靠着墙,放到门廊的条木地板上。门廊里有荫凉,并且我意识到今天早晨的太阳已经开始火热。“我会把我的东西放在这里,”我说,“这将是我肯定返回来的信物。”
我把手伸进裤兜里,年轻的哨兵立即警觉起来。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晃动着身体,双脚牢牢地踩着木地板,用他的来复枪指着我。
“只是拿包香烟而已。”我说,“有谁吸烟吗?”
我打开一包尚未开封的万宝路香烟,将烟盒放在门廊的栏杆上。作为一种不那么昭彰的小小贿赂,这招在此前一直颇为奏效。
“太阳镜”摇摇头,再度一笑:“不,谢谢你。”“你是否清楚,”他接着说,“阿伦纳查尔•普拉代什是旅游者行动受限制的区域?”我点点头:“是的。”
“你是否清楚你的签证上没有附带一份限制性区域许可证?”我又点了点头。
“既然是这样,”他说,“那么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想要进入阿伦纳查尔•普拉代什地区旅行——想要经过利多公路到达‘班哨关’——你就需要办理限制性区域许可证。如果你没有获得这份证件,那我也爱莫能助。我既不可能为你签发一份,也不可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必须把你遣送回去。”
我告诉这名士兵我曾如何与印度驻华盛顿的大使馆联络,如何等待了足足六个月以接受取得限制性区域许可证的各项调查,以及在这半年的煎熬之后,印度使馆官员却通知我说,鉴于我以记者身份出访印度,这份许可证恐怕还是难以到手。我对他谈起使馆的官员们甚至建议我来这个边境哨卡,直接找戍守的卫兵们碰碰运气。特别是因为我只打算在阿伦纳查尔•普拉代什停留——多久?——才半天而已;不过是沿着公路走上十八英里——倘若能笔直地穿过丛林,只有区区六英里的距离。
“我很高兴能在斋兰普尔待上一段时间,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指着我的背包,说道,“我已准备了一个星期的口粮:鲜咖啡、大米和豆子之类的,还有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很乐意把吊床悬挂在那边……”我伸手指向公路另一侧,警备室旁边的两棵树。那厢的机枪手还在原地待命,虎视眈眈地把守在他的致命武器后面。
“太阳镜”又在露齿微笑:“韦伯斯特先生,你尽可以待在边界的这一侧,欢迎备至。但法律是很清楚的,你不可以进入阿伦纳查尔•普拉代什。没有一份限制性区域许可证,你就不可以前往班哨。实际上,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射击任何敢于违反该项法律的人。先将他们射倒在地,当其丧失行动能力之后,再调查他们为什么非法穿越边界。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你明白吗?”
我一面点着头,一面将目光投向那条河流。我飞越了大半个世界来到这里,坐在拥挤不堪、令人筋疲力尽的汽车中在印度跋涉了六天,晚上睡在硬板床上,靠扁豆汤充饥,还要忍受本地人像看马戏一样注视着我的神情。而眼前——就在距“班哨关口”区区几英里丛林旅程的地方——一排枪林弹雨竖起的围墙却即刻将我与我的目的地隔绝开来。
“当然,”“太阳镜”接着说,“你也可以返回德里,再次申请一份限制性区域许可证。正如你所说的,前景并不乐观,可能要花上几周甚至几个月等待被批准。但你也不妨一试。很遗憾我无法提供进一步的帮助。”
“你可以亲自陪同我去班哨,”我抛出提议,在苦苦哀求的时候努力让自己笑容灿烂,“在你今天换岗之后。我会很高兴为占用你的时间而支付费用。我这么不远万里地跑过来,在离目的地这么近的地方被拦住,未免太令人沮丧。”“不行。”他说,“法律规定得很清楚。我再说一遍,我很遗憾。”
在检查站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木板棚子,看来是一家与哨所卫兵长期共存、相伴相生的饭馆兼杂货铺。“太阳镜”朝那房子的方向喊了一声,他走到门廊边上,伸长脖子四下张望,直到看见棚子里木头板凳上坐着的一个小个子男人。“太阳镜”用地方土话交代了几句,那个男人站起身来,走到了店铺柜台的后面。一位当地纳迦部落的老妇人向铺子门外窥望了几眼,在她的脸上,自发际线往下经过双眼以及鼻翼两侧镶嵌的黑色小纽扣之间,都刺有暗蓝色的线纹。我向她挥了挥手,她却慌忙躲进了屋里。
“太阳镜”转身面向我,“请你理解,韦伯斯特先生,这些法规不能违犯。本地走私猖獗,叛乱分子众多。这些法律之所以存在确乎有着充分的理由。我并不乐意下命令向你射击,但那就是法律。”他居然还在笑着。
“现在,”他继续说,“我为咱们点了壶茶。你的茶里想加些牛奶,糖,还是二者都要?”“都要。”我说。“太阳镜”朝杂货铺里的男人又喊了起来,而我将脖子伸出门廊另一侧的围栏,试图让目光穿过小镇、掠过山谷,一直望到班哨关口。我目光所及只有连绵的丛林与山峦。甚至那条路在拐过第一道弯之后也消失匿迹了。这糟糕透顶的十八英里啊!
茶送来了。我们在门廊里找到两把椅子坐下,然后又多聊了几句,这只是更加深了我的挫折感。几分钟之前,这个家伙还以一种毫不含糊的口气告诉我,如果我不照他说的去做,他就会一枪毙了我。现在他却端给我茶水和淡黄色的糖果茶点,而我则把我妻子、孩子们的照片拿给他看。
或许那些老战士们是对的。或许我的确不应该前来找寻这条道路。不管怎样,我眼前的情形都越来越带有一种超现实的色彩,它的彬彬有礼几乎不能掩饰“太阳镜”所暗示的生命威胁。小口地品着茶,我终于理会到:倘若我拔腿往“班哨关”的方向跑去,他们真的会在我生日的这一天,把我乱枪撂倒在这破烂的街头。枪弹抑或是友谊?阻挠抑或是协助?前行的通路被堵死,但我又极不情愿转身后退。而争论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无论如何,进一步谈判的可行性被这种边疆风味的茶道表演彻底扼杀了。
终于,坐在尘灰满布的门廊阴影里,当我的沮丧与绝望在晌午蒸腾的闷热中几乎达到极限时,我忽然破颜一笑。我意识到,较之这世界上其他任何人,唯有史迪威最能理解我此时的心境。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