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访冯唐:女生说“暖男”的时候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无奈

近日,冯唐带着他的新书《女神一号》和译作《飞鸟集》来到上海做新书发布和签售活动,并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
上海是他此次全国巡签的最后一站,从9月1号开始,冯唐又要投入到一份新的全职工作当中。
以前全职工作的时候,冯唐每周除去工作的八九十个小时,再除去睡眠时间,剩下的10来个小时全部用来写作。辞职后,“除了写作还能有点自己的生活,喝个茶,沏个咖啡,可以和过去很久没有联系的老朋友吃顿不用谈正事的饭。”
关于写作《女神一号》的初衷,冯唐讲道:“这个社会有太多正常的看法,我这本书试图提供看似不正常,但有好多真实性的东西。”所以,他的《女神一号》书写的是“干净纯粹自然美好的人性”,“其实在我的作品里一直试图表达的,无论人性还是人体,都可以是简单干净纯粹美好的,只是有时候人自己把自己给弄偏了”。现在他手头在写一部关于美食的长篇,也会突出描写抑郁症患者。
随着年岁的增长,冯唐作品的故事性也在变强,虽然他之前并不屑于写故事。“《女神一号》的故事性比我之前的长篇都要强一些,所以早晚要拍成电影。”
谈到如今流行的“暖男”以及大家吐槽的“直男癌”,冯唐说女生提到“暖男”的时候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无奈,而太把男性当回事以及人太傻X了,才让“直男癌”成了贬义词。他觉得,“暖男”和“直男癌”这两个词正好在女性生活中形成两种情绪,但都不是她们想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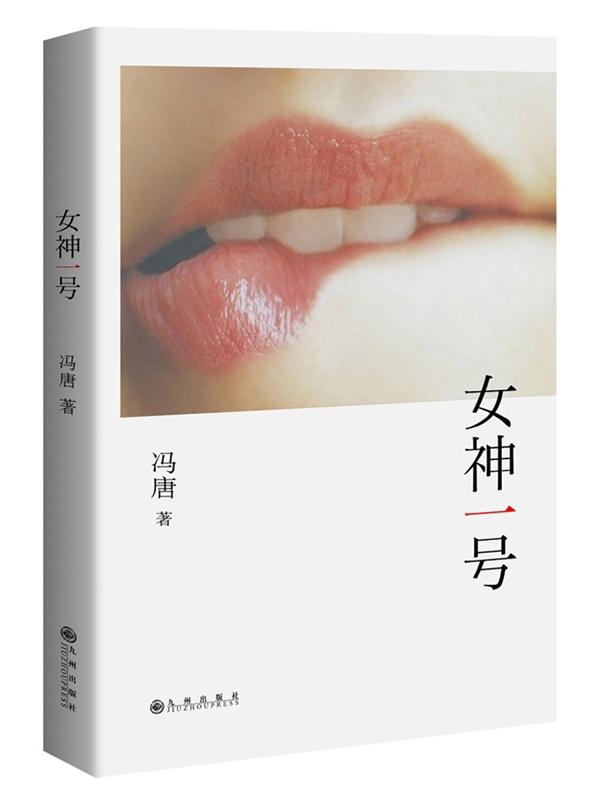
冯唐: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个所谓的“解情困”呢?这个也简单。我发现周围有些人,跟他/她的生活境况、身体状况、名利、教育背景和美丑都不相关,还是会为情所困,你会发现原来一个特别聪明的人还会去私奔,还会在现代生活中想出这种事情,到底为什么?
在现代社会中,为情所困到底是个怎样的状态和思路?它的起承转合是什么样子的?虽然看了那么多这方面的作品,但都是把情节或者细节弄得很简单,而围绕具体一个点挖得很深的,我还没太见过,所以就有了这么一本书。
澎湃新闻:您的小说里很多都有“爱情”这一话题的存在,同时试图通过爱情折射人性。能谈谈您如何看待爱情和人性之间的关联吗?
冯唐:爱情本来是一个人造的词,但人们却不能很精确地定义它。如果纯从医学的角度看,我越来越觉得人很大程度上被激素控制。如果人真的能不被这些化学品控制的话,那戒毒不应该成为问题,也无所谓上瘾。
在爱情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激素控制,比如肾上腺素决定了是否一见钟情,也就是所谓的要不要扑倒,它激发了原始的愿望。还有类似一种中间时效的激素,持续一两年,接近我们所说的爱情。两个人在一起时都对,两个人不在一起时都不对,有可能你在生命中某一个阶段遇见一个人就会产生这样的感情。它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不像肾上腺素作用时间很短,所以也有统计表示谈恋爱两年结婚的几率最大。
还有一种可能和婚姻有关的长效激素,能够产生亲密的愉悦感,不会欲仙欲死,但会让人很舒服,相濡以沫的感觉。
我更愿意把爱情当做人性的一部分来看待,并且当做男女之情的一部分,男女之间也不仅仅只有爱情。有时候这种界限不是特别清楚,就像女生看男生会有暖男和直男癌,男生看女生同样也有邻家小妹或知心大姐的感觉,是两性关系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爱情应该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它的位置才会显得更加清楚。
澎湃新闻:“女神一号穿插了一点形而上的描述,涉及地球之外的时空,因而从广义上而言,这也是冯唐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论?
冯唐:我觉得挺好,我以后应该会尝试更多的题材,比如科幻、武侠、悬疑、同人都有可能,这也算是某种尝试吧。把一些科幻的元素加进去,其实这里面有两个,一个是第二章里的@,理科生有时爱问一些终极问题,从无机到有机再到生命进化这一切小概率事件的总和,会产生“这背后会不会有看不到的力量在控制,有可能是一个人,也有可能是一套规律”的疑问。就像书里王大力遇到倒霉事后总会问:“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他诉诸的对象不是自己也不是别人,有可能就是这个@。第二个科幻成分是故事最后,女神一号实际上是台机器,现实里没有女神,他就创造了一个。
澎湃新闻:通过科学编码来解读爱情,和通过文学解读爱情,两者有何不同?您认为哪一种效果更好?
冯唐:现在我们的科学进步程度不够,这么复杂的事情可能现在文学还要起到一定的作用。我想或许科技进步到某一天,就可以做到文学现在能做到的事情。我把文学定义成解决其他科学技术无法解决的人性问题的存在,这个应该是文学研究的主体。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天,或许也不会,现在很多事情还很难说清。医学发展到现在依然无法治愈感冒,而科学也无法完全解释一棵树为什么长成现在的样子。随处都是解释不了的事情,文学在这个角度有一点点像中医,不能分析出其中每一步如何起效,但求整体效果。
一部好小说的整体宣泄与揭示效果是确实存在的。现在还不能完全解释是怎样的一套作用效果,或许有一天这个过程非常清楚了,就可以直接通过调节各项生理指标来产生各种情绪。这实际上也是女神一号最后想说的,主人公田小明已经在尝试向那个方向努力。
一首诗,简简单单的白纸黑字就可以令人震撼,并不借助各种高深的科学技术,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
澎湃新闻:如果跳出《女神一号》,您如何看待主人公对两性之间关系的认识?
冯唐:其实我觉得田小明是一个非常轴的人,特别拧巴,他写了一本书叫《论一切》,这在女生看来那就是纯傻X,但他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实代表了一堆人,只是没有像他这么极端。大家也有各自想不明白的事情,无非是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列出来,可爱又可恨。我觉得这样的男生女生在生活里多数是不太幸福的,多数是很难幸福的。多数人随波逐流,而把田小明单独拎出来,一方面是因为这种随波逐流也会有一两个怎么也过不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觉得看看这些“永远过不去的人”对自己会有一些帮助。还有就是我们要救助的多数还是极端情况。重症患者要进ICU,普通感冒发烧则不需要太过关注。
澎湃新闻:作为男士或者男性作者,您如何看待现在流行的“直男癌”和“暖男”的标签?从中能够看出女性怎样的心态?
冯唐:从直觉上说,一般女生说一个男生是“直男癌”的时候,往往会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他太把男性这件事当回儿事了,第二个心态是这个人太傻X了。这两层意思并在一起才让“直男癌”变成贬义。如果女生遇上特别好的男性,她会说那也OK,那倒真的挺好的。但为什么会遇上直男癌呢,这个人达不到女性心目中男性的标准,而且差了好远,然后这个人又觉得自己是最好的男性,所以女性就会觉得这是个二X。如果要真是要相貌有相貌,要礼貌有礼貌,要情商有情商,要智商有智商,她觉得是个挺好的男子,那是不是直男癌就无所谓了。但往往一个女的觉得这人是直男癌,肯定是他审美差,什么都差,还觉得自己特好,心里就觉得这个人找骂。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而对于暖男呢,我觉得女生说“暖男”的时候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无奈。就是说暖男能给女生一定的温暖,能有一定的用途,比如说你生病的时候能看看你啊,你难受的时候可以安慰你一下,但是无奈的地方在于说“暖男”这个词的时候缺乏兴奋感。我觉得“暖男”和“直男癌”这两个词正好在女性生活中形成两种情绪,但都不是她们想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对象。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会选择翻译《飞鸟集》?
冯唐:练笔是主要的原因。当时辞职之后去美国,觉得过去那么忙碌,现在空下来,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方式稍稍练练笔,休整一下。我过去写作的方式用锻炼来进行比喻就像“以赛代训”,就是纯靠写书的过程来练笔。我大概20岁靠后,30岁出头差不多就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当写作之路还要进行下去,我就想用翻译来练笔。所以我选择翻译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东方人——泰戈尔的作品。
有意思的是,泰戈尔是印度人,他本身会孟加拉语,但《飞鸟集》是用英文进行写作的,而且还受到日本俳句很大的影响,因为《飞鸟集》很大一部分是在日本写的。然后我再用汉语翻译过来,对我自己练语言和丰富汉语都可能有一定帮助。
第二个原因,我自己也写诗,同时觉得翻译是件非常难干的事情,而且尝试过后我更坚信这一点。我花了小三个月才翻完这8000字,原来不可能这么慢。我想在翻译诗的过程中摸索一下诗的本质是什么。之前常说诗意会在翻译之中失去,但我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诗意也可以是翻译之中增加的”这个观点的。其实之前的翻译人士追求“信”,但因为翻译的过程本身就是扭曲的,既然做不到百分之百的“信”,我想的是为什么不能侧重“雅”和“达”,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一点真实度,试试更多的“有我之境”去翻译会是什么样子。
第三。我觉得写诗挺有意思的,就好像有个东西哽在那里,它不像做采访或者写杂文,给一定的时间就能出稿,而诗很难在限定的时间内写出来。我自己的诗就是在比较集中的两年写出来的,一是十几岁青春期的时候,二是四十岁之前中年危机的时候。后来诗就写得很少了,翻译诗也可能让我再起兴写诗,事实上翻译也帮我做到了这一点,我后来又在陆陆续续写诗。
澎湃新闻:那您如何看待诗和小说的关系?
冯唐: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内容本身,诗意是小说很重要的东西,能让小说有魂。我觉得人也要有点诗意。小说虽然长,但有了诗意之后,可以把小说看成一首特别长的长诗。
第二个是具体的意象和行文,或是说在技术层面,诗能够帮助小说。读一本小说就好像走到森林里面去,忽然发现:“诶,出现一个动物!诶,出现一朵花!诶,忽然出现一条溪流!”这些形容其实是小说里面诗性语言的一部分。如果小说中能有一些意象和诗句很舒服地融进去,其实对整个小说提精气神特别有用。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现在网络文学中“玛丽苏”这种现象?它是这个时代特定的产物吗?
冯唐:首先我觉得要表明的是网络是一个渠道或者媒介,就是它并不比纸媒的地位低,而是一种新生的传播方式。当然某种新方式刚产生的时候可能没有传统方式的这种优雅、复杂和完善,所以至少现在说一个人是网络作家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贬义的感觉。在网络上写作,没有编辑,也没有篇幅上的限制,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形成的文体节制性会少一些,但速度快,及时性会好一些。对于作者宣泄的功能可能多于传统作家对人性的探索。
我想玛丽苏这种现象的存在一定有它的意义,对于作者来说是一种宣泄,对于读者来说也有消解的作用,不是也挺好?但这种作品在一个时间段内的流传可能还行,而留住的可能性会小一点。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这种自己写着是为了发泄,别人看着宣泄的文章。其实早期上海的鸳鸯蝴蝶派里的才子佳人很多人也看得很开心,再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有一大堆的武侠小说,但现在真正剩下的其实不多的,当时除了金庸、古龙和梁羽生之外,还有很多类似你说的YY小说,就是主人公出生贫贱、受尽欺凌,掉进一个山洞里学了绝世武功,所以女生都喜欢他,叮了咣啷从头打到尾,见谁灭谁。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纯文学写作或者阅读纯文学最大的意义在何处?
冯唐:接着刚才的话题讲,人生里面有时候光是YY是没有用的,并不解决问题。我之前做过一个比喻,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很大的一个差异非常像医院和按摩院之间的差别。我是学西医的,西医是这样:偶尔治愈,更多缓解,永远安慰,不一定能治好你的病,但目的一定是治病,一定要帮你解决问题。所以去医院的时候发现,医院不能保证病人舒服,甚至会让你痛。但是按摩院不一样,会问你轻还是重,它的初衷就是让你舒服。在按摩院,这一会儿舒服了,但过了半天该怎么疼还是怎么疼。
所以通俗文学不能改变习惯和三观。我一直觉得严肃文学应该做到直面人性中的问题和困扰,然后试图表达这些困扰,提示可能的解决方案,大家读了之后觉得:“哎,这事儿还能这么看。”至少给人们另外一个看问题的角度。比如说《洛丽塔》里的故事在很多国家很多时候就是违法的事情,但是这种心理对一些人就是存在的,如果没有《洛丽塔》这本小说,这些人会对自己充满了自责:“我就是一个人渣,就是一个怪物。”但是看完《洛丽塔》后,虽然自己坏,但并不孤独,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巨大的怪物,毕竟还有类似的人,还有作家写过这个事,我觉得至少对心理上有点缓解作用。
人是挺逗的,尤其是心理问题,一旦从正面去面对,有个舒缓,这个病就好了一小半,甚至对有些人来说好了一大半。只要哭诉、描述和宣泄出来,可能就不会自寻短见或者有特别激烈的行为。
第二个作用,我觉得文字有自身的优美,阅读文字是一种审美的,需要一定能量的愉悦。有点像跑步锻炼,需要一定的意志力。在跑步之前,会有挣扎的过程,会告诉自己不能坐在这里狂翻手机,应该去跑步,但一旦开始运动到运动结束,会给你内心中愉悦的补偿,会觉得神清气爽。看一本相对难的小说,背一些诗歌,看一些好的散文,也有类似的一个过程。需要一定努力才能读进白纸黑字,但是读进去之后就会发现文字会给自己带来某种愉悦。
第三个我能体会到的作用,和第一个有点像,但又不完全一样。就是说哪怕自己没有什么要命的毛病,但有时我看看前人写的一些东西,会对自己有一些指导作用。那些人在那样的境遇中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他们怎么安生立命。或者是他们的境遇和我有关联,或者是他们的年龄段和我现在的年龄段有关联,或展现给我之后的年龄段会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能起到的指导作用有时候会比简单的心灵鸡汤或是泛泛的人生格言要来得真切。这三个作用可能是你说的那种“玛丽苏”或者“杰克苏”这种文学所没有的。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个人经历的多样性对于写作的帮助如何,尤其是曾经就读医科的经历?
冯唐:人认识世界总是从有限到无限,从已知到未知这样一种认知的过程。如果你的知识结构相对丰富的话,你会有更多的参比。而这种对比容易产生趣味性,并且容易揭示某种真相。《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把两种不相关的意象放在一起却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就是这样一种体现。
我原来是学医的,我可能就会很自然地把看到的现象,比如感情和行为,为其寻找背后的原因,也就是生理基础。我希望给大家一个常人不太给的视角。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