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谁杀死了谁——文学与电影中的弑亲
2010年11月8日,加拿大万锦市的一户越裔家庭遭到入室抢劫。母亲梁碧霞当场被枪杀,父亲潘汉辉重伤,唯一幸存的女儿珍妮弗在歹徒离开后拨打911。随着案情的披露,这起案件在当地引发越来越高的关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珍妮弗成为杀害父母的头号嫌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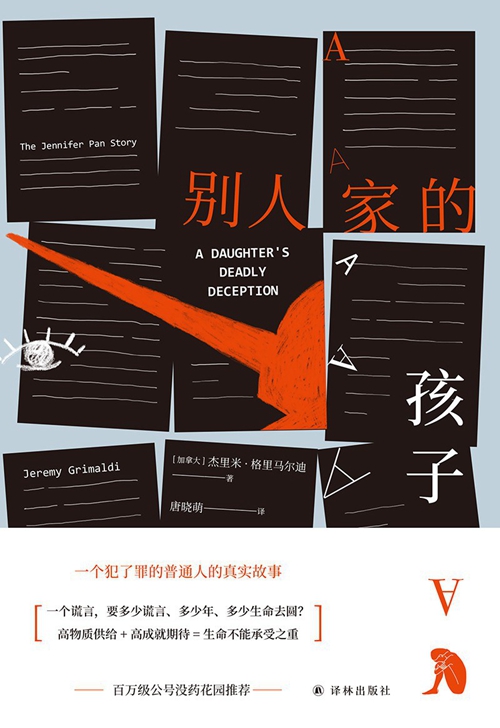
加拿大记者杰里米·格里马尔迪曾以法庭记录者的身份听审,耗时十个多月跟踪案件进展,最后写下这本《别人家的孩子》,回顾了这个越裔家庭以悲剧收场的异国越迁史,还原珍妮弗——少时“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在长大后成为“弑亲凶手”的过程。
潘汉辉于上世纪70年代越战结束后移民加拿大,和同为越南移民的梁碧霞结婚。在两人共同的努力下,他们获得了在异国扎根下去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跻身那代移民里的中产阶级。1986年,两人的第一个孩子珍妮弗出生;1989年,第二个孩子费利克斯出生,一家人从市郊搬去了生活更优渥的社区。
即便在异国生活多年,子女也都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潘汉辉一家依然遵循着东亚式的家庭文化和生活方式。男主外女主内,潘汉辉负责赚钱养家,梁碧霞打理家务、养育子女。像千万东亚家庭固有的亲子关系,珍妮弗和费利克斯只需听从父母的安排,以“出人头地”、完成父母设定的大小目标作为成长中的头等大事。
这其中,父母对长女珍妮弗的要求更为严厉。少时的珍妮弗“听话又孝顺,严格的家教让她不断超越,成为完美的别人家的孩子”,父母的高压之下,珍妮弗不允许自己出错。进入中学后,珍妮弗成绩下降,为了不让父母失望,也为了逃避父母得知后将会带来的更多管束和压力,珍妮弗对父母撒了谎,伪造了一份成绩单。
从此之后,珍妮弗开始了“两面人生”。一面是成绩下滑、恋爱、升学失败;一面是伪造成绩单、伪造录取通知书和毕业证。一面的珍妮弗在餐厅打工,一面的珍妮弗毕业后在一所儿童医院工作——当一名医生,这是父亲对她最大的期望。
正如珍妮弗在第一次造假成绩单时担忧的那样,事情败露后,珍妮弗受到父母软禁一般的管束。她被收掉手机,限制出行,跟外界的接触必须受到父母的监视。导火索最终被点燃,珍妮弗策划了谋杀父母的计划。当歹徒将潘汉辉和梁碧霞拖进地下室时,潘汉辉看见女儿“随意地在家里四处走动”,像跟歹徒认识。
家庭生活里持续产生过高的期望和压力,源源不断积累的矛盾爆发后酿成恶果,珍妮弗的案子并非个例。

日本作家角田光代在小说《坡道上的家》里写一起弑女案。新手妈妈安藤水穗给女儿洗澡时,失手溺死了女儿。小说的主角里沙子被选为陪审员,参与这起案件的审理。曾是一名新手妈妈的里沙子在旁听时发现自己与安藤水穗类似的经历——为了育儿成为全职妈妈,放弃事业,不断被孩子和家庭剥夺属于自己的空间,付出再多也被视为理所当然。面对孩子没有由来的哭闹,时常感到无助和恍惚,孩子出现问题后还要受到丈夫和婆婆的责怪,被看作是没有尽好身为母亲的责任。

剧集《坡道上的家》剧照
回想当新手妈妈的那段经历,里沙子想起自己有过不堪压力和指责拿女儿泄愤的行为。她也曾不断怀疑,自己配做母亲吗?每次需要孤身爬过坡道才能抵达的家,是自己最初想象和想要的吗?
不健全的社会文化和家庭结构下,女性被赋予崇高的形象,天生自带神圣的母性光辉,育儿对她们来说是彰显天性、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经之路。只是,生下第一个孩子的女性都是第一次成为母亲,面对因孩子到来的种种困境,她们同样会慌乱,感到束手无策。施加在她们身上的母性光辉也好,天性也好,未必有一次来自周围人的实际援助有效。
回到《坡道上的家》,安藤水穗在长期精神疲惫的状况下失手害死女儿的行为无法被原谅,里沙子拿女儿泄愤也显然不对。试想,如果她们的丈夫能承担应当的育儿责任,理解第一次成为母亲的妻子,或许恶果就不会发生。
当父母养育孩子时,他们牺牲自己。同时,他们要求孩子放弃部分甚至全部的自我来满足他们。——《坡道上的家》与《别人家的孩子》在这里形成了家庭惨剧的因果闭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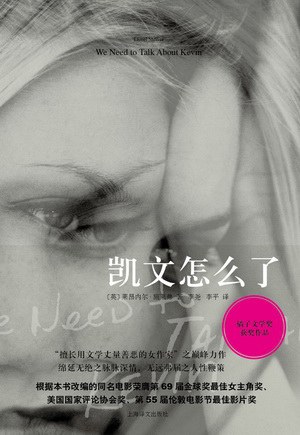
美国作家莱昂内尔·施赖弗在小说《凯文怎么了》里面塑造了一位喜欢周游世界但同样因为孩子逐渐远离过往生活的母亲伊娃。小说以书信体展开,伊娃向丈夫讲述自己现在的生活和对过往的记忆,回想星期四事件发生之前她与儿子凯文复杂又紧张的关系。叙述中,凯文是一个时刻与她作对的孩子,拒绝跟她讲话,拒绝听从她,通过在父亲面前伪装成一位“乖小孩”引起她的嫉妒和失落。与其说是伊娃在养育凯文,不如说是凯文在时刻掌控着她的行动和情绪。
在凯文身上感到挫败的伊娃决定生第二个孩子。女儿的到来未能改善家庭关系,反而将家庭引向分裂:凯文和丈夫是一起的,伊娃跟女儿是一起的。凯文开始通过伤害女儿来伤害伊娃,毁掉了女儿一只眼睛。在凯文十六岁生日的前三天,凯文用箭射杀十一个人,其中包括伊娃的丈夫和女儿,以及九个学生。

电影《凯文怎么了》剧照
凯文身上的暴力根源难以言明。他的父母开明,从未给他任何压力和要求;他的生活环境优渥,成长在知识分子式的中产家庭。与伊娃在叙述中提到的那些因感到虚无或者被忽视后枪杀周围人的少年相比,凯文似乎也不同,甚至瞧不上这些跟自己犯下同样罪行的少年。如果说莱昂内尔·施赖弗的这部小说试图借一起弑亲案留下什么,那也只是谜团,既没有根源也没有结论。
写给死去的丈夫的信的结尾,伊娃宽慰自己,与凯文无休止的斗争是在通过对抗来赢得爱,重复推开的动作为下一次拥抱做准备。这样特殊的母子关系重新拓展了关于相爱相杀的定义,用真实的暴力和死亡涂下爱充满残酷、冷漠和野性的一面。在这一切风平浪静后,爱依旧愿意延续下去。伊娃写,“倘若出于绝望,甚至懒惰,我会说,我依然爱我的儿子”,“我无法预知他出来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子。不过同时,在我的公寓里还有一间卧室”。
回顾珍妮弗案,潘汉辉与梁碧霞紧张的婚姻关系也给珍妮弗带来了压力。在珍妮弗看来,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时常冷战,夹在父母中间的珍妮弗更需要用完美的表现来讨好父母。

这让人想起美国作家吉莉安·弗琳那部《消失的爱人》。外人眼中的尼克和艾米有令人羡慕的婚姻,每个结婚纪念日,艾米都会准备“寻宝游戏”维持与尼克的新鲜感。在第五个结婚纪念日,艾米突然失踪,完美的“婚姻故事”走向意想不到的方向。一边是尼克在媒体面前深情告白,寻找自己消失的爱人,另一边,一本艾米的日记将矛头指向尼克。这个镜头前扮演的好丈夫才是爱人消失的原因——他杀害了艾米。
艾米的日记本里,披露了这段完美婚姻里种种不为人知的细节,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如何在日复一日地互相索取、剥夺后消磨殆尽。艾米认为自己为这段关系献出了全部的自我,换来的是日益冷漠的尼克和他的新欢,她与她对婚姻的美好想象已经被尼克“杀死”数次。当艾米在日记最后写下“我早晚会被这个男人杀死”时, 她已经在实施报复计划,伪装自己被谋杀的事实并嫁祸给尼克。

电影《消失的爱人》剧照
如今来看,这部充满噱头与惊悚元素的小说似乎已经难以引起读者强烈的情绪。现实中,婚姻里的弑妻与弑夫发生了太多。反倒是小说迎来反转,艾米从这场针对尼克的复仇闹剧幕后走出来,那句道破婚姻真相的话更让人不寒而栗:“是的,我爱过你。可后来我们做的一切只有互相怨恨,互相控制,带给我们的只有痛苦。这就是婚姻。”
如果说《消失的爱人》描绘中年婚姻的倦怠和极易爆发的不稳定,迈克尔·哈内克的电影《爱》通过一对老夫妇给予了所谓历久弥坚的婚姻想象致命一击。
电影里,安娜和乔治斯是一对结婚几十年的老夫妇,女儿成家,无人打扰的二人过着平淡自足的生活。直到安娜半身瘫痪,乔治斯既要照顾安娜,体谅她因病愈发多变的心情,还要应付女儿伊娃时不时的责难。某天晚上,乔治斯给安娜喂完水,跟她说了一会儿话,拿来一旁的枕头将安娜闷死。

电影《爱》剧照
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将电影片名里的“爱”引入复杂又危险的境地。乔治斯细心照料安娜,为她请护工,为她拒绝女儿的来访——因为他明白安娜不希望在女儿面前展示自己不堪的一面。他爱安娜,只是他无法为安娜突破爱的局限。他闷死安娜的动作之所以让人吃惊,恰恰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爱的局限,而情愿将“爱”当作可以摆平任何生活问题的神圣解药。我们不愿意正视爱的平庸、爱的无力、爱的险恶……我们在彼此身上赞扬爱,也在一次次伤害中杀死彼此身上的一小部分。在这些故事里,弑亲是所有伤害累积后的一次清算。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