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海@1949的第二年:“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旧在场”
现代性的一个最大特征或许就是人之周遭世界连及内心种种价值、认同的多变、善变与速变。如果说在十九世纪前,尚可以将百年作为一个变化之世代的话,那么到二十世纪后半期则可能十年,甚至五年就要“笑问客从何处来”了。今日的上海人只能在老照片和老电影上观看和回味还未成步行街的南京路、周边是一望农田的徐家汇和热闹熙攘的梵王渡火车站。从这种“经变已无影,无影仍有迹”的意义上来说,上个世纪的上海已然成为一个轮廓迷离、似在雾中的都市。不过也正因为她“似在雾中”,反而更吸引历史学家到神秘的“寂静岭”来一探究竟,张济顺教授的新作《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以下简称张著)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拨开迷雾,解剖地方历史的范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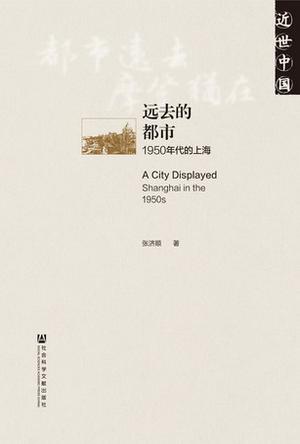
第一,魏氏师从“莫扎特式的史学家”列文森,从日后的作品看,魏氏拥有不逊色于老师的惊人史学天赋。这种天赋从表象上说是读其书如读侦探小说般过瘾,若学术性地概括则表现为:跨地域文化的感受能力、史事之前后左右的联系能力和对政治、社会多面复杂性的穿透能力。基于此,魏氏经常会感到“任何现成的西方概念都难以容纳现代上海历史的丰富与多样性”(第3页)。
第二,魏氏研究上海,一方面掌握有丰富的史料,他的“上海三部曲”引用的资料“大到系统的档案卷宗,小到各式市井小报,各式文献和图书资料达数千种,很多极为生僻,即使根据名目按图索骥尚不易寻得”(韩戍:《三个时代的上海警察与社会治理》,《新京报》2011年9月22日)。但另一方面,魏氏不会被史料所束缚,他用娓娓道来的叙事描绘现代上海的多元文化和不同时期的各方权力争斗。
第三,在上海史研究中,魏氏特别强调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相关性和连续性。以《上海警察》为例,他要建立的就是“晚清改革、国民党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间的联系;抢劫者和革命者之间的联系;警察和罪犯之间的联系;不同背景的特务之间的联系;从1910年的天津警察、1931年的上海公安局到共产党中国之间的联系”。
这些基本思路在张著中都有一定的体现,据作者总结:“魏斐德教授的意见促使我带着明确的‘转型与延续’相统一的问题意识跨入1949年以后的上海史研究,不再为‘规律’、‘必然’与政治褒贬所构成的‘目的论’或‘决定论’史学所左右,也不再让丰富的历史材料成为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等二元对立概念的填充物,而着力去发现1949年以后天翻地覆的政治改造表象背后延续着的历史本身的逻辑发展。”(第3页)
张著不太彰显,但也极其重要的另一条学术脉络则是她多年来对大陆上海史研究成果的“继承性反思”。读书自无定法,但笔者以为张著较为适宜的读法或应从附录的七篇文章读起,它们无论是对于理解本书还是上海史研究的深入都有着“旧文新读”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第一,当下治国史者除少数几位最出色学者外,不少研究都难脱从1949年谈起的“横空出世”之病。这些作史者往往因缺少晚清和民国的“前史”积累而造成其成果一往前推就露出马脚。而附录中的《论上海里弄》和《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两文正为我们理解第一章五十年代上海的“里弄换颜”提供了长程的视野和“前史”的关照。
第二,作者自1990年起已经对历史自身的复杂发展与以简单褒贬为表现形式的“历史意义”挖掘间的紧张性做出了思考,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并未正式发表的《上海租界研究的思路更新》一文上,作者写道:“如果把上海租界视为一个多元价值体系,将研究思路从褒贬相加的价值判断转向价值关系的阐述,上海租界研究可能会向客观和全面靠近一些。一切与上海租界有关的历史素材都应当进入研究的视野,而不是根据既定的褒贬判断进行筛选。”(394页)这段话写在1993年,恰在作者赴美之前,但它又与前引作者受魏斐德影响后的研究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呼应,足见一个学者对于另一个学者的“影响”并非仅是单向度的关系,“影响”对于一个好的研究者而言,很多时候是等待着一把钥匙来打开她内心早已准备好的呼应结构而已。
第三,作者对于如何研究“上海社会史”做过不少自觉的方法论反思。在《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界说》一文中,作者特别强调:“基层上海人一旦成为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的主角,其意义就不限于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决定作用,而会牵动这一研究时限的变化”,因此“上海统治者的更换在某些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而在一些更为基本的方面,特别是市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文化范式,则可能无关宏旨”;考察基层上海人在近代化进程中的经历,“阶段的划分要模糊得多,甚至可以不考虑阶段的划分问题……上海的家庭模型、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很难用阶段来区别”(350、351页)。
这些方法论反思都证明作者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考虑“转型和延续”并存、互动和共生的关系。“立足基层,模糊阶段”虽然是精彩洞见,但一旦落实到具体研究时,会遭遇重重困难:
首先,近现代中国素以“变”而著称,所谓“阶段”的划分正是立足于变得多、变得广和变得深的预设之上。虽然近年来“变与不变”的交错互生已被不少学者所重视,但要讨论以“变”为鲜明特色的一段历史中的“不变”部分着实并不简单。
其次,为基层人物写“民史”是自晚清梁任公就积极鼓与呼并得到一大批读书人众声响应的作史思路,但时至今日,要切实地书写“人民群众自己的历史”又谈何容易。
最后,具体到张著处理的“国史”中,近年来的有趣现象是上层政治史的重构因档案的开放程度等问题而进展稍缓,反而是基层各种类型的史料层出不穷,精彩异常,为撰写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突破的可能性。但这种上下层的错位与不平衡,也极容易造成地方“社会史”研究的碎片泛滥和诠释瓶颈,那么张著是如何应对这些艰巨挑战的呢?
在笔者看来,作者是以包含了多种武器的“地方解剖术”来应对的。这里先谈其中最醒目的一件武器,即通过“重构延续性”来再解释1949年之“巨变”。作者并不否认1949年后上海社会的巨大变化,但她不能认同的是对于这种巨大变化的两种看似清晰、实则过于简化的历史诠释:一是中共对上海旧的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基础进行了彻底的清除,并在此过程中以原来的底层民众为核心重构了社会,构建了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另一个则是1949年后党国体制走向顶端,国家吞噬社会,上海社会经历的天翻地覆的改造正是“极权主义”的一个佐证(24、25页)。
在作者看来,这两种诠释看似方向截然相反,却分享着相同的预设,即“1949年是一条巨大的鸿沟,彻底截断了历史!”但历史又怎么可能被彻底截断?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中的一段话最为深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张著中的话则是:“重建历史转捩点的丰富与复杂,打开重新解释1950年代之路。”(23页)
它一方面说明张著的“重构延续性”承认1949年是历史的转捩点。因此作者在各章的处理中都未淡化和忽视五十年代“改男造女态全新”的一面。如第一章指出:“在居委会的有效运作下,非单位人群投身政治运动之热烈可说是史无前例,保甲组织无可企及的政治功能也得以充分发挥,几乎每天的报章广播都报道这类消息。”(48页) 又说:“邻里间相互监督的强化一方面有助于加强居委会作为国家控制工具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使得政治运动渗透到居民的‘开门七件事’,成为里弄生活的日常方式。邻里和家庭的政治色彩更加凸显,共存关系持续紧张。”(71页)第五章总结说:“好莱坞的被驱逐(绝迹上海滩达30年之久)使上海电影市场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称雄数十年的美国影片从上海文化市场上退净……1950年底,上海电影市场已是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的一统天下。”(276、277页)
另一方面这句话又告诉我们所谓“延续性”不等于“相似性”,更不等于“重复性”,而是要凸显历史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如鲁迅所言:“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作者在接受访谈时也曾说到一些国外学者关于“延续性”的开拓性研究。她一方面肯定这些学者筚路蓝缕的创见,但另一方面亦尖锐指出若单纯比较政策相似性,则可能慢慢“也会走到一个死胡同”中去。
因此重构“延续性”的焦点应在于考察“延续当中怎样发生转型和裂变”,即“历史的非凭空创造和有负担前行”。所以一方面,作者对各章不囿于1950年代的部分极为重视,有些章节文字虽不多,但或有前期研究积累,或体现在背景梳理与行文点睛之中,另有些章节则直接将民国上海与五十年代的上海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第四章《约园内外:大变局中的黄氏兄弟》就把时限定为1930-1966年。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与历史延续性相关的问题,如“教会大学的消亡、高等教育的体制转型及校园政治文化的变迁如何侵入学人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和精神世界,个体的能动性是否就此消解,个人的思想、精神与情感世界是否就此变得单调,个人的特殊经验又如何转化为新的政治文化意义”(193页)。这种贯通前后的提问方式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亦为上海城市史研究打开了“新路”。
另一方面若聚焦至五十年代,张著对当时上海社会与新政权碰撞互动时的复杂历史图景多有深刻而精彩的展现。第一章就梳理了当“新政权遭遇旧里弄”时所要应对的三大难题:一、上海基层社会的人口流动过频与空间分布过密;二、各阶层杂居,彼此职业不同、生活条件不同,福利要求亦有所不同,因此难以用一种政治号召驱动绝大多数居民的政治热情,也不可能存在长久的利益共同体;三、建立何种组织,既有别于旧保甲,又能有效地掌控社会,依靠哪些人去取代保甲,去建立和运行这样的组织。
正因为有这三大难题,之后的历史过程就不可能是一个按照“国家逻辑”,运用“阶级净化机制”彻底清除近代上海里弄中的社会基础的过程,而是“上海里弄社会的积淀之深、关系之复杂,利益之多元,远远超过了新执政者最初的估计与想象”(79页),然后新政权“一方面推动、允许或默认了社会按照自身诉求,营造一方‘新型’的自治空间;另一方面,沿用革命时期的政治动员经验,掀动底层,一波又一波专门针对里弄居民的清理整顿与普遍的政治运动相呼应”(80页)。最后革命、国家、社会共同建构了共和国早期的上海里弄。
在“重构延续性”之后,面对让基层民众发出声音和上下历史沟通的困局,作者动用了第二件武器——“建立机制性”。基层民众自然不可能完全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其绝大多数没有属于他们本身的史料。可是通过史家在史料之海中的艰难爬梳,抓住蛛丝马迹,建立非表面的历史机制本身的运作逻辑,基层民众亦能够在大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而非仅仅是大历史的背景和注脚。张著第二章就凭借对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普选的地方开展机制的剖析,让小人物生动鲜活地走入了历史。
在这个故事里既有吞金自杀的女工C,又有上了党报的老工人李杏生,更有成为区人大代表的女工李小妹。作者讲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并不是展示细节后的讲完罢了,也不是要通过他们来证实或证伪普选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勾连关系,而是要回答在普选的三个主要阶段:选民资格审查、选举动员和选举人提名到最后选举中,是什么让女工C因为选举而走向自杀,又是什么让一个默默无闻的老工人成功登上党报,同时令一个“极为普通甚至在政治上不善表现的女工”(108、109页)李小妹脱颖而出成为区人大代表?
以李小妹为个案,张著就从“天时”——选举法定程序(联合提名制与等额选举原则结合)对她的助力、“地利”——李所在的纺织行业和供职的仁德纱厂在选举中的独特政治优势以及“人和”——仁德纱厂的“微观政治环境”令她成为了厂里既符合“官意”,又符合“民意”的候选人等三个方面梳理出了一条看似顺理成章、实则玄机重重的底层“劳动人民”跻身人大代表行列之路(108-113页)。
而就上下历史沟通这一难题而言,“上层史与下层史的研究不仅不相冲突,而且是互补的,若能两相结合,则所获甚丰”(参见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张著可能正是一个“两相结合、所获甚丰”的例子。她在第二章中对新中国第一次普选中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与底层民众自我认同之间的张力给予了充分关注(132页)。除了探究普选运动本身的机制外,她更努力去寻找中共在1953年初迅速启动普选和制宪的原因。对此作者与张鸣等学者有类似思路,即与斯大林的强力推动有关(129页)。同时中共又非全盘,而是有选择性地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这主要是因为中共认为“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基本大法”、通过普选将“联合政府”渐转化为“一党政府”(129-131页)符合这一阶段革命的需要。然后作者将上层史研究之成果与上海的地方普选勾连起来,提出了一个多面相的结论,即中共高层的认识和理念使得普选在为底层民众打开上升通道、激发其政治热情的同时,又和制宪一起成为中共“继续革命”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环节。
如果说“重构延续性”与“建立机制性”这两种武器具有一定的学术方法论意义,那么作者还有一种武器或许就属于“独门秘技”,使得此书具备了鲜明的个人风格,此即“区域体验”。
做“区域”或者“地方”之困难往往在于如何展示和凸显“区域”的独特性,使得区域不再是“全国一盘棋”中与其他棋子类似的“又一枚棋子”,同时又要回答这种独特性是以哪些方式和各种普遍性相联结的。而作者因自己的“区域体验”有着解决这一难题的优势。
从附录中的《从小溪到大海:上海城市历史和现代教育》一文可知作者的曾祖父是清末上海梅溪学堂的创办人、南洋公学(交通大学之前身)首任华文总教习张焕纶。作为上海城墙内的“老上海人”后代,她对上海的历史变迁有一份源自于家族血脉的独特感受。一方面作者系怀于历史的苍凉与无奈,看到了“消失在大上海百年历史之中的,远不止张焕纶这个具有新思想的老学究,而是整个上海老城厢和它的居民”(413页),但另一方面使她感到震撼的是,取代城墙内“老上海人”的新上海人在成为现代都市人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增添和强化了上海文化的开放和宽容的特质”,塑造了令人瞩目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海派文化(414页)。
当然对于新上海人取代“老上海人”的历史,或可以有更多的话可以说一说。现代上海的开放是一个“面向世界”直至“走向世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西潮、新潮澎湃而汹涌。如何在潮流中站定脚跟,海派文化究竟因何而成立就变为一个令人颇难回答的问题。回溯以张焕纶等为代表的“儒家经世读书人”的经历,则为问题的回答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沈恩孚写的《张先生焕纶传》就曾说道:“其(张焕纶)立教以明义理、识时务、体用兼备为主旨。其教科为国文、舆地、经史、时务、格致、数学、歌诗等;甲申年始增英法文,旁及洒扫;应对进退与夫练身习武之术……尤尊重德育,选古人嘉言懿行为常课。”无疑张氏强调的不是无根的“海纳百川”和无原则的“有容乃大”,而是一种“胸有定见,心有固守”式的开放,其定见与固守来自于儒学,又部分超越了儒学。“张传”又说:“中法之役,俾学生受军事训练,率之夜巡城厢,闻履声者皆知其为梅溪生矣”,这体现了“儒家经世读书人”的胸襟抱负系于天下苍生,而具体实现则多立足本土本乡。既立足本土本乡,在晚清的衰世中“从事教育”为其中一正途。因此张焕纶被私谥为“宏毅先生”,沈恩孚亦能从其事迹追慕他“陶铸时彦,警醒后学”的流风。这种流风曾长久地泽被江南各地,在民国时期乃至今日亦能见其余绪,听其回响,却慢慢与上海的都市文化绝缘。今日返观,当多有长思。
回到张著,我们可以发现,正是有了结合长程历史和私人生活对上海本乡的独特体验,张著在不少地方展示了如何用体验性来突破做“区域”之难题。
首先是体验性对于“档案话语”的修正与穿透帮助极大。张著处理史料之最大宗无疑是形形色色的档案。这些档案可以视作关于五十年代地方政治运作中的各种“表达”,这种种表达是由无数意识形态化的概念、词汇和语言所组成,稍不留神就会跌入前文所述的“又一枚棋子”的陷阱。但作者因熟悉上海的社会与文化而在档案处理上颇有独到之处。如她在讨论上海五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热时,就充分挖掘出政治话语掩盖下上海市民特别是青年们乐看、爱看、追看香港电影的那些简单、直白、生动的理由,进而重现被档案所遮蔽的多彩生活。如有人说就是专为看“主角陈思思面孔漂亮”,才千方百计去觅得《美人计》的电影票;又有人说:“香港明星是‘人嗲,演的嗲’”;也有人说:“我三天三夜(排队购票),就是为了《新婚第一夜》,今后找对象,就要夏梦一样嗲的女人。”(289页)而有了观众群的考量,作者亦注意到电影经营者依旧延续着“在商言商”的特性,往往努力规避政治束缚,追求上座率,想方设法多多放映“打得结棍、苦得厉害、既轻松又紧张”的香港片(290页)。
第二,在档案和其他历史资料之外,作者善用个体记忆与作为上海人的集体记忆来描摹“最难以呈现”的感觉、体验层面的历史,第五章即指出优秀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人物给上海观众留下的印象竟往往不如片中的“反面人物”。如1958年的国产电影《英雄虎胆》,上海人记忆最深的是其中的女特务“阿兰小姐”,而不是深入虎穴的英雄曾泰。“阿兰小姐,来一个伦巴”成为了当年许多上海人茶余饭后讨论这部电影时能脱口而出的一句台词(293页)。这种观察如果没有植根其间的“区域体验”,大概是很难得到的。
第三,上海作为一个超大型都市,其“多元异质”的社会特性要长期生活浸淫于其中方可能抓住一点神髓,而张著对这种社会特性往往能通过寥寥数语传神地表达出来,如说到上海里弄内的“异质人群”,作者就用上海邻里间表征彼此关系的许多称呼来证明“五方杂处之近密”,如老山东、小广东、亭子间好婆(苏州人对外祖母的称呼)、阁楼大大(扬州人对伯父的称呼)、前楼爷叔(上海人对叔叔的称呼)、后楼阿娘(宁波人对祖母的称呼)等(30页)。
综观全书,作者着力揭示的是一个“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旧在场”的1950年代上海。所谓“远去”指的是“1950年代的上海,确实称得上天翻地覆,国家的动员与掌控能力前所未有,一个统一有序的上海社会奇迹般地出现”(15页)。这段“远去”的历史无论是史家还是读者或相对还比较熟悉。但“摩登依旧在场”,“上海历史与上海经验并没有在1949年这个历史转折点上戛然而止”则是张著对1950年代上海史“去熟悉化”后重新书写的一大贡献(17页)。
相较各种沉溺在追慕摩登、怀旧往昔情绪中的历史书写,从张著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一个上海人——她成长于1949年后,曾在艰难时世中暂时远离过这座城市,后来又因其专业而熟悉了解这座城市“由溪入海”、走向现代的复杂过程——其内心更大更深的关切,即上海的世界沟通、上海的地方文化之根与各类上海人鲜活的生命故事。在这种关切里联结了人性与历史,老城厢与新都市,霓虹灯内和霓虹灯外,地方、国家与世界乃至历史的亲历者、书写者与阅读者,正基于此,读这段历史就不能不有所感慨,同时又不能不有所感悟。 ■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