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深度︱“良妻贤母”是怎样炼成的:日本女性为何不热衷工作?
在人们日常置身其中的话语空间中,一些包含性别意识的说法往往容易惹人耳目,兹举几例。比如,此前高考结果发榜后,“女状元”的多数出成为话题,甚至出现了高考制度对男生不公正的分析。再比如,近年“女司机”一词频繁出现在一些媒体中;它所包含的戏谑语气尽管极其轻微,但却足以引发一些女士的不快。与这两个语汇不同,“女汉子”一语因其通常用于年轻女性的自我调侃,似乎通行无碍。而近年逐渐消失的“女强人”说法,在言者与听者中引发的观念则要相对复杂一些。另外,近年带着时代新意登场的“女神”称呼,似乎让人皆大欢喜,无人对此蹙眉。
这些有关女性的说法并非无关紧要;事实上,它们之所以会获得有意无意的关注,正因为它们包含了一个社会或隐或显的特定的性别意识,反映了一个社会特定的性别秩序。如此说来,问题的严肃性即刻呈现了出来:人们日用而不知的这些语汇,究竟透露出怎样的性别观念,并关乎怎样的性别平等?若与其他社会进行一番简单的对照,我们或许会对这个问题的复杂与重要程度有所认知。邻国日本当代女性的情势,当是一个首选的参照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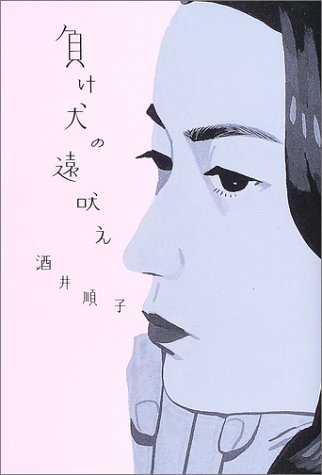
与这个形象浓烈的说法相比,“干物女”的流行则超出了日本自身,遍及东亚大陆,人们对它也更为熟悉。这个新奇的词语源于女性漫画作家火浦智在女性杂志《KISS》上连载的漫画《萤之光》(2004—2009年,共15卷)。漫画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雨宫萤的27岁的独身女性。与职场上颇为飒爽的风格相比,她周末在家里的个人生活可谓散漫到了极致,被偶然发现的男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训斥为“邋遢”。由于很享受目下的快乐生活,她放弃了恋爱的想法(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日本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为29.2岁)。在漫画中,恋爱状态被比拟为“活蹦乱跳的鱼”,放弃恋爱故被称为“干鱼”(即日文“干物”),女主人公由此获得了“干物女”的称号。由于雨宫在职场和个人生活中展现了截然不同的形象,其生活方式在日本年轻女性中引发了很高的人气。2007年7月,日本电视台制作了同名的电视连续剧,由当红女星绫濑遥出演,进一步引发了日本女性的共鸣。
让我们言归正传:上述两个关于女性的说法,反映了日本女性的怎样的自我意识?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两个流行新语皆源自女性作家之手,引发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接受与共鸣。换言之,这两个语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女性的自我认同。事实上,这两个流行语关涉的女性议题很明确:恋爱,婚姻,工作,家庭,可以说蕴涵着当代日本女性整全的自我意识。这种指向女性自身特定生活方式与状态说法的流行,其背后有着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女性的历史。对历史的简要回顾,有助于我们理解今日事关性别平等的观念与实质内容。
日本女性为何不热衷工作?
在进入历史回望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关注一个问题:日本女性的就业率为何偏低?根据日本内阁府的调查,2012年日本女性(15岁以上)的就劳比率为48.2%,远低于男性的70.8%。在有工作的女性群体中,有三成的女性在结婚时会选择离职;而当女性孕育第一子时,又有四成的女性放弃工作(2013年数据)。据此,人们或许不难指出如下原因:日本社会男女不平等、男尊女卑;男性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女性则被束缚于家庭当中,处于从属地位。那么,这些似乎掷地有声的说法是否靠谱?其实,在复杂的社会事实面前,过于富有想象力与作为其反面的想象力贫乏在一点上别无二致:它们对事物的判断往往缺乏要领。让我们继续看若干组有关现实的数据。
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白皮书,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2012年持“赞成”或“二选一的话选赞成”(以下简称“大致赞成”)的比率,女性合计为48.4%,男性合计为55.1%,并未显示较大的分歧。这就是说,无论是作为全体还是性别群体,有大约一半的人群基本赞同日本的性别分工。事实上,在统计开始的1979年,上面两组数据分别是70.1%和75.6%;此后,这一表达“大致赞成”的比率逐渐下降,在最低点的2009年,双方分别支持的比率是37.3%和45.9%。最近数年,这一比率稳步回升。这里面的问题是,大约一半的当代日本女性基本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这种是被迫的选择,还是基于主观的意欲?
日本关于“男女平等”意识的直接调查,提供了一种说明。在回答“完全平等”的具体项目上,67%的受访者认为“学校”中的平等程度最高。排名第二位的项目,就是“家庭生活”,有47%的受访者认为男女在家庭生活中完全平等;不过,认为男性或女性“大致占优”的比率,分别为43.2%和7.4%,显示了较大的差距。在事关工作的“职场”项目上,回答完全平等的比例是28.5%,而认为男性“大致占优”的比率则高达57.7%。问题进一步呈现了出来:既然男女在职场上未完全平等,女性应该以何种方式面对工作?
我们首先看一下作为工作对立面的余暇。依据1986—2011年间的统计数据,女性参与观赏舞台艺术(演艺、戏剧、舞蹈、古典与流行音乐会等)的行动比率在保持在10%—20%之间,而男性群体则在稳定在10%以下。据此我们可以推论说,日本女性享受的精神与文化生活,为男性群体的两倍。换一个角度说,在作为享受经济成长结果的余暇方面,女性事实上超过了男性。
另一方面,日本女性就业的具体行业也能说明部分问题。事实上,日本女性在艺术、文化相关领域的就业人数,远高于男性。统计显示,在诸如文艺·著述、雕刻·绘画、演艺·舞蹈、记者·编辑、音乐、设计、摄影、体育等领域,女性就业者比率均超过男性;比如在差距最大的“音乐”领域,女性就业者数为男性的四倍(2005年)。可以说,女性是当代日本艺术与文化活动的主要支柱(参见《从统计数据看日本(2013)》,日本统计协会编,第133页)。这种职业分布,与学生接受教育时选择的学科有关。在日本大学“家政”“艺术”“人文”“教育”学科,女学生居于压倒性的比例;比如,女生占艺术类学科的71.5%,人文学科的65.9%(2012年)。这些事实意味着,日本的性别分工有着相对成熟的社会基础。
让人瞩目的是,最近十数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在促进提高女性的就业机会。1999年,日本制定《男女共同参加社会基本法》,试图以法律的形式促进女性进入社会。2013年6月,在日本内阁通过的《日本再兴战略》中,“充分发挥女性中潜在的高度能力、让女性充分活跃”被置于该战略的核心地位,并在“女性活跃促进”、“兼顾工作与家庭”、“男女共同参与育儿”等领域设定具体的方案。比如对于女性创业,日本设置了特别的融资渠道。这些法律与战略,或许会进一步促进日本性别的平等。
不过,女性最终选择就业与否,或者选择以何种方式就业,完全是个体的生活方式问题;日本政府若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尚需提供更多的物质与精神激励。对于女性个体而言,由于她们正在享受着经济发达的成果,如何实现个人福利的最大化,就成为她们社会行动的出发点。进一步而言,如果就业无法增进她们目下享受的福利,增进个体的幸福,她们为何又要去额外拼搏呢?这种说法,进一步引出了关乎平等实质的问题。
我们这里并不打算冒险进入有关平等问题的讨论,而只是要指出如下一点:如果说作为关系的“平等”本质上属于政治社会的事项,那么个体对平等与否的观念的内化与切身的感知,就具有实质意义——社会条件的不平等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个体福利将遭受同等程度的损失。正是在实质福利的水准上,我们看到了日本社会事关平等的另外一种样相。
那么,如何测定个体享受的实质福利的多寡?除了上面提到的余暇外,我们还可尝试给出一个指标。我们有必要在方法上先做如下三个假定。第一,享受福利的多寡将体现在个体的生命指标(诸如健康)上;第二,在生物学的意义上,男性与女性对同等程度福利(或相反的不利)的受益无显著差异;第三,福利与个体的生命指标成正相关,即享受有利的物质与精神条件愈多,则在健康与寿命等状态上会有更优异的体现。我们这里只观察一个关乎生命的实质性指标,即自杀率。根据日本内阁府2014年发布的《自杀对策白皮书》,在2013年全年自杀的27283人中,男性为18787人,占68.9%,为女性自杀者数(8496人)的两倍以上。依据我们的假定,这组有关自杀的数据或许有益于我们对性别平等的进一步理解。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卫生组织(WHO)2014年发布的《预防自杀:面向全球的命令》白皮书显示,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是一个全球普遍的现象。但作为极少数的例外,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印尼与伊拉克为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几个国家都属于伊斯兰教国家,这是一个让人注目之处。依据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其名著《自杀论》中的看法,个体的自杀与社会条件有着高度的关联。
回到本节的话题,日本女性就业意愿的相对偏低,或者反过来说日本女性与家庭之间较高的关联,与日本女性个体自身的判断有紧密的联系,而并非仅仅是“男性居于统治地位”这一状况的某种逻辑结果,因而也丰富了人们对性别平等的理解。事实上,日本社会相对稳定的性别分工,有着特定的历史过程。这是我们在考虑日本女性就业意欲时,不可忽略的要因。

同所有社会一样,日本女性在近代经历了被“发现”与“发明”、即女性群体由男权社会所意识并纳入政治轨道的历史进程。不同于一般的观念,日本女性的上述过程与开启历史转型的明治维新的步伐并不一致。事实上,明治维新二十年后的1887年,一直走在时代之前的日本知识精英才开始全面关注女性问题的存在。
在这一年创刊的《国民之友》杂志上,女子教育、家族制度、废娼、参政、劳动等作为社会问题,提上了国民意识变革的日程。1892年,作为女性版《国民之友》的《家庭杂志》创刊,日文词汇“家庭”一语成立,并获得新的意涵,并被赋予了诸如“家庭即仙境,其中花开鸟鸣,天丽日永;一重墙之内,若桃花流水,杳然若世外”之类的形象。不过,这些美丽辞藻的目的并非歌颂家庭的乌托邦;如同“社会为男子之战场,家庭为妇人报国之地”这一说法表明的一样,作为“人间之幸福”、“地上之天国”的家庭,其构成的必要条件就是专职的家庭主妇的存在(参见上野千鹤子:《近代家族的成立与终结》,岩波书店,1998年,第106-122页)。就此而言,近代日本女性“诞生”于家庭内部。
观念的变革最终成功转换为社会政策,开始自我实现。1899年日本颁布《高等女校令》,规定日本各县均需设置一所女子学校。不过,这并非仅仅是日本女性解放史中光明的一页;女性的命运毕竟无法脱离时代的氛围。在明治政府大力宣传的“家族国家观”中,将女性培养为“良妻贤母”成为必然选择。比如,1902年,日本文部大臣菊池大麓在“大日本妇人教育会”上发表讲演时宣称:“成为良妻贤母是女子的天职。因此,当家庭主妇,是非常重要的本职工作。若想培育优良的国民,作为其源头的家庭首先必须优良。优良家庭越多,国家越繁荣;相反,不良家庭占多数的国家,必然要衰落。这就是说,家庭为一国之根本;改善家庭正是当下的要务”(转引自加藤千香子:《近代日本的国民统合与性别》,日本经济新闻社,2014年,第35页)。
此后,“良妻贤母”逐步被建构为主流意识形态。比如,《妇女新闻》在1919年宣扬说,“我国正处于作为一等国家进入新世界的时期,家庭改造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并具体论及“服饰、饮食与住宅的改造”和“精神与思想改造”;后者进一步涉及到婚姻、妇女婚后的地位、财产关系、家庭教育等。作为更具体的举措,该文提倡“主妇每日读书三十分钟”、“为主妇提供书房”、“为中流家庭提供托儿所”等(参见永原和子:《近现代女性史论:家族、战争与和平》,吉川弘文馆,2012年,第268页)。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的女性与家庭开始被赋予军国主义的最新意识形态。在1937年发布的《国体本义》中,有如下论述:“我国国民生命的根本,既不在于个人,也不在于夫妇,而是在于家庭……所有人在诞生的瞬间,就将其一切命运托付给了家庭。亲子关系是自然的关系;亲子是生命的连续。父母是孩子的本源,孩子是父母的发展。”显然,论述的主旨是对作为妻子或母亲的女性进行规训:育儿是关系国家的公事,而非私事。日本女性就此被塑造为“军国之母”。同年,日本通过了《母子保护法》,当母亲们无法完成其天职时,国家提供资助。1941年,日本政府制定《人口政策确立纲要》;翌年,日本发布《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纲》,提倡国民致力于创建“健全明朗”的家庭,要求日本的母亲们在修习日本妇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科学的教养”、“涵养健全的兴趣”并“炼就强健的身体”(参见加藤千香子:《近代日本的国民统合与性别》,日本经济新闻社,2014年,第257-258页)。
显然,这一系列有关女性与家庭政策的主旨在于确保战时人力资源;随着战局的日益变化,日本女性被纳入战争轨道中来。当然,“战场”仍主要局限于家庭。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并未给日本女性带来过于苛刻的负担;不过,由国家发动的战争事实上强化了女性作为“主妇”——作为一家经营管理之主的妇人——的地位。简言之,作为战争的结果,女性与家庭的关联得到强化的同时,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如同当代日本著名的女性主义者上野千鹤子指出的一样,现代日本社会呈现出的“家庭重视”的特征,并非源于日本优良的文化传统,而是明治以后近代日本的一项全新的“发明”(上野千鹤子:《近代家族的成立与终结》,岩波书店,1994年,第69页)。我们看到,在近代日本特殊的“家族国家主义”观念下,将女性塑造为“良妻贤母”成为政治的必然选择。日本女性被限定于家庭内部,正是日本国家权力运作的必然结果。
二战结束后,日本学者开始用“妇女解放”这一话语描述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女性史进程。然而上述简要的介绍已然表明,这种进程远非单纯的相对男权的“解放的历史”;它同时是源于国家权力的“压抑的历史”。不过,这种辩证法式的结论绕开了根本的问题:由于它对至关重要的“解放”与“压抑”存而不论,有关女性的相应仍然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解放”似乎并不是一个恰当描述女性近代史的语汇。
提到“妇女解放”,人们容易联想到马克思主义传统,尤其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如下有名论断:“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2页)。基于这种分析,在前苏联等国家的实践中“妇女解放”被等同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或者说,“妇女解放”重属于“无产阶级的解放”。
这种基于阶级主义的解放学说,在日本并未获得实际的进程。相反,对于家庭与家务劳动有着特别体验的日本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男性参与家务劳动,根除作为女性压抑物质基础的“家父长制”(即父权制或男权制),才能真正实现女性的解放。这是日本迄今为止关于“解放”实质内容的最明确的说法。尽管如此,具有高度意识形态意涵的“解放”话语,对于女性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的历史经验对此无法给出更进一步的回答。

相对于日本或其他社会,中国近代以来妇女解放运动历程之壮观与剧烈,为人类史所罕见,具有特别的启发意义。比如,在革命胜利后的1950年代初期的数年间,事关中国女性命运的婚姻法的颁布与实施、禁娼运动、城乡妇女的扫盲运动、土地改革、妇女参政等,均得到了轰轰烈烈的展开,至今仍为人们所记忆(参见刘晓丽:《1950年的中国妇女》,陕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共和国青春时期以迅雷之势展开的这种女性“翻身”与“解放”实践,有其特定的历史路径。
中国女性进入近代史,大体可追溯到清末戊戌变法期间。1897年《事务报》刊载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女学》,女性问题登上了帝国的政治议题。翌年7月,中国第一份女性报刊《女学报》诞生;到共和创建时,据统计有近三十种女报问世。在诸多女报中,1904年创刊的《女子世界》,为后世留下了慷慨激昂的女性宣言。比如在发刊词中,作者金一有如下说法:“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这种“中国的灭亡,挽救于女子,亦未可知”的观念,拉开了中国女性进入历史的帷幕(参见夏晓红:《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9-101页)。
然而,作为近代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第一个身份,晚清女报中的“女子”并非女性自我意识的萌生与流溢,而是扮演启蒙角色的男性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延伸。如同女性史学者夏晓红指出的一样,女性的“自由与独立”,只能从属于“救国事业”(同上,第107页)。这种作为“新中国”与“救中国”手段的女性认知,将一种特定的政治角色赋予了女性;或者说,近代中国女性的“发现”与“发明”,源于一种国家意识与男性政治意识的结合,而不关乎女性自身的自我意识与角色担当。
上述特定的意识形态必然“召唤”同型的历史主体。从晚清“女子革命军”、“女子光复军”,到民国时期的“女子革命军”、“上海妇女北伐敢死队”,中国女性以最直接的暴力方式,参与到了“新中国”与“救中国”的历史进程当中(参见李木兰:《性别、政治与民主:近代中国的妇女参政》,方小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8-64页)。这种实践对形成中的女性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女性的公共身份的标签,此后随着革命进程的展开,虽然最终转换为“妇女”,但其本质含义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比如,在1939年于延安创刊的杂志《中国妇女》中,毛泽东专门撰写了发刊词:“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转引自刘晓丽:《1950年的中国妇女》,第295页)。在这种有着鲜明时代特征的铿锵语句中,“妇女解放”的首要内涵或者说是唯一的内涵,得到了不可辩驳、无可置疑的历史构成。在关乎民族存续的大时代,中国女性与中华民族共度了一段艰辛、残酷的岁月;今日回顾起来,依然让人有荡气回肠之感。
不过,历史与故事并不如此简单,也未就此打上休止符。中国女性史与历史进程之间朴素、高度的同型性,意味着什么?如果将家国天下的政治叙事框架暂时悬置起来,这种进程对女性的意义就显现了出来。如前面言及的一样,这意味着作为主体的女性的不在场,意味着“女性”的内涵依然由国家权力与男性权力所决定。中国女性在一个多世纪、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她们所获得的“解放”首先意味着女性的“国民化”。然而,问题正在于这种“国民化”,在于这种“国民”的社会历史内涵——它事实上等同于“男性国民”。中国女性只能通过男性国民化的方式,才能获得自身的政治与社会地位。这种状况对于女性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占中国女性人口绝大多数部分的农村女性,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具有典型意义。
革命胜利后,农村妇女得到了政治与经济激励,走出了家庭,参与了社会生产。这种从家庭获得的解放,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女性地位的改变,正是时代赋予的“妇女解放”内涵的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观念与理论正在爆发其特定的强力,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不过,回到历史的现场,人们无法对下述事实视而不见:农村女性“一肩挑起了两幅重担”,要同时从事家务劳动与社会生产。比如,在1950年代中期,陕西关中地区女性被大量动员到棉花生产劳动当中,可谓是时代的一个缩影。女性史学家高小贤对此所做的一项口述史研究,为人们留下了历史证言。一位受访妇女回忆道:“妇女白天干地里活,黑了回来才干家里的活,推磨、喂面、做鞋、管娃。黑了还要访话搭布(织布),一家人穿的、用的都靠织布呢,经常一熬就是个透透夜(指通宵)。地里不去不行,分不下粮食,你要生活嘛。”这就是说,身体感觉背离了当时事关“妇女解放”的日常话语。
这种高强度的双重劳动,必然会以女性的健康为代价。一位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回忆道:“五九年那年中棉花……我生了娃3天就跑到地里看棉花去了……过了十几天就给棉花拔草去了。蹲在那,结果弄得脱肛。我说这咋办呀?把那个推上去。那就是月子里落的病,挣的,在地里硬捂、硬挣。”而省卫生厅负责妇幼卫生的干部的回忆,更为沉重:“五八年大跃进,人人要到地里劳动,妇女刚生了孩子也要去。所以子宫脱垂比较多。……当时省卫生厅也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去治疗子宫脱垂……我们查到全省有子宫脱垂的妇女5万多”(参见高小贤:《“银花赛”:1950年代农村妇女与性别分工》,收录于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5-276页)。
意味深长的是,上述口述史所表明的女性个体与群体的生活史,一方面为正史、即男性书写的国家史所忽略,另一方面又被还原为近代中国以来“妇女解放”的宏大叙事,从而得到了历史性的正当化证明。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女性最终完成了特定方式的国民化。然而政治所承诺的“妇女解放”的具体内涵,也只能理解为这种国民化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女性“解放”的历史进程起点是一个世纪前女性得到“发现”的瞬间,而这个起点同样是终点。对于中国女性而言,家庭、工作、女性自身(即作为自然的与文化的性别),依然是有待认知、尤其是有待女性自身认知、反思与述说的对象。
当然,我们当下正处在这一历史进程当中。这一进程与1970年代末开始的伟大的改革开放,有着同样的历史方向与前进步伐。女性主义批评家张念关于中国妇女解放进行的深刻而细腻的论述,表明了这种步伐踏出的时代韵律。作为女性对自身历史的透彻反思,她论述道:“如果‘女人性’是反革命的,那么性别认同就是革命的,我们需要制造一个‘女人’的观念,同时再制造一个‘男人’的观念,去理解‘人性’的深度以及国家政治的内涵,而性别政治的任务也就是让单独的男人和单独的女人如何说出自己,并在这个当代政治的开局处,活生生地演示出差异,演示出对抗,演示出既关乎内部,又关乎外部的差异思维,从而打破过去所有的‘完满性’、‘纯洁性’与‘封闭性’”(张念:《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88页)。这或许是另外一种起点。
性别话语、政治与幸福
出于审慎的原则,本文将止步于上述关于女性社会史事实的简要勾勒与描绘,因为继续的讨论将把议题带进观念领域,从而引发与本文主旨无关的争议。我们知道,事实的朴素、客观与坚硬,会有效制止观念、尤其是偏见的独行,为人们的思考提供安全可靠的出发点与场所。
我们已经看到,有关性别的话语——从抽象的平等原则到当下的流行话语、再到历史性的宏大观念——以及作为具体制度的劳动、婚姻与家庭的具体内涵,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构成,反映了该社会具体的文明样相。不过,仅仅指出这一点并不令人满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过程中,是否意识到各种权力对人自身的制约乃至越界的侵凌,这是保证每一个个体追寻有尊严的生活的根本前提。简单而言,我们要有清澈的自我意识,包括性别意识。这种意识源于具体的生活感受,首先是作为人、作为个体的有着生物身体性别的人的真切感受。如果说幸福归根结蒂是个体的感知,是个体的心灵状态,那么这种幸福与否只能由个体说出。
不过,这么说决不意味着政治与社会在个体幸福面前的免责;恰恰相反,迄今为止有关性别的“发现”与“发明”的历史表明,政治社会只有为个体自我意识的生长、充盈与实现提供恰如其分的物质与制度条件,而非任何形式的庖代,才能守住其本分。作为个体的男性与女性是否真切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是否具有清明透彻的自我意识,这是一切好的政治行动的出发点。人必须为自己的生命状态负责。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