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朱天文:侯孝贤和唐朝在哪里见?《聂隐娘》的剪辑机上

不说时间说光阴,因为时间是有死线的,此片却不大理会交片的死线压力,做手工艺般剪剪停停还补拍,一度迷茫到似乎永无完成之日。
其间,谢海盟的书《行云纪——聂隐娘拍摄侧录》早早已写毕。我一直对这部电影极度悲观,即使戛纳首映后一面倒的佳评,也得了奖,仍不改我的悲观。这时候,便把海盟书(《行云纪》即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拿来翻看解忧,这本我称之为“留下活口”的证词之书,以此打气,以此立志。
海盟写了从剧本讨论至拍摄结束的全部过程,显然她并非以剧组成员的角度来写,如果那样,她势必很难脱开电影的专业范畴,与电影的工作伦理。好比备受赞誉的摄影和美术,却是拍摄过程中最困扰侯孝贤的两组阻力,若说这部电影的成绩是侯孝贤跟这两股力量搏斗的终局,亦不为过。海盟记下这一切,她采取了在电影之外仿佛人类学家的距离来观察电影拍摄,包括身为编剧的自己也在被观察之列。是这样的距离,放宽了,也放远了,才足以解我之忧吗?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此所以海盟写了前半段,而我将写海盟没写的后半段——剪接。并且我要学学海盟的距离,来试图把剪接如此电影的专门物讲得非电影人也懂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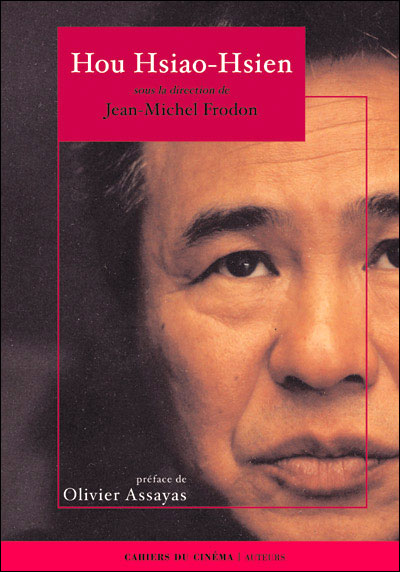
这段王派彰翻译的中文我校订过,谈话当时有法语口译,由法国《电影笔记》出版成书,之后又译为中文出版,几经转译,已陌生化,现在我引用自己的言谈,仍很诧异,也奇怪彼时没把错误订正?想是既然法文版这样了,也小误不碍大意,就不改了吧?因为实况是,侯孝贤不仅用说的,还用两掌框成摄影机运镜,还哼吟配乐。那些自吟自创的配乐,剪接中,亦不时随片子进行流转而出,我不敢惊动,暗赞再没比这更宜洽的配乐了,只恨徒手徒械毫无办法能够键录,而它就像晴空飘过阵雨,待仰目寻觅已杳踪迹。那些自创曲,倏起倏无,一支也不曾来得及录下。
陌生化的中文,如常说一遍会是这样:“职为电影编剧,每次看自己参与的片子放映时,每次都觉是在喝浓缩原汁给稀释到只有百分之一的加味水。我已世故(几近于虚无)的理解,因着现实条件限制,做不到的就是做不到,影片拍摄永远成为一次七折八扣的执行过程。”
过去许多年,对电影工作我是失去了热情,这趟有海盟生力军加入,不免老给她打预防针,我那句颇遭传播括引的老实话“电影是导演的,编剧无份”,拿来洗脑海盟,毕竟也要照顾一下新手的心理感受:“好失望齁。”盟说不会。不会吗?盟说:“不会,因为是侯孝贤的电影。”
吓,海盟比我坚定。

而导演,他身处于影像的那方。
那么,在我们文字方来看,那漫长又无赖(光阴无赖是穷秋)的拍摄现场,那折扣再折扣的拍摄过程,影像方的侯孝贤,他怎么看?啊,他迫不及待地要奔赴现场。经验告诉他,现场一定不辜负他,凡呼必有应。未知的现场静候着他,会带他到他要去的地方。
这样的现场,显然,不再只是一个执行剧本的所在。换角度言,剧本并非施工蓝图照表操课,“一个萝卜一个坑,怎么可能,我哪受得了”,侯孝贤说。所以剧本之于现场比较像,投石问路。像钓者垂钓,肯定是钓鱼啰,但鱼从哪里冒出?鱼长什么样子?最神采的时候永远是,你发现的东西,未必是你所期待的东西。
侯孝贤常拿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话来说,说多了连我也以为是他说的,因为那正是他拍片的写照:
电影在脑中想的时候是活的(我们的剧本讨论阶段)。
却死于剧本的纸上作业(我将之整理成白纸黑字,工作情形像一名秘书,而非编剧。所谓剧本,是写给剧组据此以执行摄务,侯孝贤一向并不看。同理,若像电影工业大国那样,剧本排长龙地等着他读他选他拍,那是从来也没发生过的事,他只会拍他独自的脑中物)。
然后在拍摄当下复活了(布列松甚至极端的表白,影片成绩,在“即兴创作”时突升,“执行创作”时,跌降)。
然后死于底片,而在剪接里再次复活。

往后,侯孝贤经常挂嘴边已成口头禅的是:“看看有什么,剪什么。”或是:“这些都难说,要剪了才算。”或根本像决胜前夕撂下话:“剪辑机上见。”或这次海盟的侧录说:“有类事情,你要进了剪辑室才知道。”
因为剪辑在他,既不按照剧本,亦非依循分镜,如今我很明白,他货真价实是“剪辑机上剪辑”。剪辑的判准,他唯听命于自己的眼睛,凡不好的,悉数剪掉,只留下他眼睛审核通过的。这些不要的东西,无论它负荷了什么重要的讯息,担当着关键的环扣,他眼睛看着不好,心狠手辣地,剪光光。正是,在这剪辑的时刻,导演跟编剧分家了。
这种差别,对电影实作的启蒙震惊(或是大惊小怪) ,便写成了三十年前我那本《恋恋风尘——一部电影的开始到完成》。但《聂隐娘》这回的差别,在我看了初剪的时候,差别到决裂的程度。正确描述,导演固然不理忧心忡忡的编剧在那里辩谏怨声,也不理所有千辛万苦追随过他的拍片同志,包括他视为珍宝呵护有加的演员、明星,当然更不理砸下去的巨大时间精神物力财力,我们全部,都像火箭升空时一节一节燃烧殆尽的推进器给卸弃于大气中。
抓狂的编剧,堪堪维持住最后一点礼貌:“拍不到是罢,现场没东西了。”
另一位菜鸟编剧已头抱钢盔奔逃到百尺外,却躺着也中枪遭我出租车上吐槽:“你写的侧记比电影好看一百倍。”想想,又吐恨声:“还好有你的书留下记录,不然我们简直像一群傻瓜。”

九个月后,第二次看,海盟不看了说不愿卷入编导大战。看完我说:“哇这么原理,极简到没有感情。”
遂走路去搭捷运,板南在线一站又一站的无语,换换刚通车的信义线吧,出地面,东门吃韩国菜。侯孝贤遂发话:“那是怎么样呢,不过就是个电影。”
我讲起不久前看的《星际穿越》(Interstellar),在星际之中,我说:“你升空去了,在星际里翱翔,不理我们人间了。”我又把当着年轻剪辑师直言不讳的评议再说一遍,你选择这样剪法的结果,是需要取得观影人无比的善意和耐心来支持的,八○年代自然是,九○年代本世纪初也还有,但我怀疑,这样的时代空气已经过去了,不会再有了。
此言说得似乎感伤,不合侯孝贤的味,他笑说:“你每次看我片子不是都这样,你们什么时候满意过我的电影了。”
感伤亦非我习惯,只会叫我生自己的气。过两天我连连写传真到剪辑室,直呼芝嘉、侯导,芝嘉还呼在前面。这位个儿小小剑眉浓浓似蜡笔小新的年轻人,原是此片场记,《聂隐娘》拍掉底片四十四万英尺(《海上花》二十余万英尺,《南国再见》二十三万英尺),多到剪神廖桑也没奈何,让位给既快又准又记性超优的芝嘉(人称芝加哥)。我问芝嘉剪来剪去,烦不烦?她倒插剑眉圆眼看我好似我是路边大婶,她说:“有哪个导演,有谁会让一个从没剪过片子的人来剪接?”
生平首度,我被迫动用了编剧的信用发言,再发言:“对影像美学严苛至洁癖的要求下,是否可以想办法拉出一条线索给观影人循线进入影片的迷宫。”我提点的意见,皆冠以“强烈建议”四字。
芝嘉回了我手机短信:传真清楚收到感谢。此由于我不用计算机,联外器材手机与传真机皆古董中之古董,屡屡只呈现乱码,令我必须追电确认收妥。侯导则在别事电话联络时顺带一句:“你的传真……(抱歉似笑)动得很大,要想想一个星期后再来看。”
为何是一个星期?安抚语吗?真不祥(吉祥的祥)。就算尽言责吧我告诉自己,但终朝萦绕发着热温,我可能更是中邪了。
数日后,没错不到一星期,猛然我一醒,这提的什么意见啊根本不搭到一种地步的。也果然,他两位并未受影响,连动摇一下下的影响都没有。至于一个星期后,是休剪一星期,芝嘉呆在中影厂捞片,还有一批底片转成数码待看。原来,编剧是介入不了的。影像的判准,剪辑的法则,出入其间者是他俩,即便新人如芝嘉,又岂会听我的。
那么倒要来问了,影像的判准依据是什么?剪辑机上侯孝贤看着不好的剪掉,好的拿来剪,这好与不好,准何而定?直觉,当然是。不过直觉很难说也无由说,我应该试讲讲别的。此时,眼前浮起往事,带着今晨露珠的往事闪着光,何曾如烟,亦不许如烟。

黑泽明开门见山,直抒最欣赏《戏梦人生》,看了四遍,是他没办法拍的。他们是片厂长大的导演,不自觉受片厂规律和制度影响,拍人一定要拍得清楚,不可以只拍手或脚,这一点沟口健二颇跟侯孝贤像,也不太移动摄影机,不过沟口亦受片厂约制,不可能在那里一直等演员端饭。如《悲情城市》,黑泽明最爱最后一个镜头,大家一直吃饭,这在他们绝无可能。而最有意思的,是那些非职业演员,常常挡住主角,若是专业演员会很留意不去挡住主角,所以片子没什么男女主角之分了。
(影评人王瑞祺的说法比较有学问,他评《戏梦人生》是独据一隅的破格电影,因为一反传记电影做法,侯孝贤每把李天禄的角色放在人丛里,主角的面孔夹混在人丛里不知所终,却让不知名的群体向观众展现出生之力量。其破格而出即在此——我请你告诉我你的一生,你却不大提自己或个人的成就得失,而只管惦记那一一逝去的人,彷彿在说,与我终究不离的,真正塑造了我的,是这些早我谢世的人。其独据一隅,若干程度上很有划时代的意味,至少在今后,有传记体裁电影问世,《戏梦人生》足以成为同类影片的一个参照。)
黑泽明说:“我也希望有你这样的自由,你的影片会令人想到frame以外的世界。但是连摄影师也配合不了,他们丢不掉片厂的习惯。我认为这是你最厉害的地方,因为你有完全的自由,frame外的世界也一样真实。”
这太讶人了,侯孝贤有完全的自由?我从来只看到现实环境对他的限制。想必黑泽明说的自由,是另外一件事。
景框,frame。
此乃电影之所以为电影的载体,终归是,最后全部都上了那块白幕。
影像给装在框之内,框是封闭的,这便是黑泽明所谓片厂的规律和制约,就算导演想变动,摄影也丢不掉这个框。而侯孝贤的自由,框是开放的,似有若无的框,是黑泽明认为侯孝贤最厉害之处。

海盟书里写到剧本讨论阶段投入的田野调查工夫是在造一座冰山,影片虽只露出冰山十分之一角,但冰山绝不可不造,这是剧本人物一切编排的判准根据。侯孝贤的电影一直是,框内只露出少许,影片魅力便从那没露出的庞大真实世界来。其魅力,“无穷尽的因果网,一团乱丝,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隐隐听见许多弦外之音齐鸣,觉得里面有深度阔度,觉得实在,我想这就是西谚所谓the ring of truth——事实的金石声”(张爱玲语)。
但侯孝贤很缓慢、缓慢到安静的电影,如何做到能有金石声?他如何做到框之内的影像能与框之外的真实世界,两者无缝接轨?
以电影术语,他用长拍长镜头(long take long shot),深焦(deep focus),场面调度(mise en scène)。长拍是不打断时间,深焦呈现前景中景后景完整的空间不切割,场面调度即人在这时间空间里的活动。
故而爱用非演员。布列松每称人模(human model),以此表示电影里的人,也以此区别来自戏剧表演的演员(actor)。布列松说不要演员(不必指导演员),不要角色(不必揣摩角色),不要表演,只要生活中活动的人模。演员动作,由内而外,在舞台在戏剧,演员得让观众相信他的动机。但人模,动机不在他身上,他不知而行,行于所当行。舞台上演员创造性的诠释完全成立,其可观其力道,都在这里。但电影之中,他的表演却涉及简化,反而抹消了他本我所蕴藏的矛盾暧昧。电影那逼真的表象,叫表演给毁了。因为人模,重要的不是他们让拍摄者看见的,而是他们隐瞒的,那些他们具有的却自己并不知道的,可摄影机都看见了,捕捉了,记录了,留待拍摄者随后的考察分辨。
于是剪辑。这当口,剪辑机上的影像,与其说是拍摄者在汰择,不如说影像在校正拍摄者。影像揭示出来原先想法的错误,剧本的谬漏穿帮,细节不合又扞格,一概,删除。
身为编剧的文字方,我感受关注的却是思路的辩证。因为 ∕ 所以,虽然 ∕ 但是,那么 ∕ 不过,故而 ∕ 因此,然则 ∕ 却说……往前往深推演的思路,努力说服大家相信这样推演得到的结果(或没有结果)。编剧擅长靠对白推动进行。
然而影像方的侯孝贤,他苛求着框内影像之无缝接轨于框外真实世界的那种真实,摄影机看见的会告诉他,什么留下,什么不要。留下的,他再看如何安放,细细安放在最对的位置。
这次《聂隐娘》,核心是凭什么可以杀人?于是编剧建立了巩固了诸般理由。然后是从杀到不杀,编剧先就得说服自己相信为什么不杀,此若不成立片子也不必看了。所以目睹关系着这核心的几场重头戏全部剪除,编剧真的苦到无言。而导演的回应总是“看着不像”(我看很像啊),“她不像会说这些话的人”(呵呵舒淇的台词从她自己数过的只有十六句又减成了剩下九句),“你以为这样说过来说过去有用吗,没用的”,“没办法剪不进去”。
以上侯孝贤云云,这么多年了我亦非没听过,何以这回我这样波动,我想是因为唐朝。
唐,春风吹渭水,红绡满长安,好个国际大都会长安。鲁迅喜爱唐人柔和明亮的生活氛围。侯孝贤拍此片老在说,恨不得有个时光机器去到唐朝看一下,他就会拍了。过往,他将剧本的纸上作业扔给我而迫不及待意欲奔赴的现场,过往一定不辜负他凡呼必有应的现场,静候着他会带他到他要去的地方的未知现场,现在,是唐朝。谁也没看过的唐朝,求未知于未知,现场在哪里?框之外的真实唐朝,又在哪里?此所以剧本讨论时我们都同意,用戏剧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意味,景框是封闭的,拍法必须改变。
那种长拍不打断时间的不论是固定镜头、或推轨镜头(《海上花》开场九分钟推轨一镜到底,从此李屏宾上瘾了),都不该用。那种不切割空间保持与现实空间一致、让人在其中来去的场面调度拍法,由于内景搭建纵深不足,又缺乏生活细节供人活动,也不能用。侯孝贤大胆极了,想动用BOLEX来拍,到处鼓吹。
BOLEX是手动发条,上满一次可拍二十至三十秒,一个镜头二十几秒便得再上发条,但演员只管继续进行并不停止等摄影,这是逼迫摄影无暇它顾,二十几秒只够他全力以赴去抓住人。侯孝贤且决定用1:1.33的标准银幕(新艺综合体是1:2.21,新电影时期新导演改用1:1.85),这种比例的框里人,最漂亮。
BOLEX拍,摄影师和剧组皆曰不可行,也终至于未能行,但BOLEX的精魂已徘徊在编导脑中不去。与从前剧本讨论大不同,这次我们着力以戏剧时间来结构剧本,完成时,侯孝贤信誓旦旦而我们也同样振奋,这会是一部好看易懂的电影,情感华丽,着色酣畅,充满了速度的能量。
当然,当然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影片了。长拍的,写实的,“没有看过这种有生活的武侠片”(英文字幕译者Tony Rayns语)。唯这次多了一件,美,大家都叹美,向来冷刻的英国《卫报》也说美得目不暇给更胜《一代宗师》。
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象的唐。汉唐汉唐,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这次侯孝贤的框之外,不是真实世界的唐,却是诗词歌赋自古以来无数人想象里的唐,拿安德森的话说,想象共同体,唐的想象共同体,不美都难。
原来框之内与框之外,内外有界,实则分别了电影的两脉系统。电影记录真实的一脉,电影蒙太奇(montage)的一脉。而电影诞生于记录真实。
一百多年前,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拍摄出人类第一部电影《火车进站》,白幕上火车对着观众驶来,吓坏了大家四下逃窜,电影逼真得吓跑人。因此比起文字的探触和探索真实,一百年对数千年,电影是个幼儿,有着幼儿般只看、不想的本质。影像一思考,电影的幼儿神便不爱。影像具意义,不如说影像饱满。饱满含有自我悖反、自我歧义、也自我一体的,全部的内容都在这里了,此外并无内容。
影像记录真实,这个我们日日行走其间不知觉无意识的真实世界,景框,将之框了出来让人看见让人知觉,咦这是我们?怎么长成这副德行?惊异有之,羞见有之,满意是肯定没有的。是此框,把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真实稍稍陌生化了一下,框之内,不在说了什么,而在露出些什么。因为这露出的部分,与框之外的世界,本是织结连绵的,拍摄者做的事,彷彿只不过在现实空间里暂且,界限出一方景框。弱水三千,拍摄者只取一瓢饮。
他似乎无所作为,只是记录。他客观中立,中立到简直没有自己有时真叫人着急。他极少的自我,也许就只在框出界限。无边世界,形形色色,何以他要选择框出这一块,却不要框出那一块,这充满直觉几率的选择不选择,也许就是他对世界的意见和主张了。
这样抑制的姿态,这样低调的自我,自然无法满足人,电影诞生后二十年遂出来了电影的蒙太奇。
蒙太奇来自苏联导演爱森斯坦,他倡导把现实影像割裂,重新排比,整理出线索和因果次序,通过剪接,组合成为蒙太奇美学。重新组合的现实影像,已不存在现实时间,框内是蒙太奇的时间戏剧的时间。蒙太奇的影像携带着作为,我要你看这个,我要你看那个,《战舰波将金号》是此理论精彩实践的代表作。其所以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苏联,那是他为要烛照社会的不平等,唤醒阶级意识。时至今日,蒙太奇狂用到一秒一个cut,切得大家神志涣散,便用更咸重更快速的切来抓住心不在焉的观众,这是连一般市民公民也晓得应该批评的影像消费文化矣。
其实不待今天,六十年代巴赞(André Bazin)早也写了他那本电影现实主义经典《电影是什么?》,请循其本,抬出灰扑扑的电影小儿神清洗一番。长镜头、景深镜头、场面调度,以及用作真实素材的非职业演员、即兴创作、采自然光源不打光,皆他说开来的。他提出作者论,摄影机是一支笔。
跟他同时代的布列松说:“简直没有执行剧本的动力,除非,在超过你原来的想象之上,替每一个镜头找到一件新的激素,那是即席创作,再创作。”他根本认为,将戏剧加进来的电影,不是电影,那是影剧(编导),或影戏(演员)。电影的表现是在影像和影像、声音和声音之间的关系,而不在言语和表演姿态的模仿。银幕上演员一身是戏,愈要靠近来,愈是贴不住。因为真和假的混合,产生假,那是影剧或影戏。
因为,同性质的假(最佳例子是京戏的按步行步,全部是程序),却能生出真,那是剧场。
真假相混,真的叫假的现形,假的叫人不相信真的。几年前一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日片《入殓师》,用偶像剧拍法讲一个真人真事,是真假相混结果出个假的绝妙范例。好莱坞电影工业大国时有好片,那是工业分工之下各部门全体在一个高度专业水平上,所以封闭的框内能够以假做真,好看。而在框内偶有岔开一下的东西,侯孝贤说那就很厉害了。
布列松谓来自剧场的影剧影戏,摄影机唯有复制。而源于电影的电影,摄影机是创作。这我也才明白,1996年科波拉担任戛纳影展评审团主席,偕评审们看了侯孝贤的《南国再见》,首映时被人发现从后门悄悄进戏院又看了一次,因得奖无望,他遇见台湾媒体便单刀直入对记者说:“你们一定想知道我对这部片子的看法,虽然我的同事很多人看不太懂,但我完全知道它在说什么。它对台湾当代生活的描写非常有趣。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因看不懂而讨厌它,但我了解它。”记者问他喜欢此片的什么,他说喜欢片中简单的摄影。
科波拉所云,刊于当日《民生报》(又一份消失的报纸)头版头条,次日他宴席间又数度说,此片简直像梦,昨晚还梦见它。
是吧电影,那种借影像跟声音的接触、错位、平行来表达的表现方式,那种在影像、声音、寂静之间寻找关系和作用使之选妥了最对的位置,各自安坐在那儿诸般心甘情愿的,那种迷人的真实。
当年《戏梦人生》,杂志社编辑人云亦云问黑泽明有否同感,李天禄是操纵布偶的人,人的命运也冥冥中有人操纵?“不是!它就是完成的电影,就是cinema!”黑泽明呵斥的语气至今在耳。“我感动的,它是从任何角度看,全部都是电影。我自己拍电影有时会觉得不像电影,可是看你的电影感觉就是电影,新鲜而清新方法的电影……”
《聂隐娘》,我看过第二回之后过了大半个月,又邀我第三回看。看完我眼湿说,隐娘好可怜。有一种人是这样,傻傻的,愚执的,木讷寡言,好事总之轮不到他,坏事倒全推给他。晚上睡时我想着隐娘,像科波拉夜里梦见,次日仍想着。我对侯孝贤说:“这不是我们原先的隐娘了,你跟着舒淇走,剪出来的隐娘有一种纯直。”
对侯孝贤,后来我援引小津的“余味”之说:“电影和人生,都是以余味定输赢。”只觉哀哀的。
去年春某日,砰一大响连我家窗户也震了震,是我们社区路口的慈惠堂地下室瓦斯爆炸死了一人,往后我经过,见灾墟里黑污污的神龛并也黑了脸的西王金母,心想活在数位影像今天的电影小儿神,处境堪比。莫怪九○年代初电影人要膜拜伊朗阿巴斯的电影,欢呼感泣着小儿神毕竟又复出。那届戛纳影展阿巴斯任评审,是他跟另一位葡萄牙老导演力挺到动怒了,《戏梦人生》才得奖。黑泽明家客厅进门的地毯乃阿巴斯所赠,说是“让好朋友都能踩踩”。而那位与布列松与巴赞同时代如今还活着故而状若疯癫老人的戈达尔(Jean-Luc Godard),旷野之声般力赞阿巴斯的《生生长流》,那部拍摄于伊朗大地震之后一年、阿巴斯剧组去寻找演过他们《何处是我家》片子里的那个小男孩不知还在否的旅程记录,戈达尔导演以电影小儿神的权柄加冕此片道:“这是有电影以来,最伟大的电影。”
我是悲伤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