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用了二十八年时间,逃离「妈妈凝视」
原创 塔门 塔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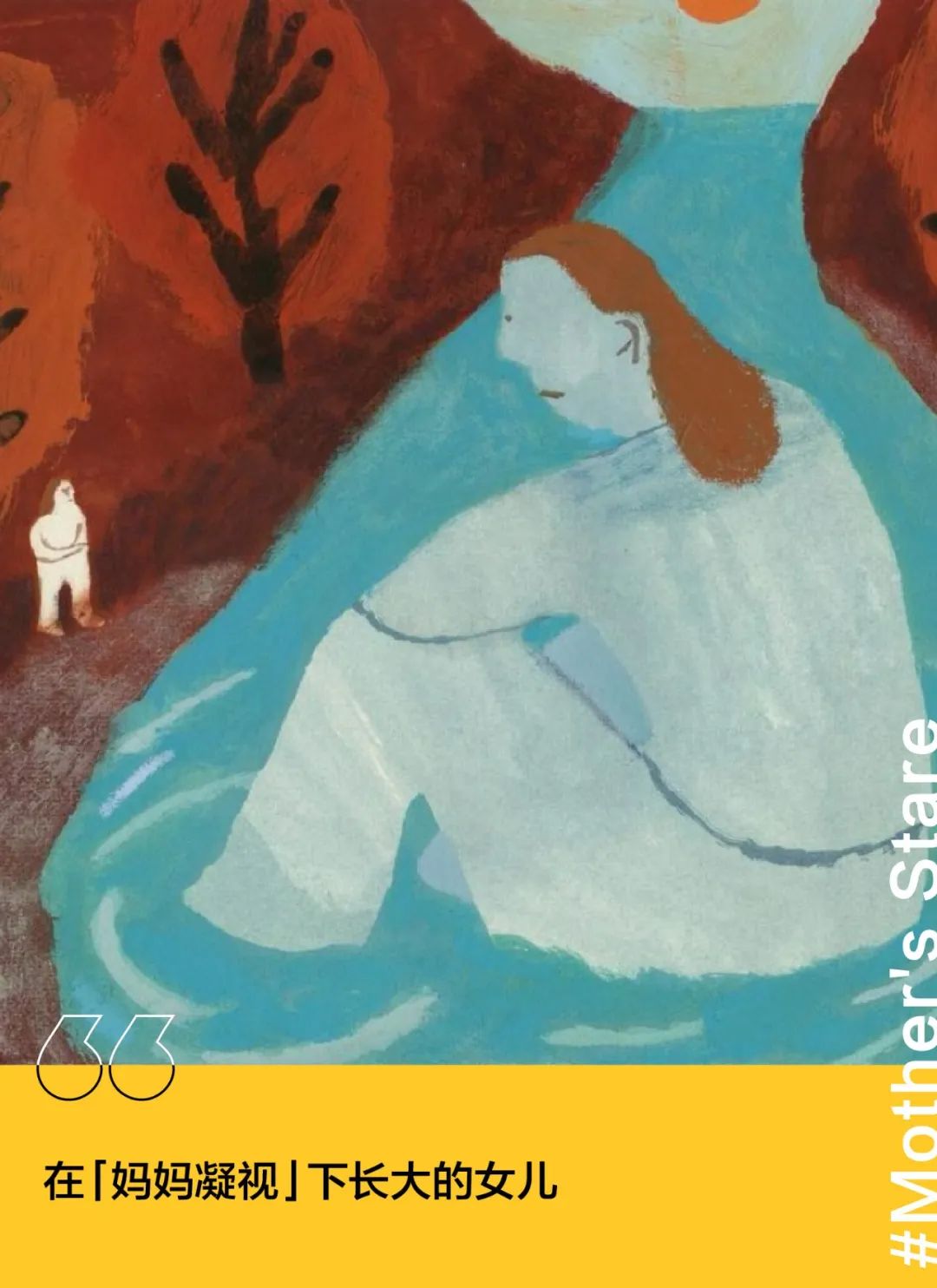
「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母亲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一个母亲。」但在当代,「让下一代人拥有自己生活的权利」,早已成为一个不容挑战的基本信念。而这种以下一代权益为中心的理念的结果,反过来就是越来越不尊重母亲作为人的权益。
上周,我们邀请了 Uko 来现场谈论她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在录制过程中,录影棚突然沉默了一阵。声音回来时,Uko 说,人生过到了哪个不容易的阶段,常常下意识会去怨恨父母。
在当代,当妈妈是一件风险巨大的事,除了激增的育儿经济成本、情感劳动、精力消耗,还有「妈妈」这个身份的需要背负的「原生家庭」指责。对一个「不够理想」的母亲的抱怨,经常会出现「没有准备好,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但对第一次当母亲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要背负往后数十年的当妈责任,又有多少人能够准备好。一旦一个女性成为妈妈,她们是否有随时选择结束婚姻的自由?她们面对孩子是否能发泄抑郁、焦虑、愤怒、脆弱的情绪?如果平衡不了家庭与事业,她们的人生是否有权利追求名利、地位、金钱、梦想、欲望大于追求「当好一个妈妈」?
抽象的妈妈是很容易理解和体谅的,但真实的妈妈带来的,往往比单纯的「母爱」或者「怨恨」要复杂得多。Uko 认为自己是一个「妈妈凝视」下成长起来的女儿,她数十年一直在反思自己和母亲的关系。
以下是 Uko 的自述。
大概七八岁,
我对我妈开始失望了
上个月,和我妈通完电话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希望能记得她的样子更多一点。有些时候,我想起她时脑海里打开的那副卷轴,更像水墨画而不是写真集。我关于妈妈的记忆很淡,也许是因为小时候那些本该记住妈妈的瞬间,她都不在场。
长大以后,有老师问过我,作为孩子来说,你希望你父母能教给你最好的事情是什么?我很认真的想了想,我可能只希望妈妈在那儿让我找得到就够了。

我妈是一个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发展很有主张的人,她在很少有人会开车的年代就一个人考了大卡车的驾照,那会,她刚从农村来到城市,跟我爸爸结了婚。对她来说,未来无限可期。但我一出生,她的计划全乱了。
我是个早产儿,出生的时候,医生说这个小孩不行啊,她长大了也可能是个智障,大家都说要放弃我了,只有我的外婆说再抢救一下,然后我才生活下来。
我妈是很束手无策的。于是,从我生命的刚开始,她就没有刻意地去练习作为妈妈要承担的一些实操性的事,比如整宿整宿地哄小孩睡觉、喂奶,这些她都错过了,因为我是由外婆一手带大的。后来我妈解释说,那个时候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外婆出现了,外婆带得的确是比她自己带得好,她就放心让我外婆去带了。
我们家是一个很庞大的家族,外婆经常会在兄弟姐妹家里接住,因为我跟着外婆长大,所以我也经常住在亲戚家里。于是,我从小吃着百家饭长大。对我来说,「家」这个概念里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更多的是一场场饭局,一个个不同亲戚家的小卧室形成的流动的形态。
后来我才发现,很多人从小长大的家是有一个固定的居所和准时的饭菜的一个稳定的生活状态。生长环境会给每个人一个出厂设定,比如我从小就很快地体会到了人类的「多元性」,每个人都有他们生活的道理,没有非要遵从传统习俗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也确实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

我对于「妈妈」的渴望,是希望妈妈会出现来照顾我。哪怕她不会做饭,衣服皱了就扔掉。但就像象群中的小象在一旁酣睡,母象会用身体遮荫,同时用鼻子卷起小树枝左右摆动,配合甩动的尾巴为小象驱蚊赶蝇那样,我小时候也会期待妈妈能成为我的依靠。
但她很忙,我爸也是,都忙着工作、应酬、打麻将。有次我生病了,打电话给我爸说,爸我发高烧了,他挂掉了;我再跟我妈说,妈我发高烧了,她也挂掉了。我知道他俩都在打麻将,就自己去了医院。这事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约莫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逐渐的感受不到自己和别人的情绪,慢慢的活成了一个 ai 机器人,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对我妈彻头彻尾地失望了。
初中的时候,我爸我妈在反复的离婚复婚中,终于忍受不了对方而决裂了。随着父母的最后一次离婚,我们家的矛盾由「冷」变「热」,争吵和指责都一个一个浮现在了我的眼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之间又出现了新一轮的问题,就是我不能见我的妈妈,我开始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和妈妈的关系,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和爸爸的关系。我第一次觉得我没有家了。
然后我选择了出国。我割裂成了两个「我」,美国自由的土壤培育了我,我幸运地遇到了非常棒的宿舍爸爸和妈妈,第一次感受到了无条件的爱和支持;但是我每次回国,我都会遭受非常严重的道德指责,就变得很撕裂。
我刚成年,我妈就急不可耐
带我去整形医院面诊了
那时候,我妈展现出了一种并非典型的「掌控欲的母亲」的形象:由于精神上对于女儿的寄望,她不断地督促我减肥和整容。
我出国第一年的时候,胖了大概二十多斤。我妈在机场看到我时就惊呆了,她从头到尾扫视了一眼说,你怎么跟「猪头疯」一样。在杭州话里,「猪头疯」指的是当你得了腮腺炎,就会像猪头一样肿起来。我能明显的感觉到,我妈妈对我很失望,而我开始害怕了。

我其实不怎么在意我长得好看不好看。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很受欢迎的人,男孩女孩都特别愿意跟我玩。只有我妈觉得我的人生太惨了,每天都活在一个「我女儿要是不好看,她的人生就会过得无比凄惨」的恐惧里面。
因此,我会对自己的外貌和身材感到焦虑,都源自于「妈妈审视」。我妈会直接地告诉我,我品味不好,长得还黑。然后她就会打量起我的脸,看着我的眼睛,露出一个深思的表情。可能在思考,哎,这里割一刀会怎么样呢?
这让她比干涉子女填高考志愿的「传统慈母」更难取悦,因为她并没有家长对女孩的刻板印象,比如非要我留着长发、白幼瘦,这些都没有。但是,我妈对于时尚是有自我认知的,她觉得女孩应该有专属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精致,至少对于自我的「精气神」是有要求的。
我打个比方,如果我们一起去见一个亲戚,我那天没有化妆的话,她会要求我涂完粉、涂完口红再下车。如果我没有达到她的要求,她就会在情绪上表达非常大的不满。
她非常明确地知道,每个期待背后的「美」是什么样的,要求我的「好看」是要合时宜和场合的。如果我要面对大众场合,那我必须要有保持大众接受度高的「好看」;但是如果我是面对小众群体,我只符合他们的审美,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此,她不能接受我太怪异,因为我曾经觉得「脸」就是我的画板,有大几十盘彩妆,什么颜色都敢往自个儿脸上怼,恨不得在脸上画个猴子。我是很喜欢这个过程的,我个人对于「有趣」的诉求要远远高于「好看」。
昨天我妈还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接受采访的话,那你穿得好看得体一点。我口头应付了下她就挂了,跟我的朋友说,吓死了,我妈又这样子了。你看,直到现在,她对我依然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场面」上的期待。

2011年,我刚成年,我妈就急不可耐地带我去整形医院面诊了。医生用牙签在我的眼皮上撑了一下,说你看就是这个效果,我自己都没看,但我妈露出了些许满意的眼神。
那个时候,为了取悦我妈,不管什么我都愿意去做。你不就是想要我变漂亮吗?我整容吧,整吧。第一次整容时,我刚满18岁,非常草率,一切发生在十分钟之内,我就上手术台了。
如此草率的结果自然是,我第一次整容失败了。从此,我妈对我的「容貌审视」还加了句,哎,怎么会那么不自然呢?到了第二年果然带我去修复了。
第二次面诊时医生建议我再隆个鼻,看到效果图后,我妈又露出了些许欣慰的笑容。那都看到她这样了,我自然就同意了。
术后,我整张脸都是肿的。而且要养鼻子,不能戴眼镜,我眼睛就跟着瞎了三个月。我才发现原来整容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对我来说就是生活真实的不便了。那个时候我想出去吃饭,我妈就会说,「你不要出去吓人了行不行?」
但是,第二次整容又失败了,眼综合后我的两个眼角都长疤了。我妈疯了,我也疯了,我疯主要是因为「我的妈妈还没有满意」。到了第三年我回国,她带我去打了除疤针。这是我这辈子打过最痛的针,痛到我哭着挣扎,你们不要打了行吗?直到所有人一齐按着我,把针打完了。但这针根本没有效果。
那一刻我是绝望的,我整了三次容,但我妈在看我的那一刻,她还是失望的。我清醒地意识到我妈的期待跟我再无关系了,她就是她,而我只能长成我想要的样子。我就此解脱了。
时至今日,如果你们见到我妈,她静下心来回过神来看她女儿的时候,依然会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她脑瓜子又开始动,「你这个眼睛有点不自然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会说你给我打住,我不会再为了哄你高兴去整容了。
后来,我也的确享受过「美」带给我的一些东西,关注、肯定、赞美......但这都是在我开始打拳击和跳钢管舞以后,我自己对「美」这件事怎么看待了。我妈从来没给这些朋友圈点过赞,我猜想,是不是因为「她对于自己看不上的东西,是不在乎的。」
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我明确地知道我恨我妈
大概有三年的时间,我明确地知道我恨我妈。我说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你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我就来了。我人生一切的痛苦都是源自你。
那时候我刚上大二,确诊了焦虑症,抑郁症,伴随着饮食障碍。我从小就有一点症状,但不是太严重。从上大学开始,病变得特别严重,我会随时失去意识突然昏倒;一吃东西,就会呕吐或是拉稀;还有明显的自杀倾向。

我在我妈面前发过病。有一次我们去朋友家里玩,吃完饭回家路上她跟我念叨,别人家的女儿多漂亮多优秀,再瞧我今天穿得多难看。我俩就在凌晨的公路上吵了起来。等到了红灯的时候,我跳车滚在了路边。我妈在那一瞬间她吓儍了,她冲着我喊,「天呐我造了什么孽。」
我还干过更过分的事。我俩去日本玩儿,在路边发生了口角。我就把她一个人丢在马路上,她无助地快哭出来了,但我狠心地扭头就走了。
其实那时候她也在自我内疚,看到我的痛苦,这也是妈妈的痛苦。双方都在拧巴和痛苦中无法自拔,相较于母亲,女儿的痛苦都是在成长过程中累积下的,是小时候得不到照顾下身体脆弱痛苦的怨恨,是关于「妈妈凝视」的怨恨。
我曾经下定决心,我一旦出国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哪怕他们可能也会想念我,但是我不想回来了,我太痛苦了。
但我的亲弟弟给了我全新的视角,他喜欢我给他做饭,开车带他出去兜风。我意识到做姐姐是什么感觉,被人信任是什么感觉,我心中有了个牵挂的对象。我决定回国的时候大部分是为了弟弟,我就想说 OK ,那么我要开始去面对一些之前逃避的事情。
每一年我对我妈的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年我很明显地感知到是我对他的恨造成了我现在的痛苦;第二年,我知道妈妈也有她的一些局限,比如由此我弟弟说他想吃鸡蛋,我妈就煮了个咸鸭蛋,她以为这就是鸡蛋了,看来我妈的确没有当「妈妈」的天赋。「如果女儿变好看了,人生或许会更容易些。」这也仅仅只是,从她的视角里,她能给到的具有诚意的祝福。
到现在,我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妈妈的责任是养育,是陪伴,但对我来说,「妈妈」这个身份是创造。 冥想练习里,有一种练习方法叫做慈悲心的练习。这个方法是为了让我们去感受爱、去表达爱、去传播爱。我记得以前老师会在慈悲心的练习里和我说,对父母要感恩,「我的生命经由你而来」是一切感恩的源头。我后来才意识到,原来爱就是创造。爱和感恩是一体的,爱的时刻就是创造的瞬间。只有我妈生下了我,我才能去体验这个世界。这才是一切创造的开始和起点。生命的演变生生不息,周而复始。
她只是我人生中
一个叫做「妈妈」的过客
如果你仔细推敲「原生家庭创伤」这个词,会发现我们正在滥用这个词,导致丧失了自我的主观能动性。原生家庭的影响是长久性、系统性的,这就意味着,它不仅仅只有创伤这一面,它也包含了无数其他的切面。如果我们只是把它搁置在了一个原因上,那就非常片面。我在书上看到了这个词汇,我现在痛苦是因为小时候的某一瞬间,是我的原生家庭带给了我这么巨大而长久的创伤。那就是一个很偷懒的行为,如果这样去简单的定义因果关系,那就放弃了我们作为人的成长性了。因为我们不再为构建自己的幸福做任何努力了。
虽然我在内心依然非常渴望我妈跟我说声对不起,「我当时应该陪伴你的」,「我当时应该带你去医院的」,「我当时不应该挂掉你的电话」,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再纠结也没有用。
我妈也和我「和解」了,因为她现在忙着唱越剧,她收获了她想要的鲜花和掌声。11月,她要唱一个主角的大戏,售票,在大剧场里。我还挺欣赏我妈的,如果她是以朋友这个身份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我想我会对她更温柔些。

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母亲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一个母亲。但在当代,「让下一代人拥有自己生活的权利」,早已成为一个不容挑战的基本信念。而这种以下一代权益为中心的理念的结果,反过来就是越来越不尊重母亲作为人的权益。
有次我妈来广州看我。我的老师看见我和我妈站在一起,说了一句「你妈妈好漂亮比你好看很多」。我妈有点小得意,说「正常正常」。后来我又观察了下,我发现当别人夸我妈更好看的时候,我妈就会非常开心。其实一般来说妈妈不都会推诿一下说,「哎呀,那女儿大了更好看」,但是我妈会非常自信,说「对,我的确比我女儿好看!」。
当我把自己的身份从「母女关系」中抽离出来的时候,我更能理解妈妈了。她是否有享受「被夸奖」的权利?她是否有随时选择结束婚姻的自由?她面对孩子是否能发泄抑郁、焦虑、愤怒、脆弱的情绪?如果平衡不了家庭与事业,她的人生是否有权利追求名利、地位、金钱、梦想、欲望大于追求「当好一个妈妈」?
我们这代人对「生育」这件事秉持着相当开放的观念,但却不能原谅我们的父母没有当好一个理想的父母,这难道不是一种「双标」吗?我会经常自我反思这件事。
其实我也想窥探我妈的内心世界。比如,我说的这些,她的视角是什么样的。作为妈妈的体验是什么。
但这一切暂时还止于我的好奇,我还没做好准备,能处理她面对面和我说这些的情绪。
作 者 | 沈 慧
编 辑 | 王朝靖
插 图 | ins @charlotte.ager
题 图|ins @charlotte.ager
谈谈
你有过「原生家庭创伤」吗?
原标题:《我用了二十八年时间,逃离「妈妈凝视」》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