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访香港儒家陈祖为:我的课题不是反现代,是怎样面对现代
【编者按】
自上世纪初以来,反对古代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思潮的发轫,其中占据古代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更成众矢之的,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百年中,随着传统社会的瓦解,生活方式的变化,儒家文化似已成云烟往事,虽时有儒者赓续其 学、振发其旨,却难挽其颓势。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向传统价值和传统生活的转向,所谓“国学热”即其明证。一批被称为“新儒家”的学者正努力应 对社会现实作出调整,以求在古代思想中,挖掘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
儒家学说,特别是儒家的现代政治学说,在如今的中国究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是潜龙在渊,大有可为?为此,澎湃新闻陆续刊发对当代儒学学者的访谈与文章,以求展现这种社会思潮的大致轮廓,供读者讨论。
其中,身处东西交融的香港、接受过扎实的西方哲学训练的新一代香港儒家学者会带来怎样独特的视角?以下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方旭东,对谈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陈祖为,并授权澎湃新闻编辑整理首发。访谈稿已经两位审阅。
陈祖为,香港人,1960年生,从本科至博士研究生先后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BSocSc)、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MSc)、牛津大学(DPhil)。1990年起任教于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要教授政治学理论,研究领域为儒家政治哲学、当代自由主义与至善主义、人权、公民社会。在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等专业期刊发表论文多篇,著有Confucian Perfectionism: 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1999-2000年在哈佛燕京学社访问。2002-2004年、2011-2013年任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

认同基督教、儒家、亚里士多德等古典的观点
方旭东:陈教授你好,首先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学思历程。
陈祖为: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念的大学,主修政治,辅修哲学。当时我已经对政治哲学很有兴趣。后来我想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做政治哲学,是不是真的有兴趣,所以本科毕业就去伦敦政经学院读了一年政治哲学的硕士,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走这条路是对的。
我那时开始全面认真地读政治哲学的经典,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罗尔斯这些人,就发现我对古典政治哲学的观点很有同感。我念亚里士多德的Nichomachean Ethics(《尼各马可伦理学》)和 Politics(《政治学 》)的时候,发现他很多观点与我的想法很相近。比如他将政治与人的美好生活连在一起,他说城邦是要去帮助人过一个美好的生活,我就觉得这个是对的。
我就想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基督徒(现在不是),所以我对virtue(德性)、对一个社会环境怎么样影响一个人的道德和美好生活比较重视。另外本科时我也念过一些中国哲学,我就觉得儒家跟这一套也是很相似的。所以我对基督教、儒家、亚里士多德这种比较古典的、前现代的一些观点就比较认同。
后来我申请到太古奖学金,就去牛津Nuffield College念书。到牛津我就念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本来我是想比较亚里士多德和 Thomas Hobbes(霍布斯)的,后来发现太难了,就单单做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但是我只去了两年,当时香港大学就有教师位子空出来了,我就申请,他们就请我,也不要我先完成我的thesis(论文),所以我就可以回来一边教书一边写完我的博士论文。往后几年的暑假,我都返回牛津见导师和写论文。
我研究亚里士多德也不是纯粹的政治哲学史,我的论文一半是重构哲学史,另一半是用当代的政治哲学方法来探讨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能不能成立。所以是将哲学史和政治哲学方法两方面结合来做。
一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始做儒家政治哲学,都是西方为主。
方旭东:你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念的本科。我们知道,香港中文大学是由新亚、崇基、联合(书院)组成的以中文为主的学校,新亚书院还被称为港台新儒家的大本营和发源地。那么,你当时在中文大学念哲学,是不是很自然地和那些新儒家有接触?
陈祖为:我是1979到1983年读的大学,已经很迟了,并没有经历过唐(君毅)、牟(宗三)的时代。我只听过牟先生回校来讲座,但我完全听不懂牟先生的口音。而唐君毅1978年就过世了。钱穆也已经离开香港去台湾了。所以我并没有直接上过他们的课。
给我们上中国哲学史的是唐端正,而唐端正是唐君毅先生的学生,所以讲课的时候他会讲一点。另外我念了很多唐、牟的书,像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的特质》,还有他的宋明理学著作;唐君毅的也看过几本书,像《人文精神的重建》、《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人生之体验》、《中国哲学原论》这些都看一看。所以我当时对他们做什么有一定的了解,但不能说很熟悉。我当时的兴趣还是更多在西方政治哲学。
方旭东: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研究兴趣有意识地从西方哲学转向了中国方面呢?甚至用儒家思想来展开自己的研究?
陈祖为:我本来想到50岁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因为我想在西方政治哲学打下很好的基础。但是1990年我就回来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书了,有很多机会要参与学术会议。我记得好像在1992-1993年,新加坡、马来西亚就开始讲“亚洲价值”了,后来中国也讲一点。有些这方面的国际会议在香港召开,我就被委派做评论,给西方学者的评论。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问,从中国文化的角度,Asian values(亚洲价值)讲不讲得通?我的著作就开始写这些。之前都写西方的,后来就开始写Asian values,Human rights(人权)。因为外国人会来问你们怎样看Asian values,我不能说我不知道,于是这就提到我的研究计划里面了。
我记得参加了一个这样的会议,是Daniel Bell参与组织的一项颇具规模的国际性“三年计划”,为了出一本书开了三年会,书叫The East Asia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东亚对人权的挑战》),1999年剑桥大学出版的。收录其中的,是我第一篇从儒家角度去看人权是怎样一回事的文章,从1996年开始写的,所以我正式开始写儒家的东西是1996年。
这篇文章直到今天仍是我个人被引用最多的一篇有关儒家的文章,标题叫“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Human Rights for Contemporary China”。除了中国搞儒家政治哲学的人,西方研究人权的人也看的,后者要处理人权跟相对主义的时候,需要看不同的文化传统,儒家是其中一个。那一篇文章也不是所谓哲学史的角度,而主要是基于孔孟的思想来看“人权”。此文1999年出版,在那之前之后我已经开始探讨其他问题了,民主、自由、包容、社会公正,一路研究下去。
1999到2000年我有休假,就去了哈佛大学1年。那时我就决定要写一本书,一本全面重构儒家对一系列根本政治问题的看法。我以为我可以用一两年写出来,但一写就写了十多年。最后2014年才出版,Confucian Perfectionism: 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我的方法,用英文讲是inductive(归纳的),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看的。是拿一个政治概念比如“人权”,然后就问这个概念简单的公认的定义是什么。然后问儒家先秦经典在哪里可以提炼一些看法,每一次我起码都要看《论语》、《孟子》、《荀子》三本书,由头到尾,都要看相应的章节。提炼之后我就问这个看法好不好,需不需要修改,它跟西方看法有什么不同,西方的观点又是否可接受。最后提出一个我认为在哲学上可以辩护的儒家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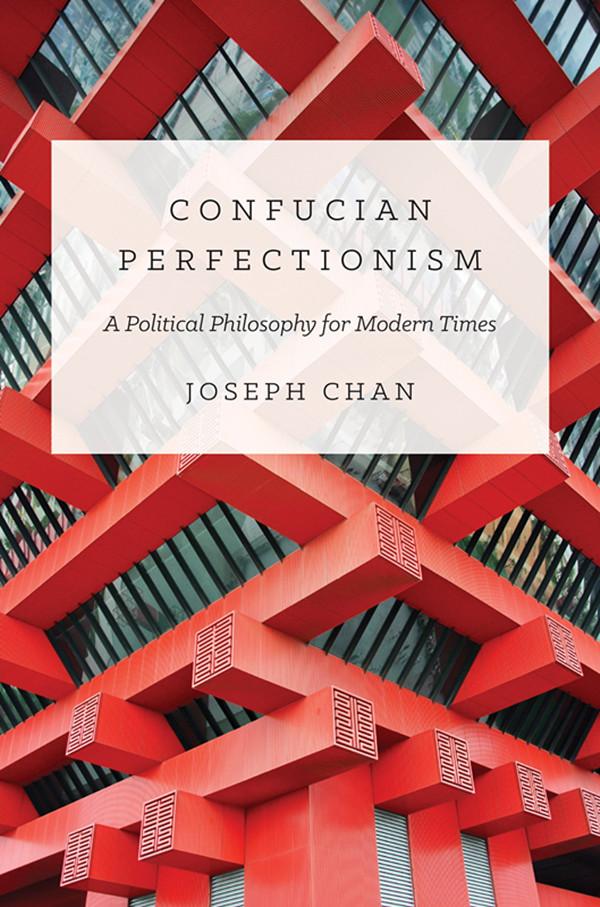
我的课题不是要反对现代,而是怎么样去面对现代
方旭东:有一种说法是:像你刚刚提到的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等,都是所谓西方价值,而儒家有自己所珍视的不同价值。那么在你看来,儒家对于所谓的西方现代价值,整体上是可以融合、吸纳的,还是根本就是两回事?
我这样问的背景在于:所谓港台新儒家,比如牟宗三、唐君毅这一代,基本上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是应该跟民主、自由、人权结合起来的,而且儒家传统里面可以发掘出这样的东西。而晚近几十年,大陆出现了以蒋庆为代表的新儒家,认为牟宗三的想法是承续了“五四”的思路、是跟在西方价值后面去跑,即所谓“西方民主自由的啦啦队”。蒋庆代表的那部分大陆新儒家会说,人权、自由、民主都是西方的价值,我们儒家讲礼、讲三纲五常,这才是儒家应该讲的东西,我们不需要西方的民主自由,我们更不需要论证我们的理论可以开出这样一些东西。你在做了非常细致扎实的概念梳理、研究和比较后,不知对此怎么看?
陈祖为:港台新儒家有两个不同的命题,我同意第一个,不同意第二个。
第一个是说,中国文化要和西方文化结合。这个结合观,我在书里也是这样讲的。但是我讲的结合,最重要是儒家价值跟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结合,而不一定要全面接受西方制度背后的政治价值。这个跟港台新儒家有一些不同。
第二个命题,是他们在《中国文化宣言》里面说,在传统儒家文化里已经有所谓民主思想的种子。这个我不同意。我认为民主、自由、人权的西方价值在儒家思想里面是找不到的。但是儒家会不会排斥这些?那就要看是哪一种自由,哪一种民主的价值,哪一种权利的观念。有一些它会排斥,有一些它不会排斥。我的任务就是选取一些好的价值表达,跟儒家的价值结合。有一些西方的价值,儒家是不会接受的,哲学上也不应该接受的,我就排除。比方说,“主权在民”。政治上平等作为一个道德的原则,不是一个制度的原则。自由看成个人的主权,或者是个人的拥有权。儒家不能接受一个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的方法(right-base political thinking)。如果这些价值是以一些很基本的天赋人权、道德人权为基础,儒家可能会对这些有很大保留。
所以儒家能够提出它自己的基础,去跟自由民主制度融合。比方我们不用讲“主权在民”,我们可以讲另外两方面:儒家的思想就是当政者要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很重要的;第二就是,当政者要获得人民的真心的同意支持,需要人民与当政者是一个互信(mutual commitment)的关系。这两个是构成儒家政治权威的基础。一个我叫作service conception,一个叫ethical relationship。这两个是儒家本身有的价值,不是西方的,它已经可以让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接受民主制度。但这两个观点会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提出一些在运作和设计方面不同的看法。所以我的书要提出一些制度设计上比较符合儒家的看法。我的理想就是这样的。
那么实行自由民主制度,是不是就是“西方民主的啦啦队”?这个名词不太好,但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自由民主是一个基本的制度设计,这是有它重要理由的,而不是因为西方的就是好的。主要是两个理由,一个是外在的理由,一个是内在的理由。
外在的理由是,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现代社会/时代,这个现代时代已经没有传统的社会制度,没有掌管一切的宗教教会、教皇,在中国已经打破了儒家的教化制度、宗族的权威、皇帝的权威,这些都没有了。经济上的现代是指市场经济,每一个人都自己筹划自己的生活,没人可以指正你。第三个方面,韦伯说现代是一个价值多元社会,没有一个独大的意识形态可以告诉你怎么样去生活。还有工业化和城市化,人们的流动、职业和居住的地方,以及旅游很多。所以自由就是一个根本上的事实,你无法不配合这个事实。
内在理由是,儒家解决不了在上的人不够有德性的问题,和贪污、滥权没有好的管制的问题。它执迷所谓“大一统”的思想,不能分权,即皇帝最高,天子不能放权。所以它解决不了精英缺乏制度上的限制的问题。它也不能接受法家用很重的刑罚和奖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背后不能接续它对道德人格的理想。我就提出,民主制度跟自由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是儒家过去想不出来的。
方旭东:那么有一些人就会说,面对这样一个“现代”的事实,我们恰恰要恢复原来的东西,如今正是被现代性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要顺着现代性,而是要逆着现代性。同样一个事实,并不一定能推出我们就应该迎合现代性,有人会说我们应该回到原始的儒家,更加fundamental的儒家。
陈祖为:我的回应比较简单。我从来不觉得往回走是一个现实上需要严正考虑的alternative(选项),因为我觉得不可能,不能走回头路。
你看中国的发展,政治上是要保守,但经济上仍跳不出市场经济,人们做什么职业、在哪里住,基本全都自由了。这个自由人有时候不会那么容易被取消的。所有制度都在推动这个社会里人的流动、个人的发挥,经济的基础已经是不能改变的了。如果我们能够回去的话是不是最好,这是另一个问题。但事实上我是觉得不能回头了,totally unrealistic(完全不现实)。
当然,我也不是说现代的都是好的,或者西方的现代性就是唯一的现代性。外国的学者比方说是S.N. Eisenstadt(艾森斯塔特),他们提出multiple modernities (多元现代性),后来杜维明也用这概念。我基本是同意的,现代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文化系统里发生的变化有所不同,面貌也有所不同。我的课题不是要反对现代,而是怎么样去面对现代。我的工作就是将古代的一些精神价值,跟现代的制度和价值连结,找一个比较平衡的modernity(现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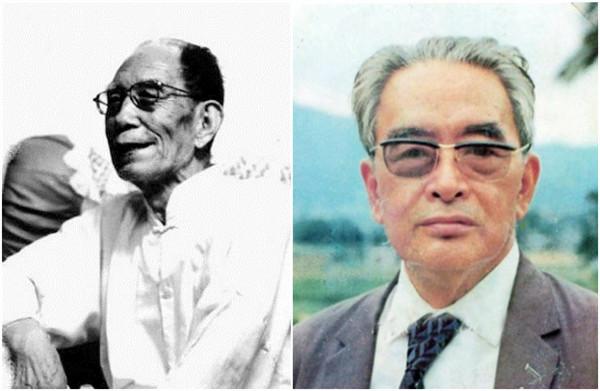
儒家注重用人的道德动机,不能接受法家式太严厉的惩罚、太多的奖赏
方旭东:我注意到你对中国儒家的一个整体上的重新思考和重构,是从政治权威开始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政治哲学问题。而且也正是在这里,儒家可能有它自己的某种坚持。
前段时间李光耀去世,中国国内学界也在热烈讨论。讨论李光耀,其实就是在讨论新加坡的模式,就会讲到威权政府。有提法认为新加坡是威权政体,而同时新加坡的人民似乎生活得很幸福很富裕,现代化程度也很高。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政治上能够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因为显然新加坡和地道的英美议会民主不一样)?西方民主制度对儒家来说是不是必需的?
陈祖为:不是必要的。我刚才说儒家政治权威有两个基础,service + relationship。我可以想象有其他的制度如果运作好的话,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所以我告诉你的是,民主不是唯一满足这两个要求的。再退一步,一个皇帝,一个很好的、贤能的皇帝,他也可以解决人民幸福的问题,又可以获得人民的信任,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说我觉得在制度上这需要满足很多条件。我觉得给皇帝一个制度,能够在制度上多一点的表达信任。因为从service来说,民主制度下如果service不好的话,人民可以不投票给执政者;从relationship来说,投票就是去表达信任的最明确的一个方法。当然有其他方法去表达,比如李光耀过世,很多人出来哭,也表达了很多的信任。
新加坡的service做得很不错,但relationship是不是真的很好呢?我觉得儒家也会对它有所批评的。有两个批评的方面,第一就是对所谓异见分子,处理的手法太凶,让他坐牢、干涉他们的反对,政治言论自由不够。真正儒家的圣王或贤能,不怕反对,也不会意见不同就让人坐牢。所以relationship部分在新加坡包含压制的元素,跟儒家的理想有一段距离。第二点是,新加坡过去二十年,他的领导产生虽比较注重贤能,但是他们的工资世界最高。按照儒家贤能的理想,用钱才能留住人是不好的。
方旭东:你的意思是,儒家认为不需要付给贤能的人最好的报酬?
陈祖为:需要好报酬,但不需要最好。你看,新加坡政府官员会认为,比如我是商业部长,我管这么多的机构,那些CEO都是年薪一两千万,我怎么可以两三百万呢?我起码要跟他们差不多,才能有地位跟他们谈判。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儒家的观点,而是法家的观点。所以新加坡的统治方法,其实有很多法家的内容在里面。
方旭东:新加坡一贯以来讲高薪养廉,这和香港也有相似的地方。现在政府官员贪污,在中国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不是说新加坡的高薪养廉,你认为是不可取的?
陈祖为:那倒不是。我是说新加坡不是高薪养廉。开始的时候是的,但现在不是了。香港政府的工资也不低,但新加坡是香港工资的三倍,现在已经不是养廉的问题了,他们要的是recognition。商界的巨头拿这么多工资,我们官员怎么能少他们这么多,我们是政府的CEO,权比较大。所以他要equal recognition,recognition of power, recognition of ability。这是merit(应得),完全不是养廉。
方旭东:我之前正好和范瑞平教授有一些交流。我们谈到一个不完全相同但相关的问题,他就讲到医院的医生收红包。范教授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医生怎么说也是社会的精英,受那么多教育,工作量也很大,他们应该得到一个非常值得的报酬。当然他并没有直接说新加坡这种高薪给政府官员的做法就是对的,但是他提出来一个讲法:儒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支持给有德者相应的地位或者说报酬的。
陈祖为:我不反对。但他这个“相应”的程度不能太离谱。我们知道儒家很注重用人的所谓动机,moral motivation(道德动机)。你要信任那些人是为人民服务的吧?如果你用这么高的薪水,那么你信任的人可能就不是出于真心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钱去做这个事情的。这个在贤能方面是有差别的。我不是说我们要给很低的工资,但是新加坡的例子是太离谱了。所以过去这四五年,新加坡人民开始不同意了:为什么要给官员这么多钱?后来政府就下调了一点。大陆则是另一个极端,完全不理物质的要求。
而我整本书的理论方向就是所谓dual perspective(两重的观点)——即现实与理想的连结。我们需要提出一些可能的办法去解决现实的问题。所以一定的惩罚、一定的奖赏都是需要的。因为现实的人不全是圣人。但如果只谈赏罚,成了唯一最重要的moral motivation,那就有问题了,那就是法家了。儒家就不能接受法家,儒家不能接受太过严厉的惩罚、太多的奖赏,因为那会改变人们道德的培养,否定儒家的道德理想。所以dual perspective就是如何能将现实的办法,放到儒家的理想里面去重新结合起来。

民主制和贤能君主制,孰优孰劣?
方旭东:刚才我有一点没有太明白的地方。你讲民主不是唯一满足好领导者要求的制度,也承认如果贤能君主能满足service和relationship两个要求也是OK的制度。所以从理论上来讲,你是不是也同意国内有些儒家学者说的,回到所谓君主立宪的思路上去?国内学者最近两年有在讲所谓“康党”,甚至还有往前推得更厉害的,推到霍布斯那儿去了。所以在你看来,民主制度是比贤能君主制度要好一些,还是说这两个没有高下之分?
陈祖为:在理想情况下,如何比较是一个很奥妙的事。很多人将贤能政治最好的状态和现实民主不太好的状态去比较,这并不公平。所以公平的比较是,都在非常理想化的情况下进行比较。
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是什么样,就是你能选出最好的贤能的人,他也是通过选举的产生。所以哪一个好一点?我觉得民主好一点。
但这都是在最理想的层面。而在现实层面,所谓的民主制度还是所谓的贤能君主的制度,都不能保证选出真正贤能的人。
方旭东:所以如此说来制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陈祖为:你说得对。我认为儒家一直以来都没有唯信任何一个制度。历史上一开始可能是禅让,认为禅让制度很好。然后发现君主世袭,继承是比较稳定的,能解决所谓承继的问题。诸如此类。这不是因为儒家有什么很大的道理或理想,儒家就是哪一个制度在现实上能够发挥效用,它就接受,它就用儒家的理想来改良。
比方说君主制度是不是一定会产生贤能呢?当然不是。很多君主都一出生自然就是太子,并不能保证拥有贤能。那么怎么办?就是要培养他,然后还有首相制度、官僚制度,辅佐他,教他提升。民主也是这样。儒家是不是尽信融入到民主?我觉得也不是。但是它在现实上觉得这个比贤能政治制度可能好一点。
所以回到我要讲的东西,怎么样比较理想、一般现实和最坏情况三方面?最好的情况就是,贤能政治和民主制度中执政的都是有贤能的人,那么相较而言民主是不是好一点?我觉得是,因为它有制度上的表达,人可以投票,同意你是贤能就选你出来,制度上的表达比较清楚肯定。一般现实就很难说了,新加坡可能比印度好,但是可能芬兰跟丹麦又比新加坡好。最坏的话,两者相较,民主应该也是好一点。
我觉得我们儒家的观点就是要在民主制度上吸收贤能的元素,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最好。
方旭东:所以你的观点是否可以概括为:以民主为基础,然后辅以儒家的理想。
陈祖为:对,这是在制度上。在价值基础上还是儒家的,制度基本上是民主的、自由的。但是制度的设计和运作,要用这些价值去补充、修改。
如果一个国家只发展经济不发展民主,不是不可能,但是很难
方旭东:你谈到了一些核心和关键的点。你认为关于比较的模型,要从三个方面来比,贤能制和民主制在最好的、一般的和最坏的情况。最后你得出的结论还是民主制度要比贤能政治要好一些。所以你最后是说,儒家要在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对它做一些修正或者补充?
陈祖为:但我不是说任何国家都要搞民主。这个要看条件。
方旭东:那么符合搞民主的条件是什么?
陈祖为:有一系列的条件。第一就是经济条件,国家不能太穷,不能太落后。太穷的话人们最关心的是生活和温饱,那么政治的票对他们来说是很遥远的。第二就是,经济发展会带动教育和公民素质的发展。第三就是,官僚制度的能力、国家管理的能力也跟经济发展有关。你有民主制度,但官僚制度非常薄弱的话,很难解决问题。另外,一般西方学界认为如果社会存在宗教的矛盾、种族的矛盾、阶级的矛盾、语言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矛盾越大,民主就越难发挥它的功效。最后就是政治文化,拥有一定的包容,能尊重不同的意见,才能发挥民主的效用。
方旭东:这里面我感觉似乎遇到了一个悖论。我同意民主是需要一些条件的,但对那些暂时没有达到民主条件的国家,它要实现这个条件似乎又不能不通过民主的方式,那么它怎么才能够达成那些条件?比如以教育为例,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很难保证教育公平。而统治者可能非常乐于让老百姓保持愚民的状态,因为那是最好统治的。所以这不是一个悖论吗?
陈祖为:我觉得这在以前是可能的。但现在,假如公民的教育程度低,国家在经济上根本不能跟人竞争。从经济发展来说,你也要给人民高学历、高能力去拼。
方旭东:但有种说法恰恰认为,中国现在之所以会有竞争力,就在于中国人力低成本的优势。
陈祖为:当它意识到低成本优势不能继续发挥作用的时候,它就需要高层次的教育是不是?还有你看东亚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就是权威政体推动经济发展,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这四小龙都是因为经济发展,教育提高,中产阶级出现,它们就有压力有需求去发展民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如果一个国家只发展经济不发展民主,不是不可能,但是很难。李光耀去世之后,可能新加坡也会走向多一点民主的道路。所以这个悖论是正常的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经济改变上层建筑。
方旭东:你似乎比较乐观,觉得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民主条件的实现。
陈祖为:经济的发展会给民主发展带来很大的推动力,但是这个压力也不一定就会变成民主。因为历史是有它很多偶然因素的,比如新加坡就有一个强人这么厉害,可以说服民众。
方旭东:但你是从理论上来肯定这一过程是必然的。
陈祖为:我不说必然,社会科学不说必然。我是说会有一个很大的tendency(倾向)。

儒家的道德教育能为化解西方民主中的冲突提供方向
方旭东:你刚才说儒家能采用民主这样一种制度,但可以用儒家的一些价值来改善它修正它。这方面具体是怎么样的呢?要修正哪些价值?
陈祖为:我觉得理念、文化是一方面,制度设计是另一方面。理念和文化方面,因为儒家不承认人天生就有政治权利。拥有政治权利的人,不应该将这个首先看成是我的一个 privilege(权益),而应该看成是一个责任。民主给每个人一票是为了能够达到民主的好的功能,表达relationship的功能,以及为了serve the people better的功能。
方旭东:你觉得应该从权利转换成为责任?
陈祖为:对,政治责任。公民是一种责任。当然有权利,但其精神是要发挥公民用自己的思考去关注公众利益。这个责任不是说我要做顺民,不是上面讲什么我就要服从什么,而是当一个好的公民。好的公民就是要知道社会需要什么,不应该将自己个人的利益放在公共利益之上。
另外就是文化政治的道德教育。我们会发现西方民主中有很多冲突和斗争,很多时候会变质,民主的过程会产生很多不好的东西。这就需要,用西方概念来说就是civility(礼貌,文明),公民文明的教育。我觉得儒家的基本道德教育,能为此提供很多很好的方向。西方的公民教育比较着重批判,着重知识的掌握,critical thinking。我觉得在此之外也需要强调civility,就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尊重你的意见。另外可能还需要compromise。儒家讲很多比如和而不同,要礼让啊、要尊重啊,我觉得儒家的道德教育是比较好的。
方旭东:我同意你的讲法。
陈祖为:细部的设计方面,我就提我书里的内容。比如下议院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上议院就是用贤能选拔,通过推荐和挑选。
上议院的设计主要是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在现实社会里面,并非人人都是有文化的人,势必有部分人比较有贤有能。怎样知道他们在哪里?有些人从事公务二三十年,他们会表现出来。所以我主要是吸收这些资深的、有政绩的人。那么一般老百姓可能认识他们,但不知道他们好不好,所以你首先要选一些能够认识他们的人。是什么人呢?三方面,第一是他们的同事、自己人,可能分属很多不同岗位,法官、外交官、立法委员,和政府委员会那些人。当然这是香港的情况。其次,去为这些人服务的行政官僚和秘书,他们是独立的,每一天跟那些资深官员工作,最清楚哪一个比较贤能。第三个是跑政治、跑公务线的记者。比方说有一些提名出来,有这样三批人去打分,“贤”一个分,“能”另外一个分,然后就加起来。过了某一个程度的分就当选。
方旭东:听起来似乎比较合理。也避免了让不了解的人去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一种尊重专家的意味。
陈祖为:这个是通才的专家,不是科学的专家、工程的专家。
方旭东:其实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政治方面的专家。
陈祖为: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儒家讲的。关于具体什么是“贤能”,我们也不能完全根据儒家的说法,要修改一下,但是主旨上也符合儒家的。“贤”就是你是公正的,你个人比较有开明的态度接受不同的意见,有原则,也有责任感。“能”就是对一般的公共事务的掌握能力,具备思考的能力,清楚、准确和到位的表达能力等。都是generic qualities。
方旭东:从你前面的表述来看,你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的确非常深入,而且已经形成一套有说服力的想法,这对大陆的读者思考儒家政治哲学会有很好的参考意义。谢谢你,这次访谈就到这里。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