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罗伯特·达恩顿:如何制造名流?
罗伯特·达恩顿在5月21日的《纽约书评》撰文,谈名流是如何产生的。

但是, 安托万·利尔蒂(Antoine Lilti)研究名流(Celebrity)的历史著作《公众形象:名流的发明(1750-1850)》(Figures publiques: L'invention de la célébrité 1750-1850,2014年8月),却在一开头就直接正中落在了这条禁令上:“绝代艳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简直就是戴安娜!”这个原本出自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Francis Ford Coppola,他是2006年上映的《绝代艳后》的编剧和导演索菲亚·科波拉的老爸)之口的评价,是个绝妙的时代错误的例子。电影本身也如此,在电影中,摄像机呈现了凡尔赛的华丽细节,这位青涩的王后,置身路易十六宫廷令人窒息的礼仪中,表现得跟克里斯汀·邓斯特演的美国青春期少女似的。


利尔蒂并没有指责《绝代艳后》是重建历史的失败尝试,相反,他赞美这部片子正是他所谓“名流文化”的表现,“名流文化”是一个历时弥久,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现象,1750年左右在巴黎和伦敦第一次扎根,现在传播到世界各地——看起来,甚至已经传播到了朝鲜,在《刺杀金正恩》中,好莱坞视野下围绕着金正恩的个人崇拜,制造了一种影像与现实之间具有煽动性的混淆,和那位法国王后的情况如出一辙。
这并不是说利尔蒂本人拥护时代错误。他是将名流作为一个历史主题来分析,他的研究非常精确且具有原创性,就像他在更早的著作《沙龙的世界:18世纪巴黎的尘世社交》(Le Monde des salons: 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2005)中所展示的那样。但是对科波拉的评论,他的确是当真的。在他看来,不仅玛丽·安托瓦内特和戴安娜王妃之间存在类同性,伏尔泰和卢梭也与猫王、玛丽莲·梦露有共同之处。这个共同之处,利尔蒂认为,就是名流。那么,名流到底是什么呢?
利尔蒂将名流概念定位在两个更古早的概念中间:一个是声望(reputation),它是由跟一个人有相对直接交往的人给出的对他/她的评价;另一个是荣耀(glory),由于做了让声名远播至超过个人交往圈子之外的伟大事迹而赢得的声誉,荣耀流芳于世长久于生命本身。类似于声望,名流也是短暂的。类似于荣耀,名流也能够单向传递到很多人那:作为名人被广大公众认识,但是他或她并不认识他们。
然而,公众对名流的认识是肤浅的。它紧系于媒体所传达的人物形象,包括印刷的小册子、粗糙的木刻版画或者电影,以及Facebook。而且,名流往往是双刃剑。它可能是令人向往的,但是一旦获得,又会产生让人痛苦的副作用,比如当真实自我(true self)因此而蒙受损害的时候,会感觉自己被公共自我(public self)所束缚。
名流这个概念可能看起来有点眼熟,因为它已经成为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以及记者最喜欢的话题。想要了解这个主题的各种变奏,可以查阅一本很实用的选集,《名流文化导读》(The Celebrity Culture Reader,2006)。利尔蒂也用到了这份文献,但是通过揭示名流的历史,他把这个主题提升到了另一个高度,他挑战读者的地方在于,他把他的论证推到了时代错误的最边缘,却没有陷入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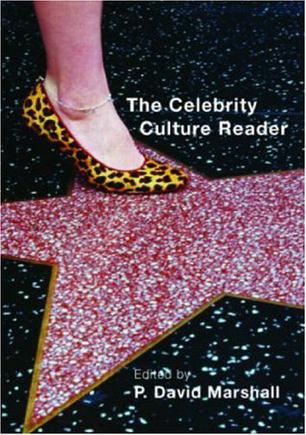
在案例研究中,他展示的是尼克拉斯·尚福尔的例子。尚福尔是18世纪巴黎的著名作家、才子,当名流这个词开始在法国被广泛使用的时候,尚福尔嘲讽地定义名流为:“名流是种优势,就是你被那些不认识你的人知道。”像利尔蒂指出的,尚福尔的这句话常常被错误引用为“名流是种优势,就是你被那些你不认识的人知道”。然而,在尚福尔这句评论的原本表达中,实际上指示了一样比认识上的不对等更为狡邪的东西。它指示出一种新型公众,他们牢牢纠缠于被文学评论、咖啡馆流言和街边小贩叫卖的廉价版画所创造出来的著名作家的形象。
在对信息的渴求中,这个饥渴的公众试图刺探进作家的私人生活,同时作家们则为保护自己残存的自我而挣扎,而这自我已所剩无几,尚福尔说的“优势”实则是个讽刺。在尚福尔说的另一句妙语中,他说“名气是对优点的惩处,是对天才的惩罚”。在他自己成为名流之后,他发觉代价真是太昂贵了。他停止发表作品,并退出公共生活,直到法国大革命允诺改变作家和公众的关系。但是大革命并没有信守诺言,在深深的幻灭中,当面临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逮捕时,尚福尔试图自杀,并且最终死于自残不医。

对于表现名流早期经验中的内在紧张而言,更不用说对于今天的名流生活,尚福尔的例子可能太戏剧化了。但是利尔蒂认为,今天的大众媒体其实也极大地增加了公众人物身上的压力,内在自我(inner self)感觉的丧失,并进而导致失去生命,通过这种方式,公众人物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之间的不一致性被放大了。在花了很大篇幅讨论卢梭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后,他援引了玛丽莲·梦露和科特·柯本(按:美国著名摇滚歌手,被誉为圣人,27岁自杀)的死亡。这个并置应被指责为时代错误么?
让我们想想今天无所不在的名流。名流这个词每天都出现在任何一份报纸上,散播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2014年12月20日的《纽约时报》,专题报道了“名流嘉宾”斯蒂芬·科尔伯特,那时正是《科尔伯特报告》(The Colbert Report,按:著名政治脱口秀节目)迎来最后一集,文章提出像科尔伯特这样的名流如何面对本真自我的问题:当科尔伯特摘下喜剧中心(按:美国有线频道的一档节目)的面具,必须在“最后一场秀”中做自己时,他如何能够应对?文章宽慰地答道:
“实际上,在舞台上他不需要比莱特曼先生(Mr. Letterman)、吉米·坎摩尔(Jimmy Kimmel)或者塞斯·梅耶斯(Seth Meyers,按:以上几位都是脱口秀主持人)表现出更多的真我,脱口秀本来就是表演性的工作,区别的地方只在于主持人是在表演自己而不是小说中的人物。他们所维持的公共角色,往往和他们私下是什么样的人没有关系。”
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18世纪,这种经验是新鲜的,那时媒体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力量,名流的观念刚刚成型。虽然名流这个词早就存在,但是它原本是另外的意思。来源于拉丁语celebritas,célébrité所指的是17世纪一种庄严的官方仪礼。利尔蒂展示了在1720年这个词的现代用法如何开始出现在字典中,并在1750年之后广为流传,这能够被谷歌Ngram viewer的数据统计所证明。(在英语中,“Celebrity”一词也是如此演化的,但是它的用法相对复杂,因为有近义词“fame”。)
但是,名流这个词并不对应于某一观念,而且名流现象也无法被思想文化史的惯常方法所把握。名流属于法国人所谓的“集体想象”。它是被全体大众所共享的精神风景中的新元素,是普通人在整理日常经验时所独创的思考方式。
利尔蒂展示给我们,以上这些经验如何聚集到一起,从而在18世纪的巴黎和伦敦开辟了一个新的概念空间。社会史学家早已研究过以下因素:城市化、增长的财富、消费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产业的膨胀,特别是印刷媒介。到处都有书籍、报纸、杂志、小册子、雕版术和海报——它们在商店的橱窗里和货架上被出售,在小贩的包裹上被展示,在建筑物的立面上被张贴,在咖啡店被传阅和租赁——只要公众聚集的地方,就能轻易看到它们。
公众、公共领域、公共意见这些概念加强了利尔蒂的论证。在当下社会科学的大量著作中常见这些概念的身影,利尔蒂尤其利用了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埃德加·莫兰、皮埃尔·布迪厄的相关著作。但是他也从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那里得到启发,塔尔德是19世纪的社会学家,他的思想被其对手涂尔干夺取了光彩,但是最近有所复苏,这多亏了伊莱修·卡茨(Elihu Katz)和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的研究。
塔尔德将集体意识的发展与阅读经验联系起来,特别是报纸的阅读。他认为,在品读每日新闻的时候,读者意识到另有人也在同样的时间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由此发展出一种共同体的感觉,即便他们并不相互认识;而且随着新闻在谈话中愈加丰满,特别是在咖啡馆里,读者发展为公众,并以公众意见的方式表达自我。
“名字制造新闻”——虽然利尔蒂没有引用这句谚语,但是在他的论述中,这句话占有一席之地。新闻围绕着知名人士产生,特别是八卦和绯闻类的新闻。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讨论大众通俗新闻的著作《感伤的谋杀》(A Sentimental Murder,2004),包括了对“交头接耳”(Têtes-à-Têtes)栏目的描述,即从1760年代开始出现在《城乡杂志》中的专题,专题中会绘制著名人士的头像,下面是对他们爱情绯闻的报道。在1770年代,因笔名“拳击教士”而闻名的亨利·贝特(Henry Bate)和以“毒蛇博士”闻名的威廉·杰克逊(William Jackson)让《伦敦晨报》和《先驱晨报》成为卖得最好的绯闻报刊,内容比今天的八卦小报尺度大多了。

巴黎没有可与之同日而语的报刊品牌,但是以写私生活闻名的绯闻传记在地下书市中流通广泛。私人生活成为公众消费的素材,出版物标示了18世纪读者的集体想象。因为取消私人/公共的内在区别,媒体让成为名流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折磨,对他们而言,他们所遭受的痛苦跟今天的电影明星是一样的。
利尔蒂毫不犹豫地将“明星”这个词应用在18世纪的名人身上,并且称他们的追随者为“粉丝”,他这么做,让人吓一跳,毫无疑问冲击了已经被确立为正统的对于历史的系统化观点。在别的历史学家定位为分期断点的地方,他看到了延续性,他把自己的论证放置在一个与众不同的时间段,1750–1850年,又跳到20世纪,好似法国大革命没有对集体意识产生决定性的改造。因此他将奥诺莱·加里布埃尔·米拉波(按:法国大革命中的活动家)与拿破仑视为同之前的卢梭和之后的莎拉·伯恩哈特(按: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名的法国演员)同样的名流,他们都陷入相同的漩涡中:被奉承,也被臧否。
这听起来比较夸张,要想论证这个结论需要多花费些笔墨。利尔蒂并没有就习常的革命阐释有所论辩——不管是1789年革命,还是1830年革命,抑或1848年革命——他并没有试图写一部关于名流的通史。相反,他只是研究这种现象的“机理”,展示各种基本要素如何在1750年之后汇聚到一起,并且持续至今。他解释说,塞缪尔·约翰逊懂得,对名声的渴望会如何占据一个作家,然后,如果意识到的话,会割断他于其他人类的联系,剥夺他的本我,最后把他变成公共消费品。即便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也审慎地感觉到,他在巴黎精心培育出来的个人崇拜——直言不讳的贵格派教友、无畏的科学家、人民公仆、“亲爱的爸爸”——让他看起来很可笑,沦为玩具,或者一个胖老头模样的小玩物。

伏尔泰非常担心他的公共形象会将他置于惹人嘲笑的境地,最为著名的就是吉恩·胡贝尔(Jean Huber)以伏尔泰在费尔奈的私生活为背景的一组画,伏尔泰最怕这个了。实际上伏尔泰并不非常适合作为利尔蒂的名流典型,最适合的是卢梭,他1750年发表的《论科学与艺术》,让他一举抱得大名,这让他不得不承受痛苦,因为他相信他自己的错误思想因此而被散播,他晚年的作品,特别是《忏悔录》和《卢梭对话录》,可以被理解为驱除这个诅咒的尝试。

在卢梭的生活和作品许多年来被做了如此众多的研究之后,仍然能够作出有原创性的解释,实属过人之处。不过利尔蒂的解释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他没有就卢梭的被害妄想症说这可以被视为偏执狂的表现,而是展示出,这传达了一种因为面对过度曝光而导致的自我嫌隙的情绪。粉丝们如潮的来信、对他肖像的海量复制、对他著作无休止地重印,跟外界的每一个接触,都向卢梭证明,公众已经褫夺了让-雅克(在据说真名叫埃尔维斯或者玛丽琳的那个站在新桥上拔牙的巨人托马斯之外,卢梭是当时唯一的名流)。

他试图通过逃离公众的方式解救自己的真我“卢梭”,但是不管是逃离到瑞士,还是到休谟那里寻求庇护,甚至是当他隐名埋姓在巴黎靠抄写乐谱维生的时候,他都发现,根本就没有避难所。不管在何处,他总能觉察到敌人躲在恩主和折磨者的面具之后,装作被他的著作感动,利用作品的坦率透明,刺探他的灵魂。
这个例子太极端?是有点。但是利尔蒂在其他的案例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元素——从玛丽·安托瓦内特到米拉波到夏多布里昂,再到拜伦、李斯特、维多利亚女王、加里波第,又跨过大西洋,到乔治·华盛顿和安德鲁·杰克逊。人们当然可以提出反例,并质疑利尔蒂的挑选,但更明智的做法是,不管是真是假,让我们先享受这趟徜徉于18、19世纪的旅行:以我们不熟悉的光照,呈现我们熟悉的这片领域。
本文原标题为“How to Become a Celebrity”,译者是贾忠贤。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