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白毛女》七十年:革命中国如何讲述白毛女的故事
与其它“样板戏”一样,芭蕾舞剧《白毛女》也是一个被重新讲述的故事。只是这个老故事的历史最长,影响也最大。
鲁艺与周扬:歌剧《白毛女》由谁创造?
探讨歌剧《白毛女》的生产过程,必须从《白毛女》的作者——鲁迅艺术学院和《白毛女》创作的组织者、鲁艺的领导人周扬谈起。

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延安创办的文艺学院,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种文艺专业。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拟定、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鲁艺的“教育方针”中,鲁艺被赋予了如下的职责:
以马列主义的理论和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材,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

周扬是左联时期著名的红色理论家和领导人,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苏联文艺理论的深厚造诣著称。1933年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率先向中国文坛介绍了苏联文学界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36年,由于在解散左联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等重大事件中工作的失误,以及对鲁迅缺乏应有的尊重,周扬被免去了党内职务,于1937年进入延安。
在延安,周扬通过较为系统地翻译、介绍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试图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很快成为延安文艺界的重要人物。1938年7月鲁艺组建了文学系之后,周扬担任了文学系主任,1940年2月担任鲁艺副院长,1943年,鲁艺并入延安大学,周扬任延大副校长并兼任鲁艺院长,1944年4月任延大校长。
“白毛女”:是人还是鬼,要看活在什么社会里
歌剧《白毛女》的诞生,经历了一个从民间传说向知识分子改造的革命文艺演变的过程。1944年5月,正尝试在小型秧歌剧基础上发展大型歌剧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发现了一篇登载于《晋察冀日报》上的报告文学《白毛仙姑》,产生了将这一故事改编为歌剧的念头,他们将这篇报告文学转交给周扬,与此同时,周扬也看到了在《晋察冀日报》工作的林漫(李满天)根据流传在晋察冀西部山区的这一民间传说创作的短篇小说《白毛女人》。周扬认可了改编这个故事的想法,决定在《兄妹开荒》、《周子山》等秧歌剧、歌剧的基础上,由鲁艺排演一个新的大型歌剧,向即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献礼。
报告文学与小说中的“白毛女”的故事大同小异,主要情节如下:
八路军解放了某山村后,工作难以开展,主要原因是该村村民和村干部都很迷信,而且确信有浑身雪白的“白毛仙姑”于夜间在村里出没。她寄居在村头的奶奶庙,命令村民每月的初一、十五两天给她上供,还说“不敬奉仙姑,小心有大灾大难”。
一天,区干部到村里召开村民大会,但村民都未到会,区干部了解到,这一天是十五,村民们都给“白毛仙姑”上供去了。当晚,区干部和村里的民兵带着武器,隐藏在奶奶庙里。三更时分,果然看见传说中的“白毛仙姑”到庙里来拿桌上的供品。区干部和民兵冲出来大叫:“你是人还是鬼?”“白毛仙姑”吼叫着向他们冲过来,区干部开了一枪,“白毛仙姑”被射中倒地,接着带伤爬起来逃走。区干部和民兵紧追不舍,后来跟着进了一个山洞,看到“白毛仙姑”怀抱着一个小白孩。区干部和民兵举枪对她说:“你到底是人是鬼,快说!”“白毛仙姑”突然跪倒在他们面前,哭诉了一切:
九年前,她才十七八岁,被村里的恶霸地主看中,地主以讨租为名,逼死她爹,把她抢走。她到地主家后,被地主奸污,怀了孕。后来地主订了亲,在筹办婚事时密谋害死她。一女佣得知后,在深夜里把她放走。她逃出地主家,无处安身,只好逃进深山,住在山洞里,并生下了一个孩子。她晒不到阳光,吃不着盐,几年过去后,便全身变白了。她以野果野菜充饥,还吃奶奶庙里的供品,顽强地活了下来。
区干部和民兵告诉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了,世道改变了。他们把“白毛仙姑”救出了山洞,重新回到了村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周扬主持了一个由编创人员参加的会议,进行动员,并亲自为这个新歌剧确立了主题:“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周扬主张,写这个戏,应该突出这个主题,应该抓住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这个重点,把两个时代、两种社会制度进行鲜明的对比。

1945年歌剧《白毛女》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出,王昆饰演喜儿,张守维饰演杨白劳。
1945年4月28日,费尽周折终于定稿的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党校礼堂正式演出。党的“七大”代表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观看了首次演出,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当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一同起立鼓掌。演出的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到鲁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三点意见: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黄世仁应当枪毙;第三,艺术上是成功的。
歌剧《白毛女》果然很快流行起来。从1945年4-5月间在延安公演开始,《白毛女》一连演出了30多场,“演出时间之久,场次之多,在延安是罕见的”。从这出戏开始公演的那一天起,剧组便不断地收到观众的来信与书面意见。提出这些意见的人,大部分从事非文艺专业的工作。在演出过程中,剧组人员根据观众的意见和建议,几乎每天都在修改。1945年10月到张家口以后,他们又对剧本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这次修改主要是突出了农民的反抗性,增加了王大春和大锁反抗地主狗腿子逼租的情节,还添写了赵大叔讲红军故事一段,意在反映埋藏于农民心底的希望。
1950年,歌剧《白毛女》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同名故事片,在全国放映,使《白毛女》成为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
不断革命:芭蕾舞剧的杨白劳开始反抗了!
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文艺的功能发生改变,在整个1950年代影响最大的叙事文体长篇小说开始退潮,戏剧——准确地说是不包括以写实为主的话剧在内的重在写意的戏剧文体如传统戏曲、西方芭蕾舞剧、交响乐等开始迅速发展。1964年京剧现代戏的成功更给这一新兴的戏剧浪潮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戏剧革命”不只局限于京剧领域,而且开始波及到其它以“写意”为主体的戏剧门类。1964年,在北京舞蹈学校将《红色娘子军》改编为革命芭蕾舞剧的同时,上海舞蹈学校也将歌剧《白毛女》搬上芭蕾舞台。
与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一样,观众在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改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最初完成的改编本基本上重复了歌剧本的主题和情节:除夕之夜,躲债回家的杨白劳与喜儿欢聚,却在黄世仁逼债下被迫自杀身亡,最终喜儿抵债被黄世仁抢走。这一基本情节受到了批评。在一次听取码头工人意见的座谈会上,一位中年码头工人愤愤地说:
要我说杨白劳喝盐卤自杀太窝囊了!当年我妈受了地主的侮辱,我就是打死了那个狗杂种才逃到上海来的。杨白劳得拼一拼,不能这样白死!
这位码头工人的观念,显然是多年的政治—文学教育的结果。杨白劳无力还债,被逼自杀身亡,这一在歌剧《白毛女》中从来没有受到质疑的的基本情节,如今变成了问题,说明时代精神的变化。改编人员以及负责人深受震动和启发,他们决定不受歌剧剧情的局限,强化阶级斗争的主题思想,进一步突出农民的反抗性,为此他们设计了杨白劳拿起扁担三次奋起反抗,最后被黄世仁打死的情节。
这一情节的修改,既适宜于舞蹈的表现,又突出了杨白劳内在的斗争性格,且加强了矛盾冲突,也为喜儿后来的报仇和反抗做了有力的铺垫。当时为了加强创作力量,应邀前去担任艺术顾问的著名戏剧家黄佐临,提议黄世仁可用手杖杀死杨白劳,认为这样一方面使这一情节更加合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对这个恶霸地主阴险凶残形象的刻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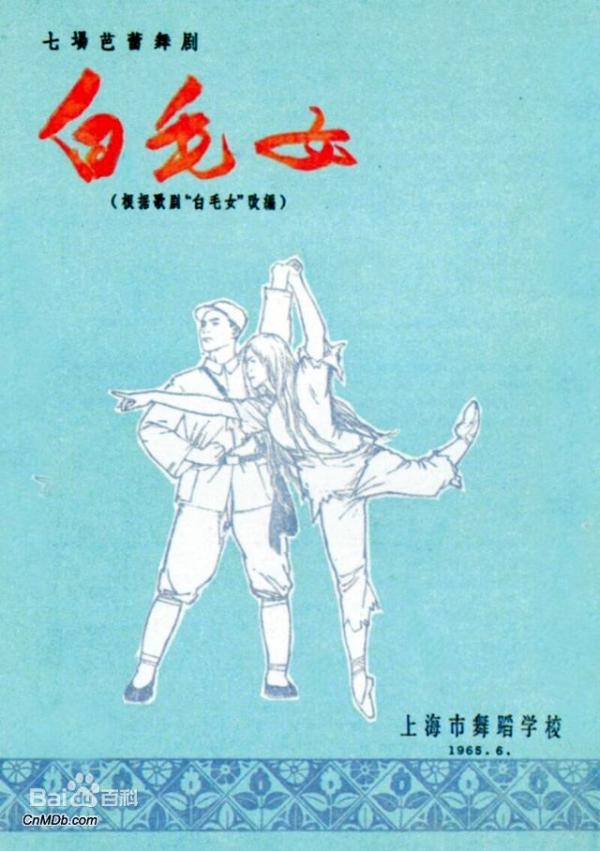
在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上,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首次公演,轰动一时。周恩来先后17次看过此剧的演出。1967年,上海市舞蹈学校在北京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演出了芭蕾舞剧《白毛女》,4月24日,毛泽东亲自观看了这个剧目,并接见了全体演员和剧团工作人员。同年,新《白毛女》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以及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一起被命名为“八个样板戏”,成为“文革文艺”的典范作品。
芭蕾舞剧《白毛女》大获成功后,上海舞蹈学校曾经这样总结经验:
我们革命派在创造这块样板的过程中,发扬了不断革命的精神,努力把剧中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去掉,使芭蕾舞剧的改革沿着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不断前进,让这颗新生的艺术明珠发出更夺目的光辉。
“不断革命”是“文革”的经典口号。在上海舞蹈学校开始改编歌剧《白毛女》时,歌剧《白毛女》的第一责任者周扬已经因为不能“与时俱进”而变成了“阎王殿”里的“活阎王”。曾经引导鲁艺艺术家们创造出“划时代”的革命主题的周扬如今已经远远落在了革命的后头。在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主创人员中,凡是主张保持歌剧基本情节的人都被视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的“代理人”。芭蕾舞剧初版中逃上荒山的喜儿的唱词:“……我等待时机,不争朝夕……”,被指为“蓄意贩卖刘氏(指刘少奇)《修养》中的黑货,宣传听天由命、取消阶级斗争的反动观念,恶毒地与毛主席‘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唱反调”,而有的编创人员试图保留大春和喜儿的爱情关系的努力,更被指控为“企图把《白毛女》复辟成‘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反动剧目’《天鹅湖》”,“令人十分恶心”……“无数事实证明:环绕《白毛女》怎样改革的问题上激烈地进行着两条路线你死我活的搏斗,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走改良主义道路从而使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白毛女”故事可能会有的不同模式
“白毛仙姑”的故事最早是一个流传于晋察冀边区的民间传说。传说的原本面貌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看到了,但我们却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素材被讲成什么样的故事。在鲁艺接触到“白毛女”这一素材之前,这一民间传说曾经被改编为报告文学、小说、歌谣等等。对于包括周扬在内的鲁艺的改编者来,如何处理这一题材,或者说如何重新讲述这个故事,显然并不象我们在贺敬之的回忆中看到的是那样顺理成章的事。其实,即使在延安文化圈中,《白毛女》也应当有不同的写作方式。
我们不妨设想由赵树理来创作《白毛女》,习惯于为党的具体政策服务的赵树理几乎肯定会让我们看到一个“破除迷信”的故事。
或者赵树理会注意到故事中隐含的爱情线索,那么,他很可能会给我们留下另一部《小二黑结婚》。描写一对青年恋人费尽周折,破镜重圆。
稍有文艺细胞的人都不会忽略“白毛女”故事中蕴涵的爱情元素。将其处理成革命与爱情的故事,在延安文学中,就有现成的例子。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描述的就是共产党的政权建立后给青年男女带来了生活和情感的解放与自由。李香香的遭遇尤其能显示新旧力量的较量对个人命运影响的程度。在旧社会李香香虽深深恋着王贵,但由于地主崔二爷的迫害而难成眷属,崔二爷借口王贵参加革命活动而逮捕了他,并欲置之死地,香香给游击队报信,救出了王贵,共产党来了以后香香和王贵终成眷属,但在游击队转移中,香香又重新落入崔二爷的手掌,正当崔二爷大摆酒席娶香香为妾时,王贵随游击队打进了村,香香“死里逃生”,与王贵欢聚。李香香命运转变的每一个危急关头都是由于“革命”和“革命队伍”的到来而转危为安、转悲为喜、转苦为乐。在这个故事中,革命和爱情是统一的。革命是爱情实现的手段,革命在爱情伦理中获得合法性。
“文革”中上海戏剧学校在总结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成功经验时,揭露了“周扬的代理人”曾经企图将《白毛女》变成《天鹅湖》的“罪恶企图”,这实际上提示了《白毛女》另一种可能的写作方式,即将《白毛女》完全写成一个发生在在大春和喜儿之间的纯粹的爱情故事。
如果在没有改造好的“五四”作家的笔下,“白毛女”还可能被处理成一个发生在喜儿和黄世仁之间的情爱纠葛。有钱人家的少爷强奸或诱奸丫鬟之类发生在社会地位不同的男女之间的情爱纠葛,是西方文学中常见的文学母题,发展出的故事模式诸如“王子与灰姑娘模式”、“痴心女子负心汉模式”、“诱奸模式”,当然还有曹禺《雷雨》式的“命运模式”等等,曾经大量出现在“五四”一代作家的视野中。
鲁艺的改编者基本上都是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因此,以上这一现代人生——艺术观念不可能不在歌剧《白毛女》的改编过程中体现出来。最初完成和试演的歌剧《白毛女》剧本,我们已经无法看到,然而在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仍能看到这种“五四”思想的踪迹。
李希凡在1967年5月19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著名文章《在两条路线尖锐斗争中诞生的艺术明珠》中转引了歌剧舞剧院的大字报的材料,揭露歌剧《白毛女》在延安排演时,周扬主张“喜儿对黄世仁应当有幻想嘛!”“幻想和黄世仁结婚嘛”,于是歌剧就出现了喜儿受辱后幻想嫁给杀父仇人黄世仁“低头过日月”的“极恶劣的情节”;在最初的演出中,怀孕七个月的喜儿误以为黄世仁要娶她,披起张二婶给新人做的红袄,在舞台上载歌载舞,表示内心的喜悦;后来喜儿在山洞里还生下了一个小孩。初稿本还描绘了喜儿生的“小白毛”在大春面前的哭叫,以显示喜儿“抚养小白毛”的“母性本质”。李希凡认为这样描写喜儿,是“肆意玩弄喜儿被侮辱的痛苦,其用心何其毒也!”“歪曲、污蔑、诽谤”了“贫苦农民的喜儿”。这些细节显然在后来的修改中被不断地擦抹,在1950年代初的定稿本中,我们已经完全找不到相关的情节了。
(本文摘编自《〈白毛女〉七十年》,原题为《〈白毛女〉——在“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之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经出版社授权转载,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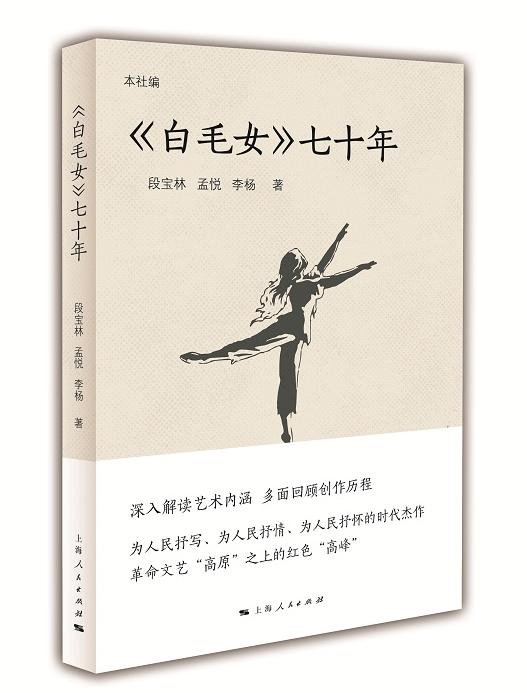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