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从章太炎到鲁迅:“疯子”和“狂人”为何走上歧路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苏州。几个月后,身染沉疴的鲁迅写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纪念这位曾经的老师。在文中鲁迅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他回忆自己在清季,“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XX’的XXX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XXX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在民初动乱的时局里,他称赞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次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高度称赞乃师的革命事迹。
然当众多章门弟子为老师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时,鲁迅却皆不参与。他与许寿裳谈及此事,说道:“旧日同学,多已崇贵,而我为流人,音问久绝,殊不欲因此溷诸公之意耳。”言下之意,自己早已不属于学界所艳称的“太炎学派”。诸多昔日同门,或身居上庠,或游走政界,受当道青睐者不乏其人,但鲁迅自己却寄居沪上公寓中,与文坛各种明枪暗箭作斗争,同时借杂文唤醒大众,批判社会之污浊,世风之浇漓。此文撰毕不久,鲁迅也因病去世。但即便如此,章太炎与鲁迅在精神气质上,甚有其一脉相承之处,此为理解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之间思想传承与变化的关键。

章太炎的“疯子”精神:独立于浊世
近代以来,西方势力大举入侵,传统社会内部积弊丛生,中国遭受巨大危机。有识之士开始质疑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与思想学说,伴随着救国救民之路的探寻,批判也日渐犀利。
例如,青年时曾饱尝家庭伦理之苦的谭嗣同痛陈:“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因此“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此外在他看来,“五伦”唯有朋友一伦最为平等,其他皆属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谭嗣同疾呼“冲决网罗”,就是希望人们打破旧的、腐朽的社会关系,培养独立、自主、大无畏的豪迈人格。
章太炎在当时也是如此。他指出:“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呼吁人们摆脱传统社会里各种束缚人心的伦理关系,摆脱种种名位与金钱的诱惑,面对浊世,虽千万人吾往矣,同时以救世之心,重建社会组织,让人与人之间能真正团结,形成“大群”,即近代民族国家,使中国步入独立富强。
但改造社会,谈何容易,不但要覃思精研,探索救国之道,还要面对各种困顿或诱惑。章太炎1903年对好友吴君遂感慨,教育原理,应“全学社中宜毁弃一切书籍,而一以体操为务。如是三年,其成效必有大过人者。”因为传统旧学,不足应世变,西方新学,又成为博取利禄的终南捷径。青年学子“知识愈开,则志行愈薄,怯葸愈甚”。许多留学日本者,“当其始往,岂无颖锐凌厉者,而学成以后,则念念近于仕途。”如此焉能指望彼辈为国尽瘁。
因此章太炎1906年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说时,特别指出他心目中的自立之道。在他看来,世间惊世骇俗之论,往往出之于疯子,而且也只有疯子,才能言行一致,不畏险阻,实践所言,世间能成大业者,多出自此辈。若是所谓的“正常人”,在种种阻碍面前,绝难百折不回,孤行己意。因此他十分愿意别人称他为“疯子”、“神经病”。世人常称章太炎为“章疯子”,便是出自这里。

在他眼中,“疯子”、“神经病”就是能不惧艰难险阻,不被名利诱惑,意志坚定不屈,具有勇猛奋发精神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艰巨的革命事业里有所作为,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独立。
而在章太炎看来,传统儒学远不能塑造出这类人物。他认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所以“用儒家之道德,故坚苦卓励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基于此,他希望“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他所谓宗教,乃是具有“依自不依他”性格的华严、法相二宗。“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同时他表彰长期被视为儒门异端的《礼记》中的《儒行》篇,发扬其近乎侠道的慷慨激越之气,提倡“知耻”、“重厚”、“耿介”、“必信”四种品德。

“狂人”的抗议与彷徨: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章太炎的文章,在清季鼓舞一世人心,他被许多人视为“革命文豪”。但民国建立之后,无量金钱无量血换来的却是吏治腐败、民生凋敝,袁世凯弄权于上,军阀政客跳梁于下,这让章氏深感失望。与老师一样,鲁迅也陷入四顾彷徨之境。
他曾经尝试“沉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想借此驱除寂寞,当此举近乎成功时,昔日同门钱玄同来劝他为《新青年》杂志撰文,鲁迅起先颇感疑虑,认为唤醒铁屋中的沉睡者而无解救之道,实非善道,但又想起摧毁“铁屋”也非不可能,于是遂答应了钱玄同。这第一篇文章,便是小说《狂人日记》。
在小说中,鲁迅借狂人之口,对当时的社会展开批判与控诉:“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他以文学意象,写出当时社会如何令人窒息,无时无刻不在压制人、摧残人,更有甚者,国民性之劣根代代相传,就连孩子也渐染其风。鲁迅将传统文化视为这一切的祸首,而只有成为别人眼中的“狂人”,才能众人皆醉我独醒,认清这吃人社会的本质。仔细分疏,可以看到,鲁迅笔下的“狂人”与章太炎眼中的“疯子”,何其相似乃尔。
面对斯景,狂人该怎么办呢?在小说里,狂人对周围亲友苦苦相劝,劝他们别再吃人,可是没人理睬。更有甚者,吃人成性的人感到气愤,抿着嘴冷笑。这时他大哥高声呵斥道:“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没有人搭理狂人,全当他是一不正常的疯子,因此他只能期待“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呼吁“救救孩子”。
然而鲁迅并未一直让狂人“狂”下去,在小说开头,他说狂人“已早愈,赴某县后补矣”。狂人不再“狂”,他没有狂到推倒一切的地步,而是融入了吃人的社会,成为其中一员,这体现了鲁迅对中国前途的悲观。在他看来,“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大多数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在《野草》中,鲁迅援引裴多菲的诗:“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说:“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白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飘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他知道改造社会,绝非易事,国民性中的劣根,存在久矣,个人面对“铁屋”,结局往往是头破血流,只是因为或许还能为下一代创造光明,所以不得不努力奋斗,与恶同归于尽。相较于胡适“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鲁迅撰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系列著作,悲凉之中蕴含深刻,那种强烈的批判力透纸背,直入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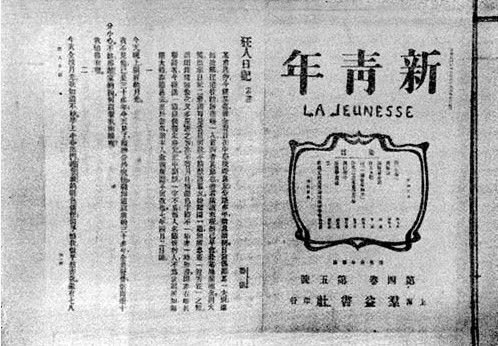
改造社会之道:鲁迅与章太炎之间的歧路
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社会组织日渐解体,许多青年学子与知识分子聚集于大城市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较之往昔,已大不相同。当时一位青年人写道:“在街上,红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灰色的,高级人群的海。这都市的繁华面,行走着威风凛凛的官僚政客,挺挺的大腹贾,蛇头鼠眼的密探和杀气腾腾的警察与宪兵,还有,贵族的公子,小姐妖媚的眼睛。”而另一面,“这都市的贫民区域,有了听不清的啼饥的孩子,有了无数颤颤号寒的老妇。畏缩,蹑足,从门缝里出来了年轻卖淫的姑娘与母亲。”因此他称都市为“动乱的天堂”。
对这一幕鲁迅也深有体会,因此在1920年代末期,他开始宣传左翼文学,翻译了许多苏联的文学理论著作,提倡文学应写出普罗大众的喜怒哀乐,批判当权者对民众的压迫,号召广大民众起身反抗。后来“左联”成立,鲁迅被青年左翼作家奉为“旗手”。他晚年的作品,多为揭示与抨击社会权势阶层及其附庸文人的诸丑态,鲁迅的杂文,被人视为匕首。当“狂人”找到了“信仰”时,他开始与整个旧社会作毫不留情的斗争。

章太炎晚年也耳闻目睹世风时局种种乱象,但他不像许多人那样,将这些现状归结于中国传统不适应西方政治与文化,进而开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视此为中国历史演进中各种消极因素交织而成,在今日凑合呈现的结果。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晚年力倡“修己治人”之学的重要性。在章太炎看来,今日提倡“修己”之学,实为乱世里的救急之术,而非借此修身成德,优入圣域。因此他一反晚清之时对王学的批评,开始表彰后者的积极作用,认为服膺王学能使人一介不取,身处污世而有所不为,此乃居于今世所最应提倡者。此外,他揭出《大学》、《儒行》、《孝经》、《丧服》四部经典,在文章与演讲中对之极力宣扬。希望能让人们行有操守、刚毅英勇、超脱流俗,同时不忘故常,以礼持身,从敬宗收族出发,循序渐进,臻于对民族国家的热爱。而在“治人”方面,他主张应从中国历史本身的演进中来认识现状,并且目睹当时国步维艰、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因此在许多场合提倡读历史,视此为致用之道。他主张读史应识大体,熟知历代政治社会变迁,以及疆域沿革梗概,通过对于历代史事的稔熟于胸,能够从中吸取足以为当下所借鉴与取法之处。
就这样,章太炎与鲁迅在对社会认识与解决之道上产生巨大分歧,他们后来基本已不相往来,原因就在于此。二人孰是孰非,尽可平心商榷。但“疯子”与“狂人”的精神,却永不磨灭。当面对世俗的漠视嘲讽、无人理解时,当身处困境而四面碰壁、蹇蹇独行时,是深感无助而气馁,还是不畏险阻而奋发,先哲精神不朽,愿与世之有心上进者共勉。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