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常识》之外的潘恩:“世界公民”为何被遗弃
一度显赫,身后寂寞
1809年6月9日,在美国纽约州长岛,初夏的天气闷热难耐。一支由十几个人组成的送葬队伍,用平板车拖着一只破败的大木盒子,沉默地前行。队伍里没有牧师,领头的是死者的房东——一位白人妇女。可怜的死者于头一天早晨在长岛南端一个小镇去世。
由于亡者生前冒犯了该地的贵格会教友,本镇墓地不接纳他,于是有了这支七零八落的送葬队伍。几天后,在他的墓穴旁,妇人竖起一块石碑,上面仅有几行小字:“托马斯·潘恩,《常识》的作者,卒于1809年6月8日,终年72岁。”

潘恩1737年1月29日生于遥远的大洋彼岸——英格兰东部小镇塞特福德。由于家境贫寒,他只读过几年语法学校。18岁开始,他离家谋生,做过远洋水手、税吏,开过小酒馆。几十年过去,眼看快到40岁了,他仍然籍籍无名,一事无成。1774年底,他怀揣着本杰明·富兰克林(当时身在英国)的介绍信,渡海前往新大陆,尝试自己的运气。结果在殖民地的独立事业中暴得大名。
潘恩追随时兴的技术创新之风,一头钻进铁桥实验。1787年4月,就在彪炳史册的费城制宪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月,他包裹好铁桥模型,乘船前往欧洲。与当年他来北美尝试运气不同,这一次,他的航向相反,命运女神也不再垂青。他本可以在大陆会议奖励给自己的一座农庄里安度晚年,结果却在遥远的欧洲大陆卷入又一场大革命。一开始被奉若圣贤,堪舆国是,最后却深陷牢狱,受尽毁谤。
1802年,他身心疲惫地回到北美,老之将至,孑然一身。农庄已经面目全非,世风渐变。风烛残年,陪伴他的是一位法国妇女及她的3个儿子。他们与周围的人们很难相处,最后只得移居纽约。
终其一生,托马斯·潘恩奔走于英法美之间,横渡于大西洋两岸。四海为家,居无定所;一度声名显赫,最后却少人问津。人称其“世界公民”,半是赞许,半是揶揄。
以笔为旗:有史以来最好斗的人
潘恩一生写下大量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常识》。如果单从《常识》看,很多人无法理解,这样一位对大西洋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为什么在晚年得不到人们最起码的尊重。“古来圣贤皆寂寞”,然而潘恩的问题似乎不在于此。实际上,如果在《常识》之外,再读一读他的《美国危机》、《人的权利》及《地权正义论》等著作,就会稀释人们心目中因《常识》而带来的简单化、符号性的形象,还原其思想底色,为理解潘恩的悲剧下场找到某种思路。

《常识》通篇没有一处常识,而是充斥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反叛言论。常识通常是平实的,但《常识》的语句具有很强的煽动性。事实上,《常识》最初的书名并非Common Sense,而是Plain Truth. 在这本小册子里,除标题外,Common Sense这个词语只出现了三次。总体上,潘恩并不是在表述某种现有的常识,而是用强有力的语言,将独立意识包装成常识,使其深入人心。《常识》的读者甚众,但读者中并非全是拥趸者。甚至一些革命者也反对《常识》,约翰·亚当斯晚年说此书“大而无当”,他不喜欢潘恩提倡的激进民主方式。对于《常识》的成功,古文诺·莫里斯不无揶揄地说:“一个不过是从英国来的冒险家,没有财产,没有家眷或亲属,甚至连英语语法都一窍不通的人,居然会高踞这种地位。”
如果说《常识》点燃了独立的火焰,那么可以说《美国危机》帮助这星星之火抵御寒风,形成燎原之势。战事即开,大陆军处处被动,殖民地人对独立的前景十分忧惧。1776年圣诞节前夕,潘恩在费城再次拿起他那生花妙笔,写下第一篇《危机》,开篇留下千古名句:“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文章很快被送到30英里之外特拉华河对岸的大陆军前线。两天后的圣诞节夜,华盛顿集合部队,中士在冰天雪地里向冻得发抖的士兵高声朗读这些文字。士兵们听罢神情凝重,静静而有序地集结好船只,趁着夜色渡过特拉华河,成功地奇袭了英军营房。
《美国危机》不止一篇。在历时7年的独立战争中,潘恩共写下13篇论美国危机的文章。在《美国危机》第三篇中,潘恩继续批评贵格会的“和平主义”。但是,政治上的犀利风格一旦挪用到宗教上,伤害的将不仅是利益,而且是感情。潘恩的这种宗教观在他后来的著述中表现得更加肆无忌惮,应该说,在宗教问题上树敌过众是他的悲惨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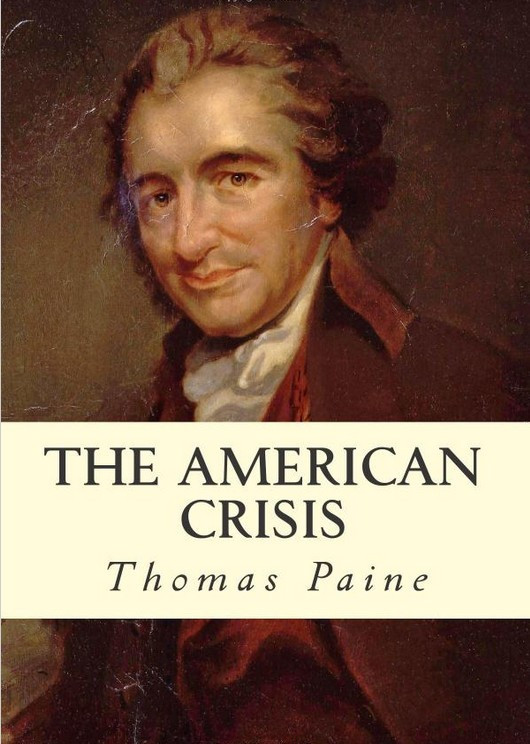
《人的权利》是潘恩与伯克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战的产物。1787年8月,潘恩带着铁桥计划来到伦敦,受到英国下院议员埃德蒙·伯克的接待。1789年7月14日,法国爆发了大革命。身在巴黎的潘恩,将这一重大事件写信告诉了伯克。次年,伯克在议会演讲基础上,发表小册子《法国革命沉思录》,批评法国革命。潘恩读到这本书后,表示“对伯克先生的做法深感震惊和失望”,着手写文章批驳,取名《人的权利》,副标题是“答伯克对法国革命的攻击”。
潘恩将《人的权利》题献给美国总统、自己的老朋友华盛顿。但是华盛顿似乎并不领情。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努力改善与英国的关系,在他看来,《人的权利》中对英国君主制度的批评对此不利。1792年2月,潘恩发表《人的权利》续篇,副标题是“原理与实践相结合”,这一次他题献给曾经赴美支持独立战争的著名的法国贵族拉法耶特。英国首相皮特扬言要逮捕他。伦敦的一些民众抬着潘恩的蜡像游行,全身插满针头。1792年9月,在好朋友的催促下,潘恩草草收拾行李,在前来抓捕的警察眼看就到时,匆匆赶往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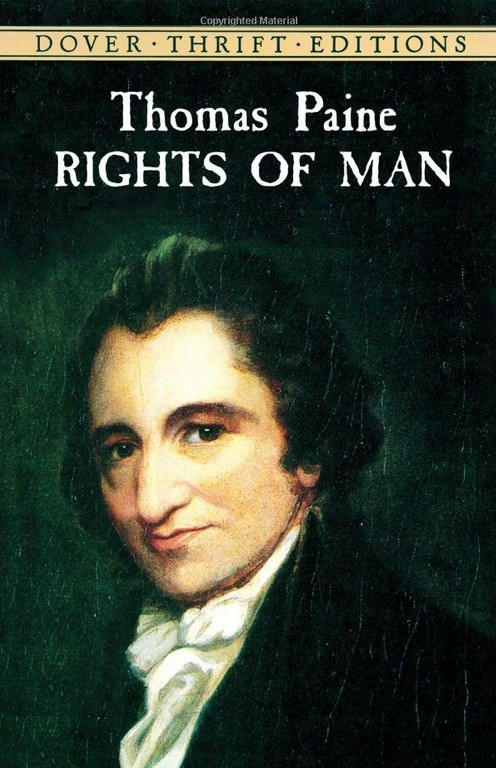
潘恩到达法国加来码头时,受到热烈的欢迎,有人喊“潘恩万岁”。他来到巴黎,很快出现在新诞生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国民会议中。他发表演讲,主张人的权利,赢得了革命者的称赞。他不会法语,茫然四顾,不知道大家在吵些什么。革命政府禁止外国侨民担任公职。1793年圣诞节,潘恩被雅各宾派关进卢森堡监狱。一个月后,罗伯斯庇尔下台了,潘恩终于在11月份走出了监狱。1795年2月22日华盛顿生日这天,潘恩致信华盛顿,发泄心中压抑已久的愤怒:“你看到自己当上了美国总统,而我却在法国成为阶下囚。在这种情况下,你竟然袖手旁观,忘记了你的朋友,缄口不语。”一年后,潘恩竟将这份《致乔治·华盛顿的信》在美国公开发表,引起轩然大波。对华盛顿的攻击使潘恩在多数美国人中名誉扫地,很多人叹息:革命的“剑”与“笔”分道扬镳了。
1793年12月28日,经过被解除国民议会公职后一个多月的闭门写作,潘恩完成了《理性时代》。1794年,该书在美国出版,潘恩将它题献给“我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同胞”。与以往的《常识》、《美国危机》等著作不同,《理性时代》并不贴近紧迫的现实问题,而是针对一般性的宗教问题。潘恩根据自己对启蒙运动的理解,以及自己在法国革命中的经历,鼓吹理性,驳斥《圣经》中关于“感孕”、“神迹”、仇杀的记录,甚至诋毁圣徒,批判宗教组织。
这部著作触动了人们最敏感的信仰神经,在美国再次引起轩然大波,人们指责潘恩堕落成了无神论者。实际上,潘恩对宗教的理解和对理性的鼓吹,与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一致的;只不过,他将这种思想移植到新生的美利坚时,遇到了语境障碍。在那两场“姊妹革命”中,正如劳德·阿克顿深刻指出,“法国人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是革命的理想,而不是他们的政体理论——是他们一刀两断的气魄,而不是修修补补的艺术。”古维诺尔·莫里斯形象地批评法国人“以天才人物取代理性作为革命的指导,以实验代替经验,在闪电(lightning)和阳光(light)之间,他们更愿意选择前者,也正因为此他们一直在黑暗中摸索。”
《地权正义论》出版于1795年,这本关注穷人处境的著作是潘恩最后一本小册子。潘恩指出,在美利坚,失去土地的人应该得到生活保障,但这是他们的权利,而不是一种慈善。他用较大篇幅计算了土地的各种收益及其分配方案,但显得粗略、理想化,并带有激进色彩。潘恩承认:“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就各种可能性做充分的探究,从而以尽可能大的确定性做出推算。”潘恩对自己心目中美好社会的设计能力,似乎远远低于对社会制度的抨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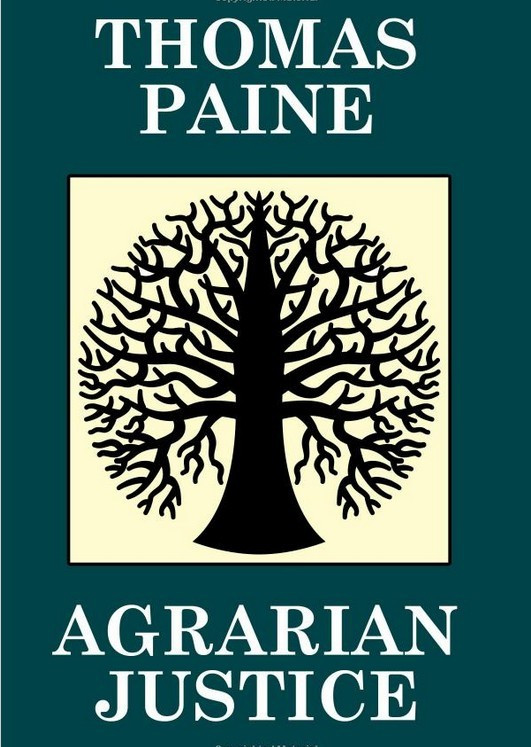
贡献卓著,为何被遗忘和抛弃?
潘恩的生平与著述都是不平凡的,至少在他那个时代如此。但对于很多读者来说,潘恩身上最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这样一位对美利坚合众国建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为什么在晚年乃至后世被人遗忘和抛弃?今天的人们又应该如何评价潘恩的是非功过?
潘恩是一位激进的斗士。他出身低微,对于社会等级制度有着天然的抵触。他有一句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潘恩个性倔强,四处树敌。早年在英国做税吏时,他经常与上司争吵,他的收税记录是一笔糊涂账。到美洲后,在《宾夕法尼亚杂志》做编辑时,与观念保守的老板艾肯特频繁争吵。当听到有人说“潘恩是有史以来除马克思之外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小册子作家”后,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接着说:“他是有史以来最好斗的人。”确实如此,他是这样好斗,以致与人权之外的一切权力为敌。他与伯克论战,与华盛顿吵翻,与前来拜访的拿破仑不欢而散。他以《常识》反对常识,以《人的权利》反对政治传统,最后以《理性时代》反宗教传统——他的著作几乎构成了一场对十八世纪社会的全面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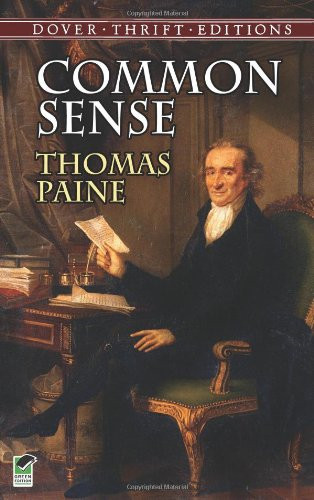
潘恩是一位出色的政治鼓动家。他的小册子之所以畅销,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犀利的言辞与独特的文风。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指出:“潘恩之所以独一无二,就在于其开创了一种新式政治语言。”美国当代历史学家、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索菲亚·罗森菲尔德指出,潘恩高度创造性地使用了“常识”这一术语。他融合了苏格兰常识学派的观点,即普通人能够对政治问题做出判断。19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小莫拉姆评价说:“潘恩显然远不足以跻身于伟大政治思想家之列。……潘恩并非哲人,而系宣传家,其力量之源泉在于以通俗语言承载激进政治思想的卓越能力。”
时势造英雄。潘恩成功地将启蒙思想、殖民地困境与自己作为通俗小册子作家的鼓动才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不羁文风结合到一起,在当前的危机中一举成名。但是,危机过后,百废待兴之际,当初鼓动反叛的人变得不合时宜了。实际上,潘恩的确一度“告别革命”,他的铁桥计划最后在英国获得了成功。他本可以像富兰克林、华盛顿那样选择激流勇退,安享晚年,但是,由于机遇的不同以及个性差异导致的不同的选择,特别是在宗教问题上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终至于众叛亲离、潦倒而终。
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众叛亲离经常是时代先贤的难免结局,卢梭如是;荣华富贵通常也并非仁人志士的初衷,华盛顿如是。然而,盖棺定论,潘恩的成功主要不是作为思想家,而是作为作家;潘恩的落寞主要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世道人心,而是因为他的话语失去了往日的语境。潘恩是“永远的反对者”,是人间与天堂的“双料捣蛋”。他不竭的斗志为美利坚的独立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但独立后的美利坚没有为他提供持久的舞台。潘恩的身世不是个案,它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某一类英雄人物的历史意蕴;《常识》不是潘恩的全部,他的其他言行可能会淡化读者心目中的某种神话。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