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劼人诞辰130周年|“狐狸型”作家与自然主义
李劼人,这位民国报刊主编,法国自然主义文学译者,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似乎被遗忘了。更为准确的说法是,他被放进自然主义文学的抽屉里,紧接着就被遗忘了。这个自然主义抽屉,自然是不存在了,乃至于说,它所附属的整个家具都清理出了房间。真实情况要惊心动魄得多,也更令人费解得多。在历代文学史编撰者的书中,李劼人,要么直接被忽视,要么只是被看作一个次要的人物。当然,不乏一些翻案者,如曹聚仁、刘再复等人,刘再复甚至将《死水微澜》视作(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小说史中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但放在整个文学评价体系,对李劼人的重张并不太成功,且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证明和想象。在近四十年的学术研究中,李劼人自然得到了某种公允的认知,他被看作是巴蜀世界或者四川世界的重要作家,地域性、时期性被着重强调了出来,可以说,关于李劼人的真实想象似乎还没有出现。很多问题仍然有待解决。首先,浪漫主义在中国有存在的踪迹,现实主义也有,象征主义也有,甚至古典文学在中国也有存在的踪迹,为什么自然主义凭空消失了?其次,以自然主义命名李劼人的文学是否就已足够?最后,为什么李劼人从文学史中“消失”了?

李劼人
关于李劼人的被遗忘,赵毅衡有一段评价,或许可以作为重启李劼人想象的开始。“李劼人之所以被遗忘,对他的反对或批评,都无法成为定论,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贯穿始终的主张,也没有前后一致地努力。三部曲的耀眼光泽,淹没在大历史的话语洪流之中,反复修改,只能越改越死板。好在妙手偶得一气呵成的杰作《死水微澜》不可能被改动以迎合时代精神。这不仅是李劼人的大幸,更是中国文学史的大幸。”不过,赵毅衡言中的李劼人与文学史的互动关系反而不是我比较关注的,我最注意的是,赵毅衡说,李劼人始终无法贯彻某一种主张。在中国文学史的视角下,主张几乎是应有之义,鲁迅有,莫言有,某个淹没无闻的小说家也应该有,此外,主张又联系着立场、现实感、态度、叙事等等。需要注意的是,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主张,常常类比于古典文学的讽喻,毫无疑问,在文学史书写中,前者几乎取代了后者,但从实际层面上来看,前者只是占据了后者消失后的那个空白。回来说,言下之意,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主张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作家怎么会没有主张呢?怎么独独李劼人没有主张?

《死水微澜》
带着这个疑问,我找到了新的资料。在《关于李劼人的文学》,海谷宽写道,“我越发感到,他(李劼人)的思想并不是向心性的,而是扩散性的。”为了佐证扩散性思维,海谷宽还特意说,中华民族对事物的反应并不十分敏捷,这个民族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实现其目标。内在传统如此,想改变也改变不了。姑且不论,李劼人与此类民族潜意识是否有前后关联,且说李劼人的扩散性思维。从具体的阐释来说,海谷宽显然较赵毅衡更进一步,当赵毅衡还在商讨李劼人和文学史的互动时,海谷宽已经思考着李劼人和共同体想象的关系。对比之下,赵毅衡的造像是教课书上的李劼人,海谷宽的造像是生活与历史中的李劼人。不过,海谷宽无疑与赵毅衡的说法遥相呼应。实际情况不单单是,李劼人没有主张,他选择了无主张的策略,实际情况更是,李劼人本来就没有主张,他的思想里没有一个“心”。海谷宽所言的心,其实是一个锚点,它便利文学书的书写,便利影响与往来,可它并非真正的便利,这就过渡到了心的另外一层意思,它是一个被造的心。李劼人的无心,恰恰就是一种心,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心。
在某种叙事里,有心无心构成了一组平衡和矛盾,有心的犹如刺猬,无心的犹如狐狸,这个区分肇始于阿基洛科斯。在《刺猬与狐狸》中,以赛亚·柏林对此有详细的说明,“一边的人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另一边的人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连,甚至经常彼此矛盾,纵使有所联系,亦属于由某心理或生理原因而做的事实层面的联系,非关道德或美学原则……”在这个说法中,李劼人就是一只实打实的狐狸,他站在了莎士比亚、蒙田、巴尔扎克的行列之中。李劼人是一只狐狸,但李劼人的毛色、记忆、饮食习惯显然不同于伯林所列名单里的狐狸们,他是一只东方的狐狸,他狡猾到从来不透露自己的立场,并且避免了各个立场在系统中的冲突,这一点或许只有莎士比亚可以比拟。
如海谷宽所证言,李劼人随着历史的摆动而摆动,他尽可能地取消了自己的主观意识,以及任何可能的主观意识。他无意书写革命,也无意成就某段叙事。在所谓三部曲中,《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李劼人记录了1894年到1911年的历史,其最独特之处在于,李劼人从未像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小说那样,宣示某种倾向,或者剖析某种意识,又或者沉潜进某种精神世界。这在李劼人并非写作意义上的限制,恰相反,他非常接近某种具体的结果,他使用了非常之多的宣传材料,比如上谕、政府电传、权臣电奏乃至于立宪派告示、保路同志会传单,他的角色中有袍哥,有解放了的女性,集结了所有势力,但他从未代言,甚至压抑着这一切的传统。
换言之,李劼人仅仅写一个人,写被时代淘汰的人,写与时代抗衡的人,他默默不宣示地写。单纯从袍哥这个角色来讲,在历史语境中,辛亥革命前的袍哥多结义,辛亥革命后的袍哥大多作势混世。在《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中,王笛又将袍哥放入一个社会系统之中。袍哥的首领可以掌握生杀大权,任意判决和执行死刑,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愈演愈烈。李劼人选择避开此类中观空间,他要么聚焦于微观空间里的人物,其举动和心思纤毫毕现,栩栩而来,要么聚焦于宏观空间里的转景,诸如街景、市集、告示,有时候它伪装进入人物的对话中。譬如《死水微澜》中的袍哥罗歪嘴,李劼人对其袍哥身份甚少提及,言里言外也并不把他当袍哥,罗歪嘴随情节展开,时而狡猾,时而浪漫,时而仗义,时而脆弱,并不拘泥。
举《死水微澜》颇点睛的一个片段作为例证。这里可见罗歪嘴的彷徨、谨慎、脆弱,相反邓幺娘(先嫁蔡兴顺,后随罗歪嘴,后依顾天成),也即蔡大嫂,却独有一种强悍与坚韧:“罗歪嘴日间也常出去干他的正经事。一回来,把鸦片烟盘子一摆,蔡大嫂总自然而然地要在烟盘边来陪他。起初还带着金娃子坐在对面说笑,有一次,她要罗歪嘴教她烧烟泡,竟无所顾忌地移到罗歪嘴这边,半坐半躺,以便他从肩上伸手过去捉住她的手教。恰这时候,张占魁、田长子两个人猛地一下掀开帘子进来。罗歪嘴便一个翻身,离开蔡大嫂有五六寸远,而她哩,却毫无其事的,依然那样躺着烧她的烟泡,还一面翘起头来同他们交谈。”这位行侠仗义的袍哥,到了尝到爱情的境地,反而躲躲闪闪,只等到众人都原谅,他才大着胆子起来。据说,罗歪嘴的原型是邝瞎子,彼时儿子李远岑被票匪劫走,邝瞎子苦心营救,四处打点,李远岑这才安生地回来。事后,李劼人把李远岑拜寄给了邝瞎子,邝瞎子的真实身份就是袍哥,宪兵司令田伯施底下的谍查。
“时代,尤其是积变的时代,一经过去了必定要留下许多渣滓。这些渣滓有的漂浮在社会的上层,一眼便可以看出;有的沉坠到社会的下层,如果不细心经意的去发现,便永远不会为人所察觉;有的还会随着时代的巨浪漂流下来固执的存在着而披上一层美好的外衣……”,李劼人的蒙彼利埃大学(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校友周太玄在为其《好人家》做序时写道,“在那上面,如果单是鉴赏的话,可以使人换替的感觉到清新沉郁、妩媚、丑怪,因为都是真的,所以总可令人感觉有一种美……没有哪个逃得脱时代的点染,只是有是否老漂停在洄漩微涡上之分……”周太玄的说法将看似微末的角色刻画,或者人物想象,和李劼人的内在精神勾连在了一起。无论是《死水微澜》还是以保路运动为核心的《大波》,它们都放弃了事件的能动性,死亡、革命、爱情都没有一个特定的起伏和情节性演进,这些主题,以及围绕它们的动态世界,都颇为微妙而开阔,但绝没有一种事实和哲学意义上的清晰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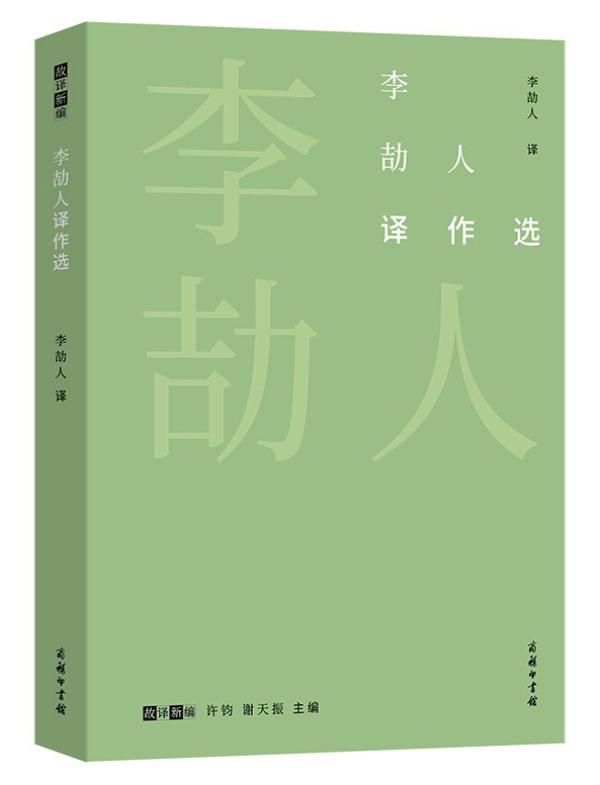
《李劼人译作选》
此处,我们正好可以说明,李劼人的文学观念绝非自然主义,尽管他翻译了大量的自然主义著作,包括《包法利夫人》《萨朗波》《小东西》,李劼人的叙事其实是中国式的,也是东方式的。不过通过某种方式的转介,以自然主义称李劼人或许颇为恰当。他的写法颇为简单,多转述,多挪用,多换场,几乎是媒体写作在小说世界的化身,而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自然主义的呈现法则,但李劼人显然抛弃了自然主义最重要的一面,也就是对于社会现实境况的直接书写,尤其是对病理的热切关注。李劼人对自然主义的理解非常标准,法式自然主义,这不同于同时期大多数人多认同的日式自然主义,法式比日式更宏大,更容易操控,但却与同时期大多数文学家对文学的进步性、情感主张的想象不同。值得庆幸的是,李劼人所支持的是后期自然主义者作家,“梅塘”作家集团的于斯曼。他援引于斯曼的话说,“至于小说,若果有力量,就应该把分开的两部份,如灵魂的生活和身体的生活,拿来熔做一片,并且使它在发展中经过反抗和争执,乃至调和。以此就应提出一句话,即是除了追随左拉所掘的那条深径外,尚需在空间照样画出一条路来…以便造成一个空灵的自然主义,这更可以自矜,更完全,更有力了。”作为一个前自然主义者,和皈依虚无的作家,于斯曼无疑照亮了李劼人的文学世界。而李劼人对自然主义的择取,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狐狸属性。
这只东方狐狸,在四十余岁的年纪,抽出了二十余天余暇,写下了《死水微澜》,他没有借此辉煌,但又在文学宗师的道路上又近了一步。后来他越来越意识到,《死水微澜》在成为名作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篇文学真空。不巧的是,后来的世界从未将此真空填补掉。李劼人被遗忘了,不如说,他所留下的真空牵引他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在那里,权力系统不再值得提起,嬉笑怒骂也变得无所谓,在那里,只存在世代不易的人与故事。每到日暮时分,你都会在不远处的路边,看到这样一只狐狸。这就是李劼人的故事:
“我开始写作的时间是一九一二年,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当时四川有个政党叫共和党,是劫夺辛亥革命成果的,很反动。这一年他们为了拉咨议局的选票,就包园(原少城公园)办游园会,请人进去游览,不买票,还有招待。我记得请吃橘子的地方,还挂上一幅大旗,写着维持大局四个大字,十分牵强。当时,革命后不久,统治阶级还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压制进步思想。成都一部份进步知识分子,就办了一个《晨钟报》,专门评论当局。我一直对孙中山先生很羡慕,对革命抱有很大希望,喜欢看《民报》《神州日报》,和地方报馆编辑也认识,大家也谈得来。报馆鼓励我写文章。我平时爱看林琴南的小说,看多了就引起写作兴趣,只是找不到题目、内容。遇到这个游园会,报馆叫我去采访。我去了,很感厌恶,就以《游园会》为题了一篇小说,人和故事是虚构的。我写了一个自作聪明的小市民跟刚进城的乡下人,两人游园,一路走一路批评,一路闹笑话。通过两个人的对话,以讽刺当时政治。这篇小说有一万多字,分期在《晨钟报》上刊登。刊出来的第一天,我非常兴奋,想搜集一下反映,就拿给熟人看,熟人捧我,说这是空前绝后之作。我又跑到街上挂报纸的地方,看看读报的人多不多,一看,有七八个人,有的看样子还很欣赏,这一下就给了我勇气,认为群众批准了。从那时起,我就立志当作家,但是到现在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还是没有成功。”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