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试图告诉人们:历史并未终结
【编者按】4月13日,就在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去世后不久,乌拉圭作家、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也在同日去世,享年74岁。他最为著名的作品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该书曾因为查韦斯送给奥马巴而广为人知。
在此之前的4月11日,“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做过一个主题为“拉丁美洲的‘鲁迅’——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及其思想”的对话。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得独家授权刊载对话内容,有删节。
对话参与者:
郭存海: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
路燕萍:法学博士,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讲师,加莱亚诺《火的记忆1:创世纪》、《拥抱之书》译者
张伟劼:艺术学博士候选人,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讲师,加莱亚诺《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译者

郭存海:在6年前第五届美洲峰会上发生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事件:已故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送给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本书,这对奥巴马来说绝对是一个讽刺,因为那本书的名字叫《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主题恰恰是抨击美国、欧洲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拉丁美洲的殖民。之后这本书迅速蹿红,英文版在亚马逊上的销量迅速蹿到第二位。中文电子版在网上也甚是风靡。这本书可谓是了解拉丁美洲的一个窗口。我称张伟劼博士为拉丁美洲思想和文化的坚定的写作者,他翻译了(加莱亚诺的)《镜子》。路燕萍博士翻译了《火的记忆》三部曲的第一部。他们二位是加莱亚诺思想的第二代(传播者),第一代是索飒。
从加莱亚诺的第一本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出版到现在已经44年了,中文版也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最近加莱亚诺又出版了4本新书--《镜子》、《火的记忆I》,第二部正在翻译、《拥抱之书》,还有《时间之口》,以及更早一点的《足球往事》。他的书大约中文版出了6、7本,其中《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可能相对而言大家比较了解一点。
我们首先请张伟劼博士谈谈他是怎么介入,或者说遭遇加莱亚诺的。
张伟劼:当时我的一个同行推荐了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看过之后发觉是很另类的一本书,它的体裁叫政治评论呢,还是叫政治经济学呢,还是叫文学呢,还是新闻报道呢,都说不上,但它有强大的吸引力让我能读下去。
翻译《镜子》这本书也是一个很好玩的经历,我是托一个去西班牙出差的朋友给我带回了《镜子》的西文版。看完之后,写了一篇书评,发在《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上。
后来索飒老师根据我的书评把《镜子》推荐给了广西师大出版社。他们说能不能联系书评作者本人来翻译这本书。
(郭存海:《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它反映的一个主题,是说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是发达国家的发达导致的。因为它里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拉丁美洲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它的发展呢,是一场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那么我不知道这本书《镜子》反映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我觉得加莱亚诺作品的主题是一致的,一以贯之的,实际上我们很难把加莱亚诺定义为思想家。我在墨西哥也听过有关的评论,有一个哲学博士就跟我讲他不喜欢加莱亚诺,他说加莱亚诺没有体系。
但是我的观点是,加莱亚诺就是要反体系。
他是一个以碎片化的书写去打动人、去表述他的想法的作家。实质上他的风格比较符合我们当下人的阅读习惯。《火的记忆》都是一些小故事,而且写得很动人。
张伟劼:《镜子》是一本世界史,他的中文译名本应该是《镜子--一部准世界史》,这表明,它是一部不同于主流世界史的史书。
加莱亚诺呢,如果非要把他套进某一个理论框架里的话,我觉得他更多是一个后现代作家。而后现代的一大特点就是碎片化,打破主线,打破二元对立的观念、结构。加莱亚诺的《镜子》的理想,就是通过这种碎片化的书写去解构我们传统的世界史。贯穿在其中的一个思想主线就是关怀边缘人物,关怀底层群体,关怀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人。
路燕萍:我真正爱上加莱亚诺应该是看他的《拥抱之书》。当然之前我教“拉美概况”那门课会看《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但我真正喜欢上他是看《拥抱之书》,当时就是喜爱得不得了。
我就从我自身的阅读体验和翻译体验来谈一谈。
我想谈谈《火的记忆》第一卷,加莱亚诺通过这本书想要告诉读者什么,想要构建一个怎样的拉美历史?要了解加莱亚诺,我觉得最好就是看他的序言,因为书的正文都是一些小故事,他的序言中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深挖的。
我挑几个点来谈谈。第一个点:他说拉丁美洲,一开始就被判处失忆。“失忆”这个词,西语是“amnesia”这个词,是加莱亚诺式的,他在很多场合都有提及。他说,拉丁美洲是被判处失忆的一片大陆。历史的失忆,加莱亚诺认为拉丁美洲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人类的记忆就像一道彩虹,一道大地彩虹。这个彩虹应该是七彩纷呈的,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人类的记忆被那些诸如大男子主义,种族主义,精英主义以及其它各种主义残害地支离破碎了。他说我们的记忆被切成了碎片。在这种碎片中我们要去找寻我们的记忆,重新构建我们的记忆。
这本书是82年出版的第一卷,第二卷是84年出版,第三卷是86年出版,虽然中间间隔了4年,但是他的写作经历了大概10年的历程。他中间花了6、7年时间去搜集资料。
也就是说跟1971年《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出版应该是隔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就像刚才张博士说到的,整个世界的历史、学界的思潮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因为他要构建的是历史和记忆,所以我觉得他肯定是受到了史学界、历史编撰学方面的一些影响。
我觉得历史界的史学观应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到20世纪初的一些思潮,比如说哲学界,语言学界的影响,就是说,历史的宏观的元叙述已经被打破了。
所以加莱亚诺应该是把这些都考虑在内了,所以他在构筑历史的时候会想到他要怎么样构筑这个历史。而且当时有一种说法是,大写的历史已经发生改变,大家开始关注小写的历史,比如说福柯,都是关注历史上一些非常小的人物,一些非常边缘的人物。刚才张博士也说到了,加莱亚诺是为底层人民而写作,确实是。
记得加莱亚诺在一次访谈中说到,拉美有一些左派人士甚至认为,那些普通的人,那些在底层的人,是只能重复上面的人、主人的声音,不能自己发声的。而我们左派,就是要代替那些不能发声的人来发声。这种观点加莱亚诺是反对的,他说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声音,为自己发声,现在我们没有听到那些声音是因为这些声音被屏蔽掉了,所以加莱亚诺要做的就是让这些底层群众发出自己的声音。
加莱亚诺这种创作观和史观仅仅从《火的记忆》中看是难以完全被理解的,一定要看《拥抱之书》,这本书是1989年出版的,其中描述的是他流亡西班牙时的经历,书中不仅有加莱亚诺自己的回忆,也有他搜集的一些民间故事。书中有一节关于“失忆”的片段,其中提到一个谚语“狮子们在遇到自己的历史学家之前,狩猎的历史仍让打猎者荣光”。这其实反映了他的一种史学观,就是让狮子拥有自己的历史学家,被迫害者能够拥有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奥巴马上台的时候,有人问加莱亚诺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半血统的黑人当选美国总统,他说:“这是美国历史上反种族歧视的一种胜利,但是我并不认为奥巴马因为是半血统的黑人所以更好一些”,从这里也能看出加莱亚诺的那种平等观。。
在《火的记忆》序言中,加莱亚诺还说过一句话“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位作家”,这表明了他的立场:他并不是一个历史的编纂者。这里涉及到历史编纂过程中客观性和主观性的问题,针对这一点,他说:“我不想写一部客观性的历史,我不想,也不能,书中的历史的叙述没有丝毫的中立性,但这部庞大的马赛克的巨著中的每一个片段都基于坚实的文献资料,书中讲述的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只是以我的方式来讲述”。
加莱亚诺说他不愿意教任何人任何东西,他不想把他的思想强加在别人身上,他是想通过他的叙述能让读者自己构建他们自己的思想。
《拥抱之书》中有一章节“艺术的功能”里提到有一个小孩没有见过大海,他的父亲带他去看海,当他第一次见到大海时,大海一下跳入眼前。那种冲击力让小男孩惊呆了,小男孩对爸爸说:“请您帮我看吧”。这就是加莱亚诺想表现的客观性,客观性犹如大海。加莱亚诺描写的故事和人物是帮助读者来了解客观的世界,重新构造一个自己的历史。
张伟劼:路老师,我想打断您一下,我并不认为加莱亚诺如您所说的那样是客观地呈现历史。
路燕萍:加莱亚诺确实不是呈现的客观历史,是主观的,但他做到了在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统一。
郭存海:在浩如烟海的材料里面,从不同的视角选择的材料并不一样,是有选择性的。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今天不在场的索飒也是这样的,她有一本书对于出版商来说吸引力不大,书名比较晦涩,叫《把我的心染棕》,不好卖。但她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写作是有立场的,历史学家是要尽可能地还原客观的历史,挖掘过去真实的存在,但作家不一样,作家是有情感有立场的。
索飒从来不避讳自己是为底层人民写作的,她是有情怀的,在她的书中,她永远是站在为印第安人和拉丁美洲的土著或底层人民写作的立场上写作的,因此她坚持用《把我的心染棕》做书名。因此,我认为不应该避讳“我的立场和写作是有倾向的” 。如果你要说我的研究是有立场的,然后你就说我不客观,我想那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路燕萍:加莱亚诺从来没说自己是个客观的人。他在《拥抱之书》里面有一个关于写《火的记忆》文章,叫“主观性礼赞”,他说“我花了很长时间写《火的记忆》,写着写着我就愈来愈陷入我讲述的故事之中。我已经难以厘清过去与现实:曾经发生的事情当今仍在发生,而且发生在我的身边,而写作是我击打和拥抱的方式。但是,想必那些历史书不是主观的。”所以他在怎么看待主观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直也在思索。他努力地在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所以他的这本书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史料可循的,而且他也尽量以简洁的语言让它呈现出来。
张伟劼:实际上加莱亚诺不光光是写底层,他也写上层。只不过他的视角是独特的。我们平时看各种专题片,拍摄者的视角实际上是非常有讲究的。虽然说被镜头拍摄到的一切都貌似是客观的,都是现实的,但事实上不同的视角会让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他在《镜子》里面也去写贵族的生活,大人物的生活,但他采用的不是一种主流的视角,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他的这种视角称为“南方视角”。
郭存海:我记得墨西哥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米格尔·莱昂一波尔蒂利亚写过《战败者的目光》。历史,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得到的是不同的判断,尽管是同一份材料且都是真实的。关于《镜子》,其实刚才我也说到,包括《火的记忆》,都是一些片段的、思想的、碎片的写作。但是加莱亚诺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统一的。那就是讨论和反思拉丁美洲今天的这种不发达。
拉丁美洲经历十年商品繁荣之后,经济又往下走了。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因为拉丁美洲的经济结构,它还是没有摆脱一种依附,当然这种依附并不是被动的依附,有时候它是一种主动依附。我们知道拉丁美洲地大、物博、人少,光出口原材料就可以了。阿根廷1914年的时候人均GDP位居全球第六,它基本靠出口牛肉和粮食就达到了这个水平。但遗憾的是,甚至到现在整个拉丁美洲基本上都没有健全的工业体系。所以,极端的情况出现了:委内瑞拉甚至连手纸都需要进口。那么这样一种结构是谁造成的呢?
加莱亚诺说,是由于边缘和中心的这种不平等的结构造成的。那么过去了这么多年,中间又经历了债务危机,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及左派十多年的上台执政后进行的调整。但结果发现越左的国家,情况越糟糕,像委内瑞拉。
我们“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的群里面有一个外派委内瑞拉的中国青年,他跟我说,委内瑞拉反对派的人都跟他说,现在如果查韦斯还在的话就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马杜罗总统无法控制当前的局面,当然反对派也没有能力上台,因为委内瑞拉穷人太多,所以穷人的选票是重仓。谁提供资源给穷人,谁就能获得选票。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投资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场景,即指责中国在拉美搞新殖民主义。
所以说,如果要对拉丁美洲有更好的理解,我们就要有同理心,去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它的现况,了解它需要什么。比如说拉丁美洲它现在需要的是工业,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仅仅需要它的大豆、石油和矿产的话,拉丁美洲人是不高兴的。他希望中国能帮助他改变过去一直没有改变的结构。因为这种结构固化了拉美的发展方向。
但这种结构固化的根源,据说在2014年巴西图书节上,加莱亚诺是有一些反思的。他说自己写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因为自己是一个记者、作家,而非一个专业人士,他的政治经济学写作功底或者说在专业方法上,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对自己将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完全归咎于外部是有些反思的。
张伟劼:事实上我对加莱亚诺还是持有一定的批判态度的。因为在加莱亚诺的书写下,历史往往呈现为一种非黑即白的历史:不是好的就是坏的;左派一定是好的,右派一定是坏的;拉丁美洲一定是好的,美国一定是坏的;穷人一定是好的,富人一定是坏的。
我觉得中国智慧倒可以给加莱亚诺提供一些参考: 我们中国人从来不认为非黑即白,我们认为黑和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加莱亚诺最极端的时候他会在作品里反对汽车的发明,说汽车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是多么邪恶的东西;他反对市场,说市场经济造成人性的恶化,造成地球资源枯竭,等等。
我曾经有一次做翻译的机会,和一位发改委的司长有过短暂的交流。我跟他提起了当代中国的左右之争。我问他对此如何看待。他说,都是假的,中国没有真正的“新左派”,也没有真正的右派,我们政府在做经济决策的时候,不会考虑什么左派经济学还是右派经济学,我们只会根据中国的现实来采取最符合中国现实的政策。我认为这一点也是中国智慧的体现吧。
实际上,我更多是把加莱亚诺当成一个作家来看,而不是作为一个舆论家或者是思想家来看。我在读《火的记忆》的时候,发现他体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建构拉丁美洲历史的意识。在翻译加莱亚诺之前,我翻译过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他也喜欢写历史,他是建构墨西哥的历史,富恩特斯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我们应该“想象过去,牢记未来”。我想加莱亚诺在建构历史的时候,他的视角要比富恩特斯更宽广。富恩特斯只是想到墨西哥,加莱亚诺想到的是整个美洲。我们看《火的记忆》不光写拉丁美洲,也写美国,把整个美洲看作一体。

路燕萍:加莱亚诺也一直在建构拉美身份。刚才张博士说,加莱亚诺的写作是非黑即白的,我觉的他确实是一个爱憎很分明的人,但是我觉得不能简单地、固定地把他归为左派,只是他一直跟左派走的比较近的。
这其中有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就是《血管》这本书并没有拿到当年的美洲之家的奖。据加莱亚诺说,美洲之家的一些评论家,那些左派的评论家们认为如果一本书要是很严肃的话,那一定是很无趣的,而这本书呢,不无趣,那它就不是严肃的,所以他就没有拿奖。后来,这本书能够畅销跟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政府禁止这本书有很大关系。而且正是因为这个他才被迫流亡。
不能简单地把他划分左派或右派,他有一个他自己的坚持,他坚持的底线,而且他一直在变,他可能在写《血管》的时候是一个热血青年,是一个偏左派的,但是之后他会慢慢去反思,这个反思的过程我觉得可以举一个例子.2004年乌拉圭总统大选,就是传统的两派,白党和红党都失败了,广泛阵线赢了.当时加莱亚诺写了一篇文章, 赞扬左派第一次在乌拉圭的历史上获得大选,人们终于能够进行自己的选举。当时还有一个关于水私有化的人民公投,可能大家看过《雨水危机》这部电影,了解电影中讲述的玻利维亚水私有化的问题,在乌拉圭也有水私有化的议案,但是人民公投反对,因此私有化没有成功。加莱亚诺发表热情激昂的文字来颂扬这一事件。但赢得大选的广泛阵线领导人巴斯克斯上台后,做出一些政策调整,引入外国资本,这与竞选时的方针不一致,这时加莱亚诺进行了批判。广泛阵线是左派政党,加莱亚诺对左派政党不是一味地支持.不管是右派还是左派,只要违背了他的坚持原则,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批判。
路燕萍:他所有的写作其实都是基于人的本性,任何人违背了人性的这一条,他都会去批判。
郭存海:索飒是国内介绍加莱亚诺最多的,同样她有与加莱亚诺一样的情怀。2014年加莱亚诺对将拉美不发达的根源归为外部原因的立场有了些改变,或者表示了反思。但是索飒说加莱亚诺不应该忏悔。我对她的观点,是持保留态度的。
路燕萍:如果你看《拥抱之书》,就会发现书中经常写到某某人和我讲了什么故事。确实,比如他当时在委内瑞拉和一些人参加了一个调查,调查查韦斯的事。他就去了一个贫民区,和老百姓说,我们现在也没录像,没录音,你就真真正正告诉我,如果你投票,是选查韦斯吗?那个人就回答:我要选查韦斯。为什么?因为查韦斯让我们被看见了。
加莱亚诺一直要做的就是让那些没有被看见的人被看见,所以在2012年那本《时日之子》的书中,有篇文章叫《玻利维亚的二次创建》就是讲的当时玻利维亚的新总统莫来莱斯修改宪法,新宪法就强调所有印第安人,女人都是玻利维亚的公民,这是一个历史上的重大改变,因为好像在之前的宪法中,玻利维亚只有3%或4%的人才是公民,其他人都是不被承认的。就这一点,加莱亚诺高度评价莫拉莱斯,他认为这就是玻利维亚的二次创建。也许国际社会上都认为玻利维亚是不可治理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玻利维亚实际上是不被看见的。这种二次创建实际上是让没有被看见的玻利维亚被看见了。所以加莱亚诺写的所有东西都是为了让那些没有被看见的事物被看见。
张伟劼:讲意识形态是一个有风险的事。可能加莱亚诺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建构一个体系。他可以反新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但是他自己没有建构一个什么主义,因为一旦建构一个体系的话,比如查韦斯和马杜罗,当他们必须紧随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路线时,他们做的任何调整都可能被按上反社会主义的帽子。
郭存海:如果要对阿根廷的历史进行梳理的话,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态度变化。它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民粹主义的历史,然后就是一部腐败的历史。拉美的历史,的确像《血管》这本书一样,很有意思,但是你读的过程中,你要是从底层去读的话,感觉到拉美太黑暗了。你要看拉美的电影的话,会觉得,不能看,看完之后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甚至想直接去街上找个乞丐施舍一下。就有这样一种冲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别在农村。拉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下层。从2010年到2014年世界首富不是美国人,而是墨西哥人、美洲电信巨头卡洛斯·斯利姆。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很多拉美国家人均GDP都超过1万美金,但是很多拉美人却说自己被平均化了,这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
路燕萍:《火的记忆I:创世纪》是从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之前一直讲到1700年的美洲大陆情况,所以中间大部分是征服史,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殖民者对这一片大陆的侵略和殖民。
郭存海:加莱亚诺有一篇散文,出自人民出版社《外国散文百年精华》一书,名为《让美洲发现自己》,开篇就写到“历史从一开始就被误解了”,然后他很有立场地又写道,“1492年美洲不是被发现,而是被侵略的”。
路燕萍:是的,在《时日之子》中10月12日那天他写了一个大发现,因为10月12日是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日子。那篇文章大概内容是,在这一天美洲的原住民发现原来自己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原来自己住在一个新大陆上,原来还有原罪,他用反讽的笔调写出了这些东西。在《火的记忆》第一卷里面,他写了一些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之前的神话传说,我觉得他每一篇神话传说对于理解整本书都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或钥匙。比如有一个故事说当时有一头美洲豹遇到一个人,便把那个人带回了家,美洲豹的老婆说你怎么能把人带回来呢,然后美洲豹说没关系,他就像我儿子一样。这样美洲豹就教人使用火,但是那个人知道火的作用并掌握了弓箭之后,就把美洲豹的女人给杀死了,也把火种给带走了,从此以后美洲豹自己就不能使用火了。
还有一个关于火的神话故事,从前有一个叫Mezquino的神,mezquino一词有“吝啬”的意思,他掌控了火和玉米这两样东西,他从不给人类玉米种子,只给人类熟的玉米,这样人类就不能自己去种植玉米,同时他也掌控着火。后来有一只乌鸦想要去偷火种,想尽办法去接近Mezquino,Mezquino总是随手从身边抓一个东西去砸它,砸了好多次后,最后抓了一个没有烧尽的小木炭砸了过去,乌鸦就把木炭叼住并带走了它。风吹木炭又让木炭重新燃烧起来了,而木炭燃烧起来以后就会把乌鸦的嘴给烧黑了。这个故事我觉得对于整个三部曲应该有一个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解读。
郭存海:我感觉谜底在第三卷,所以等到你完成这三卷之后,谜底就解开了。
路燕萍:我感觉也是,第三卷的书名叫《世纪之风》。
郭存海:张博士,在《镜子》里面有什么样关于中国的历史的记录呢?
张伟劼:中国在西方的历史叙事中一直是浮于表面的,中国人被当成野蛮人,就连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讲资本主义摧毁了中国长城,征服了野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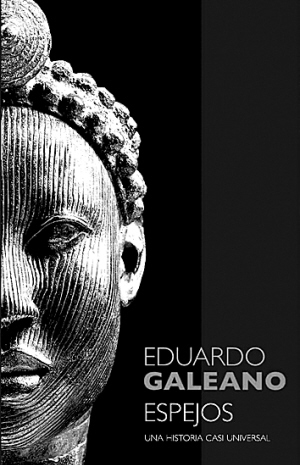

他讲到毛泽东时代的时候,吐露自己曾经亲自来过中国,那时他作为一个拉美热血青年,到社会主义中国来看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样子,我想当初西方世界所有的左派青年对中国和苏联都会存在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我曾经看过苏珊·桑塔格的一篇讲旅游的文章,当时很多国际左派青年从英美发达国家去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旅游,实际上他们的旅游都是被设定安排了的,他们参观的工厂都是一些样板工厂,他们看不到最真实的一面。
而加莱亚诺就很有意思,可能也是拉美人自由散漫的天性使然,他不喜欢按着预设的计划走,他专门注意看一些细节。他在北京看群众大游行,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没有被印出来,“我看到毛对毛致敬”,当时游行的群众们抬着毛泽东的巨像经过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站在城楼上向自己的巨像挥手。这一句话虽然讲的很简单,但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意味的对于权力形象的书写。还讲到当时中国的大跃进, “大跃进跃进了虚空之中”。如果非要把加莱亚诺说成是一个左派的话,我想他应该不是左派里面的激进派,他或许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
郭存海:拉丁美洲整个历史从外部来说是发达世界对发展中世界的一个殖民、压制的历史。因为很明显的是,拉丁美洲的经济结构、发展历史,包括文化思想,很多来自于发达世界,特别在殖民时期一个最重要的殖民手段就是通过宗教文化。
路燕萍:我自己的感觉是,加莱亚诺现在努力避免直接谈论这一话题,所以这也是他对“血管”有一定的否定的原因,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找到能让边缘国家或者第三世界国家走出困境的方法。所以他仅限于替那些不被看见的人说话,只要是不正义、不公正的事情,他都反对,而且他尊重生态文明。我觉得很多时候不能够简单得去说他的观点是对是错,是否符合全球化的经济时代,是否符合拉美经济的发展。他可能宁可要这种权力,比如说水资源是我自己的,不要私有,可能私有化对乌拉圭的经济发展更有作用,但他宁可不要那种发展,他认为水私有化之后就会用得一滴水都没有了,他认为这是对生态的破坏。他的观点很有前瞻性,但是他也提不出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应该怎样发展。
郭存海: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提问、互动,大家可以向在场的任何一个人提问。
听众:我想问的是,加莱亚诺一开始很显然是一个热血青年,但当他真正见识到社会主义的中国,当90年苏东剧变的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在他的作品里有没有体现这一点?整个共产主义进入低潮之后,他对社会主义的判断在思想上有怎样的变化?谢谢。
路燕萍:张博士翻的《镜子》是08年的,我翻的《时日之子》是2012年的。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90年代的作品仍没有被翻译过来,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还是空白。从我的了解来看,从70年代后期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非常清醒的态度,他永远不会因为你标榜的主义而一味去信服你。我觉得他一直持着一种反省、批判、或者说一种保留的态度。在他的行文中有很多次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没有看出有什么明显的倾向。
路燕萍:我觉得加莱亚诺对委内瑞拉的情况有很清醒的看法。当时查韦斯经历完政变一上台,他(加莱亚诺)就写了文章称之为“传播的恐惧”,就是传媒的力量,收录在《时日之子》里面。
加莱亚诺对这一个事件的态度不能说赞扬,但他很高兴,因为他觉得是人民选的查韦斯,能够让查韦斯在政变之后上台,他认为这是人民自己的选票,他仍然还是站在底层人民的角度去看,底层人民能够通过自己的投票决定自己的总统,他就认为这是一个胜利。
但是他好像对于委内瑞拉是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是持一个批判的态度的。所以我觉得他对委内瑞拉和查韦斯的态度不是一味的赞同,他有他的保留意见,只是他没有明确的说出来。而且对于查韦斯把《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送给奥巴马,让他成为了一个畅销作家这件事他也不是很喜欢。
张伟劼: 他不喜欢政客。因为政客所展示的一切行为都是一种表演,查韦斯的这样一种举动实际上也是一种宣示,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也是在利用加莱亚诺做政治宣传的广告。
1989年之后,加莱亚诺的创作实际上还是坚持他原来的一些想法的。实际上他没有变,他回应的是当时主流的一种声音,就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加莱亚诺一直在用他的写作来回应这句话,来挑战这句话,表达历史没有终结。也许在东欧国家历史已经终结了,好像进入了一种资本主义永远幸福的模式,但是在拉丁美洲,在边缘地区,你还听到斗争,你还听到那许多矛盾,它们在南方世界仍然继续存在。
路燕萍:对,他要努力把过去两个世纪之前的故事都讲出来,就好像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样。而且他认为每讲一遍,这个故事就再发生一遍。这是他要达到的,他强调的历史不终结。而且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是资本主义的,在后现代主义时期,加莱亚诺正好利用了这个契机,做他自己一个阐释。
郭存海:国开行的田志,刚从拉美四国考察回来,带回了很多观感,今天可能也有很多问题。
田志:既然今天的主题是把加莱亚诺和中国的鲁迅相比较,我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两位作家的异同。我想问的是加莱亚诺的出身,他的成长的经历,他的肤色。是不是比较优越?他的肤色是不是也是白人?拉美一个最成功的案例可能就是乌拉圭,他的人均收入、受教育程度等都是最好的。加莱亚诺来自于这样一个优越的环境,却关注底层,这一方面给我们很多感慨,另一方面也给我们一个思考:他对殖民者是批判,是反思,那么他有没有像鲁迅一样对(自己大陆)的国民性有一个分析?有没有对自身有过批判?
张伟劼:首先我们不应该把太多的责任加在作者身上,不宜过高地要求一位作家。如果要说深刻性,我不认为加莱亚诺的思想可以比得过鲁迅,我也很少看到他对拉丁美洲国民性的批判,谈国民性是很危险的,如何界定呢,是拉丁美洲人民还是乌拉圭人民?
我认为文学不应该和政治走得过近,文学的价值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提出问题,在我看来,加莱亚诺更多地是一个善于说故事的人,把拉丁美洲的问题说得很吸引人,如路老师所说,他把现实展现在我们面前,他把他的思想以很有趣的方式表述出来。说到他的出身和环境,当时《镜子》的中文版本出版后,老先生想要出版社送几本寄给他,提供了他的地址,我作为传话人知道了他的住址,我就把这行地址放到GOOGLE EARTH的搜索栏里, 看实景,发现他住的地方位于一个中产阶级的社区,那里的房子多带有花园,很舒服,很安静,还看到街上停着一辆中国产的QQ。乌拉圭是个中产阶级国家,贫富差距不大。加莱亚诺这个姓氏来源于他的母亲,他父亲姓修斯,身上有威尔士人血统,其实这样的情况在乌拉圭和阿根廷是很普遍的。加莱亚诺从头到脚都是白人,看他年轻时的照片,留着像马克思一样的大胡子,他从小生活环境也应该是中产阶级。
听众:他为什么会流亡,是宣扬了某种暴力么?
路燕萍:他1971年发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乌拉圭政府当作解剖学书而让其发表,后发现真实情况后就予以禁止,之后这本书在智利、阿根廷一直被禁,甚至携带都会被判刑。加莱亚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流亡。他流亡阿根廷时负责“危机”这本杂志,虽然他选择闭嘴不再发声,但还是上了死亡名单,因此他流亡到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海边小城。他在流亡西班牙时需要经常换签证,遇到很多麻烦,这些流亡的穷迫对他都会产生影响。
张伟劼:这里有个小故事,他在巴塞罗那办签证填表格时,因为要一遍遍地填表格,一趟趟地跑,他烦了,于是干脆在一张表格上的“职业”一栏写上: 作家,然后括号:专写表格的。

路燕萍:确实是,之前是哥伦布到达美洲时,当地的文明确实很发达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做文化研究时候,不能简单地以先进或者落后来评价一个文明,因为在时间轴上也不太一样,但是历史本身也不能再假设了,这个文明本身就被西方文明侵入或者被腰斩了,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惜的事情,而且在《火的记忆》中确实有很多描写,《火的记忆》中会把侵略者一些故事,从侵略者的角度和被侵略者的角度都有展示,很多篇故事挺有意思的,其实加莱亚诺还关注侵略者中的女性,因为很多女性追随着将军来,与男人一样英勇善战,但是打了胜仗后,女人和男人分到的战利品是不一样,后来命运也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来,加莱亚诺不光是关注被打败者被征服者的,他还会同时关注到征服者胜利者的一些差别,因此我建议慢慢地去读一下《火的记忆》。但是索飒老师曾表示对把这本书引进的中国来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她觉得这本书太挑读者了,因为需要读者的参与,需要读者找来很多想相关的文献来读,来构建一个所谓的美洲史。因此读这本书会比较费劲一点,建议可以结合一下拉美史相关的浅易读物一起来看,可能会有很大帮助。
郭存海:路博士说的非常好,可能是我们对拉美不理解,但是会有越来越多拉美图书的(的读者),全国的西班牙语专业都已经覆盖到小城市了,然后我统计发现中国的拉美研究中心也越来越多,未来中拉交流也会越来越多。事实上,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太小,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它。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活动呢,就是因为,左手边拉美人越来越想了解中国,然后右手边中国人越来越想了解拉美,现在就横亘着这样一堵墙,其实它不是一堵墙,它只是像几米同名绘本改编的电影《向左走、向右走》一样,缺少一个际遇,所以请大家关注“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关注“拉美智讯”微信公众号。如果你关注了,就不会错失爱,错失拉美,错失中拉文明的对话。谢谢大家!
(感谢黄思然、李佳蒙、张琨、刘倩和唐幸为整理对话文字稿做出的贡献。文字稿已经对话人郭存海、张伟劼和路燕萍审定)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