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影君子|如何“做”视觉民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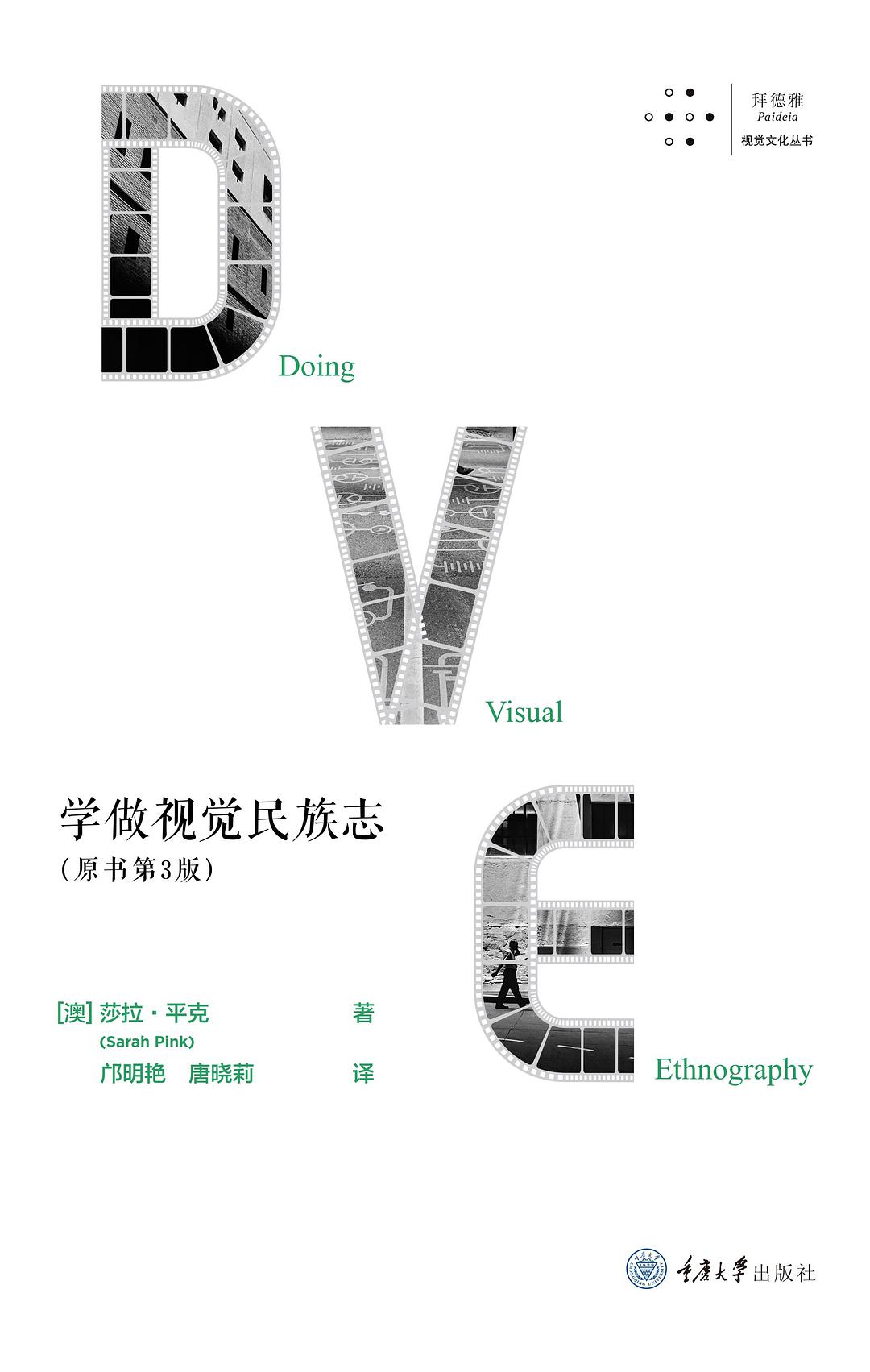
《学做视觉民族志》(原书第3版),[澳]莎拉·平克著, 邝明艳 / 唐晓莉译,拜德雅 |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摄影在视觉民族志中的地位与作用有点尴尬。若以科学“求真”的要求看,照片可以为视觉民族志的客观性与权威性有所加持与担保。但在引入照片作为证据或为达到其他目的时,其实照片的引入也同时引进了摄影所具有的主观性。这种摄影的主观性,至少体现在拍摄者的瞬间取舍、视角站位的选择以及照片的使用等多个方面。所以,如何“做”视觉民族志,以及如何“做”好视觉民族志而令研究具有相当的可信性,需要研究者对于民族志的做法保持清醒的意识,心存需要时时反思的警惕(所谓反身性),否则就有自欺欺人的嫌疑。
澳大利亚学者莎拉·平克(Sarah Pink)长期致力于民族志、尤其是视觉民族志的教学与研究多年,成果累累,享有国际声誉。本文介绍的《学做视觉民族志》(Doing Visual Ethnography)自2001年出版第一版后,到2013已经升级为第三版。本文依据的是此书第三版的中译本,由邝明艳和唐晓莉翻译,作为“拜德雅·视觉文化丛书”之一由重庆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12月出版。
平克女士在英国肯特大学获得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许大学,为以人为中心的计算系与设计系教授,也是该校“新兴技术研究实验室”主任。其研究领域涵盖智能技术、自动化、数据处理与数位未来等多个方面。她著作丰硕,出版编著了许多有关人类学的书籍。
虽然本书处处都与如何运用包括摄影和视频在内的视觉手段展开民族志书写有关,包括对于本书作者自身运用摄影展开的民族志研究所做的思考,但在章节内容方面,第四章“民族志摄影”以及第八章“摄影与民族志写作”是直接处理摄影与民族志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围绕这两章的内容作一些介绍与思考。
第四章属于第二部分“知识生产”。整个第二部分聚焦运用各种视觉手段进行视觉民族志的方法论问题。在第四章中,她“以对摄影在民族志中地位的反思为出发点”,对一些包括她自己的研究在内的实例展开讨论。在承认“从事民族志研究的过程本身可以被视为一个开拓方法和生产知识的过程”(91页)的同时,平克提出“任何照片都可能在特定时间或特定原因下具有民族志价值、意义或含义”。(97页)但她也强调“照片的意义是有条件的、主观的,取决于谁在观看、在什么时间观看”。(97页)而在作为民族志学者、研究者拍摄照片时,她特别指出“有另一个维度需要考虑,那就是我们(研究者——笔者注)在其中的参与”,(98页)即“民族志摄影的反身性意味着研究者对引导自身民族志实践的理论、与拍摄对象的关系,以及知会拍摄对象摄影方法的理论有清晰的意识”。(98页)这里其实发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所谓的参与如何被表征?被表征了的参与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参与?
的确,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参与式民族志越来越受重视,但其中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天平,尤其是在一些经济社会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地区,仍然有着向研究者强烈倾斜的倾向。因为许多被研究(拍摄)对象,处于寄希望于研究者可能会帮助其解决某些实际问题的位置,研究者如果没有能够明确自己的“不能”,一可能会形成某种自我膨胀,二可能会给拍摄对象以不切实际的承诺而最后令人失望,造成实际伤害。
平克也介绍了如何取得研究对象的信任的方法。比如,她自己“通常会在访谈的地方,为每个参与者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拍摄一张肖像照”。(103页)顺便说一句,早先中国的民族志摄影家庄学本当时在川藏地区拍摄时,也曾将拍摄的照片赠送给当地民众以取得他们的信任。
而更有新意的地方是,平克认为“我们可以将摄影理解为一个移动的民族志”,是“步行与摄影相结合”。(104页)这种和研究对象一起体验环境、放松心情的方法,“在表达特定环境的经验以及与特定环境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109页)因为“在这里,照片不是静态的对象,等待其内容被解释,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在运动中被创造出来,是作为行走在城市并探索与它有关的内部情感的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简单地被人观看的对象”。(109页)通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享也是作为研究内容一部分的空间的方式,在双方信任度加深的前提下以获得意义更为丰富的知识内容。
作为人类活动的知识生产的方法的视觉民族志,如何在民族志过程中对获得的视觉材料(照片与视频等)进行组织化的阐释(一种知识的建构),既是民族志的必要,但又关乎知识生产的性质。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建构知识的问题。平克最早以《女人与斗牛》一举成名。她在本书中以自己的工作为例作了回顾。她说:“例如,1990年代我在西班牙开展的研究中,我给三位女性展示了我们曾一起参加的斗牛表演的照片。我按照打印者还给我的顺序来保存(并编号)这些照片。然而,由于这三位女性对这些照片进行了优先排序和选择,这些照片很快就被重新排列出来。例如,她们把照片分为她们最喜欢的斗牛士的照片、她们自己的照片、她们觉得具有美感但不具有记录意义的照片。”(195页)平克认为,“她们对照片的重新排列代表了她们看待斗牛经历的不同角度,以她们自己的参与和最喜欢的斗牛士的表演为中心。……因此,对我的分析来说,比起这些女性对照片的评论和排列,我拍摄照片的时间序列并不重要,因为这是她们的认知与我的照片交织的时刻。在我的分析中,这些照片成为当地知识和个人知识的视觉表征,也成为对特定的斗牛表演和特定个人的理解。”(195-196页)她还进一步反思:“如果按照我的方式进行临时排序并拍照,以便作为对活动程序的系统记录,而不是按照这些女性向我所展示的方式来操作,那么这组照片将只不过是以通常的斗牛形式来表现特定的表演者而已。”(196页)平克以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尊重她的研究对象的意见与建议的态度。当然,我在此存疑的是,她说的“按照打印者还给我的顺序来保存(并编号)这些照片”这句话,“打印者”在此意味着什么?仅仅是交付打印照片的店家或是什么?如果是,她根据什么原则全面接受“打印者还给我的顺序”来“保存(并编号)这些照片”?如果是,我们会觉得平克真是难得的愿意放弃自己的立场而任由他人(“打印者”?)通过安排她拍摄的照片的顺序来生产知识。
正在撰写此文时,有机会与一位获得过普利策摄影奖的美国老摄影记者谈天。他说起中国的摄影家都不愿意让别人编辑自己的照片。他说,在美国,即使是一个资深的摄影师,在出自己的摄影集时,也往往是请别人,大多是资深的图片编辑来帮助他编辑。他认为图片编辑是一个需要长期经验与积累的专业。而请到他人编辑自己的照片,是一次避免过于主观与感情用事的办法,也是难得的让自己的照片(有时往往是一生的精华)有一次被他人加以客观审视与处理的机会。经过这样的编辑,对于摄影家来说,其实是一个新的自我的诞生。而对于读者来说,则可能是一次新的“知识生产”。
回到视觉民族志本身来,在完成写作的过程中,往往是研究者自己决定(其间可能与研究对象和被访者一起讨论过照片的取舍)在自己拍摄与采集的照片中,哪些照片具有民族志的价值,并且可以作为研究的一部分被放进研究著作或报告中并且发表出来。这个工作方法当然是合理的,但其实在这里仍然存在一个个人主观对于作为研究成果的一部分的照片的取舍在起主要作用的问题。如何尽可能避免主观性仍然是每个社会科学工作者要重视的问题。平克在此展示的做法,有助于我深长思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也许在许多人那里早就有无疑的答案,但我仍然愿意斗胆发问,那就是:社会科学就一定要彻底避免主观性才是社会科学吗?社会科学与一定程度的主观性的兼容在什么意义上是允许的?
如果说知识生产是民族志工作自我标榜的重要目标的话,那么如何将这些被生产出来的知识加以表征,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并且同时面临如伦理等方面的挑战。本书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表征视觉民族志”,乃是着力于提示作为民族志学者,如何利用视觉影像将我们的研究在学术出版中表征出来。平克指出:“制作文字和视觉文本时,民族志学者不仅要考虑生产表征和知识的不同形式,还要考虑读者、观看者和观众将如何面对这些表征。”(207页)第三部分共设三章,分别是第八章“摄影与民族志写作”,第九章“民族志表征中的视频”以及第十章“视觉民族志的在线/数字化出版”。
篇幅有限,无法一一述及各章内容,现仅就第八章“摄影与民族志写作”的部分内容略作评述。本章共设以下六个小节以及小结:“理解民族志写作的当代取向”“摄影与对民族志权威性的主张”“影像、标题、叙述和批判必背离”“文字文本中照片”“民族志中的专题摄影”以及“影像表征中的伦理议题”。
平克介绍,在1990年代,伊丽莎白·爱德华曾经指出,“有两种摄影类型可以被用于民族志文本”,“第一种是‘创造性的’或‘表现性的’摄影(与小说、日记、短篇故事和自传相对应);第二种是‘现实主义’摄影,这种类型将摄影当作‘记录工具’。”(222页)爱德华所谓的“表现主义”这种摄影类型,在她就是如约翰·伯格与让·莫尔的合作作品,如《幸运的人》(1967年)与《另一种讲述方式》(1982年)。他们提供的视觉表征模糊多义,结果倒是给观者的参与创造了条件。这里很重要的是,爱德华将她所说的两种类型的摄影一视同仁地视为民族志文本中的事实要素加以采纳,这就打破了民族志书写中强调“客观性”的传统,同时也承认了影像建构在民族志书写中的合法性,并且进一步挑战了科学性之于民族志书写的神圣性。但这也可能给视觉民族志带来致命的危险。
面对世间对于民族志的不无道理的怀疑,搬出摄影(包括视频)来强化其真实性与权威性,不失为一个办法,而且也是无奈的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之力图要将社会研究科学化的与生俱来的吊诡,其实最终还是要依靠研究者本人的伦理观来保证。但这个保证在人类学这样的学科显得非常脆弱,没有任何约束。因此,视觉民族志的书写,再怎么强调照片与视频因为科学器械的可靠性所得到的权威性,也只能是我们从性善论意义上的自我要求罢了。而通过引入“表现主义”摄影这一类型,同样要求民族志研究者审慎使用照片,这种使用不是鼓励恣意的“虚构”,而是要求更严谨地对待作为研究素材与证据的照片。
此外,民族志的志,当然具有记录的意义,但“志”往往还有志异之意。与摄影一样,民族志从根本上说是不异不志。但记录人文社会实践的摄影实践,因为不是社会科学本身,因此没有要科学性来担保。而民族志,其书写,从根本上说是被所谓的“他者”所吸引,非“他者”不志(书写),在“志”的过程中面对“他者”的诱惑,特别是对于如何精彩地“讲(他者)故事”的诱惑实在太大。但,当我们津津乐道于“他者”故事的精彩时,是不是会放弃自我警惕与质疑?而更有意思的是,在民族志书写中,人们会关心文字文本的书写中虚构与否,但对于照片,可能会放弃一开始就应该有的质疑,没有对于照片应该如何拍摄的要求。因为人们习惯于认为照片放在那里只是表示一种证据,而证据是不会有比如个人风格的要求。而叙事如何,即使文字本身是节制的,但一个精心编织的叙事,就其结构而言,就已经是一种主观先在的“在”了。
由于视觉民族志的表征就视觉性而言,许多情况下会与人的实际形象相关,因此牵连到身份等问题,会对研究对象产生“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影响”,在伦理上有颇多制约。不过平克认为,在因伦理问题而无法使用某些照片的情况下,不要惋惜此时视觉的缺席。如平克所说,视觉的“缺席与视觉的在场一样都具有启发意义”。(233页)她提到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位叫安德鲁·欧文(A.Irving)的学者在他发表的一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中,以“开天窗”的方式,以空白的页面标示出因为某种原因而未能发表的照片。
最后还要就学术翻译赘言几句。在说到视频相对于传统银盐摄影而言的优势时,中译本出现如下句子:“科利尔认为,与胶片的高成本且需要频繁地重新装载摄像头相比,摄像机的优势在于它可以连续运转数小时。”(131页)从上下文以及“胶片的高成本”推理,“重新装载摄像头”一语颇为令人费解。比对原文,发现原来是“reload a camera”被译成“重新装载摄像头”。其实确切的意思应该是胶卷装进照相机之意。发生这个错误的最大可能是,译者自己没有胶片摄影的经验,因此对于在胶片摄影的拍摄过程中需要反复装填胶卷进照相机一事一无所知而导致如此错误。这就引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学术翻译究竟应该是由专业学者翻译比较好,还是只是任由无专业背景的外语译者来译比较好?从这个例子看,显然前者更可靠一些。当然,专业学者也会碰到代际的问题。就此例看,也许还有一个代际问题。如果译者是相对年轻一代的话,没有经历胶片摄影的阶段而直接来到数码摄影阶段的话,无从想象胶片摄影是怎么回事,因此出错也是可以想见。
据预告,本书英文第四版将出版上市,其中第八章讨论纪实问题,而新增第九章的内容有关“干预性视觉民族志”。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