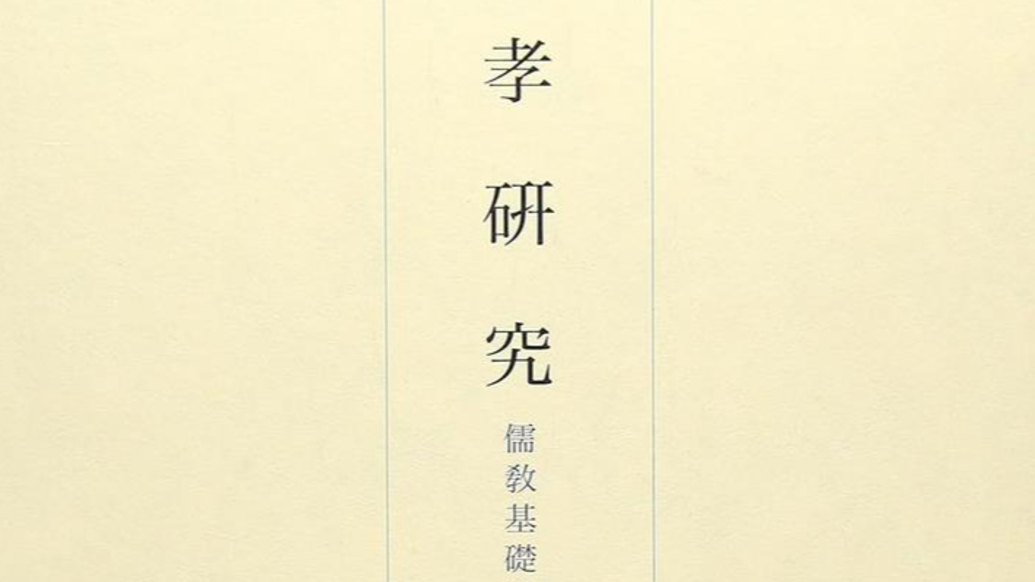- 34
- +135
狼祖传说的另一种历史真相
羊年的贺岁片《狼图腾》引起争议,焦点在狼是否蒙古人的祖先和图腾。蒙古族作家郭雪波连续发表多条微博,怒斥《狼图腾》小说和电影胡编乱造:“狼从来不是蒙古人图腾,蒙古所有文史中从未记载过狼为图腾!这是一汉族知青在草原只待三年,生生嫁祸蒙古人的伪文化!”他还说:“狼是蒙古人生存天敌,狼并无团队精神,两窝狼死磕,狼贪婪自私冷酷残忍,宣扬狼精神是反人类法西斯思想。”蒙古族学者额鲁特·日·额尔登木图也撰文批评《狼图腾》,指出小说和电影中许多不符合蒙古族社会习惯、违反草原生活常识的描写,小说改名为《北京知青养狼记》才贴切,因为狼不会是草原社会的图腾,不过是《狼图腾》作者自己的图腾而已。

这些批评也激起一些反批评,主要是指出《蒙古秘史》开篇所记苍狼白鹿的历史叙述。《秘史》首节的明代总译是这样的:“当初元朝人的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郭雪波反驳说,孛儿帖赤那(Börte-čino,旁译“苍色狼”)与豁埃马阑勒(Qo'ai Maral,旁译“惨白色鹿”)是人名,不是狼和鹿,正如姓马的祖先并非一匹马,叫龙的并不是一条龙。虽然这个理解在《秘史》研究者中绝非主流,但也值得重视。只不过,古代读书的人和听故事的人,不管懂不懂蒙古语,未必会在这个问题上很留意。正如研究希腊神话与古希腊社会生活关系的学者所说,对于古希腊人而言,“神话就是真实的历史”(Paul Veyne, Les Grecs ont-ils cru à leurs mythes? 英译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9页)。绝大多数中国古人在讲三皇和盘古(槃瓠)的时候,是不会抱着科学的怀疑主义态度的。顾颉刚猜测“大禹是一条虫”所引发的反感和嘲弄,从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历史叙述的不同敏感反应的角度去观察,就另有一种认识价值了。
蒙古族知识分子对《狼图腾》的激烈批评(必须说明,持批评立场的远远不止蒙古族,且批评者的侧重各不相同,我这里只涉及狼祖崇拜这一个问题),让我联想起一场(或多场)未见于历史记载但我确信发生过的同类型争吵。唐代前期,在长安的突厥贵族青年与唐人交往时,唐人会提到史书关于突厥人的始祖母是一头母狼的记载,而在长安长大并接受汉文化教育的突厥青年大概不会喜欢这个话题。要么否认这条记载的可靠性,要么给出另外的起源解释,总之这样的争论不会让已经熟悉汉文化的突厥青年感到愉快。而参与争论的唐人,由于深信唐朝官修史书《周书》(稍后流传更广的《北史》还加以转载),对突厥青年的回避和否认也一定大大的不以为然。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唐朝上层社会的青年中还颇有一批人倾慕突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为代表),对突厥的游牧社会投注了浪漫的想象和向往(比如承乾太子就梦想着到突厥去当个将军),他们不会觉得以狼为祖的历史追溯有什么不妥。当他们以羡慕和赞赏的语气说起突厥的狼祖故事时,他们怎么也无法理解突厥青年所感受到的羞辱和愤怒。
《周书·突厥传》记有两个不同的突厥起源故事,都涉及狼祖先。一个是这样的:突厥汗族阿史那氏的祖先部落遭到邻国血洗,只剩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虽然邻国士兵起了恻隐之心不忍杀害,还是砍了他的双脚,弃于草泽。一只母狼衔肉来给男孩吃,救了他的性命,他长大就和母狼交合,使母狼怀孕。尽管他最终还是被邻国国王派人给杀掉了,但母狼幸得逃至高昌北边的山里(阿尔泰山?),生下了十个男孩,其中之一就是阿史那。大概由于细节比较生动,这个故事对后世读者的影响最深。《周书》又用“或云”的方式,在母狼传说之外记下了另一个起源故事,根据这个故事,突厥的祖先阿谤步出于匈奴以北的索国,有十七个孩子,“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伊质泥师都“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娶二女,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阿史那就是伊质泥师都的孙子。阿史那的儿子被立为阿贤设(可还原为Aslan Šad),遂开创其后突厥的历史。《周书》在记载了不同的起源传说后,总结了一句:“此说虽殊,然终狼种也。”很显然编纂《周书》的史臣们遇到过史料选择的困难。突厥起源竟有多种说法,难以确定何者为正,史臣们只好把两个说法都记下来,好在两个说法中都有狼生的因素,可以笼统地确定突厥“终狼种也”。
《周书》的处理方式显示出唐初史臣某种值得表扬的谨慎,但还不能据此就认定他们见到的突厥起源传说只有这两种,也就是说,不能假定他们没有排除掉其他的说法,特别是与狼生无关、不足以证成突厥为狼种的那些说法。《酉阳杂俎》有一条就是与狼绝不相干,称“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还记有射摩舍利与一位海神女交往的经历。这种海神故事似乎与突厥向中亚发展的历史有关,而类似的起源故事也许还有多种,经过史臣拣选淘汰,就只剩下两种与狼生有关的说法进入了正史。研究者认为,多种起源传说的并存,说明突厥帝国的多元构成。换一个说法,起源传说的丰富多样,说明突厥帝国还没有完成对历史叙述的整理,还没有使某些记忆沉寂下去直至遗忘。《酉阳杂俎》还有一条说“坚昆部落非狼种”,似乎是强调黠戛斯的历史起源不同于突厥,可见唐人已经有“突厥为狼种”的基本认识了。也许就是因此,《周书》这样解释突厥人在旗杆顶端置金狼头以及侍卫被称为“附离”(böri,狼)的原因:“盖本狼生,志不忘旧。”
这一史料要想在现代历史学中确立其历史真实性,还要经受一番现代史学方法与观念的审视。首先我们不能认为唐朝史臣所记录的突厥起源,与突厥汗国官方的历史叙述是一致的。现在已无法确知古代王朝如何获取和整理有关域外的史地知识,估计总是以各类使者的出使报告为基础的,当然也有对域外来使的采访所得。不过,这些知识得自中间人的必定居多。所谓中间人,在中古时期主要是粟特人。突厥人自己也有同样的说法吗?突厥人也会讲述狼祖故事吗?迄今所见突厥汗国方面的文字史料,无论是突厥文还是粟特文,都没有提到狼生起源。第一汗国的粟特文布古特(Bugut)碑,第二汗国的鄂尔浑突厥文三大碑,都叙及汗国历史,但一点也没有提起狼族传说,不能不让人起疑。一些学者开始质疑《周书》里的狼生故事,怀疑狼生传说是一种外界的而非突厥自己的认知。著名突厥学家克劳森(Sir Gerard Clauson)1964年发表了一篇《突厥与狼》,怀疑把突厥说成狼的后裔是中国人的编造,目的是贬低和侮辱突厥人。这种将信将疑的局面在布古特碑发现后有了转变。前不久刚刚去世的著名突厥学家克里雅什托尔内 (S. G. Kljastornyj)在1971年发表了有关布古特碑的报告,认定布古特碑残破的碑首刻的是一只母狼哺育小儿的形象,这使得对突厥狼祖传说颇有怀疑的学者也顿时沉默了。

然而争议还远远没有结束。嗣后这么多年来,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布古特碑的学者越来越多,对碑首“狼乳小儿”主题的怀疑开始出现。我自己于2006年夏天参加一个考察队在蒙古中西部考察,曾到达著名的花园城市车车尔勒格(Tsetserleg),观摩收藏在后杭爱省博物馆的布古特碑。如果不是有母狼乳儿的先入之见,说实话现场感觉难以看得那么清楚。不过,我在一个月后代表考察队所写的考察日志里,不敢表达这种疑惑,仍然写道:“蒙蒙细雨中,碑身和龟趺都有一点黯淡的赭红色,碑顶部母狼以乳哺幼儿的雕像,虽然残缺有三分之一强,但还是那样鲜明。龟趺是中国式的,但模仿的意味很重,在似与不似之间。”这个“似与不似之间”其实也是我对整个碑首雕像的印象。回国后很长时间,我经常看我们从各个角度拍摄的照片,越来越怀疑母狼释读的可靠性。
有这种怀疑的人显然还不少。2011年3月Michael Drompp在美国东方学会年会上发表会长致辞,题为《内亚独狼》(The Lone Wolf in Inner Asia),对布古特碑首的雕像进行细致的分析,他并不怀疑狼雕像,但他否定了狼身下的小儿,因此碑首的雕像是对中国式碑刻形式的模仿,只不过用狼替代了龙形的六螭而已。Drompp的这个质疑还比较慎重,但他指出碑首是对中国碑刻似是而非的模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2012年初冬我在纽约大学的古代世界研究所(ISAW)与著有《突厥在中亚:考古与历史研究》的Sören Stark聊天,说到布古特碑的性质与所谓母狼主题的问题,他并不赞成母狼说,他认为那只是龙(六螭),但因为粟特人不善于处理石头材料,对中国碑刻的形式和技艺又不熟悉,所以碑首龙不像龙,碑趺龟不像龟。——我说这些,当然不是想证明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否定母狼雕像,事实上证据还很不充分。2013年夏天我在土耳其和参与土蒙两国联合调查古突厥遗迹项目的Cengiz Alyilmaz再一次谈起布古特碑,他依旧坚信那是母狼哺育小儿的雕像。
突厥人是否称自己为狼种?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旧唐书·突厥传》记录突厥毗伽可汗对唐朝使者袁振所说的话,有“吐蕃狗种”,是贬斥吐蕃的话。游牧文化并不贱狗,恰恰相反,狗是人类最亲密的朋友,所以成吉思汗最勇猛的四员战将被称为“四狗”。可是“狗种”的说法就不一样了,是以狗为祖宗,所以在毗伽可汗心目中就具有了低贱的性质。中国史籍中称犬戎、槃瓠之类为狗种,既含有前古典人类学的分类意义,又多少含有贬斥和轻蔑,是一种蔑称。在这个意义上,很难想象突厥人会自称狼种。但是,草原上可能很早就流传着狼生故事了。《北史·高车传》叙高车起源,就讲了匈奴单于的小女儿与狼为妻产子“滋繁成国”的故事,曲折生动,既解释了高车何以在语言和文化上与匈奴接近,且被称为匈奴的外甥(匈奴单于女儿所生),又解释了为什么高车人会有类似后世蒙古长调那样的音乐形式(“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多有研究者据此认定,狼生传说深植于突厥语(Turkic)各人群的历史记忆之中。
突厥与高车的狼生故事并不见于其他突厥语人群,特别是不见于这些人群自己的历史叙述。出于高车的回鹘(回纥)与唐朝关系最深,却不见这类记录。有学者举出阿尔泰系各人群中部族、官称、地名或人名多有以“狼”(čino,böri等)为名者,以论证狼祖传说在阿尔泰文化中的普遍性。其实以动物入专名,是人类各文化的普遍现象,和狼祖传说没有直接关联。也有人举成书于13或14世纪的察合台文《乌古斯可汗传说》(Oghuz-nāme)中灰狼引领乌古斯可汗出征的例子,说明狼在维吾尔等突厥语族群中的重要性。可是作为向导的狼,与作为祖先的狼,完全不在一个价值平台上。狼作为向导引导英雄走出困境,是草原文学一个很重要的叙事母题。《魏书·穆崇传》记穆崇遭困,遇白狼引领得救,道武帝“命崇立祀,子孙世奉焉”。穆崇家族世祀白狼,会不会被不知原委的人另作解释呢?有意思的是,这个母题还影响到中国北方。《宋书·王懿传》记王懿(仲德)从北方南逃时,遇洪水阻路,“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号,号讫衔仲德衣,因渡水”,王仲德由此得救。这像是王仲德到江左以后自己所讲的故事,很可能他借用了当时北方人已比较熟悉的白狼引导英雄脱困的草原母题。
研究者早就注意到突厥狼祖传说与乌孙王昆莫被母狼乳养的故事颇为相像。《史记·大宛列传》记张骞叙昆莫之父所在的小国为匈奴所灭,婴儿期的昆莫被丢弃在野外,“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匈奴)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昆莫长大后率旧民复国,即乌孙国。张骞大概是在西行途中听说这个建国故事的,当然不一定是乌孙国自己的官方叙述。与突厥狼祖传说不同的是,昆莫受狼乳养之后,并没有和狼交合,乌孙王族的祖先里面并没有一只母狼。不过,在古代草原游牧社会里,生与养是同等重要的。既然接受母狼乳养而得成长,那么认狼为母亦可谓顺理成章,尽管有一点小小的跳跃。这种跳跃是文化传播(神话母题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流动)过程中常常会发生的变异。从这个认识出发,我认为突厥和高车的狼祖传说并非自突厥语诸部族自身文化传统中生发出来,其原型母题是西域地区乌孙和其他印欧语社会古老的部族英雄得到母狼乳养的传说,这一起源母题的背后,正是古印欧语(Proto- Indo-European)各人群所共享的古老的“神话-传说”传统。
印欧语系各人群中母狼乳养英雄母题最著名的传说,就是罗马缔造者孪生兄弟罗慕洛(Romulus)和瑞穆斯(Remus)被弃于野外时被母狼乳养的故事。这个故事随着罗马城、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的辉煌成长,向北非和近东弥散,成为重要的艺术题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Guitty Azarpay有一篇文章《近东艺术中的罗马孪生兄弟》(发表在Iranica Antiqua第23卷,1988年),列举了大量有趣的例证。这个母题还出现在中亚7世纪的苏对沙那(Ustrushana)地区的一个壁画里。两年前去世的德国近东考古学家Burchard Brentjes有一篇《苏对沙那君长的艺术与宗教》(刊于三卷本论文集Orientalia Iosephi Tuccimemoriaedicata的第一册,1985年),有最为集中的描述和分析。不过对于东西方印欧语人群来说,这个故事母题的起点并不是罗慕洛兄弟,应该还有更深远的渊源。古波斯有关祆教创教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幼儿期传说中,有他先得牛马庇护,再得母狼喂养的故事。不过由于狼在祆教教义中属于恶魔之兽,祆教徒把这个故事略加改造,说母狼把琐罗亚斯德接纳进狼窝以后,专门去抓了一只母羊来喂养他,可参看Mary Boyce《早期祆教史 》(A History of Zoroastrianism: The Early Period, 1975年,第279页)。东方之外,古日耳曼人群中也有很多同类型的传说,比如条顿英雄齐格弗里德(Siegfried),传说他母亲在生下他之后就去世了,他靠着一只母狼的乳养才得生存。在这个专题上,Kim McCone《印欧语系的狗、狼和武士》一文进行了全面探索(载于W. Meid主编的Studien zum indogermanischen Wortschatz,1987年,第101-154页)。
乌孙王昆莫受母狼乳养的传说就属于印欧语古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一故事母题向中古突厥语(Turkic)各部族(突厥与高车)的传播,其实是突厥语自身从蒙古高原向西发展的结果。对于突厥语早期的西向扩张,我有一个假想,就是“突厥汗国之前的突厥化”,指的是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之间,大致上就是匈奴帝国崛起至柔然帝国覆灭这个时段内。匈奴以单于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在进入漠北建立帝国统治之前,是说某种伊朗语(Iranic)还是说某种突厥语 (Turkic)或蒙古语(Mongolic),我们这里不加讨论,正如亦邻真先生所指出的,进入漠北之后的匈奴势必经历突厥化过程。柔然的统治部族虽然说某种古代蒙古语,帝国的基础和主要力量却是突厥语各部族。因此,匈奴和柔然帝国时期,突厥语人口向西深入扩张,统治并同化了西部草原地带各原伊朗语部族,我称之为早期突厥化过程。即使在两个帝国之间的无帝国时期,这个过程也在持续进行中。这一过程的历史成果,就是最终推翻柔然帝国的,竟是从原伊朗语地带崛起的突厥部族,以及西突厥汗国能够动员足够的人力物力实现对中亚的持久统治。原伊朗语人口被卷入突厥语世界,古印欧语人群的许多文化因素也随之进入突厥语社会。我认为母狼乳养英雄这一母题就是这样进入某些突厥语部族的,这才引发了由乳养向狼生叙事类型的转变。
而在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崛起之前,蒙古草原上也有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蒙古化过程,也就是相当多的突厥语人口逐渐融入蒙古语部族。这个过程中,狼祖和狼生的母题也被吸收进某些蒙古语社会的起源传说中。余大钧先生说:“成吉思汗远祖原为山林狩猎人,后来走出山林西迁到草原上转变为草原游牧人,因此既继承了狩猎人祖先母系氏族时代的鹿图腾观念鹿祖母传说,又继承了草原游牧民的狼图腾观念狼祖传说,这样就形成了《秘史》开卷所载的成吉思汗祖先为苍狼、白鹿的传说。”这一解读代表了蒙古学家比较共同的认识。其实《蒙古秘史》并没有标明孛儿帖赤那与豁埃马阑勒的性别,现代学者的这种理解显然是凭借了大多数社会里先父后母的表达习惯,只是这未必符合该起源传说的本意。世界范围内的起源神话往往有某种特意的模糊,孛儿帖赤那与豁埃马阑勒就是这种类型的模糊先祖,不应该按照现实中的雌雄原则去探讨他们的结合细节。
母狼乳养英雄这一故事母题中的母狼,早已超越了现实生活中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的那些狼,而具有某种神性和天意。因此,起源传说中的狼,不可以与游牧生活中威胁羊群的狼划等号。崇祀狼祖的游牧人,出门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尾随他的畜群的那些野狼。生活中的狼,从来就不是人类的朋友。突厥语和蒙古语典籍中,多有以狼骂人的话,骂者绝不会认为这是对传说先祖的冒犯。《魏书·官氏志》记代人姓氏改革,“叱奴氏,后改为狼氏”。叱奴,即《秘史》之“赤那”(čino)。我认为,《魏书》这条记事很可能是有讹字的,改为“狼”虽然保存了原姓的字面意义,却与汉文传统有一定的不合,所以我猜这里其实是改为“郎”氏。清代满人八大姓中有钮钴禄,钮钴禄(Niohuru)即满语之狼,后改为郎氏,便是同一个道理。当然,叱奴也好,钮钴禄也好,尽管可能出自他们的部族称号,但丝毫不意味着这些部族曾经以狼为图腾,更不意味着这些部族会有狼祖起源的历史记忆。
跨语言跨文化的起源母题传播,在汉语社会中也有很多例证,槃瓠(盘古)传说就是最著名的一例。而母狼乳养英雄这一母题从印欧语人群进入阿尔泰语人群之后,也慢慢进入了汉语社会。华夏传统从没有母狼乳养某位先祖的故事类型,先秦时代只有“南蛮起源”的楚国有人接受过雌虎的乳养。《左传》宣公四年记楚国的子文初生时被弃于云梦泽,“虎乳之”。华夏(汉)社会里接受狼乳的先祖故事出现得很晚。今甘肃庆阳市庆城县有“狼乳沟”,说是周先祖后稷被母狼哺育的地方。《庆阳县志》狼乳沟条下,引《太平寰宇记》云:“陕右庆阳府有狼乳沟,乃稷弃于野,狼乳之地,后人遂以名沟。”《太平寰宇记》其实没有这一条。后稷传说最早见于《诗经·大雅·生民》和《史记·周本纪》,但都没有说后稷得到母狼乳养的事。《诗经》称“弃之陋巷,牛羊腓字之”,《史记》不提牛羊乳养。《艺文类聚》卷十引《史记》,则称“弃之陋巷,牛羊乳之”。但毕竟都不曾提及母狼乳养。把庆阳狼乳沟与后稷联系起来的文献证据,我能查到的最早出自《明一统志》卷三二:“狼乳沟,在邠州南二里,世传即后稷弃而狼乳之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转载了这一说法,遂造成更大影响。可见母狼乳养母题引入后稷故事里,当在宋元间。
狼祖传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并不会自动出现在任何与狼有密切接触的人类社会里。有人倾向于认为狼祖故事证明游牧社会与狼有着更加深切的历史联系,在我看来就是没有看到这类故事母题对于游牧文化来说,也是一个舶来品。我想,这类古老母题的跨文化跨语言流动,真是在在显明了历史本身的丰富与生动。
(本文原载于《文汇学人》2015年3月6日刊,原题为《作为历史的狼祖之说》。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























- 曲终人不散
- 3起整治形式主义典型问题被公开通报
- 六部门发文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 物美首批千款商品上线多点“外贸优品”专区
- 广东韶关: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80万元

-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二十艘神舟系列载人飞船
- 歇后语,“芝麻开花”的后半句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