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怪物迷恋:我们想象出来的怪物总是不得善终
“人人都怕血,觉得恐惧。一看到血人们就变了脸色,忘了自己的血液就藏在柔软敏感的皮肤下的静脉里。”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短篇集《怪诞故事集》中的《真实的故事》)

《怪诞故事集》,[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著,李怡楠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一位体面的教授,就在扶起一个脑袋撞到雕塑开始流血却被漠视的女人之前,还感到安全和放松,只因为沾上了陌生女人的血,成了警察的目标、人群中的瘟疫。人们害怕和他接触,像绕开那个流血的女人一样逃离他。他像所有受害者一样,难以理解针对自己的仇视。

《玛丽·雪莱》电影海报
所有受害者中,无法避开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1831年再版的自序中说,她总是被问到,一个尚年轻的姑娘怎么能构思出如此可怕的故事。初版发表时玛丽只有20岁,尽管如此,已经历了急于从中醒来的人生。玛丽的生母也叫玛丽,产下她十几天后就去世了。后来父亲威廉娶了另一个名叫玛丽、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玛丽则常常独自去母亲墓前读书。(电影《玛丽·雪莱》)珀西·雪莱便是在这块墓地中与玛丽约会的,当时他正停滞在第一段婚姻中。玛丽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带着继母的女儿克莱尔,与雪莱私奔,而雪莱的妻子当时正在怀孕。《弗兰肯斯坦》是在私奔的两年中写下的。自序中,玛丽说写下故事时珀西就在身边,这也许是相较此时珀西已经因船难去世而言的。私奔中的玛丽多病、孤独,她和雪莱的生活因负债而窘迫,而雪莱频繁与克莱尔外出。玛丽的第一个女儿因早产夭折,起初她以为自己只是唤不醒她。她写信给友人托马斯·霍格,“此刻我不再是一个母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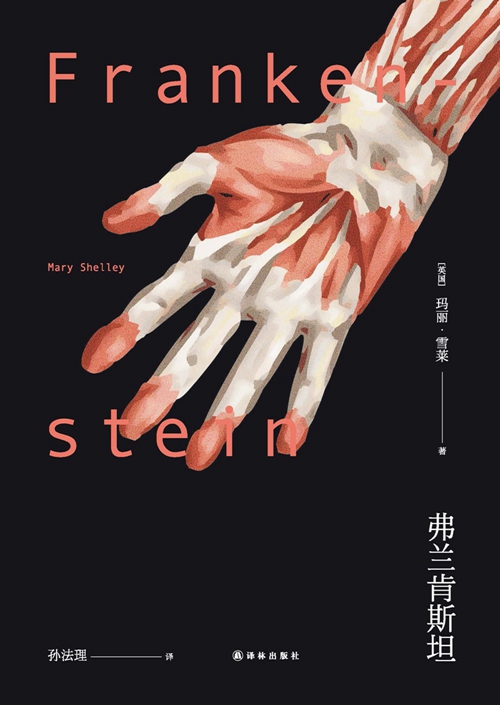
《弗兰肯斯坦》,[英]玛丽·雪莱著,孙法理译,译林出版社
《弗兰肯斯坦》初版(1817)名为《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如同东方神话中的女娲,普罗米修斯也是以泥造人的造物主。玛丽命令弗兰肯斯坦承担了“被自己造物所吞噬的恐惧”(阿西莫夫称为“弗兰肯斯坦情结”),怪物则继承了出现在这个世界非我所愿的悲剧感。他本来仁慈善良,苦难却把他变成了恶魔。玛丽· 雪莱写《弗兰肯斯坦》是一个造物的套娃。有人说女儿夭折后,玛丽曾梦见过女儿复活了。尽管这个故事的公认起源是玛丽做了一场白日梦,梦里弗兰肯斯坦一发现怪物活了,拔腿就跑,希望怪物因为遭遗弃而死掉。他睡着了,又惊醒,发现怪物就在自己床头注视着他。玛丽吓得睁开双眼,也许梦的最后,玛丽将自己代入了弗兰肯斯坦。同时,玛丽感受到的痛苦,也是怪物痛苦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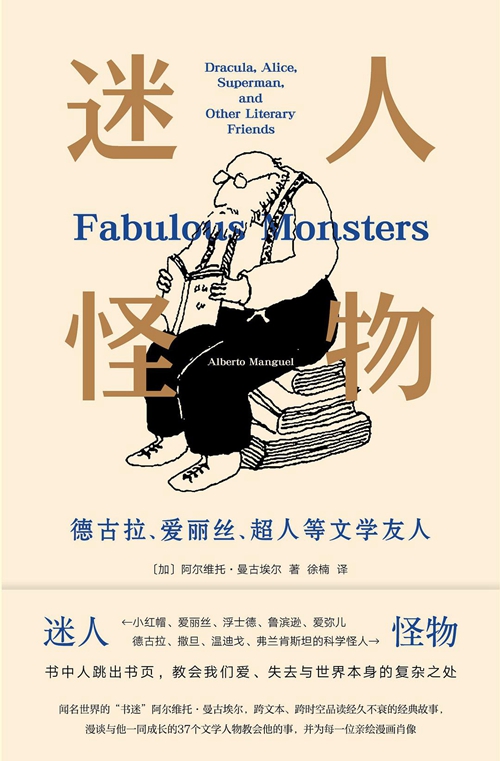
《迷人怪物》,[阿根廷]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徐楠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玛丽·雪莱钟爱《失乐园》,小说所引其中的‘创造者,难道是我请求你用黏土塑我为人?难道是我祈求你拯救暗黑中的我?’是怪物也是她的诘问,她还用《失乐园》教会了怪物自学识字。这样的玛丽·雪莱的碎片有许多。弗兰肯斯坦名维克多,维克多正是雪莱用过的笔名,弗兰肯斯坦的亲人都被科学怪人杀害,包括弟弟威廉,威廉也是玛丽夭折的孩子之一。唯一没有被赐予名字的是怪物,我们常误称他弗兰肯斯坦,把他与他的造物主混淆起来。又或者,我们没有混淆。加尔维托·曼古埃尔将怪物的脸孔比作道林·格雷的画像,(加尔维托·曼古埃尔《迷人怪物》)是“非人的自我”。丑陋的脸“并不意味着‘恶’,只是令人厌恶。”弗兰肯斯坦恐惧的,是这面多个人体拼接而成的扭曲的镜子,投映出他“不想记住或不敢记住的东西”,这也是让我们感到恐惧的东西,或许也是玛丽内心的恐惧。

《德古拉》的作者布莱姆·斯托克
布拉姆·斯托克认可恐惧的价值,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他相信“书中必要的恐怖和恶行,只会通过引发人们的恐惧和同情而净化人们的思想。”(吉姆·斯坦迈耶《谁是德古拉》)

《谁是德古拉》,[英]吉姆·斯塔迈尔著,刘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爱尔兰人,如果不是身处亨利·欧文、沃尔特·惠特曼、奥斯卡·王尔德的光环之间,人们也许会在为这部小说惊讶之前更早看见他的才华,但倘若没有他们传奇动荡的生活,或许他也不会创造出永生的文学形象,并成为不断衍生的母题——德古拉。奥森·威尔斯曾说《德古拉》的伯爵简直和欧文一模一样,伦敦兰心剧院演员亨利·欧文也是斯托克的老板。评论版的《德古拉》直接将欧文饰演的梅菲斯特作为封面,还得到了认可。吉姆·斯坦迈耶并不认为斯托克用吸血鬼代替雇主以实现复仇式的致敬。一旦走近,德古拉这个人物(怪物?)像一个装满镜子的房间,这些人彼此连接,为了回答《谁是德古拉》这个问题,构成的却是斯托克的生活。仿佛是他们在斯托克内心投下的影子不肯离去,互相重叠,而德古拉就此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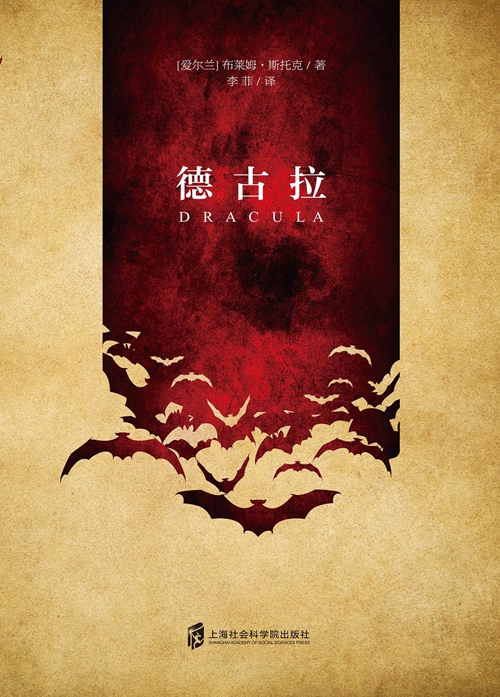
《德古拉》,[爱尔兰]布莱姆·斯托克著,李菲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斯托克崇拜沃尔特·惠特曼,尽管惠特曼因为一些粗俗不雅的诗句饱受争议,斯托克却始终对他抱持热忱,替他辩护,在德古拉身上为他延续风格。他曾经给惠特曼写过长信——迟疑过但最终还是寄了出去——向惠特曼倾诉自我,并坚定地相信自己也能得到惠特曼同样的认可。惠特曼的确给他回了信,两人甚至还见过面。虽然惠特曼比德古拉强壮得多,但就“身高、力量、蓬松的白发和胡须而言,两者有惊人的相似”。德古拉的语言也使得这部作品“带有一种优美和出人意表的诗意”。 而德古拉暧昧的欲望、阴郁的气质、对墓地的狂热,如果不是吸血鬼天性使然,更像是读惠特曼而养成的脾性。
而同样被抨击的奥斯卡·王尔德,却没能得到斯托克的包容,在斯托克包括回忆录在内的文学作品中彻底被放逐。王尔德是斯托克童年时期的朋友、读书时的校友,斯托克的妻子弗罗伦丝曾经是王尔德的未婚妻。和亨利·欧文、女主演艾伦·特丽、剧作家萧伯纳等圈内人一样,斯托克和弗罗伦丝都曾是王尔德的支持者和恭维者。而“如此伟大的王尔德”陆续发表了令评论界哗然的《W.H.先生的肖像》《道林·格雷的画像》,对和《自深深处》的收信人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之间的传闻也不加遮掩,被审判入狱后更遭遇了众叛亲离。
故意被雪藏的,恰恰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吉姆·斯坦迈耶追溯了斯托克情节的手稿,认为当时王尔德的“堕落”刺激了吸血鬼通过咬伤受害者、将他也变成吸血鬼这一设计。王尔德的言行,对斯托克所在的社会来说,带有腐蚀性的力量,正从年长者蔓延至年轻人。王尔德在接受审判回答什么是“不敢自我表白的爱”时,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它是智性的,它不断出现在年长者和年幼者之间,年长者有才智,而年幼者眼前是生活的愉悦、希望和魅力……” 文明社会的人急于逃开也不愿面对他带来的影响,就像逃避一场道德瘟疫。正是这种恐惧驱使下的新规则——传染性——的建立,将这部小说从“一部超自然的阴谋之谜变成一出超自然的道德戏剧”,而“吸血鬼猎人们要寻找的不只是一种解决的方法,他们必须发现救赎之道”。
用十字架作为击退德古拉的护身符,也是斯托克加入吸血鬼小说中的重要意象,而这也与王尔德有关。王尔德送过弗罗伦丝一枚金十字架以示订婚,爱情信物在现实中被退还,但在小说里留了下来。斯托克认为它保护了妻子免遭本可能由她承受的爱情悲剧,它也要继续保护人类不受怪物的侵略和伤害。
怪物非人,但又类人,被边缘化的怪物们要么渴望成为或回归人类,要么企图报复要将人类同化成怪物,前者反映了人类的自我优越感,后者允许作者寄托悲悯。“我们想象出来的怪物似乎总是不得善终。”加尔维托·曼古埃尔提到一种叫客迈拉的怪物,它已被击败,不再活跃在即便是想象的世界中了。与其说是怪物,它更像一个符号,不再指向怪物是否真实,而是我们是否逃避真实。“而我将向你展现不同的东西/不是清晨在你身后阔步行走的影子/也不是傍晚起身与你相遇的影子/而是一杯尘土中的恐惧。”(艾略特《荒原》)托卡尔丘克还讲过一个听来的小故事:小男孩总在夜里看到一个人,父母安慰他,姐姐吓唬他,他就这样渐渐长大也把这种恐惧遗忘了。直到最近,这个回忆儿童时光的老人说,当他抽着烟望着窗外,看到玻璃窗上自己的影子,想起了幼时的恐惧。他大吸了一口气,却不知道还能叫谁。“那一刻他也感到了真正的轻松,父母自有他们的道理——外部世界其实是安全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