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今天为什么还要读格林伯格?
文 / 沈语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在有关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的各种说辞中,有两种颇具代表性:一种说他已经过时了,另一种说他是绕不过去的。但说格林伯格已经过时了,跟说他是绕不过去的一样,都是过于宽泛的悠悠之谈,未能切中要害。要害在于格林伯格的批评方式乃至批评态度,一直萦绕在以《十月》(October)杂志批评家群体为代表的当代艺术批评中。这种批评关注艺术的品质,注重批评的本质和限度,正如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所说:“批评应当是这样的,如果X,那么Y。”亦即批评应该说清楚它能说之物,对于不能说之物则保持沉默;批评不是撰写抒情散文或卖弄辞藻和理论的场所。
反之,单纯说格林伯格是绕不过去的,也没有落到实处:在何种意义上是绕不过去的?是在艺术史和批评史的层面上,还是在批评理论的层面上?如果是前者,那么他早已被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当然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是后者,那么是他理论中的哪些问题仍处于需要回答的紧迫性之中,使得他不仅成为批评家中难以超越的巨擘,而且成为艺术理论和美学史的承续者或鼎革者,进而成为悠久美学传统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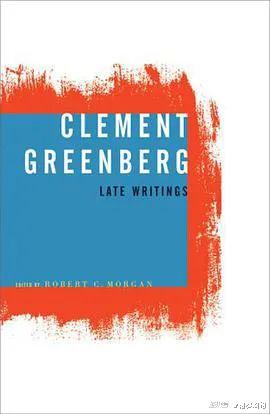
Clement Greenberg, Late Writings
Clement Greenberg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国内对格林伯格乃至整个西方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译介和研究,相较于类似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哲学理论和思潮的研究,是远为滞后的。原因可能是艺术界一直缺少一种为学术而学术,或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当我翻译了格林伯格生平唯一的自选集《艺术与文化》,又出于厘清学脉、考镜源流的缘由翻译了从现代主义内部批评他的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的名著《艺术与物性》(Art and Objecthood),以及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的杰作《另类准则》(Other Criteria)时,艺术界(包括艺术家、批评家和艺术史家)会不约而同地表示惊讶:沈先生为什么要反对自己?他们以为既然我翻译了格林伯格,那就有义务为格林伯格背书,因此也就必须刻意回避对他的批评。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实用理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态度。而我认为,格林伯格的批评理论要是站得住脚,那么,听一听不同方面的声音,正是确定其历史方位和理论要点的不二法门。
另一方面,当我在国内率先批评阿瑟·丹托(Arthur Danto)的三段论艺术史观——从瓦萨里(Giorgio Vasari)的再现论艺术史观,到格林伯格的媒介自我批判的艺术史观,再到他本人的“艺术史之后”的艺术史观——从而在某个层面上为格林伯格辩护时,[1]某些人又认为我出于党派立场(党派在这里应被理解为现代派、后现代派这样大而无当的划分)为格林伯格背书,因此这成为他们更为惊讶的来源:对来自现代主义内部的批评,我觉得可以接受;而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我则无法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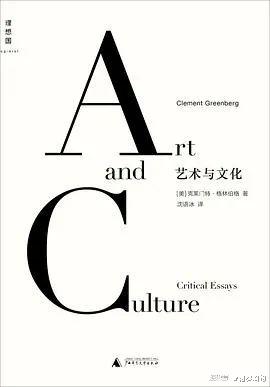
艺术与文化
[美] 克莱门特·格林伯格 / 著
沈语冰 /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实情远非如此。眼下当然不是对阿瑟·丹托之攻击格林伯格进行再批评的时机,但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也许是有必要的。对于我的现代性图景,如果说读者还有所了解的话,应该能够明白,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我眼里根本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对现代性的总体反应中某些不同的面向和不断加剧的趋势而已。事实上,我对现代主义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和观点多有批评(例如阿多诺),而对后现代主义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和观点则多有吸收(特别是理查德·罗蒂)。因此丹托对格林伯格的攻击,如果说还有什么理论意义的话,这意义远不止于简单的“党派立场”差异,而在于在哪些问题上,他俩的不同理论观念是处于交锋状态,而非意气、态度和立场之争?
这正是《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晚期文论集》(Clement Greenberg: Later Writings)值得一读再读的原因。这本书的编者罗伯特·摩根(Robert C. Morgan)所写的《导论》已经相对清晰而系统地勾勒了格林伯格晚期写作的时代背景,交代了编辑他晚期文集的意义,但他对其中的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的说明,还远不够充分和清楚。

摩根在《导论》开篇伊始就指出了格林伯格晚期写作所面临的时代已经变了。那是所谓的现代主义式微,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现代哲学、法国后结构主义)盛行的时候,这样的时代背景“瞬间将格林伯格‘解构’了”[2]。伴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变迁,文化批评已经取代了艺术批评,格林伯格那种“基于品质、独创性或个人趣味之上的判断被认为既不相干也太独断”[3]。我认为亲身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学”流行的国内读者应该不难理解当时的情形。即使是90年代以后出生的艺术学生,也不难从父辈那里了解那些年所发生的变革。
跟这一时代背景的总体变化相应,艺术界发生了两大新变:一是商业主义裹挟一切,二是意识形态变得更为活跃、两极化甚至歇斯底里。对于这两点,摩根均有言及(但又不够深入)。首先他说明了上世纪70年代之后艺术发展的侧重点已经转向商业性质的艺术,驱动力来自爆发性质的新兴市场。特别是“在新的经济压力下,艺术机构被迫屈从于逐步升级的现代艺术的市场价值,独立批评家的角色即使不被攻击也面临着挑战”[4]。然而,正如摩根所正确指出的,格林伯格从不相信市场是造成“糟糕艺术”的原因,但格林伯格似乎忽视了利益扩张与随之而来的损失(人们对他视为关键的问题丧失了兴趣)之间的秘密联系。我认为这一点也不难解释,因为自由主义者很少将问题的症结归结为市场经济或商业主义——不管什么样的问题,艺术问题当然也不例外。遗憾的是,格林伯格不仅并不追究商业主义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不是问题的要点),也不追问新的商业主义环境与他所主张的艺术观的衰落之间的关系。因此,人们可以提出来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市场价值能否从审美价值中独立出来?当两者发生对立甚至冲突时,格林伯格,或者说一个持有格林伯格式美学观的人将如何取舍?

塞尚,《红屋顶城堡》(1885),布上油画,65cm×81cm。私人收藏
摩根指出的格林伯格所面临的第二大新变,同样值得大书特书——那就是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根据摩根的复述,格林伯格的对策同样化繁为简、斩钉截铁:“他相信对自身审美兴趣的保护是文化得以源远流长的表现。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承认艺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分离。”[5]而这同样激起了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大部分强调语用(或实用)效果的后现代主义,以及几乎所有女性主义阵营在内的知识界的围攻——这些“主义”虽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对审美价值可以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的这种观点的批判。因此,读者可以提出来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审美价值能否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艺术与政治意识形态究竟能否做到适当的分离?
关于第一个问题,格林伯格的前后思想其实经历了较大转变。在前期,特别是在其文《先锋派与庸俗艺术》(Avant-Garde and Kitsch)里,他的先锋派艺术概念,是在与庸俗艺术的对立中成立的。所谓庸俗艺术,在格林伯格那里有着明确的所指:既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艺术、斯大林主要用于宣传的艺术,也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艺术。因此,从前期的主要倾向看,格林伯格所赞成的先锋派艺术与他所批判的政治化和商业化的艺术存在着明确的对立,也说明了先锋派艺术不可能包含商业艺术,商业艺术也不可能进入先锋派艺术。到了中晚期,由于格林伯格政治立场的改变(从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向政治自由主义的转变)他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市场经济或商业主义并不能影响、更无法改变艺术的审美价值,即从根本上说,商业主义与艺术品质问题无关。这些观点在他的晚期写作中反复出现。到晚期,他的主要观点成了高级艺术(先锋派艺术当然包括在内)总是取决于少数艺术家事业的前十年,即在他们的作品被公众和市场接受之前的十年,市场并不能影响其作品,因此当他们的艺术成功地进入公众视野和市场时,其作品品质的倾向已经确立。从艺术史的以往经验来观察,这好像总是正确的。但是格林伯格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急骤扩张,艺术品已作为稀有资源成为资本最主要的争夺对象之一。形势已经完全改变了:现在,不再是艺术品去寻找市场和资本,而是资本和市场在寻找潜在的投资对象。因此,格林伯格大可以以个人趣味为由,将沃霍尔(Andy Warhol)等明星艺术家和市场宠儿干净利落地打发掉。而且,我相信,根据推测,他也可以将杰夫·昆斯(Jeff Koons)、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等人同样干净利落地打发掉。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当艺术品不断地被拍出天价,资本市场将艺术品当作潜在的投资对象和需要争夺的稀缺资源时,艺术品生产和消费的整个环境已经彻底改变了。所以,关于艺术与资本,或者说艺术品的审美价值与商业价值之间关系的全部理论,需要被重新加以论证。

在对格林伯格的所有批评中,我认为没有比以下批评更为常见、更为猛烈的了:格林伯格那种试图将审美价值从政治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的观点是幼稚的、不可能的。我已经在《格林伯格的政治与美学》和《格林伯格的双重遗产》等文章[6]中,对格林伯格的接受史,特别是格林伯格关于艺术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复杂性的理解,提供了许多说明和阐述。这里,我想补充一个新的观点:我认为与其纠缠在艺术的审美价值能否从其历史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这样一个纯理论问题,还不如澄清格林伯格的关切究竟是什么。目前,从学界的大趋势来说,无论是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还是从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以及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那里,已经很难再听到艺术的审美价值可以从政治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的说法了。即使在西马一端,关于艺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性的论说,也足以构成从强势的(或硬性的)到相对中立的,再到弱势的(或柔性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整个光谱。例如,在关于纽约画派的研究中,居尔博特(Guilbaut)认为抽象表现主义乃是美国政府发动的意识形态战争产物(尽管他本人反对认为抽象表现主义乃是美国政府阴谋的产物),采用的就是一个硬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国家或政府的主导观念;克拉克(T. J. Clark)认为抽象表现主义乃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抗”,采用的是一个相对中立的意识形态概念——半真半假的流行观念和符号游戏;莱杰(Michael Leja)认为抽象表现主义乃是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主体性建构的产物,采纳的则是一个柔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一套隐性符号系统。[7]尽管他们彼此之间对艺术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但总的来说都坚持认为艺术不可能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左派如此,包括后现代主义的保守主义在内的右派同样如此。[8]

毕加索,《山上房屋》(1909),布上油画,65cm×81cm。私人收藏
细观格林伯格的晚期写作,可以明显地发现一个意思更清晰的表达,即他并没有(如摩根所说的那样)想要将审美价值从政治意识形态当中分离出来。他反复强调的是,艺术可以有其历史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但是艺术最初的(或者说最基本的)形态应该是审美价值的载体。换言之,格林伯格并没有为以下强论辩辩护:审美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价值,可以而且应当从其他价值中分离出来;而是说在艺术所拥有的各种价值中(它们可能交织在一起,难于截然分开,但是正如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中,仍然存在着“双方”),审美价值应该有其优位性(priority)。我认为这个论辩大体上是可以得到辩护的。正如我本人在中国艺术史的语境里反复强调的那样,艺术品当然可以作为考古材料(所谓美术考古),也可以作为历史证明(所谓图像证史)——请注意美术考古和图像证史在我国语境里的大肆流行——但艺术品首先是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亦即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和风格存在于世的独特物。因此,从这个角度说,从形式和风格上研究艺术品(特别是对艺术品做出审美判断)也应该被赋予某种优位性。
而这正是格林伯格的意思。例如,在《批评的现状》(States of Criticism)一文里,他首先批评了当前的艺术批评只讨论艺术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等等,就是不讨论(或忽略)审美价值:“艺术将会被解释、分析和解读,会在历史地位、社会、政治等方面被提及。但是,那些把艺术作为艺术(而非别的东西)来体验的回应却被忽略。”然后,他十分清晰而又坦率地承认:
艺术可以被当作一些别的东西来谈论,比如作为文献,作为征兆,作为纯粹的现象。它确实被越来越多的人津津乐道,其中评论家对它的谈论并不比艺术史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要少。这没有什么不对的。只是,它不是批评。适当的批评意味着首先把艺术当作艺术,这意味着要处理价值判断。[9]

假如我们可以承认格林伯格所要辩护的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甚至如摩根所说的)一个强论辩,即将审美价值从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当中独立或分离出来,而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弱论辩,即在艺术的诸种价值中强调艺术本身的价值亦即审美价值的优位性,那么,我想我们就获得了对格林伯格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艺术批评家的一个新的历史定位:我们可以把他定位于欧美哲学和思想传统中那些强调传统重要性的价值维护者和文化维护者之中。

布拉克,《伊斯塔克的房子》(1908),布上油画,73cm×60cm。伯尔尼美术馆收藏
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传统的重要性有着充分认知。没有传统,就谈不上创新,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却是迥异的。学院派也讲传统,甚至可能比人们一般理解的先锋派更讲传统,但是学院派所讲的传统只是僵死的教条,而格林伯格所讲的传统则是艺术品质量的动态比价关系。格林伯格反复强调的一个针对普通学者和大众对现代艺术的最大误解,就是现代主义是某种无奈之举,是迫不得已的创新,是为了使自己的艺术比肩于古人,而不至于沉沦。格林伯格反复强调马奈的重要性,就是证明这个观点的一个例子。在他的晚期文集中,马奈可能是被提到次数最多的艺术家之一。马奈的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缘于使19世纪后期的绘画品质不至于全部沦落到学院派水平的动机。出于这个目的,他果断地抛弃了学院派,转向委拉斯开兹和戈雅。当然他也吸收提香和乔尔乔内(Giorgione)的绘画,这种现代化的策略同样高明无比。因此,如果没有威尼斯画派和西班牙画派的传统,人们很难想象马奈的成就。这就是马奈的意义。
另一个在传统与创新之间艰难探索的例子,毫无疑问应该是塞尚。看一看塞尚是如何在大师与印象派、大自然与人造技术、恪守惯例(固有色、立体造型、明暗)与创新技法(外光、透视变形、色彩渐变)之间来回跋涉、循环往复的,就能够明白,没有一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创新不是在传承有序的传统中实现的。但是,人们决不能将格林伯格对传统重要性的强调,与学院派那种因循守旧相混淆(早在《先锋派与庸俗艺术》一文中,格林伯格就将学院派形容为回避艺术中的大问题、专门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的“亚历山大主义”)。我认为,跟T. S. 艾略特一样,格林伯格是20世纪上半叶少数几个能把西方艺术的传统和创新问题讲清楚的人之一。相比之下,他同时代和稍后的那些研究现代艺术的名家不是大讲特讲“新异的传统”(the tradition of the new),[10]就是沾沾自喜于“新艺术的震撼”(the shock of the new)。[11]

塞尚,《浴女图》(约1895),布上油画,47cm×77cm。哥本哈根奥德鲁加特收藏
关于这一点,格林伯格在其早期写作中已经多次指出,但是没有比他的晚期文集中说得更多、更清晰的了。例如,在《现代与后现代》(Modern and Postmodern)一文中,他指出:
与一般人的看法相反,现代主义或先锋派登上历史舞台时并没有与过去断裂。不仅如此,它并不是按照计划出现的,它压根就没有计划,这再次与一般的想象不同。它也不是一堆观念或理念或意识形态。相反,它本质上代表着一种态度和方向,即对标准和水平的态度和取向:审美品质的标准和水平是其起点也是终点。那么,现代主义者从何处找寻他们的审美标准和水平?答案是,从过去,从过去最优秀的艺术中寻觅,但不是寻觅特定的模式……而是通过对过去最卓越的艺术审美品质的融会贯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最终获得。[12]
这段话无比清晰地表达出了格林伯格对现代主义之于西方传统的承续性的看法。我看根本没有必要让我唠叨个没完,再去解释如此清楚的意思了。但奇怪的是,我有一个感觉,我相信许多读者仍然无法理解格林伯格为什么说现代主义第一不是与传统的断裂,第二没有一套理论或事先形成的计划,第三与传统最卓越艺术的比价关系是通过并只能通过趣味(或审美品质)来实现。
让我举个例子吧(对不起,仍然是格林伯格本人举过的例子,但我认为我有资格为他的例子增加一些分量,考虑到在过去差不多三十年里我从事的唯一工作就是现代艺术研究)。那就是布拉克、毕加索、马蒂斯的正例,以及杜尚的反例。
先说布拉克、毕加索和马蒂斯的正例。格林伯格在某个语境里谈到,在1907年的巴黎,当时有许多优秀的画作并非出自布拉克、毕加索和马蒂斯之手,然而,回过头去看,人们却不得不承认这三位画家创作了当时最强有力的作品,“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仔细审视了塞尚”[13]。因此,第一,毫无疑问,布拉克、毕加索和马蒂斯的创作绝非是和塞尚的断裂,而是承续;第二,布拉克等人并没有从塞尚那里发现一套现成的理论或模式,他们自己也没有一套现成的理论或模式(特别是考虑到毕加索和马蒂斯后来的发展);第三,他们只是“仔细审视了塞尚”,发现了某种方向感。格林伯格在另一个语境里解释了为什么仅仅仔细审视了塞尚,就造就了后来者——“为了一跃成功,你最好能分辨出在你之前最优秀的艺术家是谁;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像他们那样画画,而是为了给自己施加足够的压力”[14]。“审美压力”“传统或惯例的压力”,几乎成了格林伯格的口头禅。

亨利·马蒂斯,《舞蹈II》(1910),布上油画,260cm×391cm。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
关于杜尚的反例,格林伯格也讲过多次。在收入本文集的《研讨会之六》(Seminar 6)中,他再一次提到,杜尚几乎没有掌握立体派的真正要领。从杜尚安装的第一批“回收物品”,如1913年的《自行车轮》和《酒瓶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明白毕加索的第一幅拼贴画是关于什么的。这就是格林伯格认为的“前卫主义”(Avant-gardeism)——请注意正好对立于前卫派或先锋派(Avant-garde)——出岔子的根本原因:由于不理解刚刚过去的传统中最好的东西,杜尚走歪了。这样说也许会让读者误以为格林伯格在心目中画出了一条现代主义的直线,其实不然。仔细审视塞尚和掌握立体派的要领,并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可能性或唯一的答案,不然就无法解释毕加索(与布拉克)和马蒂斯开出了两条“后塞尚”的道路。格林伯格在这里的意思只是:从审美上去理解塞尚和立体派,处在与塞尚、立体派的压力关系之中,才是正解;而杜尚却选择了逃避,选择了一种轻松打发而不是直接面对的方式,化解了立体派的压力。对杜尚更为同情的研究也表明,这不是杜尚是否理解或误解立体派和毕加索的问题,而是他有意识地想要离开以立体派为代表的最近的传统,并在对这一传统的偏离中加入新的规则,从而改变既定游戏规则的问题。[15]

杜尚,《下楼梯的裸女No. 2》(1912),布上油画,151.8cm×93.3cm。费城艺术博物馆收藏
关于杜尚,人们当然还会继续跟格林伯格争辩。但是,至少从格林伯格的角度看,传统与创新的辩证法具体体现在趣味满足和期待视野,以及游戏的高度严肃性之中。所谓趣味满足和期待视野是指(不是定义,而是解释):假如没有由传统构成的期待视野,那么也就没有趣味的满足可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传统,那么就没有可资期待的视野,人们也就无法从趣味上对艺术品进行判断,于是不得不引进新的游戏规则。创作上如此,鉴赏上同样如此。而游戏规则的不断改变,也许会促成大量新颖有趣的事物出现,但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可持久发展的文化却始终无法建立起来。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不断引入变量的前提下,人们就无法对任何事情做出评判。所谓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比较才能有品质观念。在出现无数变量的情况下,品质的观念就无法得到维系。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格林伯格对跨媒介的批判,或者用迈克尔·弗雷德的话来说,当代艺术演变成了一场跨媒介的剧场性的雪崩。[16]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当代艺术进行评估,可能还为时过早,即使要讨论,势必也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但是有一个评估指标也许相对可靠,那就是被认为与格林伯格同样重要的批评家阿瑟·丹托在担任《纽约时报》艺评专栏作家期间,推出了哪些艺术家。与格林伯格拈出的众多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和色域画家相比,哪些艺术家得益于丹托的批评?安迪·沃霍尔?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过去的三四十年没有重要的艺术家和艺术现象,而只是说,与20世纪上半叶,或者哪怕与六七十年代相比(基本上是格林伯格活跃在批评界的时间),最近三四十年并没有形成一种类似艺术文化的东西。
这恐怕是解释本书编者摩根提到的以下现象的根本原因:
尽管不可能每个学生都拥护诸如《先锋派与庸俗艺术》中所表达的关于文化的辩证观点,或者非常赞同格林伯格对20世纪初期艺术家的批判性分析,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惊讶地发现,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的许多观点看上去愤世嫉俗且含混不清,如今看来却鞭辟入里,让人如沐春风。[17]
重复一遍,现在还不是评估20世纪后期美国艺术(或欧美艺术)的恰当时机,但我相信,重读格林伯格的重要著作,特别是重审他貌似简单直白、实质深刻复杂的观点,确实有利于读者,哪怕是一个中国读者,建立起自己的方位。因为正如编者所言:“倘若没有出类拔萃的艺术,文化将变成尘垢糠秕;倘若没有文化,文明将烟消云散”[18]。我们当然还不能说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西方文化处于低谷,但是认为它仍然处于高峰的乐观主义者会越来越少。
注 释
[1] 参见沈语冰, 哲学对艺术的剥夺:论阿瑟·邓托[M]//20世纪艺术批评.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3。
[2] GREENBERG C. Clement Greenberg: Late Writings[M]. MORGAN R C (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x.
[3] 同[2].
[4] 同[2], xiii.
[5] 同[2], xii.
[6] 均收入沈语冰. 图像与意义:英美现代艺术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7] 分别参见GUILBAUT S. 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Abstract Expressionism, Freedom and the Cold War[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T. J.克拉克. 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M]. 沈语冰、诸葛沂译. 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4;T.J.克拉克.告别观念:现代主义的若干片段[M]. 徐建等译. 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迈克尔·莱杰.重构抽象表现主义[M]. 毛秋月译. 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
[8] 哈贝马斯区分了传统的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保守主义,参见他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9] 同[2], 87.
[10] ROSENBER H.The Tradition of the New[M], New York: Horizon, 1959.
[11] 参见罗伯特·休斯.新艺术的震撼[M].欧阳昱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9。
[12] 同[2], 27.
[13] 同[2], 149.
[14] 同[2], 187.
[15] 详见德·迪弗.杜尚之后的康德.沈语冰等译. 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
[16] 参见弗雷德.艺术与物性[M].张晓剑、沈语冰译. 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3。
[17] 同[2], xxii.
[18] 同[2], xxiii.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50期,原题为:今天为什么还要读格林伯格?——《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晚期文论集》导言)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