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棉花帝国》读书会③︱流动的全球化能否跳脱“中心论”?
4月13日,复旦大学董少新教授发起的东亚海域史研究团队,联合艺术考古读书班,共同习读并讨论了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此书出版之后,在学界内外均引起广泛反响,并在近日格外成为中文知识界的焦点。
十余名校内外师生围绕此书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讨论。话题涵盖物质文化的全球流通、资本主义与全球史书写范式、“棉花帝国”与中国、陶瓷与棉纺织品的差异等等。本文在尽可能保证对话临场感的基础之上,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与润色,并经发言人审阅。限于篇幅,本次读书会整理稿分三篇发布。本文为第三篇。
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想象,还是一个历史实在?
王鑫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大家读这本书的第一观感,都是先被棉花吸引了,再读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是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
说到资本主义,可能之前读的《白银资本》让我印象太过深刻。贡德·弗兰克几乎把资本主义给解构掉了。我想,假如弗兰克来看这本《棉花帝国》,恐怕会有一些意见。因为整本书对资本主义做了一个历史研究,认可资本主义的确存在;而弗兰克的观点是,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或制度本身,就是被制造出来的,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弗兰克大概会对贝克特说,“你描述的这些事实是可以存在的,但你把这些事实组合在一起,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历史,那我不会同意。”这种归纳可能是不会被弗兰克所接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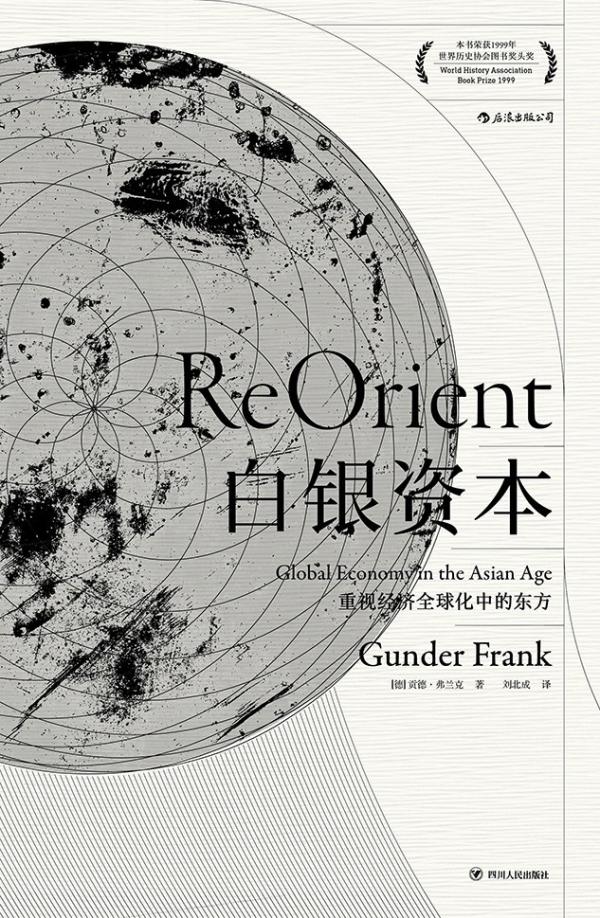
《白银资本》
另外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刚才几位同学也说了,斯文·贝克特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但弗兰克或许会说,“你认同资本主义本身就是认同西方中心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就是西方中心的。”所以《棉花帝国》这本书,虽然作者自称不认同西方中心主义,但是从他描述的事实来看,还是西方主导的一个帝国。因此在阅读的时候,我会两头摇摆。当然这只是我自己提出来的一些疑问。
刚才也有老师提到,这本书里对中国的提及比较少。我对此也有同感。我的理解是,作者在构建这本书的框架时,对于棉花帝国来说,他设置了一个边界。所以他提到美洲、欧洲、非洲和印度,但是棉花帝国再往东边,似乎就停在那里,不继续跨出去了。这可能是因为假如把18世纪以前的中国棉纺织生产纳入进来,就会跟原本设定的叙述出现矛盾。因此他可能做了有意地回避。因为整本书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的全球组织和全球分工,但近代早期的中国似乎又不是一个完全已经被改造成原料提供地的国家,而是独立运转于作者所界定的棉花帝国之外的系统,二者之间的衔接或纳入是有困难的。
当然,往后面做就可以衔接进去了。到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边界已经扩大到中国了,这是近代以来的新变化。所以姜伊威将这个时段纳入他的框架里,是可以自圆其说。
高晞
我突然想到的是,这本书里讲到全球资本主义、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但我们中国有个词是民族资本主义,在这之前或之后是否有人讨论过,为什么会存在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家应该是对应洋人的,但他们有什么特征呢?上海还有很多的报纸,他们用什么词来称呼这些民族资本家?
姜伊威
首先是1905年上海发生了影响力非常大的抵制美货运动,到1920年代上海总商会拥有了比较大的文化话语权。这个过程里,商人结合民族主义,进行了很有意图的自我形象塑造。当时会用“大王”来称呼某个领域的巨头,英文报纸有的会说industrialist。而“资本家”这个词,根据南京的徐天娜、上海的蒋凌楠老师,还有大连的刘孟洋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作为社会主义文献中的贬义词被翻译进来的,所以1920年代的时候没有人承认自己是资本家,譬如早期共产党人讨论过中国是否存在资本家的问题,他们和穆藕初论战,穆藕初就说我们根本不算什么资本家。

穆藕初
但有意思的是,“殖民”在当时的中文里是一个褒义词,梁启超写过《中国八大殖民伟人传》,1915、1916年的时候,南洋发家的华人像陈嘉庚、简照南,当时的上海小报都用表彰态度称他们是“华人殖民家”,但资本家在1920年代、1930年代一直就是贬义词。
董少新
这本书还忽略了一点,就是转口贸易。譬如欧洲人从印度购买的棉花不仅仅贩卖到欧洲、美洲或非洲,还有很多棉花是贩卖到中国,而中国的棉布还在不断出口,这一环节被作者忽略了。中国仍然是棉花帝国中的重要一环,如果作者更深入地挖掘前人研究,以及东印度公司档案这类史料,构建出亚洲转口的棉花贸易、以及亚洲本土商人经营的贸易,是可以补充这个环节的。
这可能是原始资料运用不够导致的。王希先生在导言里说“棉花帝国树立了一个研究质量的标杆:真实的全球史研究必须要有全球性范围的史料的支撑。”我也一直谈史料,而使用全球范围内的原始材料,恐怕是没有人能做到的。但这不等于这一点不重要。如果能用到更多的原始资料的话,我想这本书的论述会更扎实。
邓菲
我再补充一点。里面说到1766年纺织品占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全部出口货品的75%,然后在“战争资本主义”的部分,他讲到国家资本主义在18世纪后期的出现,使得欧洲对于进出口的管控非常严格。这是我们之前不知道的一个面向。1685的时候英国就开始管控进口商品,到1766年还是有那么大宗的纺织品贸易。期间经历了加税或者禁令,也就是说一度成为非法的贸易。所以进口是不是就像董老师说的变成了转口贸易?但另一方面,18世纪的欧洲,棉布也作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背后的元素可能很复杂,值得从不同角度思考。
董少新
我想再讨论一下,什么是欧洲中心论,这个概念需要梳理。并不是谈了欧洲就变成欧洲中心,它是19世纪的一个意识形态。它从欧洲历史本身去追溯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发展的渊源,分析它的各种各样的长处和优胜的生产关系,并且从而控制全世界,同时以轻蔑的这种心态对待所有非西方世界。
它带有一种歧视性,所有非西方世界都是落后野蛮的,都是不发展的品质,都是闭关愚昧的,甚至根本就被解决。“没有我们来用枪放来打你们,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发展出现代社会。”
这才是欧洲中心论的核心。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一本书——由于它的研究对象是那个贸易体系和网络——就是欧洲中心论。我们不可否认,在全球网络形成过程中,欧洲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就是赞成欧洲中心论。这是历史事实。
但是这本书里也还存在些许欧洲中心论迹象。所有欧洲的部分,作者可以称其为“我们的”,所有非欧洲的部分他称为“他们的”。作者是欧洲人,这种书写立场我们也能感受到,有一定合理性。他在书末做了一些反省和补充。
邓菲
他其实在澎湃的访谈中专门回应过这个问题,明确地讲自己是从欧洲出发。他也相信如果从中国出发,会有更丰富的视野。
《棉花帝国》给了我们什么启发?
戴若伟(复旦大学文博系硕士生)
我想就物质文化研究分享两点感受。第一,这本书给我的启发是通过商品如何去讲,全球视野的空间叙事。空间有不同大小的单位,例如经纬度、国家、区域,半球或大陆。通过商品连接空间,我认为一个优势,即“流动性”。康拉德在《什么是全球史》中,唯一一次引到《棉花帝国》,是第6章《全球史中的空间》,此处康拉德提到了一个词,叫做“跨地方流动性”(translocal mobility)。他说:“商品的历史则要跨越漫漫时空,追踪某些特定物品,其中最有名的要数糖、棉花、大豆、瓷器、玻璃。这些研究探究了生产地与消费地等不同地点之间的互联性,呈现出商品对个体家庭以及大型群体和社会机制的影响。而研究商品链的历史学家会更加关注市场波动与历史进程的相互交叠,考察制度条件对劳动和商品的流动轨迹的影响。此类研究最初是经济史的一个分支,但后来也成为文化史的用武之地,为审视工人和企业家,银行家和商人、购买者和消费者的动机与世界观提供了契机。商品链的重建非常清晰地显示出劳工和商品的跨区域流动,学者们通过研究某些特定地点,证实了结构的存在,这些结构促进了全球交流,同时也限制了全球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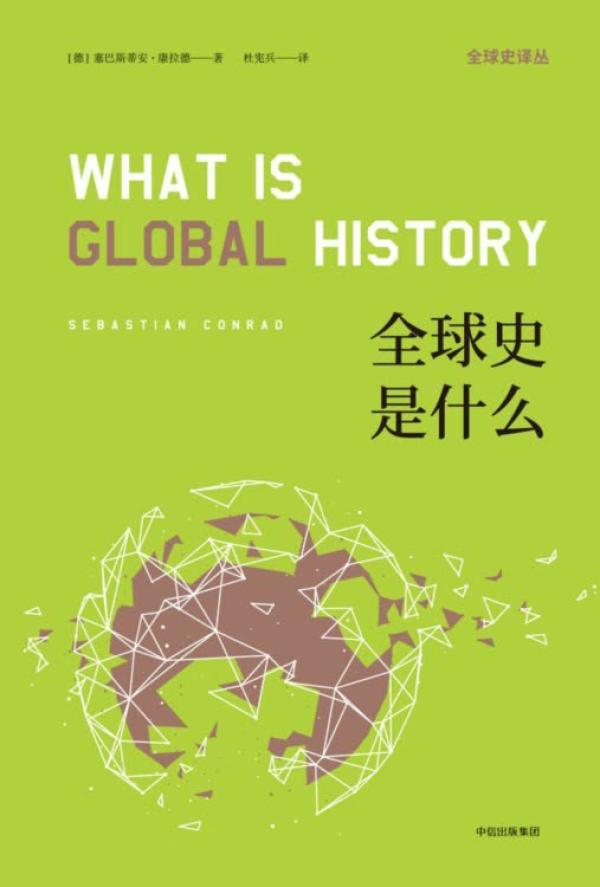
《全球史是什么》
他也提到棉花之外的其他商品,这就引出我的第二个兴趣点,那就是读棉花的全球史,不能只读全球史里的棉花。这里有两个层次,首先是棉花和其他全球商品的关联。比如说糖——西敏斯写过《甜与权力》,主角便是“糖”。它也是三角贸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和棉花有紧密关系。《棉花帝国》这本书里虽然有谈到,但是棉花和其他全球商品关联,这本书写得似乎不够。其次,棉花与其他纤维制品的关系。尽管贝克特提到了合成纤维在1990年代中期的生产量超过了棉花,但这个数据可能是要怀疑的,因为有研究表明,合成纤维在1945年之后出现了成指数的增长,在1978年与原棉产品产量齐平。羊毛、亚麻、丝绸等等,都是值得被关注的。棉花和其他纤维制品之间互相替代、互相牵扯的关系,还需要利用更多数据去探究。
此外,棉花在变成全球商品之前,英国国内是以羊毛制品为主,棉花对羊毛的替代速度有多快呢?英剧《南方与北方》里面,女主角来自南方,她到了北方之后才知道,cotton这个词指的是棉花,而不是北方的粗羊毛制品。棉花在英国国内获得广泛认知,可能也值得站在一定时间线上思索。
张梦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硕士生)
我阅读过程中受到的启发首先是视角,以棉花作为切入点。在以前受过的教育里,似乎提到工业革命首先想到的都是比较火车轮船等大型产业,对于棉花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但是通过这本书阅读,感到棉花产业才是工业革命的摇篮。
从方法论层面上,作者对我有两点启发。一是作者对于资本主义概念的新阐释,他提出了战争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三个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行阐释。
第二,我们经常说要有全球史的视野,但是历史研究者有国界和立场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怎样真正地超越民族国家?我们经常说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做真正的全球史,以及要有全球化的学术关怀。前段时间读羽田正先生的《全球化与世界史》,他批判了日本世界史研究的弊端,认为或多或少仍有本国中心的立场和视角局限;羽田正提出“地球公民”的概念,我觉得有点理想化的,因为现在各国的学者可能都在进行全球史研究,这是一个大趋势,但我个人感觉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全球史的研究可能最终需要各国学者共同努力推进。像刚才我们提到澎湃对贝克特的访谈,他想要以中国为中心,但研究者个人的能力都有局限。
另外,我认为我们应该区分历史事实和各种“中心论”。就像有些学者也批评中国中心论,拿古代的朝贡体系举例子。但我认为,要更全面地结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去探讨,而不能随便扣帽子。
胡涵菡(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生)
我读这本书时,比较关注作者在叙事框架中的空间安排,让我想到何安娜老师的新书《青花之城》,其中也反复提到了地方和全球这样一组空间概念。她指出,研究景德镇的诞生和发展,应该统合地方因素和全球因素,留意地方因素和全球因素参与全球进程的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它举了一个例子,为了理解饶州瓷器的外观和质感在13世纪发生的变化,就必须同时考虑地方因素(如窑址附近的原材料供应情况)和全球因素(比如游牧民族和中亚伊斯兰世界的瓷器消费者对大型器皿的需求)。她认为这种综合性的视角是理解特定的历史时期变化的关键。《棉花帝国》在叙事空间的安排上也是这样。一方面棉花资本主义的叙事突破了国家史和地方史的框架的局限,另一方面作者在写作中也没有完全割裂新的叙事与它们的关联。
成卓(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硕士生)
刚刚老师们也提到了,这本书对中国的叙述比较缺乏。我认为可能与棉花产业的运作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融入中国原有的稳定的小农经济的体系中是有关的。第一章作者也说到,其实元代棉花的种植就已经在农村非常普及,甚至到15世纪,中国的农民可以用棉花去抵税,这说明棉花种植已经国家的赋税体系产生了联系,完全融入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模式中去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也有提到一种关于棉花种植方式的记载,说通过水稻和棉花的轮作来提高产量,或者使得土地变得更加肥沃等等。可见,棉花在那时与其他的经济作物都几乎没有功能上的差别,服务于小家庭自给自足使用,有剩余就用来缴纳赋税,而非用于贸易或者商业,来换取利润。这《棉花帝国》书中所描绘的以商业贸易为基础的产业链条是有本质差别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在棉花帝国形成早期,中国难以融入以欧洲为中心的这样一种棉花贸易模式中去。
郑智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硕士生)
这本书里可以看到资本家的路径。首先棉花是从农业种植、生产到消费,是一个完美的闭环。在这本书里能看出来,好像这些资本家们设计了这个闭环之后,不断地优化每个环节,不断填充更多的棉花,然后更多的资本进去。这个闭环帮助了他们完成了一种无限的资本沉淀,就像有了路径之后进入了一种自动驾驶的模式。
但是刚才听到“洋布自织论”我很震惊。似乎有些揭示了李约瑟的问题。西方人带着路径思维去开拓棉花产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渠道商人,这种新型商人的出现,让种植与生产以及统筹产业链条的资本家不再是整个产业的唯一主导,这样的迁移,也让纺织品行业打开了一个,以渠道或品牌商人主导的,带有流行文化色彩的消费市场。
秦莹(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硕士生)
印度的棉布进入英国以及在英国被接受,作者也提到,这个花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对照《棉的全球史》,里面提及印度棉布进入英国之后、当时英国人的反应。棉布不易褪色和轻薄等特性,被英国人接受。与此相关,我还想到,英国的棉花和棉纺织品是如何跟印度或其他地方的棉纺织品竞争?《棉花帝国》的作者似乎叙述得比较简单,但是,印度和其他地区早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技术,英国的棉纺织品是机器生产,除了价格优势,质量或其他方面是否有不一样的地方?
《棉的全球史》和贝克特都提到,非洲对于棉布的需求比较多样,甚至不同村庄的要求都不同。《棉的全球史》中提到西非的消费者对于想要购买哪种棉布都有着明确的认识,譬如想要更简单的条纹和方格图案的棉布,并且喜欢更鲜艳的颜色。英国在出口棉布的时候也做了很多调查,逐渐开拓市场。
《棉的全球史》这本书更偏向物质文化,如果两本书结合起来看,可能会感受更深。
《棉花帝国》第二章里面作者说有些开端的重要性是在历史回顾时才得以彰显。之前课上老师说过,很多事件的意义都是后来人赋予的。棉花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很常见,但可能我们对它太习以为常了。贝克特在这本书里面提到自由劳工产生的过程,比如一开始是奴隶,后来是工人,他们最开始没有什么权利,工作时间很长,通过漫长的运动抗争获取了比较合理的劳动权益。我想我们和研究对象还是要保持一定距离,分析和探讨起来会更加清楚。
汪炀(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生)
与邓菲老师同样注意到绪论第8页中“对棉花帝国所做论断不适用于其他商品”的说法,前面讨论也认为棉花帝国相较糖、茶、瓷器等商品,涵盖由原产地、运输、交易市场、工厂加工等一系列资本主义规模生产化的环节,故而看起来具有“不可替代性”。某种意义上而言,这里也是贝克特较为绝对化的论断,更为恰切或谨慎的说法是棉花与“资本主义”(更为精确的,贝克特本书所定义的资本主义)具有更强的亲和性。
贝克特在此前的澎湃答问中回应本书有接受霍布斯鲍姆、布罗代尔以及马克思等人的启发,故而其资本主义的定义也更加注重市场网络与管理机制(当然也有生产技术,在第9页中“那些煤矿、铁路和巨大钢铁工厂的形象”)这样生产性的一侧。但像绪论注释最后一条,贝克特回顾此前聚焦某一特定商品的研究,其中最早的文思理/西敏司(Sydney Mintz)《甜与权力》一书,从(饮食)人类学着手、在生产之外结合了西方内部消费与社会区隔对糖流通的促进,由此若从消费一侧评估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像桑巴特从奢侈来立论),这就显得选取这类商品更具契合性;或者若从思想以及更为文化性的层面来看,反倒是古登堡革命以降的印刷制品对阐释这一层次下的资本主义更为有效。故而,选取不同的对象来串联,潜藏着学者各自对“资本主义”的不同理解,棉花帝国作为设定就是贝克特理解的延伸,而棉花帝国似乎也成为了其理解的合法性担保。(并且书中贝克特就资本主义在市场网络的一面与生产中心的一面上有摇摆与纠结,文中就离开东方与重回“全球南方”似乎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论说。)
另外是在这一脚注的末尾,贝克特引述了大卫·哈维对资本主义与空间的研究论著,这一点就像前面学姐所说是更为宏观性的空间机理,不同的中心变动,或是沃勒斯坦“中心—边缘”讨论的延伸。但其实如果注意到书中内附的插图,像在西方内外的生产空间(在附图中出现了纺织厂这样现代工业建筑图景),人员、资金的流通网络(在附图中出现了库房、船舱、交易所,以及当时公司绘制的种植者、经纪人、制造商之间的网络图示),以及在全书开篇收尾作为lead-in的商会交易所、棉花工业遗产,全书更为隐喻性的棉花帝国本身的网络性以及棉花帝国的中心转移,都是各种层次空间化机理的呈现。这样其实是资本流动与增殖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空间对传统吞噬的过程(具体也并非贝克特那样线性的、还是不可避免在用欧洲的发展眼光在标定,相关默会性知识与知识的无产阶级化如同景德镇的陶瓷技艺以及艾约博《以竹为生》一书的阐述),遗存及其场域对当下记忆构建与反思的过程,以及这样均质化、碎片化、等级化的空间机理在当下以棉花帝国之外形式运作的过程,相应从其中挖掘蕴含抵抗/变革可能性的过程(空间的其他层次主要是可参考列斐伏尔的论述)。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