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没人能抵御来自中情局的甜蜜诱惑

“甜牙”是伊恩·麦克尤恩在同名小说中虚构的英国情报机构行动代号。这次行动,军情五处计划通过复杂资金管道赞助十位作家,包括帮他们安排与有地位的出版人会面、举办朗诵会、暗中策动评论界关注他们的作品、用微妙方式推动这些作品获奖。此项行动的十分之一——如果精确评估的话——结果不尽如人意。考虑到这部分行动的当事人恰好是小说的男女主角(同时也是隐含的共同叙述者),那就几乎算失败。原因说起来也属寻常:所有这类机构以及他们所制定的计划,不都是粗心大意,屡屡忽略格雷厄姆·格林所谓“人性的因素”么?
这笔钱,分到每位作家头上的数目不能算多。有点像是(就小说中这位男主角来看)——可以让他们向生活讨一个长假:暂停赖以糊口的职业工作,专心写点一直想写而没时间写的东西,海鲜餐厅的“专属座位”,前菜点香槟和牡蛎,再加上几瓶口味上佳的白葡萄酒。虽然项目设计者看起来多少有点骄慢——他把行动代号设定为“sweet teeth”(甜牙,喜吃甜食),是一早就认定那些作家无法抗拒这诱惑,但涉案所有作家都欣然接受这宜人的安排,甚至当我们的男主角完全清楚金钱背后的秘密时,他仍然(当然他有一个更加文学的理由)保持沉默,签收按月给付的款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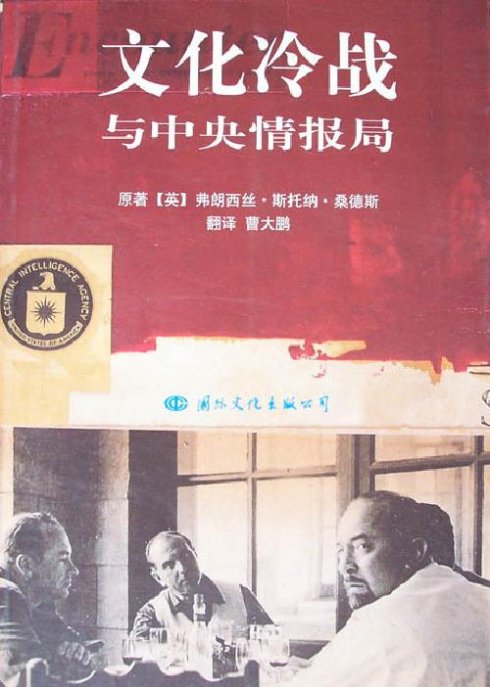
让我们猜一下,麦克尤恩之所以想到“甜牙”这个词,很可能跟他在小说最后致谢辞中提到的那本书有关(在致谢名单上位列第一):弗兰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那本书第七章的标题是“糖果”。实际上,麦克尤恩从那本书中得到的东西不止一两个关于起名字的灵感,比如那段关于“文化冷战”标志性事件的描述(在小说第十八章),1949年(在小说人物口中时间被说成1950年)纽约华道尔夫·阿斯托利亚饭店举行的“文化科学领域争取世界和平大会”,其喧嚣且又诡奇的场景,小说家大体上照搬桑德斯书中(第三章)的叙述细节。
但这无关紧要(小说家有天然权利处置素材)。重要之处在于:在阅读麦克尤恩小说和桑德斯那部当代史发掘著作后,读者多半能体会到相通的(两本书共有的)感受。从六十年代走出来的麦克尤恩,最近连续写作两部长篇小说,描写被纳入体制的“才华之士”的尴尬生活状态(前一部《追日》涉及学院机构和学科建制,这一部《甜牙》有关冷战背景下的文学体制),但《甜牙》在这种挫败感之外,更有一种气馁和沮丧,这种感受,我们从桑德斯书中不厌其烦地大量罗列人名和书刊机构名称的做法上也能玩味出来。这种感受,也正是萨义德为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所作书评(发表于《伦敦书评》1999年9月)中使用的那个词组dispiriting truth——这个让人气馁的真相是:(萨义德视野中的)“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形象,几乎没有(few)人能抵御这种(在本书中即是指来自中央情报局的)甜蜜诱惑(blandishments)。
让我们跟着桑德斯列举:T.S.艾略特,奥登,安德烈·马尔罗,伯特兰·罗素,约翰·多斯·帕索斯,阿瑟·库斯勒,乔治·奥威尔,以赛亚·伯林,戴安娜和莱昂内尔·特里林,丹尼尔·贝尔,玛丽·麦卡锡,雷蒙·阿隆,克劳德·莫里亚克,克罗齐,汉娜·阿伦特,米沃什,热内,《党派评论》,《肯庸评论》(Kenyon Review),《塞万内评论》(Sewanee Review),纽约芭蕾舞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抽象表现主义……
直接或者间接(通过所谓grant-making institutions),明知或者并未意识到,在秘密机构运作下,这些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文化形象受到各种曲折微妙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被纳入冷战体制。
萨义德这篇书评,有个看似捣蛋实则毒舌的标题:《嗨,先生,你想要脏书么?》(Hey, Mister, You want dirty book?)这句话出自开罗大街上一名小书贩之口。当时萨义德先生二十岁刚出头,正站在阿兹巴齐亚花园(Ezbekieh Gardens)旁的集市中,说完这句话,小贩就指给他看那堆书:“只要五个皮阿斯特。”在那些日子里,五个皮阿斯特可以买三块菜煎饼(falafel)。
小贩指给萨义德看的书是《失败的神》(The God that Failed)。他快速翻阅一遍,也许有点失望,因为一点都不“脏”。后来他跟父亲提起出版商,才知道这家公司跟开罗美国大使馆有关,而后者在开罗广泛发放各种图书,不要钱。萨义德说,这是他与那些知识界重要形象和文化符号的首度“相遇”——尽管特地声明这纯属pun unintended,但他显然故意使用“encounter”这个词。《失败的神》的作者是一批“转向”的前共产党人(或“同路人”)包括纪德、斯隆、库斯勒,全都是欧洲知识界大人物。
多年以后,萨义德在哥伦比亚大学找到工作,结识特里林和玛丽·麦卡锡等纽约知识圈名人,阅读、讨论——没有明说,但显然承认——受他们影响。随后,萨义德开始在《党派评论》和《肯庸评论》发表一些论文。
萨义德用简要勾勒的几幅场景回溯年轻时代的精神生活,以及(也许更重要)阅读史,试图解释他那种“沮丧”因何而起。那些他曾阅读过、思考过,也单纯地质疑过的观念和人物形象,被桑德斯这本书指证,说他们被秘密诱导,积极投身于一场世界性文化大冷战。尤其他在桑德斯书中看到,为发表他的论文与他通信的《肯庸评论》编辑,本身就是一名中情局特工。
冷战期间,秘密机构介入写作、出版、国际会议、演出、展览各项事业,此类故事遭人揭露不是新闻。每一次孤立曝光事件照例引发一阵喧嚣,有人质疑,有人失望,也有人“信者恒信”——因为现代读者内心深处早已相信,文本与作者无关。但桑德斯讲的故事要复杂得多,不仅仅是被揭露对象的数量——数量确实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如果一个读者发现在他个人阅读史上,对他形成某种观念有重要影响的作家,有相当大一批都直接或间接地领取冷战秘密机构津贴、参加由秘密机构赞助的旅行和会议、在秘密机构操控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作品由秘密机构通过貌似中立的出版人组织出版和多语种翻译,同时以各种微妙方式向各种读者和各种奖项评委推荐,这个读者将会如何回顾和审视自己业已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乃至——美学趣味呢?
简单的办法是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某种阴谋论。但阴谋论之所以是阴谋论,恰恰是因为它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观察世界,让自己在幻觉中安心(因为明知是幻觉)。或者把那些档案文献解读成某种事实上无效的意图——机构已设置、计划已制定、资金已散发、会议已召开、著作已发表,但这些并不能证实所涉及的作家在写作中受到影响。
但在桑德斯那本书之后(她近乎疯狂的列举就好像是麦卡锡主义的反面),想要真正重整我们的阅读,仍必须回到那些秘密机构的方法上,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并不像《甜牙》中写的那样,她所有的情报局同事显然都对文学一窍不通——当然那是因为小说叙述者是一个自满的作家和一个貌似谦虚的女文青。实际上,在这些秘密机构中操刀的都是内行。他们很多人自己就是作家和学者,他们也知道谁是真正值得投资的好作家。
有趣的地方是,一向被视作冷战武士大本营的情报机构,他们看中而力捧的作家往往政治色彩模糊。他们尤其喜欢所谓non-Communist left(不信奉共产主义的左翼人士),这倒也不奇怪,也只有成日玩双重间谍心理战术的情报机构才能理解这种模糊地带的价值。其中起作用的很可能包括一种逆向选择:中情局支持那些莫斯科不喜欢(或者预计可能会不喜欢)的东西。正如一位中情局官员夸口说抽象表现主义艺术是中央情报局的发明(他们赞助和组织这种艺术风格的最初一批展览),因为他们意识到,这种艺术的存在本身就会让“社会现实主义显得刻板和封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莫斯科禁止和反对的东西越多,中情局就能在它的文化武库中储存更多弹药。
秘密机构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十分老练的(sophisticated)。自1953年起供职于英国外交部情报部门(IRD)的克里斯托弗·伍德豪斯说,该部门编写各种问题的学术数据报告,按照“涓滴原则”(trickle-down theory),散发给英国知识界重要作者,让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引用。
在文学界,秘密机构帮助推动一些作品的出版发行和多语种翻译,组织对这些作品的讨论和推介。现在已为人熟知的受益作品包括《1984》《动物农庄》《日瓦戈医生》等,虽然要理解中情局为何出资翻译像《荒原》和《四个四重奏》这样的作品,甚至将《四个四重奏》空投到苏联,需要有更加复杂敏感(或者根本没有什么)的美学视野和战略头脑。就像在《甜牙》中,很多五处同事无法理解情报局有什么必要赞助男主角那部《来自萨默赛特平原》。有关这些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秘密机构的推广(尤其考虑到其中一些作品已成今日“正典”),通常会引起很大争议。但有些事实无法忽略。比如英国秘密机构资助出版的库斯勒名作《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IRD出资购买参与发行五万册),因为遭到阻击——法国共产党受命买断这本书,于是就大量重印,据库斯勒太太在她的书信中说,库斯勒就这样“靠共产党发了一笔大财”。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说,库斯勒这本书十年间销售量达四十二万册。
冷战秘密机构介入文学写作和出版,以贯彻其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战略。安德鲁·N.鲁宾的新书《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对此展开讨论。鲁宾把“世界文学”视为以歌德为起点的人类理想,这一理想在二十世纪看似几近实现,战后短短几十年间,一大批世界级文学家相继出现。这些作家为全世界读者提供衡量判断尺度,也给全世界写作者带来“影响的焦虑”。这些作家能够迅速成为全球读者瞩目的焦点,主要是因为战后出现的新型文学生产和传播方式:在冷战秘密机构和他们的代理组织推动下,这些作家的作品被多语种翻译,在全世界同步出版。尽管他们的国籍、族裔、写作题材和风格各有不同,但似乎出于某种不为读者所知的普遍标准,在全球发行的刊物上(这些刊物后来被揭露其背后有秘密机构赞助,受到操控),他们的名字和作品被并置在一起——读者像是只能从反面去把握这种标准,即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另外一些作家获得如此关注?比如(鲁宾举例),为什么是奥尔罕·帕慕克而不是哈桑·阿里·托帕斯能更好地代表土耳其作家进入世界级作家行列?
文化冷战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勾勒战后世界文学版图,鲁宾以及桑德斯的研究都无法给出答案。部分是因为那些秘密档案至今仍受到保护。但他们列举的大量事实,仍不免会让读者产生某种疑虑:我们今日的文学阅读是不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冷战机构影响、干预和操控的行为?如果当代世界文学地图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些秘密机构参与部署 / 制定标准、树立权威、划分等级、给予准入或排除在外,读者还能不能用“恺撒归恺撒上帝归上帝”那种方式来评价这些今日已成正典的天才之作?或者换一种说法,就像勒卡雷小说中遭遇重大挫败的“圆场”,意识到他们历年来所获取的各种情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分析和假设,大部分已被(对手使用双重间谍和假情报)“污染”,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在“顶楼”办公室坐下来,进行“损失评估”,我们能不能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幅世界文学图景也同样进行一场“损失评估”会议?
纳博科夫不喜欢《日瓦戈医生》。他说帕斯捷纳克的风格眉目暴突、脖子粗大,就好像小说作者的缪斯患有甲状腺疾病。当他读到这部小说时,评论它陈腐老套,充斥着不可置信的女孩和罗曼蒂克的强盗,一定是帕斯捷纳克的情妇写的。虽然这评语很毒舌,但读者可能会获得一丝宽慰,如果他不喜欢这部小说却又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在这部书向全世界范围推广的过程中,中央情报局多多少少出过一点力。虽然这不应该是你不去读它的理由,但知道这些事情,可能会让你找到更恰当的角度来阅读。 ■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