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张贵兴小说:马华文学焦虑的产物
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个流行的小说创作观是“文学即人学”。从周作人论《人的文学》,到鲁迅、柔石等作家对庶民的关切,再到张爱玲、萧红细致入微的女性描摹,人一直站在小说叙述的中心,成为主宰万物的尺度,但在马华作家张贵兴的小说里,人被拉下神坛,取而代之的是万物入主,人在小说中的命运,不再会因他是人而得到任何刻意的拔高。张贵兴在小说《猴杯》和《野猪渡河》中书写各种偶然的死亡、人们命运的荒诞,为的不只是重述现代主义的陈词滥调,他的意图需要与他对动物、植物等事物不厌其烦的描绘来结合理解,比如《野猪渡河》里的婆罗洲长鬚猪、《猴杯》里的犀牛、蜥蜴、猴子、猪笼草、丝绵树,在《野猪渡河》中,猪的分量已经不亚于人,人的境遇实际上和动物别无二致。

张贵兴
正如学者陈济舟在《原油、鬚猪和巴冷刀:张贵兴〈野猪渡河〉中的“情物”》中所说:“在有生和无生、历史和虚构之间,《野猪渡河》所呈现出的‘物’不但驱使学者重审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人的文学’这一观念,也让人试问小说构建起的生态历史情境是如何通过动物(婆罗洲长鬚猪),人造物(巴冷刀)和原物料(原油)得以呈现。”
《野猪渡河》是张贵兴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红楼梦文学奖的优胜作品。张贵兴把故事放在二战日据时期,日本南侵马来群岛,砂拉越沦陷,二十二个男人的头颅被砍下,当原住民被恐惧的阴影笼罩时,一只露出獠牙的公猪伸出舌头舔舐死者的血液,正准备与母猪交配。故事就这样在人与物视角交换的叙事中展开,野猪成为窥探人类世界乱象的一个叙事工具。在《野猪渡河》中,张贵兴不但延续了《猴杯》狂暴、骇丽如同雨林藤蔓般疯长的语言,也在对南洋历史的深潜中,书写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叙事质感。小说中人对自我的美化被无情剥夺,人和动物在叙事上近乎平等,张贵兴用雨林的湿热危险与历史的诡谲莫测相结合,在对文本的建构与打破,对叙事视角和时间顺序的打乱和重组中,张贵兴刻画出一个华美地狱般的矛盾空间,这个空间既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有源源不断的性爱、虐杀和权力更替,正因如此,《野猪渡河》超越了普通的伤痕叙事、英雄主义叙事,呈现出历史肌肤上更细致的纹路,更重要的是对人本位的小说传统做出了反思。

《野猪渡河》
但张贵兴的繁茂书写也会引发争议,有读者开玩笑说他是“马华莫言”,因为他不加节制的语言和对人与物交错叙事的偏爱,与莫言在《蛙》《红高粱》《生死疲劳》中的描写有的一拼。莫言的小说还是很好读的,张贵兴倒是更艰涩,即便是专业的小说编辑也很难一口气读完他的小说,焉论说自己能真正读懂。譬如《野猪渡河》是一部冒犯读者的小说,它的主要阅读者是严肃文学爱好者,走出圈外就回应者寥寥,而张贵兴并不因市场的受阻就改变自己的写作策略,因为他很明确自己的写作目标和写作对象,他是有意写真正质疑某些文学准则的小说,进行语言上的创新,而他小说的理想读者,是对语言的新意有所要求的读者。但这就会面临一个矛盾,张贵兴使用的语言是否就是新的,这里面繁复到要将大量读者拒之门外的叙事安排,是否在每一部小说都有其必要?这是讨论张贵兴小说可以深入的一个地方。

《赛莲之歌》
阅读张贵兴,《猴杯》也是一部可以参考的作品。这是张贵兴继《赛莲之歌》《群象》两部小说之后,“雨林三部曲”(黄锦树语)的终章,也是他的生涯代表作,小说曾获时报文学奖、开卷十大好书奖,一出版就在马华与中国台湾地区好评如潮,是一部极有可能经典化的作品。如同作家李宣春所说:“到了《猴杯》,张贵兴极尽夸张之所能,以砂拉越华人的垦荒史为轴,再密实地编织出生命力极旺盛又充斥颓败衰亡的婆罗洲热带雨林。”在这部语言如同藤蔓般疯狂生长的小说里,我们不得不屏气凝神,小心翼翼随之而来的危险。它让读者暂时忘却现代文明的规范,进入到一个蛮荒而危险四伏的境地中,感受一种汗流浃背式的阅读体验。要领略张贵兴文字的焦灼,试看这一段文字:
“曾祖担心母豹会把娃崽子饿坏,傍晚时放了一只长尾猴到铁笼子里。母豹照例埋头大睡,对猎物不屑一顾。夜半时分,母豹霍然起立,扑向猪尾猴。周复第二天清晨断气时,身上还趴着数十只水蛭,要他命的除了水蛭,还有一种两英寸不到的鲇鱼,它们寄生鱼鳃,活跃巴南河,从尿道、肛门、嘴巴、伤口潜入人体,英国官兵协守种植园区在河里泡澡时也曾经遭到这种鲇鱼袭击,必须动用外科手术才能铲除。周复的泌尿系统和内脏爬满这种杂食性小鲇鱼,在他死后因为缺氧缺水纷纷露脸。四天后,母豹在树窟里产下三只豹崽,周复十二岁小女儿小花印也抵达了种植园区。”——《猴杯》第四章
显然,张贵兴采用了一种正面强攻的叙述姿态。他不回避人性之恶,也不回避自然的凶险,他对万事万物采用了一种直面和冷峻速写的方式,哪怕引起读者的生理不适。
《猴杯》处理的历史并不是王侯将相的历史,而是在正统史书中被淹没的升斗小民的历史,《猴杯》对时间、文明的处理并没有使用一种进步论的调子,张贵兴在这里颠覆了一种线性上升的史观,而是从人的本位跳脱出来,想象人的命运就和猪狗没什么区别,人的历史也并不因为人就获得例外的崇高。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读者会觉得张贵兴对人的处理太无情,因为人命就像草芥一样,在他的小说中受到命运无情的剥夺。而小说中也描绘了各种各样挑战人忍受极限的景象,比如打架斗殴而死的学生、河边漂来的浮尸、对着骷髅头亲吻的女孩、畸形的胎儿,乃至隐藏在热带雨林中的情欲和虐杀。
在这时候,小说名字本身就成了一个隐喻。所谓猴杯就是猪笼草,猪笼草拥有一个独特的吸取营养的器官名叫捕虫笼,捕虫笼呈圆筒形,下半部膨大,笼口上有一个盖子,形状像猪笼,这个瓶状体的瓶盖复面还能分秘香味,据说汁液清凉可口,猴子很爱喝,每当猴子喝的时候,它们为了不把瓶底的虫骸搅起来,就很小心翼翼、彬彬有礼地喝。猴杯这个词不仅浓缩了热带雨林的景观,也将野兽的口腹之欲、植物的觅食方式与文明做了一个巧妙的结合,让人联想起“一切文明都是野蛮史”的经典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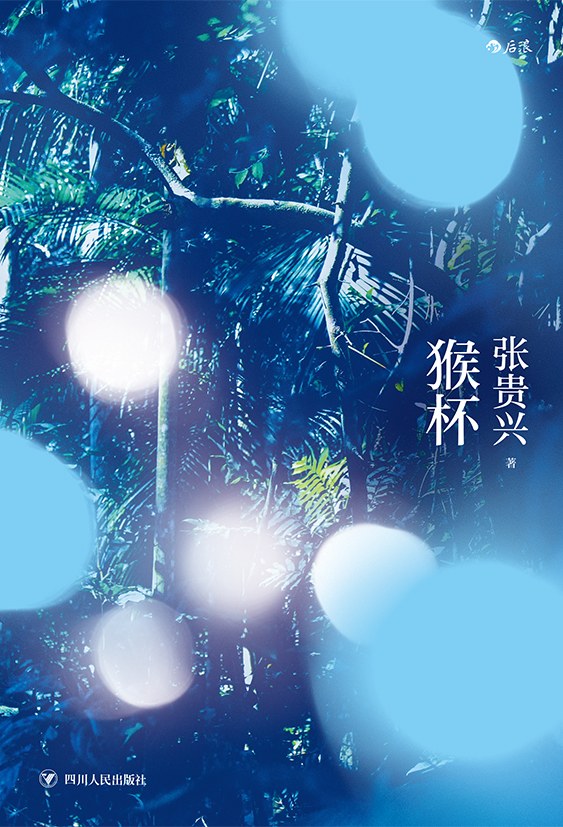
《猴杯》
张贵兴同时也是在写马来西亚地区的人们,他们身处在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在反复的王朝更迭与殖民和革命的历史中,他们的内心归属感的问题。在《猴杯》中,张贵兴常常写到畸形儿的意象,同时他也会处理那些“没有方向的人”、“被支配的人”,或者找不到一个固定的国家、宗教信仰的人,畸形儿的形象,也是马来西亚人在历史中的尴尬写照。这片地区被不同的帝国光顾,它的原住民与移民冲突的背后,是不同意识形态厮杀所残留下的遗痕。尤其是从中国南方迁移而来的马来华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更是深刻感受到一种缺乏归属地的困顿。而张贵兴的小说没有明写政治,但在文学世界中,他隐喻了马华族群的精神彷徨。
在读的时候,笔者看了部分人对此小说的评语,有人说像福克纳,有人说像莫言,笔者认为张贵兴最直接继承的是法国新小说派的精神,把小说从抒情和讲述的现实主义范式中解脱出来,取而代之的是语言的狂欢,物质、空间、感官体验在文字上最直接的呈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比《猴杯》和新小说派代表克劳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三折画》,作者不是以说书人的腔调写小说的,而是一个画家、一个拍电影的人,画面与画面间的过渡被简省,每一大段都如同精细的画作,语言在里面繁殖,像藤蔓般疯长,把读者引入到大汗淋漓乃至窒息一般的阅读体验,就好像你真的走进热带雨林,做一场天旋地转的梦,冒险、垦荒、性爱、猎杀、逃亡交替上演,人们从文明的伪善中抽出,赤裸裸面对自己的欲望,火苗升腾,化作燃烧的星空,就成了《猴杯》暴烈迷狂的画面。
《猴杯》赏心悦目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故事,而是作者天才的文学绘画能力,这样的小说,也可说是绘画小说,它最理想的状态,不是一口气读完,而是不紧不慢地,仔细去读,就像你欣赏梵高的一幅画,画是静止的,但色彩让它好像流动起来,每个细节都值得考虑。而在小说中,就是每个细节都像是自我生长,一个洞穴里又有另一个洞穴,看似繁复却又层次鲜明的文字叠加,描绘出人类意识里每一个瞬间丰富的思考,宛如夜空中一场又一场核爆。
张贵兴的文学也是马华(马来西亚华语)文学焦虑的产物。怎样在弹丸之地创作出强劲的文学,这一直是困扰马华作者的问题所在。没有那么雄厚的历史资源,没有在权力话语网络中处于中心的地位,甚至在华语地区都是边缘的存在,马华作家怎么确立自己的重要性,又使它超脱出不仅仅局限于“地域文学”新鲜刺激的层面?从李永平、黄锦树、张贵兴到黎紫书,多多少少都被这个问题影响到他们的书写。黄锦树选择深入到殖民与革命的历史,在潮湿雨林的风情画中勾勒历史的凶险。而张贵兴与黄锦树同中有异。他们的文字看起来是很不像的,但他们都有意识把历史资源和热带景观结合起来,既满足外国读者对马来的想象,也在书写中去触碰马华读者的身份认同。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迁移而来的华人,在异域会是怎样的心境?当他们面对政治的攻讦、民族的纷争,他们又如何度过历史的种种磨难,在边缘化中找寻自己的生命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不妨把黄锦树和张贵兴理解为照向马来社会的镜子,而黎紫书可能是差异更大的一面,她对欲望的纵深书写,对女性心理细致入微的捕捉,在马华文学里是一道独特的存在。而张贵兴和黄锦树受制于性别与观念,他们侧重的点就跟黎紫书大为不同,相比之下,张贵兴更狂暴、细密,黄锦树的文字则更干净、湿润一些。
联系到上文提到,友人曾调侃张贵兴是马华莫言,虽是玩笑之词,倒也颇可联想。他们共同受惠的其实是福克纳、马尔克斯、新小说派和乡土传说,他们都喜欢在民间传说中素材,杂糅巫蛊、野兽、生殖、原始景观、泥沙俱下的语言形态,像《生死疲劳》和《野猪渡河》,都是有意让动物成为主角的文本。张贵兴作品的意义更多是在创作者层面,而不是故事层面。他融合了福克纳与克洛德·西蒙的技法,为马华文学的叙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式。
所以,无论读者喜欢与否,至少他是一个努力求新的作家。但他的故事也确实难读,从通俗的角度来说,张贵兴的语言几乎是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没有耐心的读者恐怕翻几页就要被那窒息般的语言所击退,纵然读完的人也难有勇气再读一次。所以张贵兴的贡献不是在通俗的故事上,而是创作技法层面的创新上,这就像影史商业片导演和作者型导演的区别,张贵兴在作者那边的地位会水涨船高,因为他的写作难度摆在那里,提供给日后作者一个书写的方向。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