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平如美棠:父母的爱与言行,深刻影响着孩子们的人生
【编者按】
八年前,《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出版。这本讲述绕平如一生故事的书,因为平如和美棠的六十年相守,感动了很多人,也时常在2月14日、5月20日这样的日子被人们提起。今年的520,《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纪念修订版推出,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其中新增的一篇文章,是饶平如三子饶乐曾回忆父亲母亲的纪念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平如与美棠漫画
在外婆口中,母亲从小是个有主意、顽皮的女孩。外公是个开明士绅,在汉口、福建等地都有生意,经常出门在外。外婆不识字,母亲是他们最宠爱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掌管着家政。家里用度开销、记账管理居然也井井有条。母亲爱美、爱玩,她和闺蜜刘宝珍俩人形影不离,唱歌跳舞、看电影追星、购物追时尚,几乎同今天的女孩一样。
一九四八年,刚从军队回来的父亲娶了年轻的母亲。两人你侬我侬,算是一见钟情。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五八年,父亲被送去安徽劳教,家庭重担一下子压在了母亲身上。那年我大哥九岁,二哥六岁,我五岁,下面还有四岁的弟弟和三岁的妹妹。家里七口人没有一分钱收入,母亲去了里弄生产组工作。生产组没有福利,一天工钱六角,做一天算一天,月入十几块钱简直是杯水车薪。父亲在安徽后阶段有了点收入,挤出每一分钱寄给母亲。而他对自己花销的控制已是近乎苛刻的程度。这时候政府也补助了几块钱,同时,母亲不断地变卖她的首饰,勉强维持着家庭。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实行分食制,孩子每人一小盘、一小碗。每天洗碗刷锅是大哥的专利,一则我们小,母亲怕我们打破锅碗,二则锅里总归有剩余的饭粒。母亲和外婆永远是吃得最少的,长期的重体力劳作和营养不良,是母亲落下很多病根的原因。
当我们陆续念书以后,五个孩子的学费国家给免掉了,但书杂费都是一分不能少,每年缴费,母亲东挪西借伤透了脑筋。
一九六八年,大哥希曾在母亲的努力下得以在上海工作,他是母亲最大的安慰。大哥每个月除了留下厂里的饭菜票钱,直到结婚前夕工资都交给母亲,帮助抚养弟妹。他唯一的“特权”是早餐有一碗盐水泡饭。后来大哥得了肾炎,母亲总是自责,认为是因为大哥生盐吃得太多。

腌制咸菜,是当年贫寒人家的最爱。当雪里蕻大量上市时,极便宜,我家就会购入数十斤,洗净、晾干,然后加盐,用石子或搓板把菜弄蔫,放入大缸中压实。小菜场制作时,会请人站入腌缸中不断踩踏咸菜,加入作料。母亲以为二哥力气大,制咸菜非他莫属,外婆技术把关,他施展能耐。在外婆的指导下,奋力干一天。过了十数天,打开缸盖,香味扑鼻。咸菜卤水鲜美无比,母亲就会给邻居、同事送一些,也有人会专门讨要一碗卤水做汤喝。后来二哥在江西插队落户,探亲回家时会带回一些冬笋,配合咸菜炒制,那个味道真是好得没话说了。
那个年代,尽管家里一贫如洗,仍不失温馨和欢乐。夏日里,傍晚时分,家里早早拖好了地板,铺一张草席,大家席地而坐,听母亲讲一些过往事。故事中,父亲永远是憨直的,去贵州路上如何拎着热水瓶追火车;打牌,他的牌就像是用玻璃做的,别人一猜就猜着了;刚到上海租房子没家具,舅公让他去取一点用,他坚辞。为了增长知识,买了一辆自行车,他学英语,学会计,写稿子。父亲不会见风使舵,不会说假话。说着说着母亲会笑起来说:“爸爸憨?脑子一根筋,勿会转弯。”落日的余晖照在母亲的脸庞上,漾起淡淡的甜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家是异常的困苦,全家人衣着破旧。两张床、一张摇摇欲坠的饭桌、一张破沙发便是家中全部的家具。在破裂的护墙板上,外婆钉了许多钉子,挂一些她需要挂的东西。那时的晚上真是安静,我们围坐在饭桌前,或做功课,或看书、画画等。沙发上,外婆会抚着“墨球”(外婆养的猫),母亲会把报纸卷成筒,轻轻地唱歌。父亲说母亲最喜欢唱的是《花好月圆》,我记忆中更多的是《送别》《渔光曲》《夜半歌声》,还有就是《魂断蓝桥》《翠堤春晓》《桑塔露琪亚》《托赛里小夜曲》《舒伯特小夜曲》等国外乐曲。我从未学过,但却会记得,应该是从母亲那里听会的。母亲的嗓音甜美,但歌声中总带着哀婉和忧伤。现在想来,当时是那么艰难,但与母亲在一起,还是感觉如此温馨和幸福。
暑假也是母亲最操心的时候。大哥喜欢看书,经常与他的同学交流书籍。二哥申曾是让母亲最担惊受怕的一个,他身体结实,犹如牛犊,身上有太多余的精力,白天在黄浦江里游泳,晚上在浦东乡下捉蟋蟀,因此家里墙上时不时能看到他的检讨书。家里五个孩子,就他一个人挨过打,因为太贪玩,小学二年级还留过级,跟我成了同一届的毕业生。但也奇怪,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在同一个小学念书,他最顽皮,但老师却都最喜欢他。班主任仇老师给他买早点吃,教音乐的陈老师誓要将他培养成指挥家。特别怀念的是一位董老师,浓眉大眼,一脸络腮胡子,他原是教育局干部,打成右派后被下放到永安路小学。可能是相同的感受吧,他特别呵护二哥。二哥喜欢体育,他想方设法把二哥送进游泳训练班,拍证件照没钱,他拿相机来拍。四十几岁的人了还未婚,直把二哥当成他的孩子了。可惜这样一位好老师,在“文革”中不堪羞辱,身上绑块大石头,跳河自沉了。
母亲为人处世友善忍让,待人接物端庄得体。邻居、同事包括里弄干部都对她保持着些许尊重。即使在“文革”中,老邻居们仍称呼她“饶师母”,同事、干部们都称她“毛阿姨”。家里经常有访客,她的领导魏阿姨经常会来与母亲商量工作。四年级要上珠算课,母亲买不起算盘,魏阿姨立刻送一把十一档的算盘。同学们都是新的十三档,而我的算盘特别沉重,我很不高兴。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那个算盘是红木的。
访客中还有一些年轻的女人,男人或是海员或是在外地工作,她们与男人的沟通靠通信。她们相信母亲,她们不会写字,母亲就经常替她们写家书。还有一群特殊的女人,很晚才会来,讲话轻声细语,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因为她们的男人都坐牢了。她们无一例外地都离了婚,谈些什么,母亲从不跟我们讲,但临走时宽慰的神情,我们还是看得出来。一九六九年,林彪的“一号令”出来后,上海的形势也骤然紧张。上海也要疏散人口到内地去。一天,里弄干部通知母亲参加“疏散动员会”,但参加人员无一例外都是“黑五类”家属。母亲很镇定地对那干部说:“我不能去参加会议。”那个干部很惊诧:“都是‘黑五类’家属,凭什么你可以不去?”母亲说:“第一,我们老家不在农村,也没有人。第二,家里老老小小七口人,去了以后怎么办,我不同意。我在会上,你动员我,我也是这样回答。这样影响你们工作,不如不去。”那个干部想了半天,居然说:“我就说你生病了,去不了。”我们因此躲过一劫,而母亲的两个朋友却回了老家。由于我们家欠租,“文革”中房地局也来催租,不交租就交房子。一段时期也有一些人来看房子,我们都很害怕,而母亲不断地与来人周旋、交涉。当时也有人被迫搬去黑暗、狭小的房子,而我们家居然再一次化险为夷。今天想来,除了母亲的友善和智慧外,那些干部的同情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有一个街道干部,她说的话让母亲很久很久不能释怀:“你说你老公不会撒谎,老实人怎么会被政府抓去坐牢呢?”
我自小体弱,经常发烧说胡话,多感伤、神经质,加之个子不高,像个不成熟的孩子。母亲卖掉一张破旧的桌子,在店堂里,我仿佛看到桌子在哭,我也掉眼泪。自我感觉母亲对我总多一分怜爱。
一九七0年初,我初中毕业。当时实行“一片红”政策,即知识青年都要下乡务农。两个去向,一是农场,是国营的,有工资;二是插队落户,没有收入,年底工分结算。城里人到农村劳作,基本上没有人赚到这个钱,而我们出身成分不好,只有插队落户一条路。
我和二哥同届毕业,但两个学校,意味着要分赴两地了。母亲又一次奔走于两个学校,要求照顾在一起。最后经落户地江西方面的协调,二哥在我去后一个月,调来与我一起。
自小我一直睡在母亲的脚下,妹妹睡在母亲的身旁,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七日,临行前的一个晚上,母亲要我睡在她身旁。半夜醒来,发现我被母亲揽在怀里,她爱抚着我,吻着我的额头轻轻地哭泣着,我闭着眼睛,一动也不敢动。
二00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在母亲的追悼会上,眼望母亲安卧在鲜花丛中,想起那一晚,我泪流满面,俯身下去,深情地吻了母亲的额头,这也是我记事以来的唯一一次。

平如整理的相册
在农村,二哥俨然成了我的保护神,他身强体壮、急公好义,甚得老表、同学们的爱戴,永远是最高的工分。他不让我干重体力活。我是多愁善感的人,老表们都叫我“哭神鬼”,因为有二哥在,所以也没有人会欺侮我。
因为没有钱,过年了兄弟俩都不回家,怕增加母亲的负担。二哥把他赚得的几十块钱悉数买了农产品,让同学带回家,让母亲高兴。几年中,二哥还给家里陆续寄回了整套的木制家具,没花母亲一分钱。
由于出身不好,上大学、参军、招工都没资格。在农村干了六年活以后,公社干部看到我们兄弟俩表现都很好,加上同情,先后把我和二哥调入公社电影队、工业办公室。不久,有个师专的读书名额,公社决定让二哥去。因为报到期限紧迫,公社武装部曾部长让人翻窗进入公社文教干部的办公室,在表格上盖章后,紧急送往县里。此举从此改变了二哥的一生。二哥学习努力,继续深造,一九九六年通过人才引进回到了上海。
而我自到电影队后,与公社文化站的一位女同学陷入热恋。住在公社大院,我的破衣烂衫“引人注目”,她看了后十分不忍,掏钱替我置衣,从此我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块手表和第一件毛衣。
二哥上学了,但身无分文,我和她一起掏钱资助二哥。恋爱改变了我的心态,使我增强了自信心,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始终铭记着这位好姑娘。
四弟顺曾,在我去江西时还在读书,一年后被分配到上海卫生学校念书,不料毕业后仍被分配到农村。已经有两个孩子在外地农村了,政策明显不公,母亲很愤怒,坚决不让他去,由大哥负担他的生活费。四弟也很争气,在等待就业的四年里,他听收音机自习英语,温习医学专业书、翻译医学论文。今天,他已然是一位精神科专家了。
五妹韵鸿毕业后,分配在长江刻字厂工作,学习努力、工作勤奋。婚后,她的家庭生活十分美满,公婆慈祥和善。因此,父母亲会经常带着舒舒去她家小住几日,其乐融融。
大哥找女朋友了,居然是有房子的。四弟找女朋友了,也是有房子的。婚后他们都住进了女家。妹妹夫家房子也不错,我于一九七九年返回上海后,也就顺理成章地在父母处成了家。一九九六年,二哥返回上海工作,没有房子。我立刻把房间让给了他们,我睡在父母房间的沙发上,一睡就是两年,直到二哥学校在浦东分配了一间房。
二哥在江西工作期间,父母大概是认为当时他最困难,差不多每隔一年就要到他家去住一段时间。我们也明白老人家的意思,各家尽力支援他们的行程。父母就用这种形式一则看看孙子,二则帮助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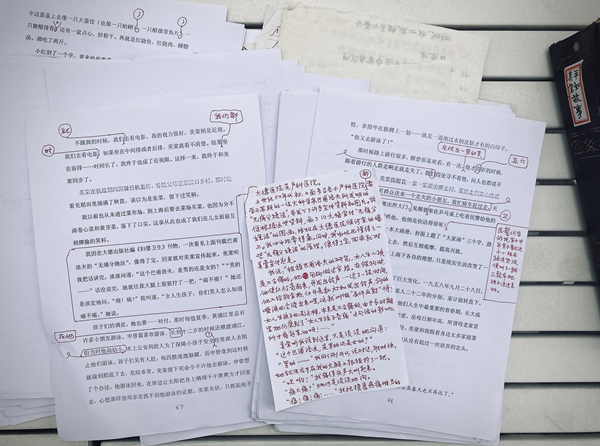
平如对《平如美棠》原文做的修改和增补
二00二年初,我想买房子了——考虑到父母年迈,老房子环境、卫生设施太差,母亲身体也越来越差,想有个房子让他们安享晚年。我的想法是买在四弟家附近,因为他和弟媳都是医生,我不常在家,老人由四弟照顾最合适。跟四弟商量,他跟弟媳极为赞同,积极寻找房源。今天,我们住的房子,就是他们找的。事实也证明这样的安排较为妥当。
母亲生病期间,大多是四弟和弟媳在安排照料,我也得以在崇明安心工作。母亲住院期间,又是妹妹天天在医院陪护,让哥哥们能正常上班工作。母亲病重期间与父亲商量好,留下了遗嘱。老人家没有遗产,唯有永安路老房子的居住权,而他们的分割都是以我和舒舒的居多,兄妹们均毫无异议。我们都明白了父母的心意,母亲最放心不下的是舒舒。她性情温和,善良可人,懂礼貌,是爷爷奶奶的心灵鸡汤。父母亲退休后的生活,几乎是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度过的。在爷爷奶奶的庇护下,她快乐而且健康。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成长历程,父母亲对我们的说教很少,但他们鼓励我们要互相友爱,要多读书。父母亲这数十年来的言行,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影响着我们的举手投足。同样地,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举止、言行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呢?这是每一个大人都要思考的问题。
二0一三年九月四日

《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纪念修订版),绕平如/著、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