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个真东西?
原创 吴琦 单读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在一个透明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然后被所有人看到。表面上看,我们就在技术许诺的“乌托邦”里,人们平等地收发信息,没人可以再欺瞒谁。但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屏幕里仿佛有一个漩涡,最后我们都围着几经转发评论的信息绕圈圈,真相到底是什么,无从知晓,甚至也无人关心,越来越多人只想活在想象的泡沫里。
吴琦为《单读 26· 全球真实故事集》撰写的卷首语《真东西》,题目取自亨利·詹姆斯的一篇小说,而他想表达的,也与亨利·詹姆斯的文学观有相通之处。小说不能脱离“真东西”,电影也是,非虚构写作便更是如此,但是从 19 世纪到 21 世纪,“所有的形式都在僭越真实”。这正是考验创作者的时候,在今天,“只有靠近现场,与陌生人交谈,触摸皮肤、物体或海洋的表面,才能使我们免于心虚。”

真东西(The Real Thing)
撰文:吴琦
之前在网上请大家一起选新播客的名字,我临时加的一个选项被留言吐槽说不知所云。心里一惊,有种想出个谜语但谜面出错了的失落感。那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一个短篇小说的名字,也是你正在读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大概两年前和陈以侃提过一嘴,他当时没有多说,但露出一个不用你说谜面就已经知道谜底的眼神。有些人的意见享受更高的权重,这么看也不算不公平。播客最后的名字还是来自亨利·詹姆斯,并且更明目张胆地抄袭了他的一个书名。《螺丝在拧紧》。因为年代久远、版本纷繁,较难确认谁是最初的译者,更早的译本还翻译成《布莱庄园的怪影》《碧庐冤孽》,想来都应该一一致谢。原创性不足,但表现力丰富——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和陈思安聊天,我说这不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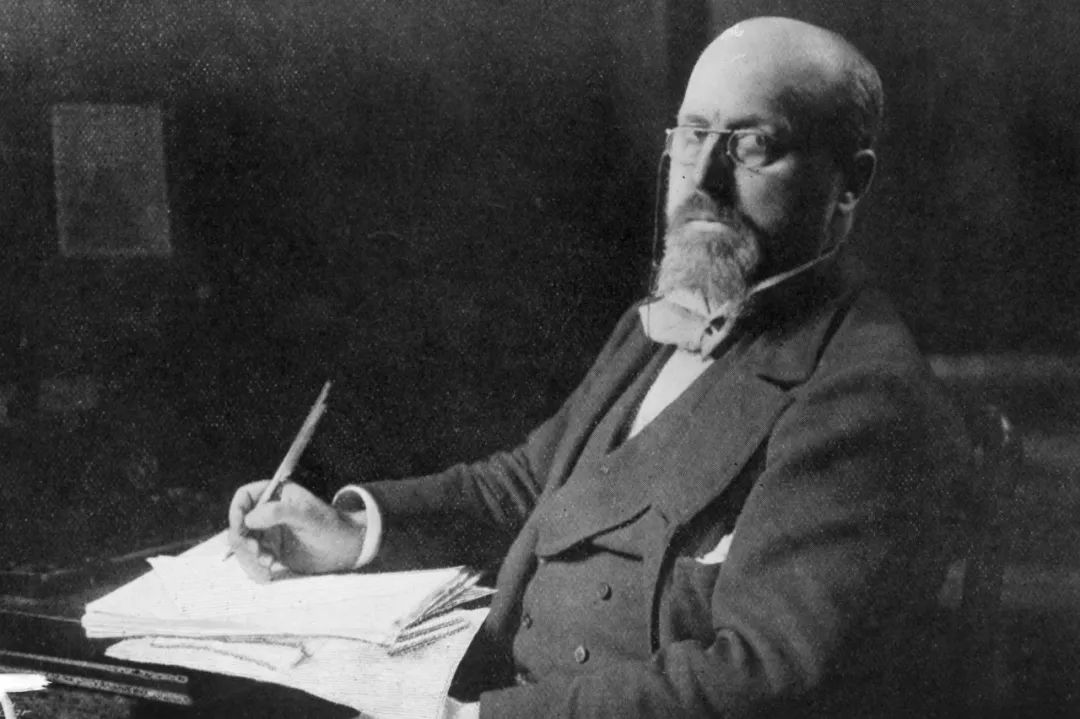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英国、美国小说家。
《真东西》这篇小说表面上是一个有点悲伤的故事。一对原本家境优渥的中年夫妻家道中落,不得不重新出来找工作,经朋友介绍找到一位插画家,想给他当模特赚钱,他们怯弱但又自信地认为,自己良好的体态和举止,理应离那些文学作品里假模假式的上等人更近。画家明显是个好心人,他的观察和小说家一样达到了细致而深刻的程度,很快发现了他们并不适合这份工作,却主要出于同情留用了他们。他在小说里说,“我正确地判断,在他们尴尬的处境中,他们密切的夫妻关系是他们主要的安慰,并且这个关系没有任何弱点。这是一种真正的婚姻,这对踌躇不决的人们是一种鼓舞,对悲观论者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这段短暂而几乎有些温情的合作关系最后还是走向破灭,画家以这对夫妻为模特的作品迅速受到朋友的批评,也不被雇主认可,他们在画面中的效果远不如那些粗鄙、生动的劳动人民,于是他给了他们一笔钱,从此再也没有见过。

这种忽然瞥见的沉沦和情谊,很容易打动我,更何况潜藏在故事背后还有一层关于艺术本体的讨论。上海译文出版社编的这本短篇集《黛茜·密勒》,还认真收录了亨利·詹姆斯阐述他小说理念的那篇文章《小说的艺术》。两篇都出自巫宁坤的译笔,形成了美妙的互文关系。詹姆斯在里面谈到,虚构小说如何必须反映真实事物,而又在哪些环节重塑了它,作家和画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很相似,他们的技艺就像是雾气凝结成水珠那种转换过程。这解释了为什么那对拥有曼妙身姿的夫妻,未必就是最佳的模特,因为创造真实永远不等于真实本身,而创作者们“对表现的东西较之真东西有一种固有的偏爱:真东西的缺点在于缺少表现”。

亨利·詹姆斯因为这一点而受到文学史的追认,身上被贴满“现代小说”、“心理真实”、“意识流先驱”一类的标签。他把小说最广泛地定义为“一种个人的、直接的对生活的印象”。在后来人眼里,这的确是和印象派同等强度的叛逆宣言,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同时代人。从那以后,创作者们获得一次解放,大胆地把“印象”用作再现活动的基本单元。这让我想到大学里曾经有一篇被自己毙掉的论文。那是在戴锦华老师的影片精读课上,我试图分析贾樟柯导演的《站台》。我当时似乎是想说,作为年轻的观众我未必能够全部理解贾樟柯镜头里的 80 年代青春,但通过那些影像和声音的碎片,以及经由它们创造出来的情绪、氛围和印象,也能构成历史记忆。哪怕这种记忆的强度随着代际更迭而减弱,也是不幸中的万幸。最后我还是担心这种论调是用懒惰的直觉掩盖分析的短板,于是按照更加周正的逻辑,写了一篇严丝合缝的论文交了上去。因为分数不高,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交的是第一篇作业结果会不会好一点。

电影《站台》剧照
这个不断碾碎人的心理空间的过程,符合自柏拉图的“模仿论”以来艺术史发展的一般轨迹。然而这只是詹姆斯文学观的一半。那篇《小说的艺术》实际上是想和贝桑爵士的一篇文章论战,针对的恰恰是那种更追求形式感、艺术性的文学观,因而不断强调小说不能脱离“真东西”,就像画家/作家始终没有被那对夫妇激怒,而几乎是饶有兴致地摹写他们。
“你不会写出一部好小说,除非你具有真实感。”接下来我再引用詹姆斯的话,可能会有点篡改,因为这篇文章的初衷不是谈论他,也不是谈论文学。那不是我的专业。而在 “真实感”这种事情上,人人都有点发言权。如果说 19 世纪小说为“真”,20 世纪电影为“真”,那么到了 21 世纪,真实已经彻底丢弃了所有形式,或者说所有的形式都在僭越真实。用“后真相时代”来命名有点太过冷静了,仿佛真相的后面还会有什么别的东西等待人类去逾越。在这个意义上,真实感具有末日的意味。而我急于为“真东西”辩护的一个动机,其实就来源于那样一些落难的人不出意外是确乎存在的。留给创作者的问题不过是,你们是否能够看见并且予以体会?小说如是,非虚构写作就更不必提。
我一直记得 2019 年在瑞士参加真实故事奖的活动时,当地市民对中国故事的那种热情,他们在小城里穿梭,在剧场、美术馆和酒吧里等待聆听记者们采集的故事。我感到自己远道而来有天然的义务多讲一些,可是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对实际上发生了什么的确一无所知,无从谈起。詹姆斯把经验解释成“一种无边无际的感受性,一种用最纤细的丝线织成的巨大蜘蛛网,悬挂在意识之室里面,抓住每一个从空中落到它织物里的微粒”。而今天整个世界, 都不断在丧失获得信息的渠道,以及被告知的权利,第二手、第三手甚至是虚假信息反而成了最成功的遮蔽物,我们也乖乖养成了一种欲言又止、声东击西的思维惯性。这时再做什么申明都显得腐朽,只有靠近现场,与陌生人交谈,触摸皮肤、物体或海洋的表面,才能使我们免于心虚。在这种危急时刻,我们前所未有地需要粗糙的微粒、丝线和蛛网,作为认知的材料,而非艺术的目的。

因而写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把之前看过和没看过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都翻了出来,摞在书桌上,它们颜色和开本各异,像一堆静静的嘛呢石,神圣而脆弱。虽然没有大师全集那样统一的庄严面貌,但它们的表现力也足够承担,人类在能力不足信心有余时所不得不借助的那类仪式、景观和符号所发挥的效用。然而它们终究不能代替我的手敲击键盘来打字,我们就是这样不得不在新世纪和机器一起上路,寻回真实的感觉。一个恋人,一道甜品,一颗子弹。据说冷战已经结束很久了。故事依然在朝最坏的那种情况发展,一个是假的,另一个还是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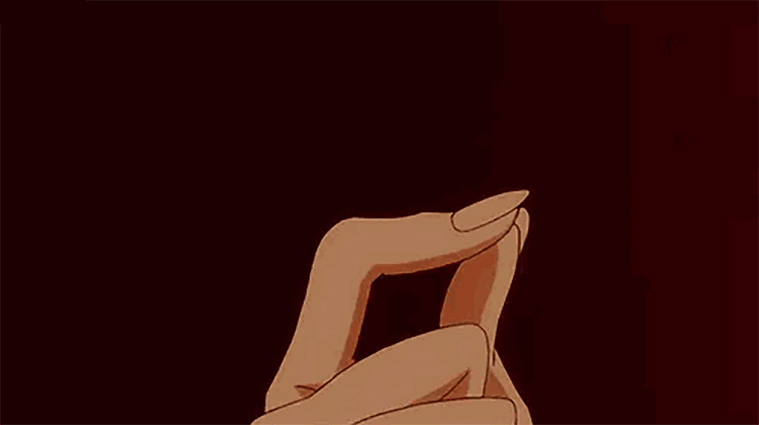
▼读点“真东西”
原标题:《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个真东西?》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