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时乖运蹇的英国教会史家伊文尼特

然而,伊文尼特绝非无能之辈,实则在自己的教会史研究天地中写出了出色当行的作品,甚至给予后进不少启发。只不过,一则教会史研究在当时的英国并非主流,他生不逢时,只得单打独斗、孤军奋战,无法构建打天下的学派;二则他天性温和,甚或怯弱,再加之人近中年便疾病缠身,故而每每丧气自贬,终没有煌煌大著传世。拙文并非要做“学术发生学”似的探讨,只不过尝试对伊文尼特其人其学向国内的读史爱史之人做一简单介绍,并希冀读者诸君可藉这位剑桥学者的人生境遇略窥彼时的学术特征。
1901年,伊文尼特生于伦敦。父亲是股票经纪人;母亲则有西班牙血统,出身大户人家,家族中不少人生活在南美。在这样的氛围中,伊文尼特很早便掌握了西班牙语,对自己家族的历史以及古代历史更是兴趣浓厚。然而,他的童年较为孤独,长期固定的玩伴只有他的姐姐。起初,他读书的学校隶属于本笃修会,但规模较小、默默无名。好在当时的校长古尔登神父慧眼识人,知道伊文尼特确有才具,便建议其母让其转学。伊文尼特的人生由此改变,在新的学校不仅结识了优秀的学友,更有机会向名师问学,开阔了眼界,为尔后在剑桥三一学院求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初期的老派文人,皆才艺多方。伊文尼特亦不例外,弹得一手好钢琴,参加过不少演出。读书期间,甚至一度有过毕业后走职业钢琴家之路的想法。不过最终,伊文尼特还是舍不得挚爱的剑桥和历史,选择以历史研究为职志。二十四岁时得到三一学院的研究员职位;二十九岁时则获教职。1939年至1945年期间,他和许多同仁一样,不得不经常中断研究,而为政府服务,共御时艰。二战后的十年间,他担任三一学院的本科辅导教师。在当时的剑桥,所谓“辅导教师”是指那些没有教学任务而要负责协调学生与学院之间关系的老师。他们可以做研究,但同时要花不少精力来处理繁重的行政事务。由于伊文尼特性格温润,不乏幽默感,对学生又有同理心,因而颇受学生爱戴。
繁重的行政事务并没有湮没伊文尼特的才华。其实早在二战爆发前,伊文尼特就是讲授政治思想史的出色教师;此外,他还教过其他几门课程。其中,他接替劳伦斯,带领本科生一起研读关涉16世纪天主教改革的重要会议——特兰托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同时以此作为主要的研究兴趣,并在二十九岁时出版了人生唯一一部篇幅较大的专题研究——《洛林枢机和特兰托大公会议:一项反宗教改革研究》。该书以法国洛林枢机大主教的教会观为切入点,探析教宗庇护四世在任时期,法国一方对特兰托大公会议之迎拒以及法国的反宗教改革思路。以今人的眼光来看,该书的研究架构不脱“教会—政治史”理路,系20世纪30年代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菁英政治史。此外,伊文尼特并没有神学和教会法学的训练背景,故而对其时极为复杂的神学教义争论着墨无多。然而,其书取材广泛,叙述细腻,对彼时的宗教冲突不乏饶富深意的点评,迄今仍具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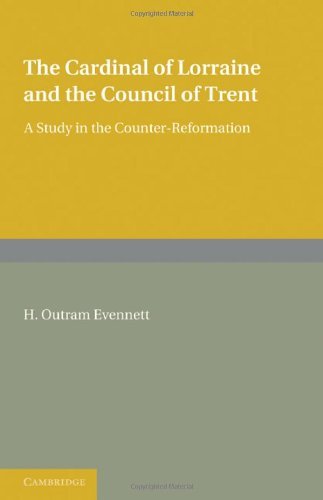
有关特兰托大公会议的第一部作品出版于17世纪初期。撰写人是出身圣仆会的威尼斯人保罗•萨尔皮。萨尔皮乃当时的著名文人,更是威尼斯执政当局的文胆;主张宗教事务的自主权,极度厌恶罗马教廷对威尼斯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干涉及享有的各种特权。此外,他还对加尔文的宗教理念持同情、理解的观点,故被时人目为加尔文信徒。萨尔皮的《特兰托大公会议史》文笔讲究、文风俊雅,但所用资料难称全面。而且,由于既有的政治观点使然,特兰托在萨尔皮眼中,乃是教宗恢复权力、强化集权的阴谋诡计。可以说,萨尔皮的《特兰托大公会议史》虽系名著,却非良史,实为政论性作品;甫推出即受新教圈子与高卢主义者的好评,成为攻讦天主教会的利器。
尔后,耶稣会士皮埃特罗•斯福查•帕拉维齐尼出于护教立场,以另一部《特兰托大公会议史》回敬萨尔皮。由于是官方的御用学者,因此帕拉维齐尼得以使用不少珍贵档案,在材料的钩稽、考辨方面远强于萨尔皮。但他文笔生涩,护教倾向明显,故其同名作亦不是信史。由于有关该会议的主要原始文献资料藏诸梵蒂冈,再加之教廷当局出于各种考量而执意不向学者开放档案,故难有信而有征的会议史行之于世。即便善于考订档案的德国新教史学巨匠兰克,也难以把握此届宗教会议的诸多细节。他曾预言,对特兰托大公会议的认识,未来只会在萨尔皮和帕拉维奇尼的两部著述中摇摆,永远不会有持平、公允的作品出现。兰克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至少一段时期之内,学者们即便有雄心壮志,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与兰克同时代的天主教大学者阿克顿勋爵,即便费尽心机,凭借深厚的人脉出入于罗马不少研究机构,最终也未能斩获有关特兰托的实质性资料。可是,随着教宗利奥十三宣布开放梵蒂冈文献,学术景观终有可能为之一变。这是兰克在在无法预料的。
到了20世纪初期,虽则学者们较之以前有更多的机会重新审视特兰托,但严肃研究的第一步还是要有机缘接触深藏在意大利各地的原始文献。伊文尼特虽然在三十岁左右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希冀在特兰托研究方面有所突破,但在彼时的剑桥,他是孤独寂寞的。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几点:首先,当时的剑桥并不是研究欧陆天主教史的良好平台,这所学校本身就有长期反天主教的倾向;而且,英国本地所藏之文献对于特兰托研究而言可谓杯水车薪。其次,在当时的英国历史学界,天主教教会史研究(当时还难言有宗教史研究)只是边缘学科;即便是有学者探研天主教,也泰半是将其作为新教(特别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对手方而稍带书写罢了,远谈不上真正的“同情之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身为普通教员的伊文尼特却对16世纪的天主教历史有兴趣,显然是当时的“异类”。他不可能得到资助或有其他资源以远赴欧陆收集材料。地利已然不具备,天时就更不凑巧。即便伊文尼特能获得资助,二战的爆发也让他不可能再有亲赴意大利的念头。
学术研究虽是学者自身在智识上的“朝圣之旅”,却也经常是学者之间的思想竞技。在相同的领域,稍有懈怠,就有可能被他人超越。20世纪40年代,就在伊文尼特空有志向、有能力却无缘获取研究资料之际,早他一年出生的德国人胡贝特•耶丁(Hubert Jedin, 1900—1980)凭多年积淀一跃而出,藉天时地利人和,以一己之力将特兰托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尔后更是开创教会改革史这一当时的新学科,彻底粉碎了伊文尼特的特兰托之梦。
耶丁二十四岁晋铎成为神父,有扎实的神学和教会法学基础。非特如此,性格上他远较伊文尼特果敢、坚韧、强悍。1926—1929年,他在罗马和那不勒斯等地广搜材料,撰写有关特兰托大公会议上的改革派、先后担任奥古斯丁修会大会长和萨莱尔诺大主教的吉罗拉莫•赛利潘多的专著。同时,也立下了撰写特兰托大公会议史的宏愿。30年代初,耶丁获得布雷斯劳大学的教职,但由于母亲是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因此后来失去了执教资格。而且,他意识到只要纳粹掌权,便绝无可能重回讲台。
为了将自己的研究继续下去,耶丁决定重回罗马,毕竟在那里才有机会整理、修订围绕特兰托大公会议的各种记录及与会人员的日记。当修订工作取得进展后,1938年,耶丁回到了布雷斯劳,在当地的教区从事档案研究。不过根据当时的种族歧视政策,他无法获得正式的档案员头衔。同年的11月10号,尚在整理档案的耶丁被盖世太保拉走,随即驱逐到了布亨瓦尔德。不过后来盖世太保在知晓耶丁是一位神父后,便将他释放了。这倒不是因为耶丁是神职人员的缘故,而是盖世太保认为犹太人不会被教会接纳成为神父,遂认定他并非犹太人。
遭此一劫,耶丁意识到唯有尽早离开德国方能生存下去。而且,他始终自信有加,认为只要以罗马的丰富档案为依托,便完全有能力超越萨尔皮和帕拉维齐尼,写出一部流传后世的佳作。为了获得资助,他去信执掌梵蒂冈图书馆的乔瓦尼•梅尔卡蒂枢机,申说缘由。后者回应积极,允诺提供经济支持。
就这样,在二战刚刚爆发后,耶丁幸运地逃脱魔掌,回到教会史研究的圣地罗马,从此如鱼得水,一待就是十年。梅尔卡蒂枢机提供的资助虽然有限,但足以让耶丁在衣食无忧之余,开展他的特兰托研究。在当时,这已是远在剑桥的伊文尼特所难以想象的极为优渥的研究条件了。1949年,耶丁计划中的四卷本特兰托公会议史的首卷刊布于世,技惊四座,赞誉之声纷至沓来。同年,耶丁衣锦还乡,在波恩大学执掌教会史席位凡十五年,著述宏富,作育英才无数,堪称20世纪教会史研究之佳话。
耶丁《特兰托公会议史》的第一卷,伊文尼特自然不会不关注。他撰写了书评,刊登于1951年4月的《英国历史评论》。文中,伊文尼特盛赞该书之出版乃教会史研究的一大盛事,并指出研究特兰托殊为不易:一方面材料浩繁难以梳理,作者要极善于整理、剪裁史料,在论述中撮要举凡,存其大体;另一方面著者自身还要同时兼具历史家、神学家、教会法学家三种角色,将三类知识化于一体,方可把握会议上神学争辩的内在理路以及16世纪教会改革的内在旨趣。故而真能胜任的在世学者,当推耶丁无疑。
那篇书评并不短,总计有六页;从中可看出伊文尼特发乎本心的兴奋之情。他是太热爱那段历史了。事实上,伊文尼特的赞美之辞是真诚的,点评更是切中肯綮。但我们如果了解当时的学术背景,便能在书评的行文中体会到伊文尼特对耶丁那种由衷的羡慕、对特兰托的难舍之情以及难以言说的微妙心态。实则当时的伊文尼特已经决定放弃特兰托研究,这既是他的过于柔弱的性格使然,也是由于他在阅读耶丁的著作中,益发认识到自己在有生之年已无望与后者一较短长。

一生谦卑的伊文尼特绝不可能想象,他自谓无甚高论的讲稿甫刊布,便引起学界关注,尔后更是好评不断。甚至1970年,美国的圣母大学拿到了该书的版权,继续印行简装版。自1975年迄2004年,这部正文不过150页的小书竟有六刷的成绩,行销学术界三十年;至今仍是相关领域研究生讨论课的必读书以及学者参考引用的经典。
实际上,在《反宗教改革的精神》一书中,伊文尼特采纳了如今所谓“敬虔史”的取径,不再拘囿于教会典章制度以及教会政治的研究面向(即耶丁的强项——特兰托大公会议),而是从属灵信仰的层面切入,以耶稣会为范例,探析15世纪以还天主教灵性生活的复兴与变化。他认为,所谓反宗教改革在根本上乃是一场深刻的宗教复兴;无论是在精神上抑或是在制度上,这场复兴运动所运用的方法都为天主教注入了生命力,使她在现代世界因应新的力量和组织,同时在教宗的引领与控制下走上新的道路。天主教在16、17世纪从地中海和法国文明中汲纳政治实力,她所运用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彼时的主流精神和准则。
在1951年的英国,伊文尼特在讲座中提出这样的看法,无疑是大胆且令人震惊的。非特如此,关注灵性生活的敬虔史取径乃意大利学者德•卢卡(De Luca, 1898—1962)在法国学者启发下,于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推动的研究课题。他主编的《意大利敬虔史资料集》的第一卷1951年才问世,伊文尼特是绝无可能接触到这套资料的。由此可见伊文尼特的原创能力。事实上,伊氏《反宗教改革的精神》几乎穷尽了1951年之前相关领域的重要著述;而且他远比自己的英国同行关注和了解当时法国新兴的宗教心态史路数。可以说,伊文尼特是非常聪慧的学者,尽管总是自我质疑,在实际的写作中却能扬长避短,藉深厚的学养另辟蹊径,终为后世留下一部佳作。
我们以后见之明来看,就教会史研究而言,无论是70年代德国学者提出的“教派化”与“现代化”命题,抑或是同时期法国史家提出的“重新天主教化”范式,皆有伊文尼特的身影闪现其中。现在学界普遍接受的“新教改革和天主教改革是目标相似却平行发展的两条支流”之说法,乃是伊文尼特在那本小书中的的首创。
耶丁一生著述(加上各种文字的译本)达717种之多,而伊文尼特一生也就留下了两部重要作品。两造几无可比性。学术界好比是万紫千红的植物园,最漂亮最耀眼的花朵往往最能引人眼球,但这并不意味着朴素、低调的小花就一无所长,没有自己的春天。它们或许一生安静,却也隽永悠长,只待有心人来采撷品鉴。伊文尼特便是这样一朵小花;他或许湮没无闻,但从未远去。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