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访谈︱李启成:晚清立宪为什么没成功?
§近代中国人早期的宪政思潮多侧重于对议会的观察,多认为议会的最主要职能是有助于上下舆情的沟通,从而为朝廷决策收集思广益之效。
§近代西学东渐,中国人虽逐渐接受西学,但这种一元化的真理观并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真理从中学移至西学而已。
§为了追求他们所认为的惟一“真理”,规则对其有利时就严格遵守;不利时,就玩弄规则、超越规则。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启成
李启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法律史。曾出版专著《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点校《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新著《外来规则与固有习惯——祭田法制的近代转型》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曹勉之,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生,主治美国宪政史,旁涉比较法律文化等。
曹勉之:在《速记录》中,议员往往秉持文明和野蛮的二元分野,在他们的论辩策略中,立宪成了建设文明国家的不二路径,立宪就能和西方平等会商,接下来似乎就能革除条约之患,收回领事裁判权。
李启成:近代中国宪政思潮的输入是在国族危机愈加深重的背景下发生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后边会细说。这里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国人早期的宪政思潮多侧重于对议会的观察,当然渐渐也注意到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上面来。他们多认为议会的最主要职能是有助于上下舆情的沟通,从而为朝廷决策收集思广益之效。在这个意义上,它完全能服务于富国强兵之目的。
及至日俄战争以日本取胜告终,被当时很多国人解读为立宪战胜专制。历史学家李剑农讲得很到位:“于是反对变法立宪的人也没得话说了。俄国的人民也暴动起来了,俄国的政府也有立宪的表示了,中国还可独居为专制国么?”既然日俄战争被如此解读,那当然专制与立宪分别代表野蛮和文明,如能立宪则会像日本那样实现真正的富国强兵,收回领事裁判权,最终与列强平起平坐。晚清礼法之争,法派最具力量的理由就是这一点。在资政院里,持这种主张的议员多为法政新青年,人数也不少。
但需要指出的是,还有相当多的议员不是这样的,比如我们熟知的严复即认为没有地方自治作为基础来开发民智、培养民德,光有国会是靠不住的。等到1910年他本人被选为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对出席常年会以及讨论议案不是特别热心,在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中仅发议3次,甚至因为开会迟到早退还受到了一些年轻议员的批评。这类议员通常被视为保守派,人数不少。他们一般而言,传统学问造诣颇深,人生阅历较丰富,崇尚中庸之道,对固有政教很珍惜。他们多赞成速开国会,但反对新刑律中那些与传统律例极相抵触的条款,这可部分证明他们的价值取向。故我以为观察资政院议员,虽同属立宪派或改良派,群体考察综合分析很重要,但也要注意到他们的个体特征,避免将其脸谱化、标签化。
曹勉之:在《速记录》中,议员对于立宪普遍怀有低姿态,一方面,这表现为对西方政教文明的虚心求教,并不刻意标榜主体性,另一方面,它或而走到了惟洋是举,以各国最新立法例为改革目标的“矫枉过正”上面。不能“虚心切己”地意识到中西之别,或而也是立宪史上的一个遗憾。
李启成:同前一个问题相似,你所说的“惟洋是举”可能只是部分议员之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否则,在晚清就不会有礼法之争,在资政院也不会有“蓝票党”和“白票党”等称呼了。这里要思考的是为什么部分议员会“惟洋是举”。一个王朝到了晚期,我们往往说它是内忧外患不断、天灾人祸并行,晚清稍有不同的是,因外患而加剧内忧,如何避免外患、实现富国强兵是当时朝野重点关注的,保国保种保教之说能引起很多人共鸣的原因也就在此。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归来,打动朝廷的不就是“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这三条吗?在当时,真正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是西方列强。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实现富国强兵,在晚清朝野看来,表面是技艺上的船坚炮利,其实是以宪政为核心的制度优势。故出路显而易见,就是要在制度和技艺层面上“西化”。及至民国成立,发现制度西化也解决不了问题,就有了“文化西化”,到这一步,就是全盘西化了。此是后话,就不展开了。
逻辑既如此顺理成章,国族危如累卵,当然他们无暇从而也无力虚心切己从系统到细节探究中西之别,确实是中国近代宪政史的遗憾。在晚清,还有不少资政院议员认为中国虽在制度和技艺上不如人,但在文化教化上却独步天下,更愿意从文化类型角度来阐明中西之异。但他们对中西文化之异的解释也多半是结论先行,回头再去找证据。这就注定了他们不可能对该问题进行学理化探究。更关键的是,为拯救国族,“西化”已是势不可挡,保守派的主张、立场当然会日趋势微。章士钊所指出的“党人不学”这一严重问题确实道出了近代中国宪政演变的症结。所谓“党人”,当然包括立宪党和革命党,也包括激进派和保守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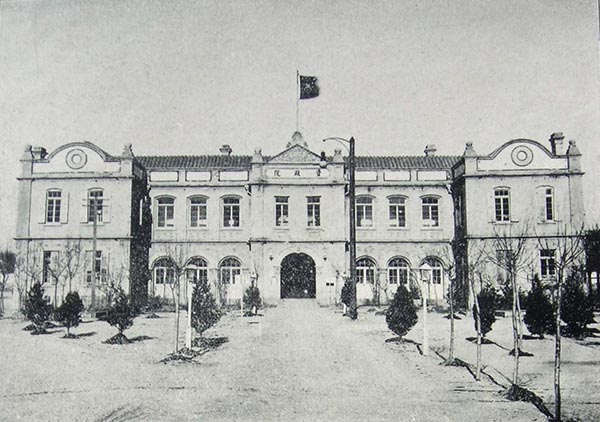
曹勉之:这里面,士人风骨和法政新知的关系就格外有趣起来,所谓资政院三杰的罗杰、雷奋等,他们的人生经历和际遇就都是很有趣的样本。
李启成:我以为,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是近代中国一个大事件,我们对其影响一直估计偏低。在这一点上,费正清等海外学者的眼光可能更犀利。科举废除之前,士大夫是以服膺圣人之道的态度来读儒家经典,个人信念和前途是相对统一的。儒学自春秋时期形成以来,随着社会变迁和王朝更迭,自身虽发生了各种变化,但在这不断的变易中,儒学尚保存着一不变的基本性格,那就是真正的儒者应以天下苍生为念,并以此谏诤于暴君,甚或直斥其非。这种性格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士人风骨。
资政院议员中的大多数人,在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前,多已成为秀才、贡生或举人,少数还成为进士。科举废除之后,恰逢留学潮,他们就到海外,主要是日本去学习法政。所以在这批人身上,士人风骨和法政新知能得到良性结合。资政院三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是易宗夔、罗杰和雷奋。
易宗夔,湖南湘潭人,1874年出生,年轻时在梁启超创办的《湘报》上发表文章,颇受瞩目。1903年赴日入法政大学学习,归国后一直在湘潭和长沙办教育。他在第一次常年会共发言419次,是激进派议员代表,被戏称为《水浒传》中的李逵。
罗杰,湖南长沙人,1867年出生,也是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回国后在本省从事教育和地方自治工作,共发言138次。
雷奋,江苏华亭人,1877年出生,为清末状元张謇门生。日本早稻田大学卒业。共发言146次。
这三人,总发议高达703次,占整个民选议员发议数的1/4左右,且他们在弹劾军机案、速开国会案、新刑律案、预算案中都有突出表现。
曹勉之:有趣的是,《速记录》所呈现的晚清立宪政治只能说是历史的一个面向,从同时代人的日记档案中,我们又能看到另外的一面。就以汪荣宝为例,您在小传中就说,他白天在议会上慷慨陈辞,到了晚间却奔走于权贵之家。
李启成:史学研究之所以需要充分利用多种类型的史料,就是要发现历史的多重面相,尽可能接近历史之本来面目。拿汪荣宝来说,他在近代中国法制史中很重要。《速记录》中的汪荣宝热心君宪、对新法制建设尽心尽力。我将汪荣宝在资政院常年会上的发言与其日记记录对照,发现汪荣宝等法派人物为了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新刑律》,集体商议,搞了很多小动作,故意让《新刑律》“分则”完不成三读程序,使得礼派在议场表决“无夫奸”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
汪荣宝将这些幕后动作记入日记,固有诚实一面,亦表明他认为如此幕后操作,没什么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模范列强,制定新律,乃是中国走向进步的惟一正确道路;礼派人员完全是程度不足,无法理喻。为了追求他们所认为的惟一“真理”,规则对其追寻有利时就严格遵守;不利时,玩弄规则、超越规则也是理所当然,没什么不应当的了。殊不知,这些规则都是汪荣宝他们所认可的。法治之真精神,必包含守法;守法之要义,不在于有利时能遵守,恰在于不利时亦能遵守,只要它本身为我所认可。在这个方面,号称“趋时”的法派议员,反不如“守旧”的礼派议员表现得好,实在是近代中国的悲哀。
传统中国越到后来,皇权专制愈登峰造极,是非实际上越来越出于一尊,强化了中国人一元化的真理观,成为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近代西学东渐,中国人虽逐渐接受西学,但这种一元化的真理观并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真理从中学移至西学而已。到20世纪初,以进化论为实质内容的天演论风靡中国思想界,而进化论是以肯定发现了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为前提的。这一时期,正是这些法派议员接触并学习西方新知的阶段。他们接受了进化论,自然更强化了其本就固有的一元化真理观。
一元化真理观表现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惟一的,那些信奉一元化真理观的人也往往倾向于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既然真理在我手,那采取各种手段以传播真理、推动真理之实现就是完全应该的了。这是汪荣宝他们超越规则行事、搞幕后小动作却心安理得的重要原因。如何克服这种自认为真理在握的价值准则,养成宽容之习惯,培养守法精神,是建设中国宪政尤其需要留意之处。

曹勉之:士人风骨似乎成了一个断裂的传统,在此之后,与立宪沾边的人物大有人在,有的议员从北京做到广州,从民元国会做到非常国会,算是两面为人,几世做官。论政治的原则或是操守,则往往荡然无存了。
李启成:在北洋时期,各种临时、正式国会开开闭闭,议员数量增加很多,但他们对政府的慷慨批评之词却越来越微弱,反之特别费、贿选总统等丑闻迭出。民国成立,大部分较为“保守”的君主立宪党人,以资政院议员为代表,因不赞同共和立宪而被边缘化,更年轻同时也更倾向革命的新一代人成为民国议会的中坚,情形有些变化,其体现之一就是真正信念的弱化,这就是你所说的士人风骨之断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士人风骨的断裂,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新一代议员成长之时,科举已被废除,儒学,尤其是圣经贤传,不再是他们自小浸淫并进而内心服膺的东西。此一价值之源被抽空,儒家经典多等同于诸子,成为章句记诵之学,不复有安身立命之大用。本来,处于近代这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包括价值系统在内的新陈代谢本就含有某种必然性,无可厚非。但代替儒学、代替科举之新学问,也就是新式法政之学,主要是给修习者提供知识和技能,却无法为其在深层次上提供价值之源、安身立命之道。建立在统一价值观基础上社会最低限度的共识没有了,为人自然就缺乏底线,议员们又何能例外!
曹勉之:从资政院议员的人生历程里,我们观察到了“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两条不同路线,革命之后,很多议员回到家乡,开始了地方自治的建设。这场立宪的高潮最终以悲歌一曲收场。
李启成:受余英时先生研究的启发,我以为,士阶层自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以来,尤其后来的儒家士大夫,其政治理想是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要实现这个理想,他们必须取得君主的绝对信任和支持,像诸葛亮与刘备、王猛与苻坚、王安石和宋神宗那样。将这种行道模式概念化就是“得君行道”。及至明代,宰相制度被废除,君主专制日渐强化,君主不再承认士大夫的政治主体地位,只是在工具层面上认为士大夫对他们治国有用而已。而明代除了极个别外,绝大多数君主都不足与言治国平天下之道。因为对君主个人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失望,以王阳明先生为代表的诸多士大夫渐渐认识到要实现政治抱负,不能再采用传统“得君行道”方式,而要“觉民行道”。
所谓“觉民行道”,指的是士大夫以宗族、乡党等社会关系为基础,以族田、义田等为物质载体,通过民间宗教崇拜、撰修族谱、制定家法族规、乡规民约等手段,为大多数黎民百姓创造了一个相对自治的生存空间,让暴虐专制的皇权进入不去基层社会。清代统治者尽管依旧不承认士大夫的政治主体地位,但认识到民间社会的稳固对朝廷长治久安有利,遂把士大夫“觉民行道”的内容拿过来自己用,即《圣谕广训》所讲的“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这种情况到了晚清,随着西方地方自治思潮的传入,士大夫逐渐意识到地方自治乃国民进步之阶梯、宪政之根本,同时这种地方自治之内容以教育、实业等为基干,恰与明清士大夫所一直努力创建的民间社会空间有相通之处,因此诸多士大夫愿意投身到此种自治活动中来。
进入民国后,当年的那些资政院议员,他们中不少人仍然坚持在君宪之下通过教育和实业之发展来改变中国的道路,并不认同以革命手段来建立共和宪政的做法,遂在清亡后,主动远离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回到生长于斯成名于斯的家乡,依旧从事基础性的教育或实业工作,以此度过余生。这些议员们在民国的归隐或者说边缘化,昭示着君主立宪在中国的完全失败。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