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梁文道专栏:危险的思想
很多年前,某大学曾想召开一场张爱玲文学国际研讨会。可是很不巧,那年正逢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所以计划只得告吹。为什么纪念抗战的同时就不能研究张爱玲呢?那当然是为了她“失足”的历史,什么人不好爱,竟然爱上了汉奸胡兰成。此中逻辑,二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是要被大多数人嘲笑的,仿佛“汉奸”是种神奇的传染病,不只会在男女黏腻间交流,而且还能潜入文字,把后来读者一一熏染成了小汉奸。于是胡兰成的文章固然不可读,就连爱过他的张爱玲也一样不准研讨。
我想,现在大部分自认是讲点道理的人,都会觉得文章和政治必须分开来看。别说张爱玲没写过一篇附逆文字,就算她有,也不能影响读者对她的痴迷。这种道理,大概已成常识;不同领域我们分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作品与人品,本来就不能轻易混淆;不以人废言,岂非古有明训?
问题是会不会真有这种情况:一个人既是我们政治上的公敌,同时又是个大文豪、大哲人,并且言行如一,政治上的邪恶完全表现在他的文字和思想里头,乃至就连读他的东西都可能是错的呢?两个月前,海德格尔遗稿的最后一部,未出版先轰动的《黑色笔记本》,终于成书上市,掀起风暴。那风暴的核心大抵就在于思想的危险。

1945年,战后不久,彼时声望甚隆的卡尔·雅斯贝斯受邀考察他这位昔日老友,看看这个堕落了的大哲学家到底适不适合再当老师。结果,他向盟军占领当局的负责机构报告:“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青年人的教育问题事关重大,责任非浅。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完全的教学自由,现在还不能马上实施。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思维形态是拘谨、专制、封闭,如让这种思想在青年教育中发生影响,后果不堪设想。在我看来,思想的形态比政治判断的内容重要。政治上的判断的进攻性很容易转变方向。只要这个人没有在现实行动中证明他已完全悔过自新的话,就不可以向几乎毫无抵抗能力的学生推荐此人为老师。首先要让青年人学会独立思考。”尽管四年之后,雅斯贝斯就又写了一封信给弗莱堡大学的校长,要求把海德格尔这位“在德国没有人能超越他”的哲学家带回学校;但他这段相当有名的证词,已然种下后来的根茎,开启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字丛林战。

然后我们就能理解《黑色笔记本》的分量了;一部一千多页的哲学家遗稿,居然上了欧陆好几份大报的社论(忍不住要学陶杰的口吻;对比内地、香港的报刊为了街头便溺交火,人家和我们似乎真有文明的差距)。你看,这里头竟然有这种话:“世界犹太主义在各处的影响深不可测,当我们在牺牲我们种族中最优秀者的血液时,他们却根本用不着介入军事行动。”犹太人之反对纳粹的种族理论,“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凭着计算的天分,就可以按照种族原则活得长长久久”。这两句话还不算什么,对于稍稍读过海德格尔的人而言,最震撼的莫过于他还把他那著名的“无世界性”概念与犹太人联系了起来,指出现代世界的拔根与空洞,多少得算在四海为家,心无所属的犹太人头上。于是,时常批评犹太人“离地”、“不够本土”的纳粹意识形态,便与海德格尔哲学对现代人之病的诊断,发生了奇诡的关系。难怪海德格尔家族嘱托的遗稿主管,是书主编彼德·图朗尼(Peter Trawny)都说:“海德格尔不只摭拾了这些反闪观念,而且还哲学地推演它们。他无法使他的思想免疫于如此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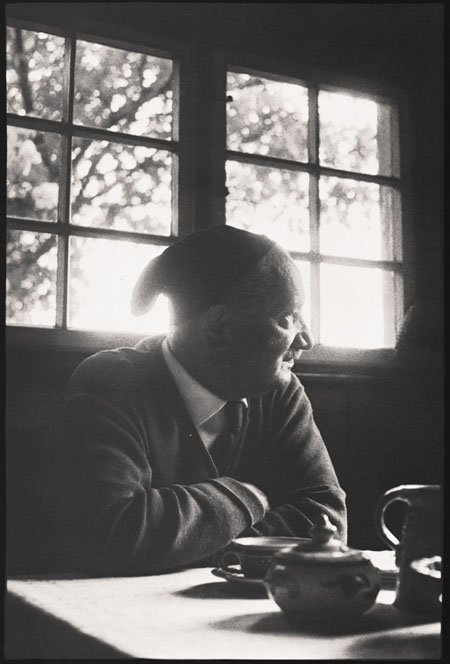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