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马识途兄弟各出百岁回忆录,《让子弹飞》里的都是真事

附:《百岁追忆》选摘
马士弘/文
一生无所悔恨
我是 1911 年 8 月出生的,那一年正好是晚清民国交替的时期,发生了辛亥革命。
我的一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讲。分界线是1949 年 12 月。那个时候我是国民党军队少将副师长,随同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在郫县起义。两个阶段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我的名字也是这个样子,起义前叫马千毅,这是我父亲给我起的名字。马士弘这个名字是我小学老师给我起的, 根据《论语》上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但当时我没有用这个名字,一直叫马千毅。起义后一切都变了, 我就干脆把旧名字也改了,叫马士弘。现在我仍用马士弘这个名字,但老家的人仍叫我马千毅。
我们兄弟从小在严父慈母抚育教诲下成长,念了一些书,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我在北平读大学时,目睹日本侵略中国,激于青年爱国热忱,投考国民党军官学校,从此注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八年中与日寇经历了大小二十余战,有胜有负,值得记述的战绩之一, 就是 1943 年的湘鄂大会战,敌我各投入兵力二十余万人,战斗四十余日。这一役我军大捷,当时我担任副团长兼营长,率领六百余名官兵,担任军的前卫营,追击日寇,曾救出五百一十二名中国年轻妇女,使她们和家人重聚。
我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了十四年,与我的其他兄妹不同。我兄弟姊妹六人,除大哥从小一直在
家务农外,其余四人,都先后成了共产党人。秀英妹还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现在来说,我似乎走错了路。但我投笔从戎,终于遂了我的抗日夙愿,无所悔恨。
家乡
我的家乡是在四川忠县石宝乡坪山坝上坝。
家族原籍为湖北麻城,明朝末年移民填川,祖辈沿着长江西行,一直来到忠州石宝寨所属的坪山坝,见到这儿前临长江,背负大山,坝长约五华里,为长江多年泥沙冲积而成,土地肥沃,适宜耕作,是一块务农的好地方,于是定居下来,世代相传,日渐发展,沿着山脚建了很多房子,连檐相接,逐渐形成一条半边街,聚族而居。
族人分地耕种,尤其以出产红甘蔗著称。红甘蔗是我们这儿的最佳特产,甜脆味纯,能当水果吃。每一年,祖辈们都要背红甘蔗到附近场镇销售。因冬季是水果淡季,甘蔗很好销售,获利不小,于是坝上土地大多种上红甘蔗,族人生活也不同程度地接近小康。
祖传种植的红甘蔗也有一个弱点,就是易生虫和矮小。我父亲见到这种情景,和家乡老农一起研制防治虫害的药物,研究如何培育生长粗壮的良种,改进耕种技术,提高产量。又研究改良靠山边坡地土质,使红甘蔗长得又高又粗壮,少虫眼,质量更甜脆,产量逐年增加,在我家乡更普遍地发展起来。为谋更大利益,我父亲又组织族农雇大木船装运出川,过三峡远销宜昌、沙市等地,获利更大。民国成立后七八年内,我坪山坝乡亲们已是衣食无虞了。
不过,我小的时候正处在乱世,四川出现了很多土匪,家乡也发生过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读小学时,就发生过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任县长来忠县报到,马上就要到县城了,却不慎从船上栽到水里,尸首很快就漂走了。欢迎仪式已经开始,鞭炮都点燃了,这种情况下,县长秘书决定冒充县长,而县长夫人也点头同意了。那时我父亲在县里当议长, 假县长还来我家拜会, 我也见到过。好几个月后,有人举报,假县长被撤职查处,关了起来,县长夫人也带着娃娃离开了。这件事,县里家喻户晓,我也告诉过五弟马识途。他后来写的《夜谭十记》里面的很多事情都是那个时代的真事,只不过做了艺术加工了。 《让子弹飞》里面铲除恶霸黄三爷的事情,也是有故事原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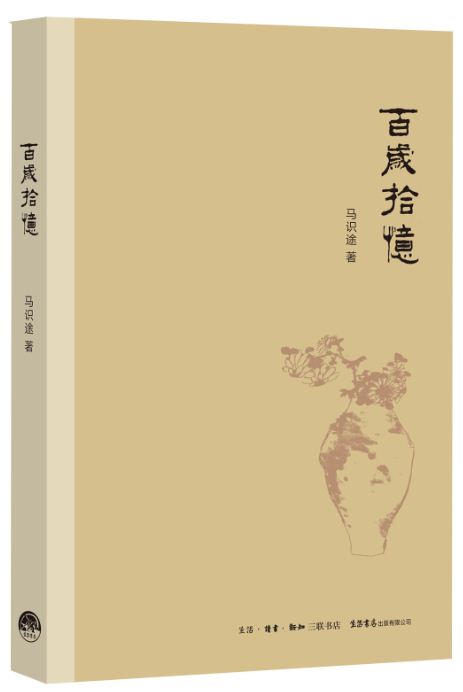
我出生在马家大院
在号称长江三峡明珠的旅游胜地石宝寨附近有一个由长江回流冲积而成十分肥沃的平沙坝。平沙坝纵横十里,三面围山,一面临江,马家大院便是建造在这坝里一个小山脚下,据说那是龙脉的所在,是马家大族得以兴旺发达的根源。大院前临一条蜿蜒流向长江的小溪,树木葱茏,翠竹森森,十分幽静,一派田园风光。
马家大院是一座颇有几分气派的所谓四角头大院子。远远望去,一坡石梯上去,一片白粉墙的中间是高耸的八字大朝门,中间大门上挂一块金字大匾,据说是四川布政使送的,那是省级的大官了。大门两边悬着“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大字对联。这个大门只有婚丧大事或接待贵宾才能打开,平常都是从两边耳门进出。
走进朝门,就望见上面一排七开正房,中间一间比较大的是大院的中心,号称堂屋。堂屋正面高墙上有个像小门楼的神龛,神龛上供着“天地君亲师之神位”的金字木牌,木牌上的那个“君”字已经用红字写的“国”字盖住,表示现在只有民国,没有皇帝了。
这个堂屋是大院举行诸如婚丧大事、过年过节,便在这里举行仪式。我们最喜欢过大年在这里向祖宗和家里的老辈人叩头,因为可以得到我们期望的压岁钱。
在正房前面的石栏杆下,是一片用青石板镶的石坝,可以摆二十几张方桌,容纳二百多马氏家族的人来这里拜年吃春酒。那九大碗的筵席和马家糟房的白酒,足够大家吃饱喝足,痛快过年的。
这个石坝每逢过年都很热闹,白天舞狮子,晚上玩龙灯彩船,唱歌,舞蹈,打倒钱,放烟花爆竹。还有夏天天旱,会在石坝里玩水把龙。这些时候,大院的人和远近乡里头的人都会来看热闹,石坝两边和朝门里的大敞厅,全都挤满了乡人。那些游艺队伍有外地来的,也有本地青年自娱自组的。他们到各大院子去巡回演出,演出完后,便向坐在石栏杆后上首的大佬们讨赏钱。每领一注赏钱,便加玩一个节目。
看游艺自然是快乐的事,可也是青年男女们得到交往的机会。有的女子点燃爆竹投给玩龙灯彩船的自己心爱的青年男子。这种示爱方式,好像并不受禁忌,甚至有的偷偷牵着手溜出朝门,到野外游耍谈情说爱去了。
马家大院是何代何年何人修建的,已不可考。住在马家大院里几十户马姓人家,有穷有富,都在忙自家的生活,没有兴趣去考校这些不能当饭吃的祖辈光荣,唯独每年在一起吃年饭,老辈子不忘记说起祖宗的光荣,并且提出在客房楼上杂物堆里那顶官轿、鸣锣开道用的“肃静”、“回避”牌子,还有那顶有野鸡翎子的官帽,就是光荣的见证。于是大家按序跪在堂屋里向祖宗牌位叩头,一同享受一下光荣。然而对那些残留光荣信物真正有兴趣的是我们大院的孩子,那是我们的玩具。
我的父亲
我们马家虽然号称书香世家,可是马家院子里的几十户后代,随着几代人的分家析产,大半已成为破落户。家道中落,住在马家院子里的男子汉,大半是只认得自己的名字,方便在按红手印时不至于按错。这些长年在田地里刨食的泥脚杆,只有在大院要举行什么仪式,又如过年祭祖,他们才从箱底翻出半新的蓝布长衫穿上,去面对书香之家的祖宗牌位。少数在私塾混过一两年,粗识文字的,能在场镇上看懂官家的告示和读懂契约文字,就算满意了。在这个大院里,真正能够继承马家书香门第的恐怕只有一人,那就是我的父亲马玉之。
我的父亲出生于前清光绪年间的 1886年,小时候读过私塾,背过四书,谙习孔孟之道,后来上了新学的中学堂,除文化古典外,还读新学的《算术》、《格致》(格物致知的理化学科)和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打基础的《修身》课,二十出头才毕业。
辛亥革命前后,父亲跟着一批激进分子,闹过一阵革命,大家去日本留学时,他却因家道贫寒不能出国,只捞到一个区督学,穿着长衫,夹个皮包,在乡下督学。后来从北京到省县都挂上五色旗,办起了议会,父亲去竞选,当上了县议会议员,由于他工作勤勉,被推举为议长,从此进入社会上层,成为有模有样的人物了。再后来,父亲被当时四川最大的军阀、四川善后督办(相当于省长)刘湘赏识,调他到重庆帮办军政训练班(有如今日的党校),刘湘任主任,父亲任副主任和训导。
父亲的积极性和能力为刘湘所赏识,于是被刘湘任命到当时土匪猖獗、豪强称霸的川西边僻小县洪雅去当县长,专治匪患。父亲在洪雅期间,软硬兼施,权谋诡计,基本上平了匪患,当地的老百姓给他送了万民伞。刘湘得知后,便把父亲调到让他头疼的家乡大邑县任县长。
和洪雅同样位居川西的大邑县,是个出产大军阀的地方,那里恶霸横行,兵匪一家。父亲带着一排人的手枪队前去上任,当地最大的恶霸刘文彩本想给父亲来个下马威,但一番较量,父亲占了上风,站稳了脚跟,深得刘湘赏识。
父亲正把大邑县治理得有了头绪,洪雅县的土匪又死灰复燃,民众上书刘湘,要求重调马玉之回洪雅治匪。于是父亲又回到了洪雅当县长。这一次,他亲自带兵上山剿匪,并且诱杀了当地的匪首,使洪雅县的治安得到恢复。他还在洪雅修路开渠,发展生产。他主持修的洪雅花溪渠,至今还在使用。前两年我到洪雅,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因为这条花渠,让他们旱涝保收。
蒋介石进军四川后,刘湘倒台,父亲也跟着垮台,只留下一块万民碑。抗战时期,偏安重庆的国民政府粮食部长,请父亲出山为重庆集运粮食,他干了一阵川西粮食专员,觉得难有成就,便告老还乡,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在我幼年的印象中,我的父亲有着颀长的身子和方正的脸,最显眼的,是他那看上去不知有多少光圈的深度近视眼镜和上嘴唇上那两撇显示出景从当时革命党人形象的八字胡。父亲经常坐在他书房的那张躺椅上,不是读古书就是读他一直订阅的天津《大公报》,还有就是捧起他那一直随身的白铜水烟袋,悠然自得咕咕地抽水烟。
那个水烟袋经常被我们兄弟擦得锃亮,那是我们能亲近有着严肃面孔的父亲的契机。隔三差五的,我们会争着抢着去擦这个水烟袋,然后装上烟丝,点上纸媒儿,把烟嘴送到父亲的嘴边,他抿着嘴将纸媒儿吹燃,含着水烟袋烟嘴,吮吸烟锅里点燃的烟丝,咕噜咕噜地享受抽烟的快乐。他高兴了,便会拍拍我们的脑袋,发出稀有的微笑,这就是对我们的奖赏。
但是这微笑会迅速退去,紧接着,就会听到他严厉的声音:“今天的书念完了没有?”这时,我们便会自觉地退到楼上我们的书房里去,读他让我们读的《纲鉴易知录》,以及我们喜欢看的《三国演义》、《封神榜》之类的小说,还有我更喜欢的《大公报》上的“小公园”副刊。
我不知道父亲从哪里讨来的那么多古圣先哲的格言,一串一串地背给我们听,教我们如何处世为人。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八个字:“胆大心细,智圆行方”。有时,父亲还要我们剪下他指定的《大公报》上的社论,要我们读给他听。
我们特别听到父亲的教诲是:“你们要自己出去闯,安身立命,一切靠自己。“因此,他有个母亲不以为然他却一直坚持的决定:在我们兄弟满了十六岁时,一律赶出三峡,到外面去闯荡,安身立命,绝对不准留在老家当游手好闲的“公爷”。我正是十六岁初中毕业后,离开家乡,走出三峡,到北平去上学的。 令我们悲痛不已的是,上个世纪 50年代初,我父亲乘木船去赶场,在石盘滩时船翻,落水而亡。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