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如果一个女人感到痛苦,不是因为她不够进步
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来一同面对“痛苦”这个词。今天的文章来自第六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翻译得主陈英的译作《碎片》。
《碎片》是《那不勒斯四部曲》作者埃莱娜·费兰特的书信、访谈和散文集,“碎片”这个词似乎正符合内容的形态,但依据费兰特自己的解释,“碎片”还有更特别的意涵,它的意大利原文是她母亲经常使用的一个方言词汇——“当一个人遭受各种矛盾情感的折磨时感受到的东西,她说她内心一团 ‘碎片’(frantumaglia)。”
之所以提到这个词,是因为埃莱娜·费兰特接到了记者的询问:她塑造的两位女性角色的痛苦从何而来?费兰特不觉得痛苦完全与清算古老女性形象的意识有关,而是说,她们要面对内心的碎片,在一瞬间,过往女性的痛苦、过去经历的痛苦和对未来的期待同时出现。费兰特对女性情感结构和身体经验的体察让她害怕把故事讲成“与过去割裂的进步”,所以她让她们处在被形容为“碎片”的痛苦中再讲述它,而这恰是她们生命能量的展现。
碎片(节选)
撰文:埃莱娜·费兰特
亲爱的桑德拉:
我感觉自己有些出息了,我们可以笑一笑了。在写完《被遗弃的日子》之后,你看看,我是怎么回答《目录》杂志那两位女士提的问题。
我有些羞愧,疯狂整理了一下房间,我打开了抽屉,翻阅了一些东西,给那些问题找到了答案。
我本可以把写出来的东西自己留着,但我还是很乐意发给她们。一个人带着激情写的东西,总是需要一个读者。所以我把这封很长的信发给你,请你转发给那两位采访者。但你要讲清楚,我不会修改这封信,不会为了发表精简内容。
假如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看一看这封信,这是游离于我的两本小说之间的文字。我想象——真的是我想象(真实的书已经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已经不属于我了)我写了那两本书。你如果看一下我写的答复,我会很高兴。
如果你写信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会非常感激。
以下就是这封信的内容。
亲爱的朱莉亚娜·奥利维罗、卡米拉·瓦莱蒂:
我非常感谢你们提议要对我进行采访,我尽量把问题的回答写得清晰直接。但是因为你们提出了一些非常复杂也很专业的问题,我觉得,简单的答复可能不是很合适。后来,我就不再考虑采访的形式,我只是想着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
旋涡
你们问我,这两本书里谈到的女性痛苦,你们还提出了一种可能,你们说《烦人的爱》中的黛莉亚和《被遗弃的日子》里的奥尔加都是现代女性,她们痛苦,是因为她们需要和自己的根源、出身,和之前古老的女性形象,还有残存在她们内心的地中海神话原型进行清算。的确有这种可能,但我必须想清楚,要想清楚的话,我不能从你们提出来的“根源”讲起,这个词词义过多。还有你们用的两个词:“古老”“地中海”,也让我迷惑。假如你们愿意的话,我更愿意深入分析你们提出的另一个词——痛苦, 这个词从我童年开始一直在陪伴着我,包括在我写这两本小说时。

由小说《烦人的爱》改编的意大利电影《肮脏的爱情》L'amore molesto(1995)剧照
我母亲留给我一个方言词汇,那是她经常说的,就是当一个人遭受各种矛盾情感的折磨时感受到的东西,她说她内心一团 “碎片”(frantumaglia)。这些碎片折磨着她,在她内心东拉西扯,让她头晕,嘴里发苦。这是一种很难说出口的苦,指的是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搅和在一起,就像是漂浮在脑子上的残渣。“碎片”神秘,会让人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它会引起那些难以名状的痛苦。当我母亲不再年轻,这些沉渣“碎片”会让她在夜里醒来,让她自说自话,又让她对此感到羞愧,会让她不由自主哼唱起一些小曲儿,但很快会变成一声叹息,也会让她忽然离开家,也不管灶火上的拌面酱烧糊在锅底上。有时候这些“碎片”会让她哭泣,这个童年起就留在我脑子里的词汇,通常指的是无缘无故的哭泣:“碎片”的眼泪。
现在已经没法问我母亲,她说的那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解释,我从小都觉得,内心的“碎片”会让人痛苦,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个人如果很痛苦,迟早就会变得支离破碎。碎片到底是什么,我之前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现在我脑子里有一系列关于碎片的意象,但都是和我的问题相关,而不是她的问题。
碎片是不稳定的风景,是一片空气,或者是水汽,都是废气,无限延伸开来,粗暴地向我展示它真正的、唯一的内在。碎片是时光的堆积,没有故事或小说中的秩序。碎片是失去带来的感觉,当我们觉得一切都很稳定持久,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得以依靠的东西,很快就和堆积的碎片融为一体。碎片就是感觉痛苦不安,这种不安缘于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声音会淹没在这堆碎片中。有时候,我会和奥尔加——《被遗弃的日子》里的女主人公——一样,也会面对她所面对的问题。有时候我会觉得脑子里嗡嗡作响,过去和现在搅和在一起,形成一个旋涡:像一窝蜂一样,飞过一动不动的树顶,向我飞来,就像在流水上忽然转动起来的风车。
我小时候看到过那种情景,在我的童年时代——成人称之为童年的那段时光,我觉得,语言进入了我的内部,灌输给我一种新的言语:各种颜色的声音爆发出来,像成千上万的蝴蝶,长着能发出声音的翅膀。或者这只是我表达死亡,还有对死亡的恐惧和不安的方式,恐惧会让人忽然失去表达能力,就好像发声器官突然瘫痪。从生下来就学会的,我们可以控制的东西,现在都各自流散,我的身体就像一只皮袋子,会漏气、漏水。

我可以继续列出我们家庭内部经常使用的其他四五个词汇, 通过这几个词汇表达所有我想说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要说清楚我笔下两位女主人公的痛苦,我只用说:她们要面对内心的碎片。我还保留了《烦人的爱》中的几页,那是后来被我删去的内容。在这几页中,我就是想说明这种状况。这一段是关于阿玛利娅乌黑的头发,这是女儿黛莉亚在那不勒斯追寻母亲死因时描述的一段。
我的头发很细,跟我父亲一样。我的头发又细又软,看起来不蓬松,也没有光泽,它们随便披散在头上,很不听话,我非常痛恨我的头发。我也没法把头发梳成像我妈妈那样,挽成一个发髻,额头上有一个波浪,几撮不听话的小发卷会出现在眉毛上面。我看着镜中的自己,非常生气。阿玛利娅真的很邪恶,她希望我永远都不要像她一样美丽,她没有把她的头发遗传给我,她的头发又好又旺。她生我生得不好,我的头发真的不怎么样,很容易粘在头皮上,就像一个深色的毡帽,颜色也不明确,我的头发是褐色的,但颜色又有些浅,真让人觉得造化弄人,不像我母亲的头发那样黑漆漆的,不是像玻璃一样闪闪发光的头发,可以吹一口气进去说,真是太美了。没人说我的头发美,我把头发披散下来,我梦想着要让头发长得很长,一直搭到脚上,要比她的头发还要长,我不记得她曾经把头发披下来过。我的头发总是乱七八糟,很不优雅、不体面地在空中飘散,根本梳不到一起。她的头发就像春天的稀有植物一样生气蓬勃,我的头发一点生机也没有。
这样一来,有一次我不知道有什么诱因,我当时十二岁,可能是我想发泄一下内心难以名状的痛苦,可能我只是觉得自己特别丑,根本没办法补救,我难以找到自己的魅力。可能我只是想挑衅我母亲,向她展示我的仇恨。我从裁缝那里偷了一把剪子,我穿过了走廊,把自己关在洗手间,把头发剪得乱七八糟,我没有眼泪,我感到一种无比残酷的快意。在镜子中出现了一个陌生女孩,一个脸很消瘦的陌生人,眼睛又长又细,额头苍白,头上长着稀疏的头发。我想,我是另一个女孩。我马上就想,头发之下, 我母亲也是另一个人。别的人,别的女人,别的女人。我的心怦怦跳,我看了看洗手池,看了看地板,看到落在地上的碎发。我有两种需求,首先我要把这地方打扫干净,我不希望我母亲看到地上的头发会不高兴;然后我要去向她展示我现在的发型,我想让她痛苦。我想告诉她:你看,我不需要像你那样梳头发了。我母亲坐在缝纫机前工作,她听见我叫她,她转过头来问,你在干什么?她叹了一口气。她眼圈发红,眼里充满了泪水,她没有叫喊,没有打我。她没有像平常那样惩罚我,我看到有某种东西伤害到了她,让她害怕, 她哭了起来。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烦人的爱》中的母女:阿玛利娅和黛莉亚
我现在知道十年前我为什么要把这一段删除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太过于揭示母女之间的关系,它会使其他重要时刻变得黯淡。现在重读这一段,我也没有改变这一想法。头发所代表的东西很明显,过于明显,我没有提到参孙和大利拉的传说,还有信使女神伊里斯剪去狄多金色的头发的典故 [1],我觉得羞怯,也不期望我所写的能被人引用、重写和改写。无论如何,我现在对这一页的内容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比如说,黛莉亚狂热地想从她身上抹去母亲的形象,就好像假如她不摆脱母亲,就无法一步步成为一个成熟女人;还有最后阿玛利娅的哭泣,这个哭泣,我不确信它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夸张了。
女儿和母亲,小孩和成人,她们看到只是动了一下头发,就好像发生了地震。黛莉亚透过镜子,除了被剪掉的头发,她看到了很多东西。阿玛利娅看见女儿的头发乱七八糟的样子,也隐约看到某些东西,一种她说不上来,但让她流泪的东西:我女儿很抵触我,我没法和女儿建立一种亲密关系。她在成长过程中拒绝我,会让我变得粉碎。这个动作触到了非常深的一根弦,一个渴望的发型,一个不能拥有的发型,很多东西都重叠在一起了,这个举动像砍断一座桥梁,切断一根连接,打开一个阀门,让人哭泣。我笔下的两个人物,黛莉亚和奥尔加,都产生于这个动作:两个很在意自我的女人,她们会加强这种自我,想把自己武装起来,但是她们发现,只是剪头发这样一个行为,就足以让她们失措、崩溃,觉得很多碎片向她们涌来,这些碎片有的有用,有的没用,有的有毒,有的有益。

《圣经》传说中,参孙被情妇大利拉剪去头发后,神力尽失
为了搞清楚这是不是真的,我翻阅了那两本书。我想看看, 我是怎样塑造黛莉亚这个人物的,但我只看了二十几页。我在看奥尔加的故事时,只看了几行,我还清楚记得我描写她的句子。最后,我选择通过文本反思这两个人,我发现她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这两个女人都有一种有意识的自我监控。之前的女人受到父母、兄弟、丈夫,还有整个社会团体的监控,但她们的自我监控非常少,假如她们进行自我监控的话,那也是模仿别人对她们的监控,就好像她们是自己的看守。黛莉亚和奥尔加的自我监控是一种非常古老,同时又很新的形式,这种监控是源于她们要探索生活和生命。我在下面尽量解释一下,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监控”通常是一个警察用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违法的事情,但它不是一个糟糕的词。它包含着一种对昏沉和迟钝的对抗,这是一个比喻,可以对抗死亡、麻木。它突出的是清醒,保持警惕,是感受生活的一种方式。男人把监控转变成了卫兵、守卫和间谍的工作。但监控,假如要理解清楚的话,是整个身体的情感设置,是围绕着身体产生、延伸出来的东西。
这是我很早之前就产生的想法,我思考在这个糟糕的行为——监控背后隐含的东西。我非常惊奇地注意到,那段描写头发的文字里就饱含着这层意思——我差不多都已经快要忘记了。那些写得糟糕的文字,有时候要比写得好的文字更强烈。监控这个动词,指的是生命的延伸,和这个词相关的“监视”和“清醒”,我觉得更能揭示监控的深意。
我想,一个怀孕的女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母亲对于孩子的“监控”:身体能感到一种光环,一种波浪在传递,没有一种感官不是激活的、清醒的。我也想到了祖祖辈辈的女性,她们对于生命之花绽放过程的掌控。我想象的不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情景:监控也是一种强加、一种矛盾,用自己的所有力量进行扩张。有些人认为,女性生命能量的迸发要超过男性生命能量,我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我只是认为,这是另一种能量。让我高兴的是,现在这种能量越来越明显。
我认为,要回到我所强调的那些词意,我所说的是对自己全新的监控形式,要关注自己的特性。女性身体已经意识到了,需要进行监控,去关注身体的延伸、能量。是的,能量。这个名词好像是针对男性身体的。但我怀疑,刚开始它只是指女性的特点,女性的活力特别像植物具有的活力,会扩张的生命,比如藤蔓植物。我特别喜欢那些警惕的女人,她们能够监控,自我监控,这就是我所说的意思。我特别喜欢去写这种监控,我觉得她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女英雄。黛莉亚和奥尔加这两个人物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烦人的爱》女主人公黛莉亚
比如说奥尔加,她对自己的审视是通过一种“男性的”角度,她学会了自我控制,自我训练,试图做出一些符合常规的反应,她最后从被抛弃的危机中走了出来,就是因为她的这种自我监控,她一直保持警惕。为了让自己清醒,她把一把裁纸刀交给她女儿,告诉她:假如你看见我走神了,假如我没听你说话,我不回答你,你要用这把裁纸刀扎我。这就好像在说:伤害我吧,利用你的负面情绪、你对我的仇恨,但你要提醒我活下去。
这样一来,那个小女孩手里拿着裁纸刀,随时准备扎她母亲,让她重新清醒过来,让她避免迷失自我,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在之前我写的一个版本里,奥尔加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她越来越虚弱,最后决定把女儿武装起来,利用孩子对她的敌意来对抗她的幻觉。那个几十年前淹死在米赛诺角海水里的那不勒斯女人的身影浮现在厨房里,这个可怜的女人没办法承受被抛弃的痛苦,像狄多一样自杀了,整个城区的人都知道。
我要给自己煮一杯咖啡,让我清醒一点儿。我来到了厨房,把摩卡壶打开,在里面放上了黑色的咖啡粉,然后又拧上。注意了!我告诉自己,你要注意自己怎么呼吸。我想要打开煤气,但我很害怕:假如我用完炉灶之后,忘了关火怎么办呢?在那一刻,我按照时间顺序,回忆了一下用摩卡壶煮咖啡的整个过程,一直到此刻之前,这些动作都凌乱模糊,很不连贯。我怀疑我在咖啡壶里没放水,我想:你没办法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没办法信任你。我把咖啡壶的上半部分拧了下来,里面有水,我的手指是湿的。当然有水,一切都很正常。但我意识到,我在咖啡壶里放的黑色粉末不是咖啡粉,可能是茶。
我非常沮丧,我没去弥补,我没有力气。我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我看见马志尼广场上的那个女人正在打扫厨房,她打扫得非常专注。后来她停了下来,向我展示了她的无名指,上面没有结婚戒指。她说:“摘下戒指时,真是非常麻烦,我的戒指摘不下来,我不得不找人把它锯开,假如我知道我会变得这么瘦, 我可能会等一等,戒指会从手指上掉下来。你看看我的手现在多丑,我的生命简直要从手指上流走了。”我发现我也没有戴戒指,我攥紧了拳头,想感觉一下手的力气。那女人对我微笑了一下,她嘀咕了一句:“你看,假如有人扫地时扫到了你的脚上,你永远不可能嫁出去了。如果你嫁不出去,就是这个原因。” 她好像要展示给我看,她开始非常卖力地用扫把扫着自己的脚。我发现她的脚脆弱易碎,扫把扫下一些带血的鳞片,这让我一阵恶心。我大喊了一声:伊拉丽亚。
奥尔加和女儿伊拉丽亚之间关系不是很好,特别像黛莉亚和阿玛利娅之间的关系。但和阿玛利娅不一样的是:奥尔加是当今社会的女人,她能够承受这个痛苦的过程,能够接受伊拉丽亚对她的敌意,她觉得这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可以对抗死亡对她的围攻。那个被遗弃的可怜女人一直纠缠着她。女儿和母亲一起, 她们一起肯定了生的价值,和之前那些被遗弃的女人不一样。这时候,我可能要想一想你们问题的核心。我刚才引用的那一段——还有一些类似的东西,我就不引用了——差不多都是你们指出的那些。那不勒斯的那位被遗弃的女人,在第一稿里充满了象征意义,它代表了从阿里阿德涅 [2] 开始那些被遗弃的女人的原型。那枚锯开的戒指,失去的生命能量,那个扫把代表家庭内部的处境,也有一种性方面暗示。不能结婚或不能再婚的焦虑,再也找不到男人的焦灼,都像碎片残渣涌来。奥尔加在那个幽灵身上看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不安,她在这个形象中也看到了自己。
但这种写法,我很快就不喜欢了,我把这些都删去了,只提到了维吉尔笔下的米赛诺角。我把这一段抹去了,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正确的讲述方法。我很害怕在古代神话原型和现代女性中间会出现一种断裂,奥尔加成了女性命运进步的代表。我选择打乱时代,比如说在《烦人的爱》中,阿玛利娅和黛莉亚两个人融为一体,黛莉亚最后的目标,也就是她生命力爆发的最高点,整个过程让人欣慰的结果是:阿玛利娅存在过,我就是阿玛利娅。我并不是要超越过去,正因为过去积累了很多痛苦,忍受了很多挫败和拒绝,所以我需要扳回一局。

希腊神话中,被忒修斯抛弃的女神阿里阿德涅
在这里要解释清楚的话,我们必须谈一谈痛苦如何改变时间给人的感觉。痛苦抹去了时间的线条,会打破时间,会把时间变成一个旋涡。时间的深夜,聚集在今天和明天晨曦的边缘。我们的痛苦根深蒂固,从远古时代就渗入了我们的身体,在山洞里激动或让人恐怖的争吵,还有那些被打入深渊的女神,到现在还紧紧跟着我们,会出现在我们写作的电脑上。那些强烈的感情就是这样,它们会打破时间,激情是致命的一跳,是翻跟头,是一个旋涡。
当痛苦袭击黛莉亚和奥尔加时,过去不再是过去,未来不再是未来,之前和之后的顺序也被打破。在写这个故事时,也出现了时间上的紊乱。讲述者“我”非常镇静,讲述语言干净利落,节奏缓慢;但当情感出现波动,写作发生了弯曲,变得激动,会吸收周围的一切,把过去的欲望和懊悔都席卷进来。黛莉亚和奥尔加应该慢慢平静下来,因为讲述者“我”要恢复一种比较平稳的风格。但这种回归非常短暂,只是为故事的进展积攒能量,然后掀起下一阵飓风。这个意象对于我来说非常有用,会让我想到痛苦来临时,就像旋涡一样席卷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激情的写作,呼吸发出的声音,肺叶的张合会产生音乐,也会让不同时代的沉渣泛起。
黛莉亚和奥尔加从内部讲述这种旋涡,当旋涡放慢速度,她们也不会与它保持距离,不会远观思索,这是处于旋涡中心的女人讲出她们的故事。因此她们不会为母亲的生活和她们想过的生活之间的矛盾而痛苦,这并不是对从地中海的古老神话开始的、从古到今一代代女人遭受的痛苦做一次清算,实现一个小小的进步。她们的痛苦源于周围环境,过去那些女性的遭遇和她们期望的未来同时出现,像影子、幽灵。比如说黛莉亚,她穿着现代女人的衣服,但她后来重新穿上母亲的衣服,作为一种释放自我的服装;奥尔加可以在镜中,在自己的脸孔上看到那个死去的弃妇的轮廓,就好像那是她的一部分。
注释:
[1]《圣经》传说中,参孙被情妇大利拉剪去头发后,神力尽失;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叙事诗《埃涅阿斯纪》中,迦太基女王狄多死亡前饱受痛苦煎熬,天后朱诺派女神伊里斯用右手剪去了她的头发,狄多的生命因此烟消云散。
[2] 阿里阿德涅(Ariadne),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之女,爱上了雅典英雄忒修斯,曾用一只线团帮助忒修斯杀死了米诺斯囚禁于迷宫中的牛头人身怪物弥诺陶洛斯。关于其结局说法不一,有说她被忒修斯抛弃, 有说她后来与酒神狄奥尼索斯结婚。
(上文摘自《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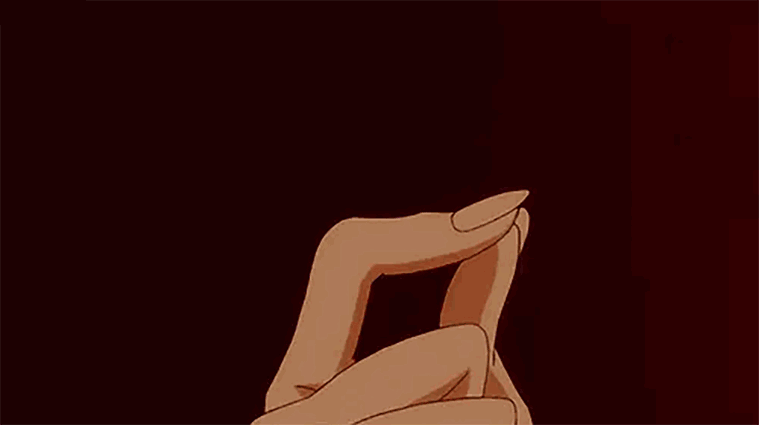
▼把时间变成漩涡
原标题:《如果一个女人感到痛苦,不是因为她不够进步》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