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战百年︱1914年的美丽夏季:一战改变“世界的命运”

十几年前,看过一部法国电影 “1914年的美丽夏季”(La Bel été de 1914),根据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一部描写一战前法国生活的小说《公共汽车的乘客》(Les Voyageurs de l'impériale)改编而成。片子由老导演沙隆(Christian de Chalonge) 执导,讲述了1914年夏季一位历史教师梅卡迪和家人到一个乡村古堡度假的故事。
那是一个“美好时代”(Belle Epoque)的普通夏季,人们在乡村度假,正如许多文献和历史影像所展示的那样:安谧,幸福。四十多年的和平;巴尔干危机已暂缓解;1894,1904年分别签署的法俄、法英友好协议形成的三国协约,虽有德奥意同盟的对垒,在摩洛哥危机问题上显出功效,更给了许多法国人前所未有的安全感。19世纪90年代开始那史家称之为“加速时代”的经济发展,给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带来前所未有的富庶。人们在“森林大街”(Avenue du Bois,今已改用一战英雄福熙元帅名——Avenue du Foch,“福熙大街”)翩翩起舞。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110万平方米展厅中各种前所未有的发明、创新为五千万访客也为全世界的人们展示着一个美妙的、梦幻般的未来。新的通讯和交通技术,不仅第一次让地处遥远的人们真切地感到彼此的连带,也让各种观念、思想、知识、技术迅速地在世界范围传递流动。那些因西方的扩张而卷入现代化进程的民族仍在各种应对方案的选择中踌躇,在传统秩序解体带来的困境中挣扎。但后来居上朝气四射的美国和野心勃勃的日本,已开始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尽管存有各种矛盾,却都没有影响欧洲到处洋溢着的那种节日式的欢愉,那种启蒙时代以来对进步所持有的乐观态度。
这一切,都在1914年那个美丽的夏季,被萨拉热窝的两声枪响打碎了。
那影片的故事早已模糊、淡忘,倒是其中一个不断呈现的画面,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条黑蛇,时时蠕动、伸延着。或许,它是导演就片中有关情欲的主题所用的暗喻,但它更像一个魔鬼的预言: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那古堡及其环绕的世界将就此彻底改变,欧洲将遭遇一场新的“失乐园”。
欧洲为何会走向一战?
大战至今,百年已逝,有关争论至今不断。战争爆发的原因,德、奥帝国或是协约国的历史责任,各种战役,战争带来的世界性的后果……文章、著作汗牛充栋,却依然留下许多令人费解的疑问——其中最让人困惑、难以解答的就是:“为何大战未能避免?”从战后第二年起就陆续公布的德国相关文献,考斯基的《战争是怎样爆发的?》,到二三十年代阿尔弗雷德•冯•瓦格纳(Alfred von Wegerner)为德国推卸责任的论述,围绕凡尔赛条约中德国及同盟负有战争罪责的231条款展开的讨论,法国左右派学者不同立场的解读,美国学者的另一种视角,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诠释,德国历史学家如费舍(F. Fischer)对德帝国战争角色的严厉批判……至今,“欧洲如何抛弃了和平走向一战”?(加拿大女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影响广泛的新作的标题,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How Europe Abandoned Peace for the First World War,2013)依旧是有关20世纪历史最重大的一个问题,不断地被人们争论着,且将长久地争论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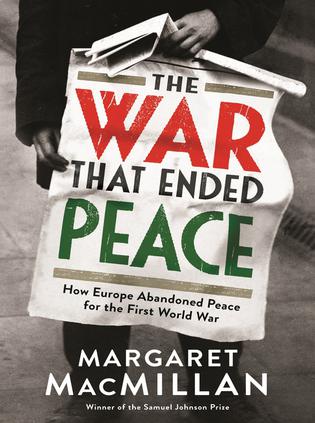
这种氛围让一些敏锐的大脑感到忧虑——也是那年,索邦大学倍受尊崇的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拉维思(Ernest Lavisse)发出这样的预言:“欧洲将发生战争,因为它准备战争。”和平主义运动在发展;左派政治人物如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呼唤欧洲工人阶级的联合,阻止战争势力的扩展,因而被诬为德国的奸细,并因此在大战全面爆发的前夜——7月31日被法国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后来的演变证明,在大浪激起之际,这些和平呼唤都没能遏抑仇杀。而事实上,即使在左派内部,也有倍倍尔(Bebel)那样著名的德国社会党人,盼望借一场世界战争引发一场世界革命,荡涤统治阶级。战前几年,有关军队扩张的法案和措施在各国竞相出台,依据的是同一种论证逻辑:绝不示弱,以强对强,都以和平的名义,相信如此方能保护自身的安全。身为德军总参谋长的毛奇(Moltke)将军那句“我们不想战争,只是用其结束战争”“如战争不可避免,那就早打最好”所表达的思路,被各国领导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述过。所有国家都对自己和盟友的力量抱有信心,又都对对手怀着恐惧和猜疑。政治家和普通人被这种强势姿态营造的安全感自我欺骗,不相信战争会真正降临——在这样一个工业时代,科技造就的屠杀威力如此巨大,谁敢轻启战事?即使在萨拉热窝的暗杀发生后,依然没什么人认定战争会真正爆发,而一个月后的7月底,人们又都忽然张慌地意识到:情况已经失控,战争已不可避免!
一战决定了“世界的命运”
像电影中梅卡迪一家一样,那个夏日因战争永远地结束了。笔者心仪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也曾在多年后怀着无限的留恋,深情地忆起他在维也纳附近度过的那个“难忘的夏季”——与往年没什么区别,天空如丝缎,湛蓝清澈;空气柔软,弥漫着香气,远处是森林葱郁的暗影。“乃至今天我每谈及‘夏季’,都不可避免地忆起1914年的那个夏季。”它成为一个逝去的时代的象征,成为“旧世界最后的日子”。(法国国家图书馆正在进行的展览的标题:Été 1914. Les derniers jours de l’ancien monde,“1914年的夏季——旧世界最后的日子”,BNF)人类历史由此被划成前后不同的时代。
8月初,被动员令召集起来的战士,满怀爱国主义的热情,担心着秋收,走向战场,信心满满地认定葡萄收获的季节,最晚圣诞节,将会重归家园。各国的将军们也都认定,那将是场短暂的冲突,所以不断地下达进攻的命令。法国军部冬季的着装都没有为部队准备。战争还带有19世纪的色彩,牛拉着大炮,士兵穿着旧时代的军服,红色的军裤让法国的士兵们惨遭扫射。几乎无人预见到,那是一场持续了整整四年,7300万军人参战,造成上千万死亡,2000多万伤残,卷入全球各个民族的巨大灾难,——战争开始后仅三周法国就有8万到15万人阵亡,10万人受伤。这场战争事实上也远没在1918年结束,它开启了一个世纪的冲突、革命、战乱,直接催生了二战;直到柏林墙崩塌、苏联解体、前南斯拉夫各国彼此间的冲突结束,这场战争或可真正称得上终结。用法国当代著名史家马斯•伽洛(Max Gallo)的话讲,一战决定了“世界的命运”。
为维系和平、达成平衡的结盟机制,只因一个地域危机,反过来成为将整个欧洲拖入战争的绞索;因欧洲统治着世界,从而又将冲突蔓延到全球。因种种民族和社会的矛盾的积累,已被各类革命和暗杀不断撞击的德、奥匈、俄等传统欧洲帝国,被大战掀起的飓风席卷而去。互为姨表兄弟、在战争爆发的前夜还在用昵称Willy和Nicky互通电报威胁对方的德皇和俄国沙皇,就此沦为异乡的孤客和刀下的冤鬼。随着贵族的大批阵亡和帝国的消失,传统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土崩瓦解;旧时王谢堂上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民主体制受到极大冲击,传统社会党势力边缘化;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极端的政治运动和思潮相继崛起。
那是一场发生在作为世界主人的男性、白人之间的鏖战,其结果,却加速了“奴仆”们的解放。美国的黑人部队出现在欧洲战场,进一步撼动了美国白人的傲慢;因人力的缺乏,大批妇女走出家门,进入工厂农田,扮演起那本是丈夫扮演的生产者角色。她们以其能力证明,她们绝不只是生育的工具,次等性别的弱者,她们也是创造历史的行动者。从此,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将其赶回家中,妇女历史性地开始登上政治和社会的舞台。那些来自殖民地的兵团在战场上直接的牺牲和殖民地因大战所付出的代价,让殖民主义更加丧失道义合法性,且因战争的消耗,老牌帝国主义加速走向衰亡。那些落后和贫弱的国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试图以一个平等的身份参与到世界事务中来。……
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个世界范围内争取权利的新时代敞开了大门。从欧洲到拉美,从非洲到远东,共和的浪潮,激进的左翼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自决原则影响下孕育的民族革命,一浪高过一浪,撞击着传统秩序的堤岸,改变着世界的面貌。苏俄建立;绵延数百年横跨欧亚的奥斯曼帝国跌进历史的烟尘;古老的印度大陆开始了争取独立的历程;中国更深陷战乱,从对“巴黎和会”的失望转向对红色莫斯科的向往,精神的参照和历史的轨迹就此更变。列宁、凯末尔、甘地成为新型的世界领袖,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不仅深刻地塑造了各自国家,也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整个世界。
一个旧时代开始落下帷幕,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一波全球化进程中断;欧洲对世界的统治瓦解,美国跃上世界领导者位阶。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在战争中宣称“这是文明(法国)对抗野蛮(德国)”的冲突;战后,轮到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来宣告整个“西方的没落”。在1914年8月22日一天阵亡的两万七千具法国士兵的遗体前,面对一个多月后在伊普尔(Ypres) 几天内死亡的五万德国大学生志愿兵的尸首,那毒气、坦克、飞机,巨型火炮、高速机枪、生物等现代武器造成的地狱般的杀戮效果,又怎能不让人对一两个世纪以来奉为圭皋的进步主义信念、对现代文明的乐观产生怀疑和动摇?人类有关时空、生命、艺术、战争、世界等各种观念就此改变。作为反思和检讨的结果,人们尝试用一种新的国际架构(“国联”)来协调地域和国际冲突;一种新的世界性的普遍价值开始孕育。至今,那时代提出的课题,启动的工作,依然在呼唤我们的智慧、想象力和道义感,依旧是人类未竟的事业。
1914年那个美丽的夏季一去不返;2014年的夏季已散出某种炎热。人们在组织各种活动纪念百年前那场突然降临的战争;有评论家在谈论本世纪初与上世纪初的某些相似之处。……是的,谁能保证今日的生活不会是另一个旧世界最后的日子?杀戮不会再次降临?——影片中那黑蛇或许依然在某处爬行,窥视。很难说一战是某国或某些人的罪过,所有人都有无可推卸的责任。百年前,是各国精英和民众的自大、短视、彼此的猜忌、怀疑、敌意和恐惧,积淀了战争的土壤。今天,我们又该怎样不重蹈覆辙?也许,保持记忆,从这种纪念中汲取理智,坚守和平、不松懈对权力的警惕,提倡不同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信任,是我们远离灾难,能继续在这个星球上共同生活的一些绝对不可或缺的条件。
(作者系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