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疼痛的挽歌:顾桃的“鄂温克三部曲”
顾桃的“鄂温克三部曲”,《敖鲁古雅·敖鲁古雅》(2007)、《犴达罕》(2013)、《雨果的假期》(2010)为他在业内带了众多赞誉,比如,《犴达罕》斩获釜山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奖,也曾入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不过,这些奖项的知名度是在小圈子内打转,能够造就的影响十分有限。我们知道,纪录片的投资、运作和市场远远无法跟剧情片比拟,鲜有观众走进影院只是为一部纪录片买单。“三部曲”充满浓郁的民族影像气质,吸引了许多专业研究者和对少数族群文化有特别兴趣的人。因此,顾桃的作品常常以沙龙、学术放映或少数族群电影专题展的形式与观众见面。它们粗粝、坦率而充满诗情,让人过目难忘。

从“复原”到观察
据顾桃自述,由于其父亲与部落老人玛利亚·索的旧交情,才让他俘获猎民的信任去拍摄。在拍摄期间,他们吃住同行,喝酒唱歌,或外出搜寻驯鹿。顾桃的工作颇带人类学的意味:长时间深入到部落腹地,与本地人打成一片。也因此,纪录片具有某种影像民族志的性质。摄像机秉持一种“不介入”姿态,要么伫立在人物面前,要么紧紧跟随。从年迈的玛利亚·索到青春洋溢的雨果,猎民对他们的生活有充沛的展现机会。影像引领我们对鄂温克族群的认知,有种桦树皮般粗糙的可感性。这些都是单纯的文字记录难以企及的。

顾桃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家主导的民族识别、调查政策的加持下,八一制片厂和北京科学教育制片场联合摄制了十六部影片,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其中,就有一部《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1959)(下称《河畔》)。现在看来,这部黑白影像的片子年代感浓厚,使鹿鄂温克(注:使鹿鄂温克也称为“雅库特”,鄂温克的另外两支是通古斯和索伦)的狩猎、分配、交换、婚姻习俗以及萨满信仰均一一呈现。拍摄是在“文化抢救”的理念下,民族学者力图利用电影技术的“写实性”去保留那些濒临消失的部落制度和文化。不过,在实际拍摄时,某些古老的仪式就已变得漫漶,族群风俗处于缓慢的衰变之中。为有所补救,拍摄工作者选择提前撰写好大纲和分镜头脚本,从而达到“复原”或“重建”的效果。模拟拍摄会请当地人穿上传统的服装,提前进行排演,以便让逝去之物重现于银幕。
“复原重建”的目的是抢救消失的文化,但其疑点重重,无法掩饰。摆拍或许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它跌破了纪录片现实主义的边界,所谓的“真实”只能残留于视觉上的直接性。摆拍犹如隐蔽的操纵,让影片深陷于拍摄的伦理困境。摄制内容上的组织,在性质上,使纪录片开始向剧情片靠近。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在此变得模糊难辨。在后期制作中,解说和字幕发挥着类似的牵制作用。在《河畔》中,与一场婚礼画面伴随的是相应的解说:新娘带来了几头鹿的嫁妆,详细地讲解整个婚礼的流程。在此意义上,影像只是为研究提供比文字更直观的素材,从而阐释特定意识形态下对少数族群的认知。这批影片拍摄的初衷,是将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史上的早期形态”用影像留存下来。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复原重建”的缺陷之一,就是在拍摄者的价值体系当中,已经存在落后/先进,原始/现代等不平等的预设标准。
与《河畔》相比,顾桃的“三部曲”恢复了以被拍摄对象为主位的伦理。除了必要的背景交代,影片中没有任何冗余的解说词,将主动权交给拍摄对象。纪录即观察,避免越俎代庖。顾桃让鄂温克人自己去阐述对狩猎文明的认识,表达他们的心声。影像的不加修饰,让“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结实地落地。通过自我表述,我们知道鄂温克人是如何遵循季节规律而狩猎,比如:驯鹿交配的时节他们收起枪支,鹿群中的母鹿也非狩猎的对象。用片中维佳的话说,打猎是帮鹿群精减老弱病残。在萨满信仰的训喻下,他们会尊重任何生命,即便微小如一窝蚂蚁。不论从生态意识还是人文精神上看,驯鹿文化都令人肃然起敬。片中,有几处新闻节目对鄂温克人“新生活”字正腔圆的解说播报,它们构成了影片中维佳、柳霞等人嬉笑怒骂、挣扎徘徊的时代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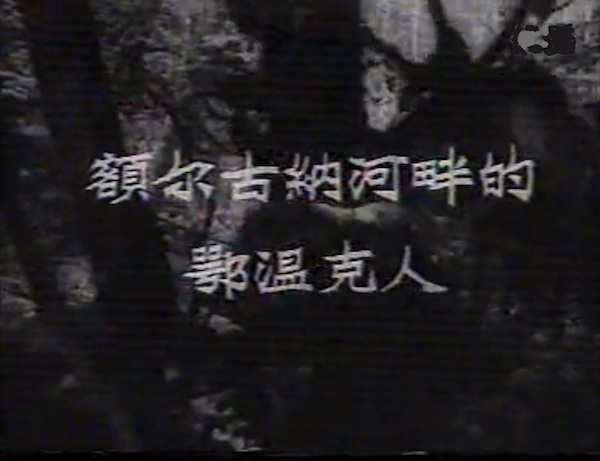
人的挽歌
在该片的豆瓣条目下,维佳的孤注一掷的诗句被频繁引用。比如:“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切/就代表消亡。”毫无疑问,“三部曲”整体上被理解为一首鄂温克狩猎文明的挽歌。
影片主要聚焦于鄂温克使鹿部落。他们最早自西伯利亚迁徙而来,在大兴安岭生活,以狩猎和驯鹿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早在1960年代,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他们建立了敖鲁古雅猎民乡,部分人实现了定居,开始了山上猎民点-山下定居房的“二元结构”生活。从2003年开始,随着“生态移民”工程的推进,政府想让鄂温克猎民彻底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定居”。搬迁之后,猎民住宿条件有所改善。但因为山下生活资料无法自给自足,大量的花销支出却缺乏经济来源,生活水平反而降低了。居民点附近的苔藓稀薄,加上偷猎“套猎”猖獗,搬到山下后猎民的驯鹿损失严重。(《犴达罕》中有一段,就是把驯鹿从山下拉回山上。)当地政府似乎并未做好充分的民意调研和搬迁预算,以致于,此项工程很难说是成功的。不少猎民无法适应彻底的定居生活,后又返回森林。影片中的三家便属其中,他们组成了一个猎民点。从2007年开始,顾桃用将近四年的时间跟踪拍摄素材,纪录一个小型部落最后的变动和衰败。
顾桃无官方背景,也没有抱研究性的目的。他拍摄的重点不再是体系性的文化角色,主角一转:那些个性突出的人物走到了镜头前面。他们的气质扑面,而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折射出族群的命运。在顾桃眼中,“鄂温克”不再是词条、界定和对民族源头的追溯,而就是维佳、柳霞这些充满冒犯与哀伤的人。
维佳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画画,后来还是返回了山里,这个人身上有种艺术与野性的综合。他画中的森林和鹿充满灵动,用色细腻而饱满,常常出口成诗。在嘈杂拥挤的绿皮火车上,他蓬头垢面,裹着棉袄大谈德国表现主义和莫迪里安尼的裸女画作。维佳长不修边幅,是大兴安岭的波西米亚人。除了森林,他似乎不适合待在其他任何地方。《犴达罕》即以维佳为主角,前半部分是他在林中的生活,包括他讲述猎民如何从“黄金时代”衰败至此。后半部分,则逐渐染上了某种象征意味。当我们看到猎民大汉蜷缩在海南三亚市的一间出租屋、乃至后来被送进精神病院时,就像一头桀骜不驯的犴终于被死死地套住。在导演顾桃眼里,维佳就是森林里最后的犴达罕——大兴安岭体态最大的动物,敏感而富有尊严。

《犴达罕》剧照
相较之下,柳霞是在林中生活的内部呓语。她是老人巴拉杰依的女儿,维佳的姐姐,爱唱歌,爱晒太阳。柳霞的牙齿脱落,突出的颧骨因常年醺酒而日益膨胀,以至于眼睛几乎挤成一条缝隙。《雨果的假期》便是以小雨果的视角,讲述他的回乡之旅。小雨果常年在外地上学,日渐与母亲生疏,而尤其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母亲屡劝不改的酗酒恶习。为让儿子开心,柳霞常常做一些笨拙的事情,比如让这个大小伙去骑一头体格比羊大不小多少的驯鹿,那场面既尴尬又让人心酸。在《雨果的假期》中,柳霞是一位深情但不可救药的母亲,她的爱笨拙,鲁莽,不得要领。
影片对人物的跟踪观察上一丝不苟,但并不意味在其他方面就毫无技术可言。比如,《敖鲁古雅》一开始,柳霞就跟一位东北口音的汉族妇女就敖乡新修的房子是否适宜猎民居住,表达不同的看法。显而易见,柳霞认为跟山上相比,定居点远不尽如人意。由此观众就获得了一个山上/山下的比较性视野,期待后续的走向。再比如,《敖鲁古拉》和《犴达罕》的结尾都是以维佳的诗句作结:“在咱们这个时代,狩猎文化消失了,惭愧万分!”尤其是《敖鲁古雅》中,随着部落老人马里亚·索牵着一头驯鹿,缓缓走向景深处,维佳的诗句再次作为画外音出现。维佳的诗不仅加强了影片整体的挽歌性,也构成了对林中生活的释意。加之画外音和民族歌谣的援引,顾桃不仅以观察为己任,更是通过剪辑提出了观点和批评。
酗酒和暴力
这些人物不拘格套,充满冒犯,对习惯于“文明礼节”的观众来说难以体认。不过,他们迸发出蓬勃的艺术感和生命力,冲击着我们疲软的认知神经。“三部曲”中出现了不少酗酒和暴力的镜头,令人侧目。柳霞和维佳姐弟二人嗜酒如命,母亲巴拉杰依对此恨得咬牙切齿。姐弟俩常常交换眼色,把酒藏在母亲看不见的地方。维佳因为无法戒酒,最终跟他的南方女朋友分手。柳霞则因为酗酒,失去了抚养儿子的权利。
除了醉酒,此外就是惊人的大打出手。《敖鲁古雅》中有一幕:柳霞返回乡下,看到屋里脏乱不堪而心生不满,在嘟囔中,她毫无预兆地就抡起板凳连续砸在维佳的脑袋上。顿时,后者鲜血直冒。柳霞因为跟人打架,头部屡次受伤,意识变得混沌不清,这从她说话总是颠倒重复就能看出。阅读顾桃的拍摄日志《忧伤的驯鹿国》,酗酒和干架似乎是家常便饭。据说有一次,有个年轻人把酒藏在了高高的树杈上,没想到柳霞为了喝酒直接把树给放倒了。又比如何协,部落酋长的儿子,猎民点最有权威的男人,因为争执被表弟连捅了四刀,刀刀致命,在重症监护室里躺了很久。
对于猎人为什么爱喝酒,我们当然可以给出许多解释,比如在森林御寒,或出于同汉族类似的“无酒不成席”的饮食风俗。但维佳、柳霞等人醺酒,超越日常调节而变成了一种病态的瘾症。酗酒和暴力的场面生猛无比,我们感到,激烈的身体行为,难以仅仅从个人脾性的层面去理解。尤其是一旦因喝酒而亡的人形成一份数据统计(维佳说他知道“喝死的就有八个”),这些言行就不可避免地就表征了鄂温克人精神状况的重要面向。维佳是这样解释的:“鄂温克人没有搬迁之前,他们不敢喝酒。搬迁以后无所事事,把枪也没收了,无所事实,就整天喝酒,喝得非常累……”“咔,喝死,喝死拉倒!”猎枪没收之后,年轻的猎民们丧失了继续在森林中驰骋的权利,身体的能量难以施展,积郁愤懑又不知如何疏导。于是,他们选择用酒精自我麻痹。
醺酒和干架,像是为鄂温克下了定义。颓废、残忍和伤感的自我放纵,表征一个族群的无计可施。它们超越了个人癖好,变成一个民族面对文化失落时的无奈反应,某种意义上抗议。然而,一旦酗酒者的形象被认领,就会造成危险的效果。任何少数族群在主流媒介中的再现中,唱歌跳舞可能是最好的标配,而零星的负面形象都会病毒般地增值。对外,考虑到普遍存在于历史教材中“社会进化的早期阶段”的错误想象,它会加剧主流世界对少数族群“野蛮”、“文明低下”等偏见。对内,在日复一日对酒精的沉溺中,昔日的猎手会把自我体认为苦难和怨恨的化身,而对外部报以敌意。当悲哀的情绪在族群内部渲染,也会造成自我的定位悲情化,笼罩于消极之中。

鄂伦春猎人在狗的陪伴下骑马狩猎。
尾声
乌热尔图也许是1980年代以来鄂温克族最重要的小说家,他的短篇曾在1981-1983年连续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获奖小说《琥珀色的篝火》(1983),讲述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鄂温克猎人尼库在送病重的妻子去医院的途中,发现几个迷路人的踪迹。在妻子的鼓励下,他选择先去解救那几个奄奄一息的城市汉人。找到他们后,尼库生火、收拾木柈、砍桦树皮烧水。他不遗余力地展现精湛的生存技艺,因为他深谙自己正在被外人所注视。
猎手与外来探访者之间的这种目光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文化间性的隐喻。在这样流动与迁徙加剧的时代,没有文化会封闭地孤存。相反,总是有人出走,有人闯入——它们恰是在边地与外省、多数与少数之间的交涉中再度生成。少数民族文化与内地的遭际,让他们开始走出自为的状态,参与到交互之中。这决定了,他们无法再孤悬地自成一体,而是在交往中言说,并渴望被承认。乌热尔图作为意欲为本民族代言的作家,正是在这样不可避免的间性关系中写作。因此在小说中,我们读到了面对造访者的鄂温克猎手是如何地竭尽全力。
然而在现实中,面对少数族裔,我们内地的汉族读者,多少都是所谓的“大写的异己读者”(the Other reader):下意识地惧怕和抵制那些同我们迥异的感觉,而希望能筛选、寻找、定位足够的相同之处。这是一种普遍的怠惰心理,因难以直面陌生的存在和环境,情愿留守于舒适区。我们习惯于把异质性过滤,只留下安心的部分。这其中存在知识上的疏忽,当然也不乏心态上的傲慢。然而,顾桃的影片恰好形成了一股冲击,让我们始料不及。在严酷的森林地带,喝酒、唱歌、哭泣。这些激烈的身体以及充沛的力比多,让我们感到疼痛。
注释:
[1][4]顾桃:《忧伤的驯鹿国》,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
[2]朱靖江:《复原重建与影像真实》,《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2期
[3]谢元媛:《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乌热尔图:《琥珀色的篝火》,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