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回望乡土与亲情,刘庆邦新作《堂叔堂》如何更新观念表达历史记忆?
刘庆邦

在《堂叔堂》里,我不打算为任何一位叔叔立传,
我想通过叔叔们,写出人生的苦辣酸甜,
写出个体生命起伏跌宕的轨迹,
并写出时代打在他们心灵上的深深的烙印。
作家刘庆邦常常被人说“写得老实”。首届林斤澜“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颁奖词称,刘庆邦就像老实本分的手艺人。“我们从他的短篇小说中看到了不受喧嚣干扰的专注、耐心与沉迷,看到那唯有保持在笨拙里的诚恳,以及唯有这种诚恳才能达到的精湛技艺。”言下之意是刘庆邦有着手艺人般的老实。王安忆评价他是个如农民爱惜粮食般爱惜文字的人,从不挥洒浪费。这近乎是说他有着农民般的“老实”。
虽然刘庆邦从不以老实自居,但他近些年却像是“老实”到了家,老老实实地接连出了几部长篇小说,像《家长》《女工绘》等,我们即使没读过,单看书名也明白他大概写了什么。而对于他的长篇新作《堂叔堂》,作家梁晓声在2021年4月11日于北京举行的新书分享会上说,他一看到书名,就立刻想到刘庆邦要写很多堂叔了,而且一定是农村为背景。

新书分享会现场,刘庆邦、梁晓声
如其所想,在《堂叔堂》里,刘庆邦就是以十二个篇章,讲述了他十四位堂叔的人生故事。其中既有大叔刘本德作为台湾老兵回乡的故事——从亲情的角度,含蓄表达了渴望两岸统一的心愿;也有一心惦记赚钱的乡村老师刘本魁的故事——侧面反映改革开放之初的人心波动;更有刘楼村第一位党员刘本成讷于言敏于行的故事——展现了基层党员宝贵的质朴无私精神。而且这些堂叔里除了一位因为尚在人世,刘庆邦用了化名外,其他十三位他都是用的本名。以刘庆邦自己的说法,这样也就强调了纪实性。但他不认为这部作品可以被称为虚构作品或者纪实文学作品。究其因在于以他的理解,再实的东西,一旦被写成小说,它就变成虚的了,就不可能完全是纪实的了。
这看似不言自明的道理,刘庆邦却说得特别实在。他说,作家写作都要经历回忆的过程,他们的写作素材就是从记忆中来的,而记忆都是有选择,有选择了以后,就不完全是现实版照相了,肯定包含了虚的,或者说主观的东西在里头。再则,在刘庆邦看来,小说肯定是要表达情感的,情感是抓不住、摸不着的,是不免有些情绪化的,就是虚的。“何况文字也是虚的。文字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汉字,单个看是实体,但语言一旦变成了文字,它就变成了一个符号了,一旦符号化,它就抽象化,一旦抽象化,它就成了虚的东西。”
刘庆邦可谓把他的虚实之道推向了极致,他像是要表明一切皆虚,也似乎是因此,具体到写作本身,他更是强调要往实里写。所谓实,在他这里主要指的细节。他这样阐释历史与人的关系:“我认为每个人都是历史的细节。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必须看到人,如果没有细节等于什么都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是空空的,只有看到人这个细节,我们才能看到历史。所以说作为作者,我们的写作肯定离不开历史,因为人都生活在历史中。你要是看到历史了,你就必须看到细节,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细节。”

纪录片《书简阅中国》剧照
与此相仿,在刘庆邦看来,每个人也都是历史的“人质”,历史的“载体”。“说人是历史的‘人质’,就是说历史总是宏大的,和历史比较起来,每个人都显得很渺小,渺小如一粒尘埃。”但以刘庆邦的理解,人再是渺小,他都是历史的载体。“我们都知道,司马迁的《史记》是写历史的,但他都是写人。不管是《项羽本纪》也好,还是各种《列传》也好,都是写人,司马迁是通过人来承载历史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那历史就是不存在的,只有写到了这些人,这些生动的人,活泼的人,《史记》才把历史承载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也是一个历史的载体。”
那我们就要问了,刘庆邦为何让堂叔来承载他要表达的“历史”?以他自己的说法,他从1972年开始写作,到明年就写了半个世纪了,有时觉得好像没什么可写的了,但回头⼀想还有这么多堂叔没写。“我过去生活的那个村子叫刘楼村,大都姓刘,我在老家的时候,我们村有三百多人。村子并不大,但我的叔叔辈有一百多个,从老太爷那一辈,每家弟兄都有好几个,都是我的堂叔。我就觉得应该写写他们。”
要这么看,刘庆邦写堂叔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在评论家贺绍俊看来,这里面是有讲究的。“如果让庆邦写一个乡村人物谱,肯定也是驾轻就熟,他可以写乡村的妇女形象、老人形象等等,对他来说这种资源有很多。他偏偏写堂叔,或许是因为这里面包含了一种特殊的亲属关系,从中我们能看到乡村社会伦理和情感之间的复杂关系。庆邦写到亲情和人的利益、人的欲望之间的纠葛,会让我们对中国这种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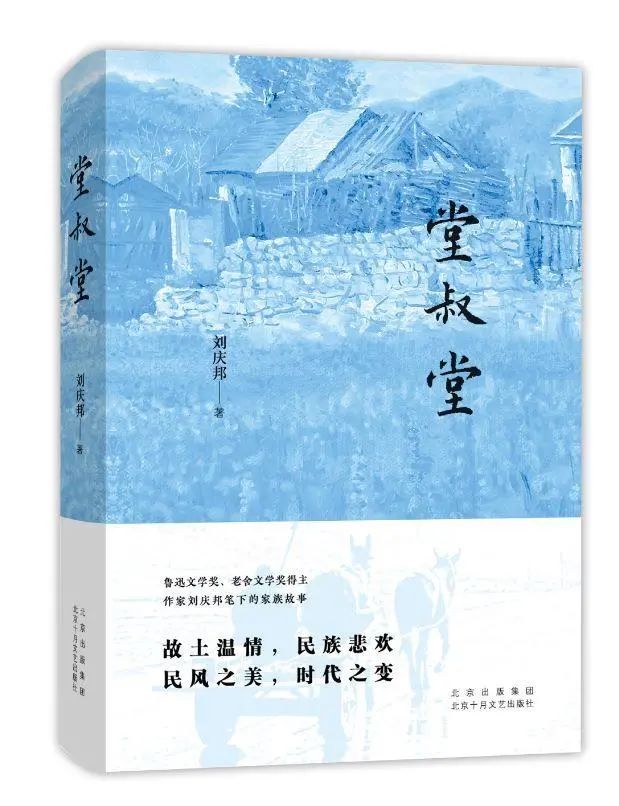
《堂叔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贺绍俊举例说,刘庆邦写到的亲叔叔是个很怪的人,他完全不讲亲情了,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伦理对他来说几乎没有约束了。“但庆邦以及他的母亲、姐姐,该怎么去对待这个亲叔叔,实际上又是一个摆在他们面前的考验。毕竟他们是正常的人,不会像叔叔那样完全违背伦理,违背亲情。那么正常的人怎么去跟反常的人相处?怎么去处理这些矛盾?刘庆邦把这些写出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也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显而易见,刘庆邦写的这些堂叔各有各的故事,他要都写是不可能的,他就挑有典型性的、有趣的、跟他有比较多交往的来写。“就这样,我写了十二章,写了十四个堂叔,其实涉及到的可能有十七八个,越写越有趣。直到最后写完了,回头看最后一章我就写了三个,我几千字就把人家写完了。”话虽如此,对其中任何一个人物,刘庆邦都可谓写得郑重其事。以他自己的说法,也许他以前的小说没有做到贴着人物写,但在这部小说里,他是真正做到了。在写作过程中,每一个堂叔都在他脑子里活灵活现,他和这些堂叔是融合的,写他们同时也是在写自己。而所谓“贴着人物写’,最早是作家沈从文提出来的,刘庆邦是从给过他“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在平实,可谓三平有幸”的评价的作家林斤澜那里听说的,当时一听他就记住了。“这个‘贴’字是有讲究的,也就是说作家不是推着人物写,拉着人物写,或者拽着人物写,这一个‘贴’字,起码表现了作家对人物的尊重,这里面有主动性,但他并不是牵着人物的鼻子走,并不是说随心所欲改变他,而是必须首先尊重人物的心理,然后才可能理解他,才可能写好他。”
写作笔记
“贴着人物写’这个‘贴’字是有讲究的,也就是说作家不是推着人物写,拉着人物写,或者拽着人物写,这个‘贴’字,起码表现了作家对人物的尊重,里面有主动性,但他并不是牵着人物的鼻子走,并不是说随心所欲改变他,而是必须首先尊重人物的心理,然后才可能理解他,才可能写好他。
——刘庆邦
当然在刘庆邦看来,“贴着人物写”也可以说是贴着细节写。他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就是得有细节之美,而所谓细节,是相对情节而言的。“拿一个人来做比较,他的出生、恋爱、结婚、生子、死亡,都是情节,而每一天的吃喝拉撒睡、油盐酱醋茶,都是细节。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细节形式存在的,如果抹去了细节,世界就变得空洞无物。”刘庆邦回忆说,他最初写小说的时候,有位编辑跟他说,写小说其实没有什么,就是重点刻画人物,简单交待情节,大量丰富细节。“就这么三句话,但怎样丰富细节是有讲究的。其实我们在写小说的时候,不仅是脑子在起作用,我们所有的感官也都要参与到创作之中,包括视觉、味觉、触觉。比如我们写到下雨的时候,会闻到湿润的气氛,耳边像听到沙沙的雨声,皮肤会感到一种凉意,全部的感官都调动起来,这样有现场感,是现在进行时,才能写细,才能把感觉传达给读者,才能感染读者。”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家写作该怎样找到细节?刘庆邦认为,细节首先是从记忆中来的。我们有了很多记忆,才会有可供回忆的东西。写小说就是让自己处于一种回忆的状态。如果我们不写作,很多记忆也许都埋葬了,但一旦写作,我们就好像找到了抓手,记忆源源而来,细节也源源而来。所以他主张写作者要多走多看,丰富自己的经历和阅历,这样记忆力才能有库存,才有可挖掘的东西。”当然在刘庆邦看来,我们还有很多途径可以与细节迎面相遇。“细节可以从观察中来,这就要求我们始终保持好奇心,对万事万物都要感兴趣。我有好多的素材、好多的故事都是我看来的,或者是用心观察来的,我们要有心目,要有内视的能力,不但看自己,还要用心目来看世界,来看周围的东西。你如果是一个有心人,你的心是有准备的心,你的耳朵是有准备的耳朵,那么当你偶尔听到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激发了你,它也可以变成小说。所以,细节也可以是听来的。”

更重要的是,在刘庆邦看来,细节也可以是从想象中来的。“想象力是一个作家的基本能力,想象力也是小说创作的生产力。我国古代四大名著,每一部都离不开想象:《红楼梦》是个人经历加想象;《三国演义》是历史资料加想象;《水浒传》是民间传说加想象;《西游记》本身就有非常强大的想象力,我认为它是幻想加上作者的想象。”而把细节写好本身,就需要强大的想象力。“艺术是需要想象的。比如一个情节,我觉得写1000字才能充分表达我的思想,它的味道才能出来,可是写着写着觉得没什么可写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作者会采取绕过去的办法,把这个情节说过去就完了,能自圆其说就行了。我的体会是绝不能绕过去,绝不能偷懒。在觉得没写充分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调动自己的想象,全部的感官都参与进来,这时候你的灵感会爆发,灵感的火花会闪现,你的脑子像打开了一扇窗户。这就是劳动的成果,艰苦劳动后的灵感闪现的一种成果。”
刘庆邦坦言,他比较喜欢王安忆的小说,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她能把一个细节写出好几页。以他的理解,这个细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心灵化的过程,在心灵化的过程当中找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找到我们自己的真心,也就是一定要找到自己。“写小说的过程就是寻找自己心灵的过程,也可以说你抓住了自己的心,就抓住了这个世界。”在评论家贺绍俊看来,刘庆邦就有抓住事物的核心,把它突出出来的本事。“举个例子,小说里写到的刘本良是到城里读过书,受过城市文化的熏陶的,所以他回到乡里能够很得意地炫耀,而乡里的孩子也都围着他,希望他说说城里的事情,比如说电灯是怎么点亮、电影是怎么看的。那些孩子就让他讲讲电影里面有什么。刘本良就说电影是看的,不是拿来说的。这个细节很有意思,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庆邦还来了一句:我们认为他像是一个吃独食的人,自己吃了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一点都不愿意分给我们尝一尝。这里面就体现了他对细节的认识,他对记忆的认识,他把这一句话写出来,读出来就有味道了。”
推而言之,在贺绍俊看来,作家怎么去认识,怎么去理解细节和记忆,说到底也涉及到历史观的问题。“庆邦有这么多堂叔,也就是说这个家族是非常庞大的,他怎么来处理这个资源?他不是从惯常家族小说的那种模式去处理自己的资源,他把这次写作看成是重新认识历史或者人生的一种方式。他的每一个堂叔,性格各异,都跟他们的经历、跟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他们一生的经历也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某个点来。”

贺绍俊
庆邦有这么多堂叔,也就是说这个家族是非常庞大的,他怎么来处理这个资源?他不是从惯常家族小说的那种模式去处理自己的资源,他把这次写作看成是重新认识历史或者人生的一种方式。
也因此,贺绍俊觉得,刘庆邦并不是企图通过这些堂叔来建构一个完整的历史图景,他是要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物跟历史的关系,还有历史是怎样塑造人的。“从文学角度来说,这是独创的,他在家族小说之外找到了另外一种处理家族资源的方式。小说重点写了十四个叔叔,我们可以通过每个叔叔的故事,对当时的历史有不同的认识,而每个故事都可以指向不同的社会层面。小说的丰富性就体现在这里,庆邦把当时历史景象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来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事实上,刘庆邦写这些人物也确实是各有侧重的,他这样写是因为在他看来他们背后承载的历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承载的是大跃进,有的人是反右,有的人是三年大饥荒,还有的人承载的是改革开放对他的冲击,他放弃做老师去做生意了。特别是最后那三个堂叔,我用几千字就写了他们的一生,是写他们人生的趣味。但我不打算为任何一位叔叔立传,更不会为任何一位叔叔歌功颂德。我想通过叔叔们,写出人生的苦辣酸甜,写出人性的丰富和复杂,写出个体生命起伏跌宕的轨迹,写出艰难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命运感,并写出时代打在他们心灵上的深深的烙印,写出历史和时代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刘庆邦之所以能写好这种关系,也因为历史和时代在他身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他1951年出生于河南农村。作为67届初中生,他赶上“文革”学校停课,跟着红卫兵全国大串联,跑遍了北京、上海这些城市,用他自己的话说,心跑野了,不甘心待在农村,就一直想摆脱农民身份。他跟从开封下来的知青交谈,心里暗暗比较自己和别人谁看的小说多。也因此,他初中毕业回乡后也没放弃读写,“当时县里的广播站有个自办节目‘广播稿’,可以投稿,我写了好几篇,播出后公社的人就知道我的名字了,就参加了公社宣传队,搞通讯报道。”

但对刘庆邦来说,他想要从农村走出来还是很难,他应征当兵,却因为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官没能过政审。直到1970年新密煤矿招工,他当了工人才算改变了命运,吃商品粮,领粮票,发工资。刘庆邦回忆说,矿上也有广播站,于是他又给广播站写稿,矿上办宣传队,他们打听到他在中学、大队、公社三个地方都办过宣传队,就让他来组织。一晃到了1977年,各地刊物越来越多,他看到《郑州文艺》上发表的小说,突然想起来自己也写过小说。“1972年,我写过一篇《面纱白生生》,写矿上女工勤俭节约的故事,就是写我熟悉的生活,这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像是一篇好人好事的表扬稿,但是我写得很用心。”刘庆邦把小说手稿翻出来后,发现纸都脆了,字迹也有点模糊了,但看了一段,有点儿感动,觉得跟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比也不差,好像还更好些,于是重新誊写了一遍,润色一下,寄给《郑州文艺》,小说发表在1978年第二期的头条上,从此他就写开了。
就是在这一年,刘庆邦调到北京煤炭部从事编辑和新闻工作。当时煤炭部有个刊物叫《他们特别能战斗》,后来改成《煤矿工人》杂志,再后来变成《中国煤炭报》,他在里面干了十九年。刘庆邦自称,那时他写得不多,白天上班,有时候看大样,有时候开会,晚上没精力写。“但我比较勤奋、勤劳,这是继承了我母亲的基因,我就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东西,写两三个小时再去上班。一个短篇能写一个月,一天写一点儿。一个人的勤劳有可能得不到回报,但是它永远构不成耻辱,勤劳什么时候都不丢人。2001年,我正好50岁,调到北京市作协当专业作家,才开始有大块的时间写长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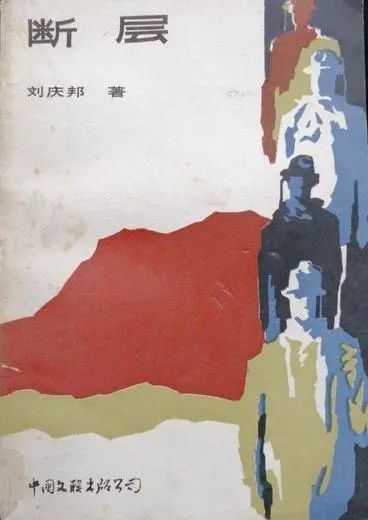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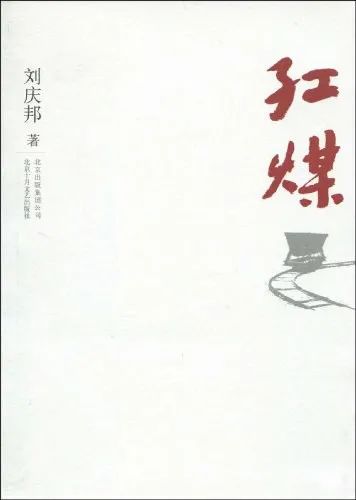

刘庆邦“煤矿三部曲”《断层》《红煤》《黑白男女》封面
此后,刘庆邦确实写了不少长篇,如《远方诗意》《遍地月光》《平原上的歌谣》《黄泥地》,“煤矿三部曲”《断层》《红煤》《黑白男女》,乃至近年的《家长》《女工绘》等。但他被认为写得最好的还是短篇。王安忆说:“谈刘庆邦应当从短篇小说谈起,因为我认为这是他创作中最好的一种。我甚至很难想到,还有谁能够像他这样,持续地写这样的好短篇。”评论家李敬泽断言:“在汪曾祺之后,中国作家短篇小说写得好的,如果让我选,我就选刘庆邦。” 更有读者赞叹他是“短篇小说之王”。刘庆邦谦称:这都只是别人对他的激励、抬举,自己从来不当真,一当真就可笑了。“拳击有拳王,踢球有球王,但是写小说没有‘王’,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不管怎样,迄今为止,确实是中短篇小说为刘庆邦赢得了更多的荣誉。他凭《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又凭聚焦煤矿生活的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也使得他为更多读者熟识,而刘庆邦也更多作为写煤矿题材的作家为读者熟识。但刘庆邦始终关注这一领域,倒不只是因为他经历过9年矿区生活,对此有深刻的记忆,还因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煤矿工人群体说话。“矿区大都在城乡接合部,矿工多数来自农村,他们脱下农装换上工装,就成了矿工,收入比农民高,但代价也更高,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性格特征都还是农民类型的,他们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个由七百多万人支撑起来的群体,为中国提供了67%的能源,但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他们的内心世界被忽视了。”
某种意义上正是源于这样清醒的认知,让刘庆邦对自己的写作有着多数作家缺少的较为明确的职业定位,那就是“关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这一转型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当然他也写了很多乡土题材的作品。刘庆邦感慨:“离开故乡以后我才知道,故乡是我们的根,人虽离开了故乡,根还留在那里。因此每年清明节前夕,我都要回老家看一看。我们村目前进入了由庆字辈的哥哥和弟弟们当家主事的时代了。可是,庆字辈的弟兄们表现得不是很好,除了少数人在村子里留守,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逃离。不要说别人,我自己就是较早的逃离者之一。不过,只有脱离了故乡,我心里才有了故乡的概念,成了有故乡的人。”
由此观之,刘庆邦写《堂叔堂》这样的作品,更可以说是他年岁渐长以后对乡土的回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贺绍俊说,刘庆邦对一百多位堂叔的故事,应该说早就了然于心,但他放到今天来写,在积累了这么多人生经验和人生智慧后来写,显然更能体现出他成熟、稳重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或者说世界观,在刘庆邦看来,是来自于一个作家的思想。“一个作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力量、思想水平。作品高下很多时候体现在你对这个世界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这其中体现了你的生命力量。你的力量不是体现在你的体力上,主要是体现在你能不能勤学善思,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以刘庆邦的理解,一个作家要成长,除了提高自己的力量以外,还得不断增加自己的分量。“生命的分量不是先天就有的,它是经过历练得来的。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挫折,甚至可能曾经失去过尊严等等,这些都可能会增加自己生命的分量。沈从文在评价司马迁的时候就说,司马迁之所以写出《史记》在于他的忧患意识,在于他生命的分量,司马迁我们知道,他的尊严曾受到太大的打击,但是他生命的分量也因此非常重。”这诚可谓一位“老实”作家的肺腑之言。
某种意义上也因为“老实”,刘庆邦多年来一直心无旁骛写他的小说。他回忆说,当年他是跟刘恒一块儿当的专业作家,他俩和刘震云一道被称为“北京三刘”,这三个人里也只有他没有涉足影视,而一直抱着小说不放,不改初衷,真正的慎终如始。“沈从文先生说,一个人走上文学这条路并不难,难的是走一辈子,难的是走到底。我自己的体会也是,我这一生能把小说写好就不错了。这还得需要意志力做保证。好多人也写过不错的小说,就由于意志力不行,写着写着就放弃了。”也因为有这样的自觉,刘庆邦才有了这样的老生常谈:“最大的技巧是真诚,一切技巧的核心在于要不失天性,守住天性,始终要找到自己。”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现场图、摄图网

1981·文学报40周年·2021


网站:wxb.whb.cn
邮发代号:3-22
原标题:《回望乡土与亲情,刘庆邦新作《堂叔堂》如何更新观念表达历史记忆?》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