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三个蒂利:学者,师者与公民 | 人物
原创 JiFeng Bookstore 回响编辑部 收录于话题#人物5个
在学院世界日益技术化的今天,指导后辈学生和践行公民职责渐渐被遗忘,学者们似乎只剩下拼职称、赚名声一途。在这样的环境下,查尔斯·蒂利不但在治学上不断推陈出新,还悉心指导学生,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后辈学人,更是学以致用,积极践行公民责任,永久改变了和平抗议的境遇。蒂利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什么是学界精英、精神导师和意见领袖,成为后世知识分子的典范。
三个蒂利:学者,师者与公民
文 | 谢 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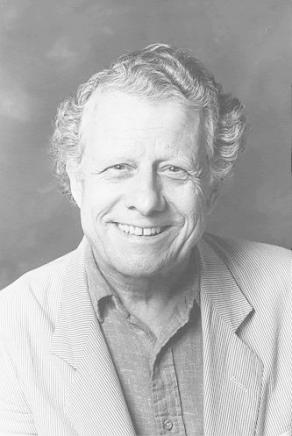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年5月27日生于伊利诺伊州的伦巴德,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和抗争政治研究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1958年,蒂利在哈佛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特拉华大学、多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纽约社会科学新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4年,他的第一部专著《旺代》出版,反响巨大,一举成为美国社会学和史学界的明星。在他近60年的学术生涯中,这位“美国最多产、最有趣的社会学家”以惊人的创作热情,出版了56部著作和600多篇论文,获奖无数,在历史社会学、现代国家的起源、抗争政治、城市社会学、关系社会学等领域无人能望其项背。
2008年4月29日,蒂利在纽约溘然辞世。就在他病逝前夕,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将最高荣誉“赫希曼奖”授予他,表彰他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蒂利逝世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联合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为期一周的悼念活动;SSRC在官网上辟出专门的纪念网页;美国多家学术期刊辟出专栏,追念蒂利的理论遗产;《纽约时报》则在讣告中称他是“21世纪的社会学之父,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一。”
蒂利逝世前后,国内也逐渐掀起一股译介蒂利的热潮。自《集体暴力的政治》首次被翻译出版以来,他的其它著作也先后在中国面世,包括《边界、身份与社会联系》、《抗争的动力》、《社会运动》、《民主》、《为什么?》、《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信任与统治》、《欧洲的抗争与民主》等。
我把不平等看作是一个迷宫,在那里,大批的人在里面徘徊,他们被由自己建立起来的墙——并不总是故意的——隔开。
——查尔斯•蒂利
蒂利出生在威尔士-德国移民家庭,祖父辈以采矿为生。在获得哈佛的博士学位之前,他送过报纸、看过大门、干过勤杂、卖过杂货……其间,还曾加入海军陆战队,参加韩战。出身的卑微与生计的挣扎,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蒂利的研究视角,使他将注意力更多地投诸于时代变迁下的社会底层民众。
蒂利在哈佛的头几年,似乎并非尝到什么甜头。哈佛社会学系第一任系主任——彼蒂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乔治•霍曼斯(George C. Homans)是当时美国社会学界的大佬,学术地位如日中天,蒂利是索罗金的助教。令蒂利十分尴尬的是,索罗金教授有个“怪癖”:经常在大清早来电话,寥寥数语通知蒂利为其代课,却从不交代讲课的内容。这样的差派每每让蒂利不知所以,暗自叫苦。索罗金带来的“苦头”还不止这些。据蒂利的回忆,每当谈起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索罗金总是挖苦道:“你的研究很有趣,蒂利先生,不过,我想柏拉图会夸你更好。”后来由于错过了博士资格考试,蒂利就借此机会改投到了霍曼斯教授和摩尔教授门下,“开掉”了索罗金这个“难搞”的导师。有趣的是,数年之后,蒂利因《旺代》的成功出版而获得美国社会学年度最杰出学者奖,而这个奖项冠名恰恰就是索罗金。
然而,《旺代》的名噪一时似乎没有为蒂利带来多大的利好,他的第一份教职是在名不见经传的特拉华大学社会学系。在特拉华并不愉快的6年工作经历之后,蒂利前往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这样的遭际在许多人看来是蒂利的“晦暗时刻”,但是,主流社会学的偏见并没能遮蔽蒂利异乎寻常的才华,孤绝的洞见终究会如星芒,刺破黑暗。在密歇根大学的十多年里(1969年-1984年),蒂利出版了多部后来堪称经典的著作,在历史社会学、抗争政治、城市社会学和现代国家建构方面,奠定了理论大师的地位,引领了社会学、史学和政治学未来二十年的发展。
1996年,在办理了退休手续之后,蒂利又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讲座教授,继续演绎了他传奇般的学术生涯。在哥大期间,蒂利最引入注目的成就是,携手康奈尔大学的塔罗(Sidney Tarrow)和斯坦福大学的麦克亚当(Doug McAdam),雄心勃勃地构造了“抗争政治理论”。在他的多部著作里,蒂利试图将他的历史社会学、政治过程理论、宏观比较历史方法,综合地运用到抗争政治研究中,使之系统化和理论化。为此,蒂利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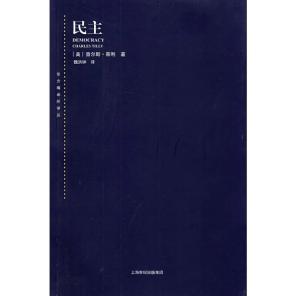
民主
[美] 查尔斯·蒂利 / 魏洪钟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5-5
蒂利在其职业生涯中,始终走在同代人的前列,为后辈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开疆拓土。人们尊崇蒂利,固然是因为他超高的智识和勤勉的学者之风,但他留给世人更宝贵的精神遗产是他在治学、为师、为人这三件事上的深厚给养。作为学者,蒂利总是乐于向权威挑战,在自己开创的领域里乐于成为年轻学人的“肩膀”;作为师者,蒂利无条件地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培养学生上,把追求真理的薪火传给后来人;作为社群中的一员,蒂利把对社会的贡献视为自己毕生乐事,尽最大可能用学理去影响当权者和普罗大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界最或缺的品格。
作为学者的蒂利
挑战传统,或许是蒂利作为学者最耀眼的品格。从第一部著作《旺代》开始到最后一部著作《抗争表演》,他始终在寻求改变,提高社会科学的解释力。
《旺代》是蒂利的开山之作,对历史社会学和抗争政治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蒂利以1793年法国西部旺代地区的反革命叛乱为研究对象,解释现代化过程中这种变异现象。但是,这种研究风格恰恰挑战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后者武断地以为,基于西方发展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的意义,现代化过程如欧美一样,是线性的。为此,蒂利在哈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大师的眼里,蒂利、巴林顿•摩尔( Barrington Moore)、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都是现代化理论离经叛道之人。借助于他们的影响力,哈佛的结构主义权威们将摩尔从社会学系解聘,逼迫亨廷顿出走哥伦比亚大学,而蒂利则“流落”到了特拉华,忍受了六年郁郁寡欢的生活。然而,这样的“驱离”并未改变蒂利在理论创造上的“抗争”精神,他的伟大成就正是建立在对结构主义的否定与超越之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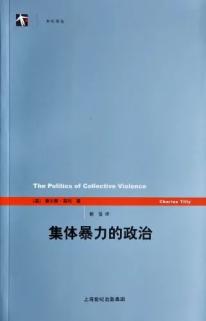
集体暴力的政治
[美]查尔斯·蒂利 / 谢岳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1-11
异于一般的学者,蒂利对建设学术共同体,总是怀着火一般的热情。他长期为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服务,是SSRC早期最活跃的成员之一。1960年代,蒂利主持了SSRC的一个历史科学研究小组,从事行为科学的问卷调查工作;70年代,蒂利担任SSCR社会科学数学委员会主席;80年代,蒂利则作为SSCR国家与社会结构委员会的成员。在SSCR期间,蒂利最大的贡献是接受了比较政治学委员会主席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的邀请,领衔研究现代国家的起源问题。他大胆地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召集到一起,进行跨学科的理论对话,1975年主编出版了经久不衰的名著,《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通过揭示西欧国家间在发展方面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性以及国家内部面临的严重社会冲突,这本著作严肃地挑战了结构主义或现代化发展理论的片面结论。蒂利领衔的这支研究团队对历史社会科学的肇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
(By LaurenSSRC - Brooklyn Heights, CC BY-SA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26472057)
抗争政治工作坊是蒂利热心建设与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又一个鲜活的例子。早在多伦多大学期间,蒂利周围就聚集了一批致力于抗争研究的年轻学者,到了密歇根之后,蒂利的追随者越来越多。通过这个工作坊,蒂利开创的“事件史”(event history)定量研究方法,帮助了大批年轻人,直至今天,这个研究方法仍在不断地惠及后来人。蒂利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抗争政治工作坊,名噪一时,成为社会学纽约学派的一个重要阵地。每周三6点,来自纽约州的学者都会聚集到哥大,提交工作论文,供大家公开研讨。过去四十年,抗争政治之所以能吸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这个工作坊功不可没。蒂利过世后,据说工作坊已经由他的学生接手,转到了纽约城市大学继续运转。
撇开同行竞争的顾虑不谈,帮助他人是一件费力费时的事情,但是,蒂利却乐此不疲。蒂利在业内不遗余力地提携年轻人,也是一个有口皆碑的故事。多位华人学者包括我本人都不同程度地直接得到过他的指点和帮助。塔罗(Sidney Tarrow)和麦克亚当(Doug McAdam)是蒂利最后十年抗争政治理论研究的主要合作者,同时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塔罗把和蒂利的合作比喻为“葡萄园里一起劳作的工人”,只不过,蒂利已经为他种下果树,并打理好了果园。塔罗和蒂利的第一次相识是在安娜堡,此后一直延续到纽约。在塔罗的记忆里,所有提交给蒂利的草稿,他都会给予批注;而且,按照他的意见所作的修改,都会比原文好很多。在合作《抗争的动力》这本书过程中,蒂利一如既往地坚持客观、公正的研究风格,对塔罗的写作从未有过不公正的批评,从不会“倚老卖老”以学术大佬的身份凌驾于他人之上。平等的关系大概是蒂利和塔罗长期保持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蒂利去世之后,塔罗亲自修订了两人合作的《抗争政治》一书,同时参与了蒂利没有完成的一部遗稿的编撰,结集为《城市与国家中的抗争与信任》,于2011年出版。

斗争的动力
[美] 道格·麦克亚当 [美] 西德尼·塔罗 [美] 查尔斯·蒂利 / 屈平 李义中 / 译林出版社 / 2006-9
麦克亚当比塔罗年轻,在他看来,自己还是一个“菜鸟”的时候蒂利已经是大咖级的学者了。正因为这种悬殊的地位,蒂利的帮助令他终身难忘。年轻学人的遭遇有时候是相似的。麦克亚当在将自己的博士论文提交给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之后,收到其中一位匿名评审的意见,不足一页纸的决定草率而颇具成见:不予出版。相反,另一位匿名评审却给出了长达12页的修改意见,评论中肯,切中要害;更重要的是这位评审还给出版社写了一封推荐信。这个人就是慧眼识金的查尔斯•蒂利。签下出版合同后,麦克亚当十分激动,想向蒂利表达谢意,蒂利却回复他,“没有必要感谢,如果真要感谢的话,请像我一样对待你的匿名评审。”
作为教授的蒂利
教书育人本是教授的天职,但在今天的大学里,为了自己的终身教职,教授们把大多数时间和精力用来著书立说成就自己,并没有太多人愿意全身心地指导学生。在这一点上,蒂利是一个例外。无论是在安娜堡,还是在纽约,蒂利不仅对学生有求必应,还主动组织研讨会、工作坊让学生参与其中——能够站上最高层次的学术研究起点,对年轻学者来说无疑是极其幸运且珍贵的。
在安娜堡时期,蒂利在家中为研究生专门组织了著名的“周日之夜”研讨会,邀请大学名流演讲或讨论研究生的写作草稿。对于刚刚踏进学术象牙塔的学生来说,能够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这样的史学巨人面对面地对话,若不是因为蒂利,简直就是“做梦都不可能的事情”。那些后来成名成家的研究生时常感怀当年的“群贤毕至”,如何深刻地影响了自己毕生的研究生涯。除了霍布斯鲍姆,更多的受邀嘉宾后来都成为学术界的精英,如普林斯顿大学的荣休教授欧洲史专家戴维斯(Natalie Davis)、法国史大家阿古龙(Maurice Agulhon)、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宗教史专家布莱克(Wayne Te Brake)、密歇根大学社会学运动研究的干将汉纳甘(Mike Hanagan)和阿明扎德(Ron Aminzade),等等。我在哥大期间也有幸参加了这样的学术活动,感受最深的是,学生提交的写作草稿若能得到最高水平的评论,日后发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论文,一步就跨入了学界一流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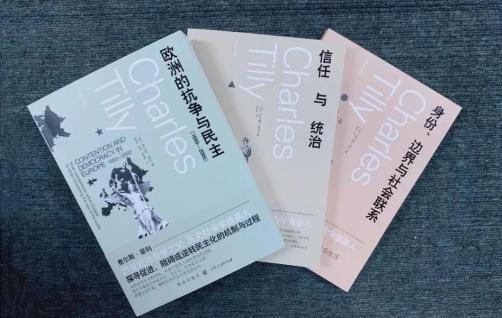
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
[美] 查尔斯·蒂利 / 谢岳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21-1
信任与统治
[美] 查尔斯·蒂利 / 胡位钧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21-1
欧洲的抗争与民主
[美]查尔斯·蒂利 / 陈周旺 / 李辉 / 熊易寒 / 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 / 2020-12
不过,“周日之夜”、“抗争政治工作坊”也常常令学生们脸红心跳。试想,一群刚刚接触微观史学的年轻人,面对宏观历史社会学的权威学者,该如何对话呢?这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蒂利的耐心、平和、宽容与慷慨,能够很快平抑学子们因身份和学识落差而带来的紧张情绪,让彼此的对话轻松自如。事后证明,这样的学术对话极大地有助于学生从事创新性的思考。一直以来,蒂利反复地提醒学生,学术思考和创新要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方法:首先,将理论关怀贯穿于民族志事业的始终,换句话说,就是外行能够从你的研究中学到什么;其次,对待历史,不能像收拾箱子那样,打开又关上,而应当打开一个箱子之后,继续打开另一只箱子,因为众多的宏大历史命题会共同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社会过程既是复杂的,又是彼此关联的,必须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中动态地观察,才能找到相似性或差异性的真正原因;最好的理论贡献一定是来自于对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如战争、革命、民主化、国家建构、社会运动等。
在学生们的眼里,蒂利就像是不求回报的“圣诞老人”,不停地给他们派发各种“礼物”,或鼓励,或启发,或建设性的批评,总能给他们带去各种惊喜——而这些往往是值得记念一生、终身受益的。
作为公民的蒂利
专业知识分子经常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回馈社会。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经世致用”。问题的答案也许不一而足,但当争取终身教职和履行社会义务之间需要权重考量时,绝大多数人会优先选择前者——毕竟,生存更为迫切和重要。但新的难题又来了:在那些已经取得终身教职并且生活无虞的学者看来,追求学术声誉通常又会成为新的优先项。于是,一辈子都待在象牙塔里,享受着来自小圈子里的学术赞誉,是很多大学教授追求的“标准格式”。在这方面,蒂利再一次成为我们的榜样。
为平民抗议正名,是蒂利留给时代的一个巨大贡献。1960年代,美国社会为黑人的民权运动困扰,警察滥用职权、过度执法的情况非常普遍,平民重伤致残乃至暴尸街头时有发生。受SSCR的委托,蒂利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为和平的权利运动呐喊,呼吁政府和社会转变态度,不要再将集体抗议看作是一种社会病态。研究报告递交到了国会那里,也影响到了约翰逊政府。此后,国会督促政府改革警察机构的街头执法行为,严格区分暴力抗议与和平抗议,禁止对赤手空拳的平民抗议者进行武力镇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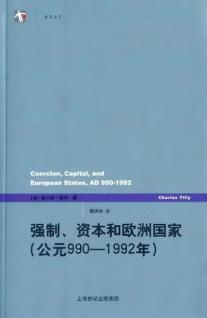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
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 / 魏洪钟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2-8
通过研究社会运动,蒂利继续走在回馈社会的路上。在《旺代》出版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由于社会运动概念暧昧不清,蒂利对这一研究领域并未作过多关注。直到1980年代,对美国学界滥用“社会运动”现象的严重不满,促使他终于开始系统地研究社会运动。1986年和1993年,蒂利分别出版了两部有关社会抗争的经典著作,《抗争的法国人》和《1758年-1834年英国的民众抗争》。他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基于两个基本的判断,一是,相对于选举等日常行为,以集体利益为诉求的社会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更加重要的形式;二是,社会运动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从西欧历史上屡屡上演的抢粮事件中,蒂利意识到这些事件和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似性。在观察英国大众政治的过程中,他又发现,1830年代伦敦街头反对奴隶制的运动似乎就是对英国选举制度改革的回应,而且与当代社会运动的形式和诉求相互匹配。2004年,蒂利推出了《社会运动》专论,指出,社会运动既是民主化的结果,也是民主化的实现途径。由此,蒂利完美地将个人职业发展与社会进步融合在了一起。

社会运动,1768—2004
(美)查尔斯·蒂利 / 胡位钧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9-1
在专业写作之余,蒂利还撰写了适合大众口味的作品,目的是将自己的研究发现惠及更广泛的非专业人士。《为什么?》是蒂利此类写作的代表性作品。他想回答困扰人类的一个常见的行为,即“人们为什么总是要为自己做过的事、别人对他们做过的事或者世上发生的事寻找理由?”两个方面的思考帮助他写作《为什么?》,一是,很少有人分毫不差地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事情的发展经常超出他们的设想,但是,人们对社会过程的描述和解释总是强调有意为之;二是,大多数社会过程都类似于一场针锋相对的对话,而不是个人独白。近乎“灵魂叩问”的《为什么?》大获成功。《纽约客》的书评写道,“这本书迫使读者重新全面检视从他们对自己孩子的说话方式到政治问题的讨论方式”。蒂利十分珍惜这种写作产生的社会影响。他表示,“如果有人告诉我,《为什么?》帮助他解决了生活中的难题,我会感到骄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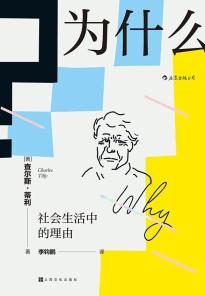
为什么? : 社会生活中的理由
[美] 查尔斯·蒂利 / 李钧鹏 / 后浪丨上海文化出版社 / 2020-9
专业人士能够扮演好“为学之人”、“为师之人”和“为人之人”的其中一个或两个角色,已然算得上是学界精英、精神导师或意见领袖了,而蒂利却完美地将三者糅进了自己的生命之中。这,才是我们怀念蒂利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原标题:《三个蒂利:学者,师者与公民 | 人物》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