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刺杀小说家:票房不能决定一部电影的生命力
原创 努力工作的 单读
上个月,《刺杀小说家》导演路阳、原著作者双雪涛和吴琦、罗丹妮一起分享了和这本书有关的故事。他们回忆了从小说发展成电影再到创作实录的机缘,就像双雪涛形容的那样,小说提供了一个火种,更多东西被创造出来了。吴琦和丹妮还聊到做这本书给自己带来的教育,关于在今天我们还可以怎样工作,怎样去谈论理想。虽然电影会离开院线,但这些故事会一直滋养我们。
这是一场“中二”的冒险
也是一次重要的教育
对谈:路阳、双雪涛、吴琦、罗丹妮

《一场“中二”的冒险——〈刺杀小说家〉创作实录》
新书分享会活动现场
路阳:电影本身就是疯狂的
2016 年春天,万娟老师(编者注:电影《刺杀小说家》制片人)来找我,当面强制我迅速地把《刺杀小说家》看完,然后马上给她一个答复,拍还是不拍。我看完之后,马上就请万总帮我约雪涛的时间,我非常想见到他,非常想跟他聊一聊关于小说的事情,以及我怎么理解他的小说。我想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我很想拍这篇小说,但是我必须要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小说。
其实 15 年我们看了很多项目书,到 16 年那个时候,已经在筹备《绣春刀 2》的拍摄了,离开机还有一个月,我有点焦虑,因为不知道《绣春刀》之后该拍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正在寻找之后的内容。看到雪涛的这篇小说,我才终于找到不用通过理性分析,完全凭感觉就知道想要去拍的一个好内容。

电影《绣春刀 2》剧照
所以这部电影雪涛满意是非常重要的。是他的这篇小说给了我们一个创作的开始,给了我们很单纯的想拍东西的想法和感受。我不想去偏离这个东西,如果说雪涛不认可的话,就说明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可能已经偏离了最开始刺激我们去拍电影的想法、念头、情感,或者那一句话。他最清楚他的小说这句话要说的是什么,他可以在一个既主观又客观的视角上去看待这件事情,他会很直接地告诉我这是不是他想象中电影该有的样子。
我在每个阶段都会把素材拿给雪涛看,每次他看的时候我都会很紧张,无论是 5000 字大纲,还是 2 万多字大纲;无论是初稿的剧本,还是定稿的剧本,还有片子剪辑过程中的无数个版本,我折腾了他很多次。包括有的时候,一句台词也会去问雪涛,这句话应该怎么说,我们俩会一块想办法。第一次把片子全部做完给雪涛看的时候,我就坐在他后面,我始终都在看他的反应。我希望雪涛能第一个看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们是能互相明白的。
我跟雪涛第一次见面,是 3 月上旬的一个下午,那天是个晴天,雾霾没这么严重,阳光还比较温暖,在我们办公室的大厅里。我的制片人张宁就说,老路,这个小说你再想想,你是不是真的要拍。我就说不用想,我肯定要拍。
虽然想要去拍的想法当时一瞬间就形成了,但在真正开始剧本创作之前,我反复地考虑过怎么去做。有很多种方式来改编小说,把它拍成不同形态的电影,但对我来说该怎么拍,想了挺久。
之所以做《“一场中二的冒险”——〈刺杀小说家〉创作实录》这本书,最开始是因为我们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踩了很多雷,尝试建立了一些新的工作方式,想要把这些工作方式系统化地记录下来,分门别类地把各个部门的工作都记录下来,也许可以提供给同行一个或许有价值的参考。拍完电影之后慢慢去想,会觉得电影其实是送给观众的,但是我又很希望能够记住制作电影过程中的很多细节,不要时间久了就把它们忘了,所以想要做这样一本书。
这部电影的很多主创我都已经合作过很多年,长的可能超过 10 年了。我对他们很熟悉,但是看了张雄老师采访完后整理出的文字,发现在他们的心里还有很多我没有想到的角落。我能看到他们对电影的情感,我特别感动。我觉得他们一直都没有变过,这是让我最开心的事情,他们一直都比我想象得要更加热爱电影,也难怪这样的一帮人会走到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也很庆幸我们当时有这样一个想法做出这样一本书,无论是交给读者还是交给我们自己,都是一个挺珍贵的东西。

电影是不能脱离商业体系的,在商业体系里面有一些规则,或者有一些套路。但是雪涛的小说给我的感觉是没有套路、完全新鲜,那种新鲜给了我特别幸福和愉悦的感受,我很想在电影里面分享这种感受。我们有一些疯狂的念头想要在电影施展出来,那些东西可能经过算计就会显得比较疯狂,但我觉得不要,那是小说以及我们要做的电影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当然我也要考量,如何通过其他办法把我想要分享的这些东西传递给更多的观众。其实我觉得电影本身就是疯狂,它必须要带有某种探索性或者冒险性才有意思。所以想把很多疯狂的想法、念头记录下来,提醒我们不要去忘掉这件事情。
电影上映之后有一件事我特别开心,很多观众会在评论里面留言,说看完电影之后要去买雪涛的书,这是让我特别高兴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文字是很独特的,文字是不可以被影像、声音或者其他形态代替的,是一种很特殊的人需要的东西。
双雪涛:小说提供了一个火种
准备把《刺杀小说家》改编成电影的时候,我刚来北京。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万娟来找我,在一个特别难吃的西餐厅喝了特别难喝的两杯咖啡。然后她跟我说,你觉得小说找谁来拍?我就想起了前几天晚上在电视上看的《绣春刀 1》,我觉得特别好看,台词特别舒适,叙事也很清楚扎实。
我之前也不认识导演,我就跟万娟说,这个导演你听说过吗?万娟说前两天好像刚刚见过面。我说咱们就去试一试。老路看完小说之后,就决定开始做这部电影。
我们俩见面就聊天,不光聊这篇小说,因为年龄相仿,天南海北地瞎聊。其实聊的内容不重要,人的感觉比较重要,两个人得找到一个合作的契合度。契合度有时候并不一定指见解完全统一,而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对于好东西的认识,有耐心甚至有胆魄来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最满意的地方是这部电影不是通过理性计算出来的。因为电影产业跟资本、工业甚至跟产品的关系越来越近了,尤其是现在,我们社会发展得越来越快,大家一个一个都变成会计了。我们能看到很多计算出来的电影,那可能也是一种做电影的方式,但是对生态是不是真的好,我是怀疑的。《刺杀小说家》是一部不经过理性计算的电影,但是它又有这么大的投资规模,所以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东西。我最后看到成片的时候,当然觉得很震撼,很激动。
我觉得这就是思想的力量。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你的一个想法变成了一个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就变成了一个产品,还可能会变成更复杂的产品,不光是电影的形态,还有很多衍生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会思考的人类很有成就感的地方。
《刺杀小说家》原著小说收录于《飞行家》
从小说到电影,其实我觉得没有一种原则说,什么样的小说能改电影,或者什么样的小说不能改电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就是得从个案来看。
我觉得文学能给电影带来的东西还是蛮多的,不是因为我是搞文学的,我客观地认为电影非常需要文学,而且我觉得电影从业者也很需要文学。有的时候我跟做电影的朋友一起合作,实话实说,我感觉到有些电影人很有热情,但是因为他的阅读和接受的审美教育可能不足够,他受限于,不是自己的热情,而是自己的能力。
我会跟做电影朋友交流,最近有什么新书可以看一看。文学对人的滋养是非常缓慢的,需要慢慢浸润。当你成为了一个文学人,同时又是一个电影人,还是一个热爱某一种美学的人,你就成为了一个复合型创作者,这样的创作者特别适合搞电影,如果单有某一项,不够均衡的话,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文学对电影的作用其实是对人的作用,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项目。
我当然希望有更多好的文学作品能变成电影,严肃文学作家们其实写了很多很好的作品,只是没有被看到。问题的第一点是,很多人认为有些卖得好的书就很牛逼,其实这是很扯淡的,很多人默默地在文学上耕耘,写了很多好东西,只是你们没有看到,那是你们的损失。另一点是,不要以为情节很复杂的小说就特别适合改编成电影,或者看起来跌宕起伏的小说就能变成一部好电影,这也是非常扯淡的。
有的时候小说提供给电影人的是一种启迪,但是需要有悟性的电影人去捕捉。小说是一个火种,把你心里的蜡烛点亮,而不是给你一个巨大的火把,把你烧毁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我特别希望我们的电影人有耐心去阅读一些好的当代作家的作品,然后他会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在认真地耕耘文学,这可能对他们有一些帮助。

活动现场
吴琦:在今天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工作
开始做《“一场中二的冒险”——〈刺杀小说家〉创作实录》这本书,其实是因为一个商务合作机会,电影的出品方之一华策跟单向空间之前做过衍生品的合作,所以我们之间互相认识,后来他们就跟我们说起这部电影。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的想法并不是把这本书做成电影的衍生品,而是希望这本书能用书的方式去记录电影诞生的过程,我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的专业得到了尊重,做书是被认可为有自己独立的专业精神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开始。
然后我们直接就去找导演了。这其实也是很离奇的一段经历,因为通常中间可能要经过很多重沟通,比如先谈条件,要谈合同,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合作,我们这些都没有谈,只谈内容。我记得我们还在导演的公司里吃了特别好吃的面条,一切都出人意料地愉快。这跟我熟悉的或者偶尔接触到的整个影视行业那种非常焦虑、高速、算计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
当时我们随手就开始找身边的哪些书可以做参照,然后导演突然想起来说,有两本书放在家了。他立刻就开车回家,把那本书取过来,我们马上就开始讨论了。这本书出来之后,导演的同事就问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赠书给导演,他已经忘记了赠书到底是多少册。
对我自己来讲,做这本书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一次教育。可能对我们小团队来讲合作并不困难,但是这样庞大的一个规模,这么艰难的专业工作,用这样的工作方式完成是很困难的,用“中二”来形容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相反,它是非常实际的。所有人在做书的过程中又再次被这样的内容所打动,他们对自己作品的那种相信、欣赏、开放。整个合作是特别美好的一个过程。
我在淘宝、朋友圈看到好多《刺杀小说家》的衍生品:面具、胸针、衣服……他们都不把衍生品当做衍生品对待,比如衣服就用衣服的结构、专业,衍生品本身的质量和审美都特别在线。所以你就看到,它变成了一个种子,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专业里面得到很多回响。

路空文的面具被做成了衍生品
我看到片尾字幕的时候非常感动。那种感动一是来自于一个庞大的阵容,二是来自于它的开放程度。这部电影在每个具体的环节上都找到了非常具体的合作伙伴,而且真的是合作伙伴,不是甲方和乙方那种利益绑架的关系。那个字幕本身带来的震撼是巨大的,而且特别真诚,所以我会觉得这部电影可能不只是一部电影而已,它从一个概念慢慢地生发,长出那么多东西。我觉得即便过了上映期,《刺杀小说家》也会一直留在电影行业,留在文学行业,或者留在其他行业里面,成为一个故事,然后成为一个重要的案例。这其实也是我们做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导演一直强调说,他做这本书并不是想要宣传自己多么厉害,而是希望把他和他的团队在完全中国的语境下,把一个高难度的强视效电影做出来的经验留存下来。日后我们的电影工业肯定会继续往前走,会有更多的导演或者创作者走同样一条路,希望他们能从中得到很多具体的帮助。
做这本书是一次教育,而且我觉得教育是泛文化意义上的,不只关于电影、文学或者出版,而是关于人怎么在今天这样一个环境下继续去工作,甚至是去追逐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已经不在公共领域讨论这些词语了,我们甚至以这些词语为耻,或者觉得今天社会里面这些词语太奢侈。
这是一部完全用信念构筑的作品,对我们来讲,要去理解信念构筑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只和电影专业的人有关,也关于你在生活中、工作中怎么与人合作,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他人的劳动。这本书很鼓励我,单读做出版以来,我自己的私心是能被每一个作者、每一本书所鼓励。
我们都是一个行业当中的链条,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在这本书中,大家会看到很强烈的小共同体的感觉。我印象深刻的是,每一次他们都会先开会,把大目标制定下来,然后再去各自工作,可能各自的工作状态导演未必都知道,大家自己去想办法,想完办法后再开会,看是不是偏离原初的想法。他们特别自觉地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忘掉一开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觉得这种“中二”、乐观的精神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方式。
这本书或者说做这本书的过程,让我找到了重新去谈论所谓理想和信念的方式,你得在具体的实践中展现它,不能特别抽象、空洞地去谈信念,信念是一个过程,信念也是一种方法,把信念作为方法。

其实我自己不是工业电影的观众,我更愿意看更文艺、艺术的电影。所以这也是一次教育,看到《刺小》的整个拍摄过程,并且用一本书的方式把过程记录下来,你会意识到,每个人有自己的审美偏好,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个意见之下,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东西,关于电影的复杂和专业程度,以及电影人如何工作,这些与你个人的审美好恶相比,的确是一个很庞大的世界,从那个世界能够得到的信息,远比说我不爱看某种电影要来得营养更丰富一些,这是对我们自己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启示。
我特别有信心,大家可以把这本书当做方法论的书。说得更俗气一点,也是一本很鸡汤的书。它提供了在今天的社会中,大家怎样去寻找调试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的方法,尤其是一起工作的人。我们听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工作不愉快,合作上痛苦,同事之间互相折磨。可是导演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状态,真的是在互相理解,互相体贴。我们和他们合作时,也不是在互相倾轧或者互相索取,而是互相给予,这些都是特别美好的经历。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工作。
丹妮:要实现理想,付出的努力是很具体的
第一次见路导以后,有个非常明确的想法,虽然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看到成片,但是我非常清晰地知道这个电影是能够支撑一本书的。有两层原因,一层是它的素材非常丰富;另外一层是,当时路导在不停地给我们讲故事,讲得非常细致、生动,我特别难忘,包括演员是怎么工作的,搭场景要怎么样去运筹帷幄,怎么解决自然光不足的问题,造型指导怎么设计赤发鬼……
我和编辑部的同事们都很喜欢电影,但是都不知道一部电影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但那一天我的感受就是,我好像可以通过这部电影了解一点点一篇小说是怎么变成我们最后在大屏幕上看到的东西。做这本书的原因,特别简单地来说,我需要知识,我需要知道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做的。
整个导演组非常开放,让我们大胆去想、放手去做,他们全力配合。我们一开始想以设定集的体例做,但是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有兴趣的是电影是如何拍出来的这件事,所以人物设定之外,创作的其他环节也非常重要。

当时就想,我们需要一位电影行业的“门外汉”来提问题,问一些我们希望知道,但对于电影专业人士来讲可能是常识的问题。而且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脉络,把相关的主创人员都问一遍。很幸运,张雄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记者,而且他也做过相关的工作,我们一聊他就说很愿意做这件事,一拍即合。
这个时候其实我仍然不知道这本书会长成什么样子,我只知道我们有海量的图片和很多愿意接受我们采访的主创人员。接下来三个月的时间,路导和他的助手一直在帮我们联系各位老师,然后张雄就挨个去采。录音很多,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整理、撰文、编辑,第一版初稿有 5 万多字。随后又补采了两位老师,补充了几万字。设计师也去了好几次工作室,剧组那边保存了海量的大图,几经筛选,最后拷贝出了五六千张作为配图素材。
面对这样一个体量,再来重新考虑,我觉得我们不能只把它做成几个主要角色的设定集,实在有太多故事和经验需要分享。所以大家今天看到,最后我们把这本书改成了创作实录的体例,包含了电影各个步骤流程的主创人员的分享。这本书我们并没有赶得特别急,没有让它一定要在电影宣传前期上市,我们还是觉得要首先保证它的质量,而且对它的长销非常有信心。
这是一本不会随着电影下线而下线的书,它会跟电影一样走得非常远,会留给很多喜欢电影喜爱文学的人。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创作者的分享,只要你对内容创新有热情,就会在这里面看到很多具体的启示。
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激动。我首先是一个读者,看过雪涛老师很多小说。那一刻我的内心有小小的震撼。这篇小说是双雪涛在二零一几年写的,写的时候还在沈阳,他写的时候绝对没有想过,这个小说决定了几年后,有这么多人花 5 年的时间,用这么多钱、这么大精力做这件事情,这非常疯狂。
同时我理解这篇小说给导演和整个创作团队都提供了一种刺激他们创作神经的元素,我觉得这是文学的魅力,有点像给人下了蛊一样,就是你觉得这东西特别有魅力,你就想投入其中。这让我作为一个读者也好,或者作为一个文学出版编辑,感到非常兴奋,这样一篇小说自己长起来了,变得像有生命力一样,然后长出了这部电影,接着,居然又能有一个机缘,让它再一次以书的形式往前走。

如果一部电影最后能让我们有兴趣去追根溯源,回到文字,看到故事起始的部分,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所以我也非常关注电影上线以后《飞行家》的销量,我很开心。 我以前觉得这部小说是有一些固定读者的,可能是喜欢作者的人,还有一些是原来印象中读小说的读者,但可能因为电影的缘故,很多本来不会打开小说的人也去看小说了,这是一件非常牛的事。
我们做这本书的一个想法也是真正去学习其他行业同事的工作方式。不同阶段的那么多素材,剧组的同事整理得非常清晰。每一次我们把文稿给剧组看,他们很快就会返回来,而且看得很仔细,让我惭愧,文稿还会有错字,还有演员的名字前后不一,他们都认真修改,而且非常快,我们每一次把照片拿过去,他们对照片的反馈,应该写什么样的图注,也处理得非常快。
编辑做一本书的生产周期大概一年,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我们投入的成本就是那样,我们都经常觉得苦不堪言。说实话,有很多槽可以吐,比如说书号难拿,作者拖稿,设计师给的封面不满意,我自己能感受到我们业态现在的工作状态。
可是去导演工作室的几次观察会让我觉得,他们很热血、也很淡然,没怎么感觉到他们身上特别倦怠的部分,是一群很乐观的人,气势昂扬,而且如此细碎的工作也没有不耐烦。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做一本 5 年后才会出的书,不知道会怎么样,而电影的不可测因素是更多的,比如说疫情期间能不能上线供应都是个问题,可是书还是有很多具体的期盼,有了书号就可以出版。
所以我会觉得做电影其实对人的心性折磨得更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书的几个人得到了一种教育,就是在不同行业的创作者,他们要真正实现一个理想,付出的努力是更具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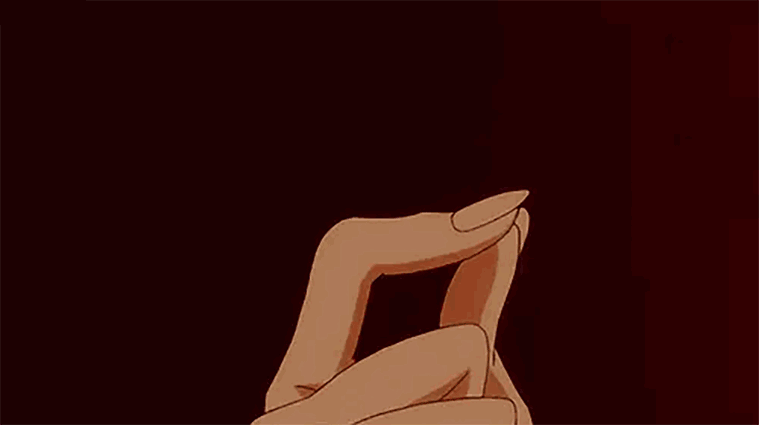
▼具体的努力
原标题:《票房不能决定一部电影的生命力 | 单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