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弹痕累累的城市,萨拉热窝不散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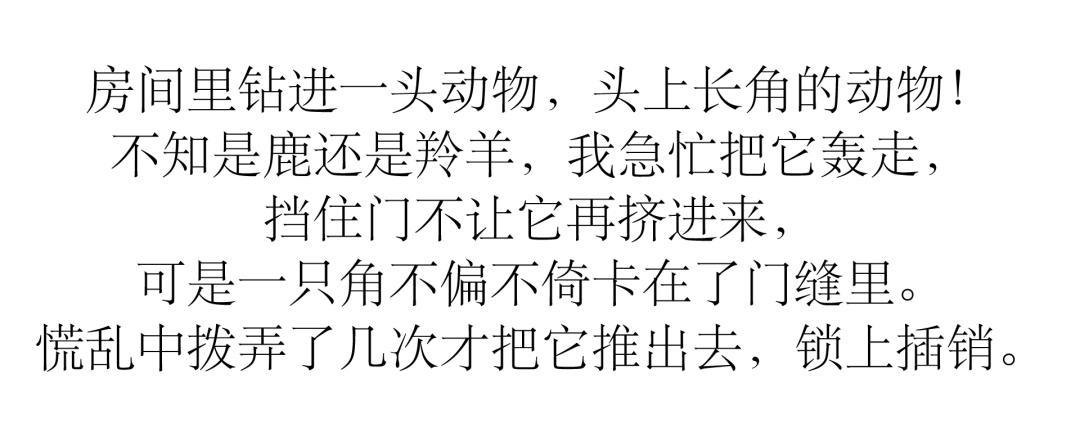

那只动物在外面“砰砰砰”以头撞门。我不加理会,走到窗边,把窗子也紧紧扣上。玻璃窗外远山如画,近处一道河谷,黑烟四起,似乎一场轰炸刚结束,四下悄无声息。楼下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柏油路,有个人推着板车往桥头跑去,看不清脸——没有声音的一幅画面。
忽然醒了。支起身子,透过玻璃窗往外看,并没有河谷、桥和柏油路,只看到几栋老居民楼,很像北京,社会主义时期单位宿舍楼那种结构与配色,后面那栋更像东德或波兰建筑——没有声音的一幅画面。
外面雨停了,地上有积水。被窝不够暖和,越睡越冷,怪不得一大早做怪梦。我没想到波黑这个小国冰火两重天,一天前在“黑”那边的莫斯塔尔,晚上睡觉要开冷气才睡得着,从“黑”来到“波”,气温跳到另一端,萨拉热窝果然是举办过冬奥会的地方,凄风苦雨,可以改称“萨拉冷窝”。

1984年萨拉热窝冬奥会留下来的设备现已荒废。
雨夜无事可做,早早钻进被子,在手机上找出苏珊·桑塔格的《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卧读。被窝不是“热窝”,要用自己体温去焐热它,桑塔格的文章标题下刚好写着“无事可做”几个字,那是《等待戈多》剧本开场白的句子。
桑塔格1993年春天和夏天两次来这个城市,第一次是作为战争的目击者,第二次变成行动者,她要为围城中的萨拉热窝市民导演一台话剧《等待戈多》,她觉得贝克特的这个剧本几乎是为萨拉热窝量身定做创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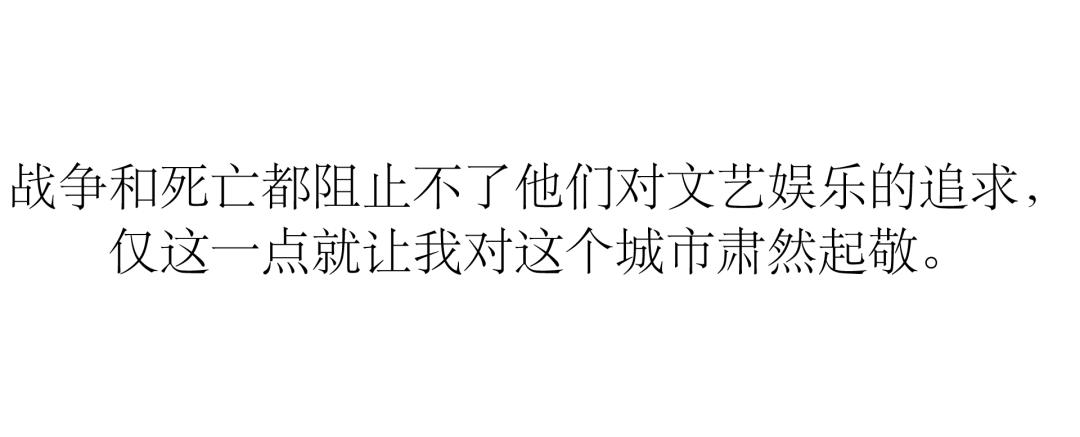
一想到演员和观众在去剧场途中和在散场后回家途中都有可能被狙击手的冷枪射中或被迫击炮弹炸死(1993年夏天,炮击最密集的时候萨拉热窝一天会遭到近四千枚炮弹的袭击),就觉得这样的演出太不可思议,萨拉热窝人太有文化了,战争和死亡都阻止不了他们对文艺娱乐的追求,仅这一点就让我对这个城市肃然起敬。
桑塔格又是如何突破炮火封锁线和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防线两次钻进围城的?这个技术问题从她的文章里找不到答案。我划拉着手机地图,忽然看到市中心有个地名叫“Pozorišni trg Susan Sontag”,查谷歌翻译,是“苏珊·桑塔格剧院广场”,决定起床出门,按地图导航走过去瞧瞧。
原来这个以桑塔格的名字命名的广场就是国家剧院正门前的广场。萨拉热窝作为一个现代城市,底子是在奥匈帝国统治时期打下的,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国家剧院设计上据说受到布拉格国家剧院和维也纳证券交易所的影响。空地上搭了一座临时舞台,不知是搭了一半还是已经拆了一半,漆成亮黄色的木板一块块随地叠放着。剧院夏季歇业,估计有些轻质的露天节目会在这里出现。桑塔格来到被围困的萨拉热窝时,国家剧院早已停止演出,她见到上一年战争爆发时的海报还在预告威尔第的歌剧《弄臣》。如今这里也同样没有任何演出,海报上在预告威尔第的《唐卡洛》,它是下一个演出季的开幕节目。另有一部话剧、一出芭蕾同威尔第的歌剧一起揭开萨拉热窝的秋冬演出季。

前往国家剧院广场要经过一条河,河面上隔不远就有一座很有年代感的石桥。跨过拉丁桥,便进入了萨拉热窝的老城。
趁着人在萨拉热窝,我又把老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从网上找出来看了一遍。小时候的印象已淡漠,只记得“桥洞像屁股”那句台词,当年电影院里演到这句台词时,底下观众纷纷学舌:“这些桥拱像什么?”“像屁股!”我很晚才知道《桥》里边那首著名插曲《啊,朋友再见》并不是南斯拉夫歌曲,而是意大利游击队歌曲,题目也不是《啊,朋友再见》,应该叫《姑娘,再见》。
现在来看,小时候对电影里萨拉热窝的伊斯兰建筑和奥斯曼帝国时代街道面貌一点感觉都没有,根本不明白这个城市有什么特别之处。五百年土耳其统治和后来奥匈帝国的统治给萨拉热窝的天际线画下一根根宣礼塔和一座座教堂圆顶,此外还有东正教堂和犹太会堂,再叠加铁托时代的社会主义大厦。电影里那座桥据说如今成了中国游客热衷“打卡”的地方,实际位置在黑山共和国,我重看了《桥》之后觉得这座桥大概没有必要去了。

这个八边形建筑,当地人叫喷泉,是16世纪从奥斯曼帝国引进的,也许是这座城市太过于悲情,如此多的鸽子在这里企盼和平。
有天下午,经过一座看上去像奥匈帝国时期的建筑,气派又沧桑,表面布满弹孔,无疑是九十年代那场战争留下来的。建筑立面上挂着“塔利斯音乐节”海报,恰好当晚八点是闭幕演出。这个音乐节我闻所未闻,从“塔利斯”这个名称推测,想必指的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大作曲家托马斯·塔利斯,那么音乐节的内容很可能是欧洲早期音乐。正要走进去仔细看,一个身材魁梧的女军官闪出来挡住我,紧接着又冒出来两个男军人,三人将我团团围住,神色严肃,着实吓人一跳!待我解释说我想了解音乐会的情况,他们马上变得和颜悦色起来,说:请你晚上八点再来,音乐会免费,但现在不准进入。查了一下,这座大楼目前属于波黑国家军队,估计是军事禁区,然而诡异的是二楼音乐厅对公众开放。
晚上这场演出,节目并非早期音乐,而是以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室内乐作品为主。“塔利斯”是个设在萨拉热窝的音乐暑期班,音乐节算是学员结业汇报演出性质,听上去像个小型的韦尔比耶音乐节,当然水平远没有那么高。有意思的是学员还包括作曲专业的,演出四首维也纳乐曲前有一个当代作品《马龙木管乐》就是一个美国作曲学员的学习成果,弦乐四重奏加一支长笛、一支单簧管构成室内乐六重奏。开始前作曲者出来解释了一番他谱写此曲的由头,灵感源于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马龙双子峰的一次背包旅行,他试图用音乐捕捉松涛、雨声和云影的印象。作曲者是个24岁戴眼镜的大男孩,样子像我一年前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分校见到的那些大学生中的一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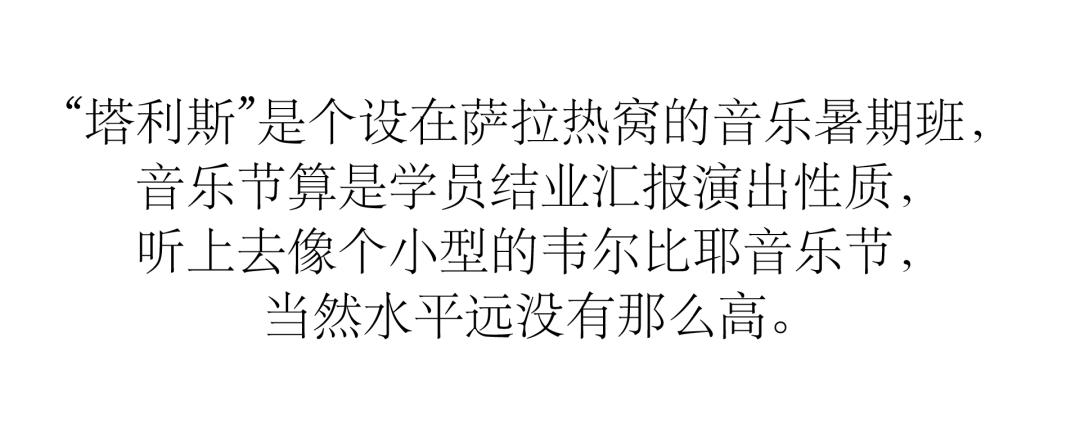
《马龙木管乐》是一个可爱的尝试,曲子结束在六件乐器持续的泛音中,这点让我印象深刻。接下来的乐曲是海顿“伦敦”木管三重奏里的第一首,两支长笛加一支巴松。以前听过朗帕尔、斯特恩和罗斯特洛波维奇的长笛、小提琴、大提琴版录音,记得还有别的改编版本。
第三个曲子我最熟悉,莫扎特G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作品K478),虽不像莫扎特的有些小调性作品那么摄人魂魄,但一、三乐章风云变幻,色彩丰富,第二乐章让人心生感慨。它被称为有史以来第一部重要的钢琴四重奏,这种体裁被莫扎特一手发展到精纯美妙的高度,他却没太用心继续深耕。
音乐会的最后两曲都是贝多芬作品,然而莫扎特之魂始终徘徊不去:一首是贝多芬改编的歌剧《唐璜》二重唱《让我们手牵手》,形式为长笛、单簧管、巴松三重奏;另一首是贝多芬降E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第4号),原是一首木管六重奏,写作上受到莫扎特钢琴木管五重奏(作品K452)启发,后来改编成弦乐五重奏。奇妙的是,《唐璜》二重唱《让我们手牵手》经贝多芬之手以木管重奏的形式演绎出来,竟有点神似莫扎特木管嬉游曲(Divertimenti)的味道。

1993年,萨拉热窝“连续十七个月成为靶场”,到现在,街道旁立有这样一块石头,上面写着“不忘1993”。
这场音乐会听得我神思恍惚,没料到在波黑度过了一个如此维也纳的夜晚,有些超现实。走出剧场,回望建筑外立面上的累累弹痕,不能不庆幸在萨拉热窝看演出不再需要冒生命危险。
1993年,桑塔格在“连续十七个月成为靶场”的萨拉热窝围城中排演话剧时,我也在欧洲,只是在安全的范围内游荡,一整个夏天都在游荡。与那场战争最接近的时候,距离只有一百公里——在奥地利南部时,我意识到国境线那边就是南斯拉夫、枪林弹雨。我在火车站遇到过逃出战区的难民,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很有礼貌地向我讨烟抽。衣衫褴褛,像是几个礼拜没有睡过囫囵觉,瘦得不成人形,眼睛却亮得吓人。我给他一支烟,替他点着,问他从哪里来,他长吸一口,缓缓吐出:“波斯尼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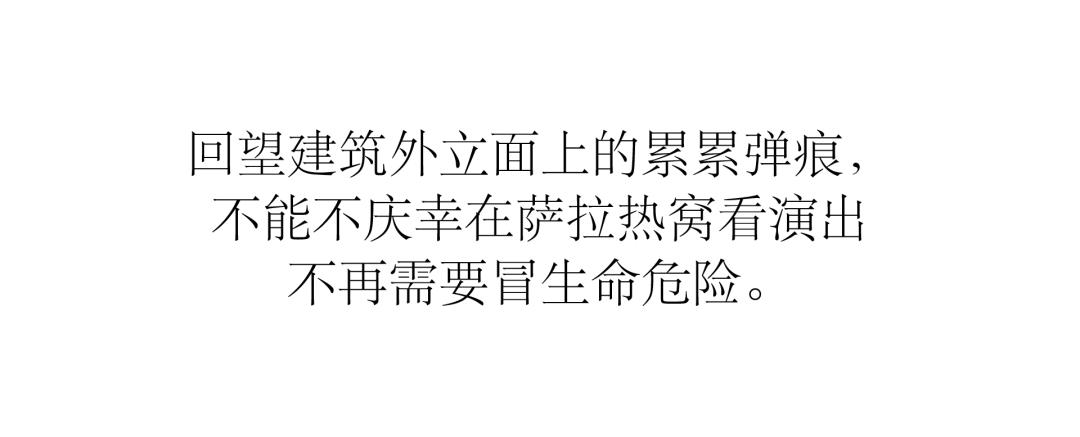
在萨拉热窝的最后两天,我特意从市中心搬到机场附近住,想看看塞族地区是什么样。这等于是给自己加戏,需要徒步穿越一国之内的“国境线”,从波黑人的“穆克联邦”地界直接走进“塞族共和国”。就连公共交通都彰显着族群的隔阂,103路无轨电车终止在分界线附近,不肯延伸到塞族共和国境内。
我看着手机地图找旅馆,旁边一个大妈问我:需要帮忙吗?你是不是在找去黑山和塞尔维亚的汽车站?就在那边。我说不用,我有手机地图。地图显示国境线那边确实有个长途汽车站,塞族共和国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联系比几公里外的萨拉热窝市中心还亲密。
波黑一侧的居民楼,墙面弹孔累累,九十年代初这一带大概埋伏了无数狙击手。分界线上有个椭圆形地带,像no-man’s land,一个黑圆柱体不知何物,被涂了鸦,画一只胖胖的阳具。走进塞族共和国一侧,文字立即从罗马字母变成西里尔字母,一个路口立了两块碑,纪念1997年6月22日死在这里的四个塞族年轻人,三女一男,不知那天发生了什么,三个女孩都不到二十岁。看得出来这个区域在发展中,也许因为离长途汽车站、机场和旅游景点“萨拉热窝隧道”都近,周边有购物中心,还有一些旅馆。我订的旅馆看上去很新,叫Hotel Yu,名字挺奇怪,像中国人的姓——于、俞、余或是虞?到旅馆一看就明白了,旧名“贝尔格莱德酒店”还没有涂掉,重新装修后改名Hotel Yu,那个Yu字显然代表Yugoslavia,像在为南斯拉夫招魂。

原标题:《Sunday Read|弹痕累累的城市,太有文化了》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