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过去的一年里,没有人比旅行从业者更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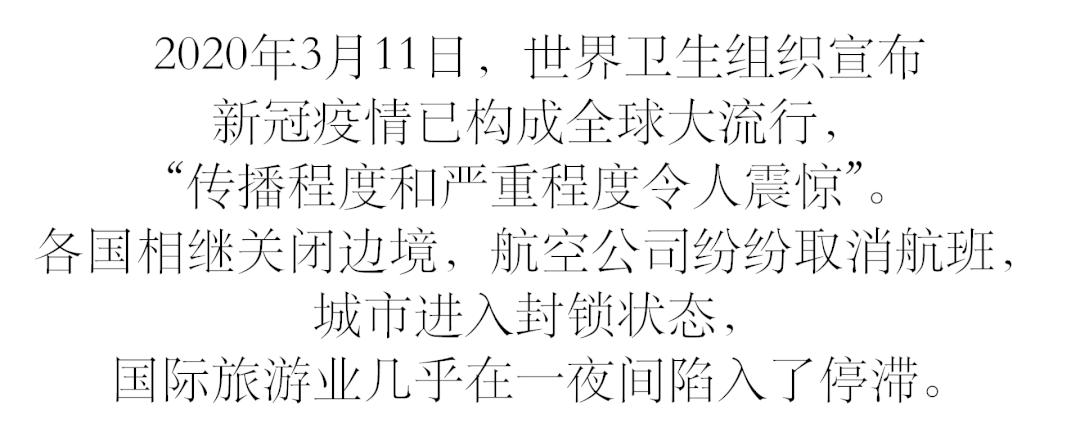
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艰难,疫情给旅游业和所有依赖旅游业为生的人带来了沉重打击。
2020年4月,全美机场国际入境人数同比下降98%,一连数月都保持在同等水平。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等到2020年所有数据出炉后,全球旅游业预计将萎缩80%左右。
在新冠大流行宣布一周年之际,我们考察了世界各地严重依赖旅游业的几个地区,看看它们这一年的境况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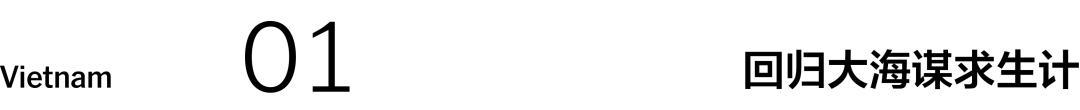
越南会安
Hoi An, Vietnam
采访对象|渔夫熊黎文(Le Van Hung)
在越南中部沿岸,熊黎文(音,Le Van Hung)怀着焦灼与期待的心情,走出了椰子树下饱经风雨的房子。他绕过咯咯叫的鸡群,爬上一条小路,感受着海浪、天空和阳光的气息。
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暴风雨后,海面归于平静,他终于可以划着篮子船到南海捕捞鱼蟹,养活一家人了。

熊黎文划着篮子船捕鱼。
多年来,51岁的熊黎文许一直在大型渔船上从事深海捕捞工作。但在2019年,他放弃捕鱼,开始帮女儿一起经营海滨餐馆。
2017年,随着西方冒险家和亚洲旅游团的到来,熊家决定追赶国际旅游的热潮,在曾经是港口城市的会安古镇开设了这家海滨餐馆。
2020年初,当新冠疫情爆发后,他们失去了游客,也失去了全家大部分收入。祸不单行,到了同年11月,一场季风又把建在沙丘上的阳阳餐馆(音,Yang Yang)卷入了大海。

熊黎文正在检查装载了渔网的篮子船,他通常会到距离岸边几百米的海上捕鱼。去年8月,他花了850万越南盾(约合2400元人民币)买下了这艘渔船,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如今,和会安的许多当地人一样,熊黎文又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领域,靠着风浪谋生。这些人一度放弃了捕鱼,转而从事旅游业,充当服务员、保安、快艇司机,或者自己做生意接待游客。
熊黎文是个小个子,有点儿啤酒肚,背也不太好。他要养活一家七口人,全家都挤在带木百叶窗的泥瓦房里,屋子只有几间,勉强可以维持生计。

日出时分,下海捕鱼前,熊黎文正在篮子船旁吃面。此次出海将耗时两个小时。
自去年9月以来,当地暴风雨肆虐,最近则刮起了大风,海面波涛汹涌。熊黎文担心浴盆大小的篮子船经不起风浪,所以一直没有出海。
2月下旬,熊黎文望着远处的海浪,凌乱的海滩上依旧能看到自家餐馆半截砖砌的卫生间。他告诉自己,也许后天就安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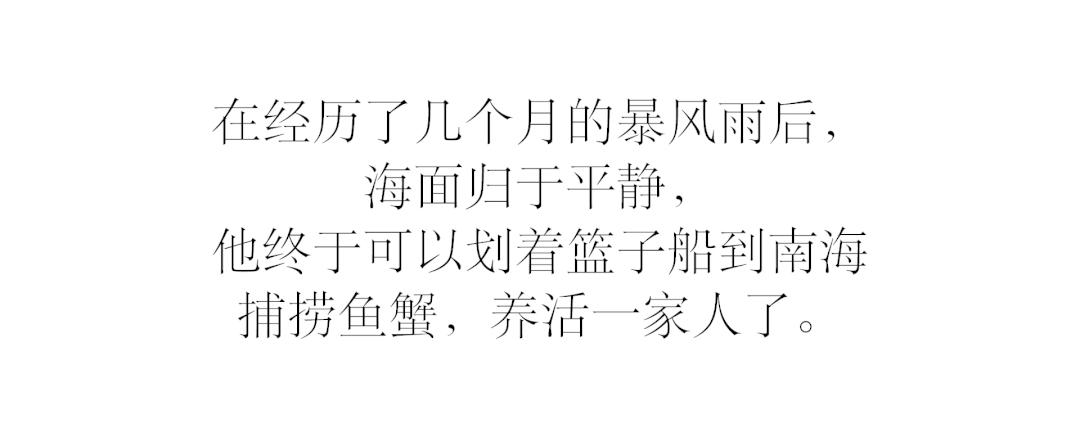
于是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太阳刚刚升起,熊黎文握着一撸船桨站在自己的小船里,乘着近1米高的海浪出海了。
他在离岸边近400米的水面上撒下渔网,然后拖着渔网继续前行,在近2米深的水下铺开了一张近500米的滤网,准备将鱼虾一网打尽。

熊黎文站在自家门前的水泥地上,给渔网栓浮子和铅坠,等待风浪平息。
熊黎文从小在会安长大。几个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一座渔村,一边是碧蓝的大海,另一边则是翠绿的稻田。古色古香的小镇上随处可见门面宽敞的木结构中式店屋,以及法国殖民地时期芥末色的建筑。
在过去15年里,越南开发商和跨国酒店集团在会安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建设海滨度假村,本地人和外地人也在古镇中心和周边地区开设了数百家小旅馆、餐馆和商铺。外国游客蜂拥而至,他们在白天占据了海滩,到了晚上则把老城区挤得满满当当。
2019年,会安接待的535万游客中,有400万来自国外。也正因为过度依赖外国游客,这场疫情对小镇的打击格外严重。

熊黎文正在将自己的篮子船推入海中。这一天,还有几十个渔民独自出海,有的甚至半夜就出发了。
在老城区附近,熊家所在的新盛海滩(Tan Thanh Beach)周围新建了许多旅馆。于是在2017年,一家人向亲戚借钱买了几十把折椅和蒲草伞,在屋后的沙丘上建了一家露天餐馆。
23岁的女儿万洪(Hong Van)会做虾鱿鱼卷等海鲜,两个儿子帮忙烧菜、当服务员,他负责洗碗。2019年夏天,熊黎文彻底离开了深海捕鱼队,因为他觉得投身旅游业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熊黎文的妻子已经去世,他通过翻译说:“我心情比以前好了,在家工作精神很放松,平时工作和家人相处感觉很舒服。”
过去,他在海上捕鱼每月收入3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850元,开餐馆的收入则是捕鱼的5倍。
然而疫情使东南亚地区受到重创,越南在去年4月大部分时间里全境封锁,他们的餐馆已无人光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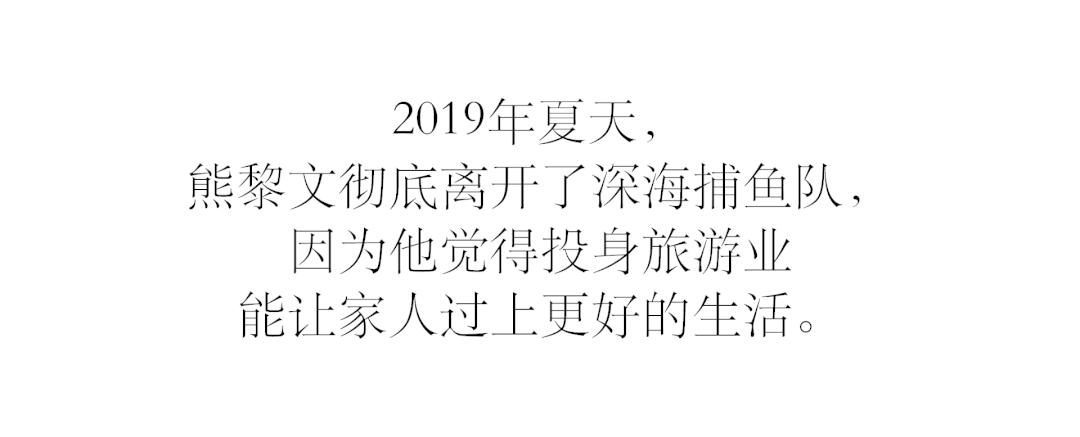
去年7月,就在越南境内游有望复苏之际,会安以北40分钟车程的岘港出现了第二波疫情,整座小镇又停摆了数周之久。
熊黎文几乎用完了所有的积蓄,他知道,自己必须重新出海捕鱼。到了8月,他掌握了在海上用单桨划篮子船的技巧,女儿则在Facebook上卖掉了多余的鱼。但2020年的雨季一直延续到了2021年,出海捕鱼变得越来越危险。

寂静的大海似乎有禅定的力量,但收上来的空网让熊黎感到颇为不安。
此时海面风平浪静,熊黎文穿着塑料罩衫,戴着手套,开始从篮子船上收网,把渔网卷成一堆。他偶尔会从网里挑出一只像冰块一样透明的小水母。20分钟后,他从网眼里挑出了一条十几厘米长的银鱼和一只小螃蟹。又过了15分钟,他发现了一条小鱼。
因为收获实在少得可怜,熊黎文划着船回家了。他告诉自己,把鱼炸着吃会浪费油,烤着吃的话还能省点儿钱。他梦想着有一天可以满载而归。
“只是心里这么想,”熊黎文说,“但海里究竟什么情况,我永远也不知道。”
帕特里克·斯科特(Patrick Scott),《纽约时报》前商业编辑,现居越南胡志明市。关注他的Instagram账号@patrickrobertscott,了解最新动态。

阿拉斯加斯卡圭
Skagway, Alaska
采访对象|镇长贾梅·布里克(Jaime Bricker)、居民阿什利·考尔(Ashley Call)
斯卡圭(Skagway)位于阿拉斯加东南,被冰川、群山、深水峡湾和通加斯国家森林(Tongass National Forest)荒野所环绕。通常在这个时候,当地居民已经要开始为夏季认真做准备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为如果算上5月和9月这两个月的旅游平季,当地人要在5个紧张的月份里赚足一整年的钱。到了夏季,生意好的时候,一天会有1.3万名游客走下游轮,体验这里的淘金时代小镇风情。

旅游业是阿拉斯加斯卡圭唯一的产业,但如今,小镇主干道Broadway Street上空无一人。
尽管一年到头,小镇人口只有1000左右,但在疫情之前,斯卡圭是全球客流量第18大的游轮港口,年旅游收入达1.6亿美元(约合10.5亿元人民币)。
据估计,2020年夏季,斯卡圭的主干道Broadway原本可以迎来130万名游客,这条街上开设了不少历史悠久的沙龙和用旅馆改建的纪念品商店。
斯卡圭是一座完全靠旅游业支撑的小镇,就连镇长安德鲁·克雷马塔(Andrew Cremata)也在码头上兼职推销旅游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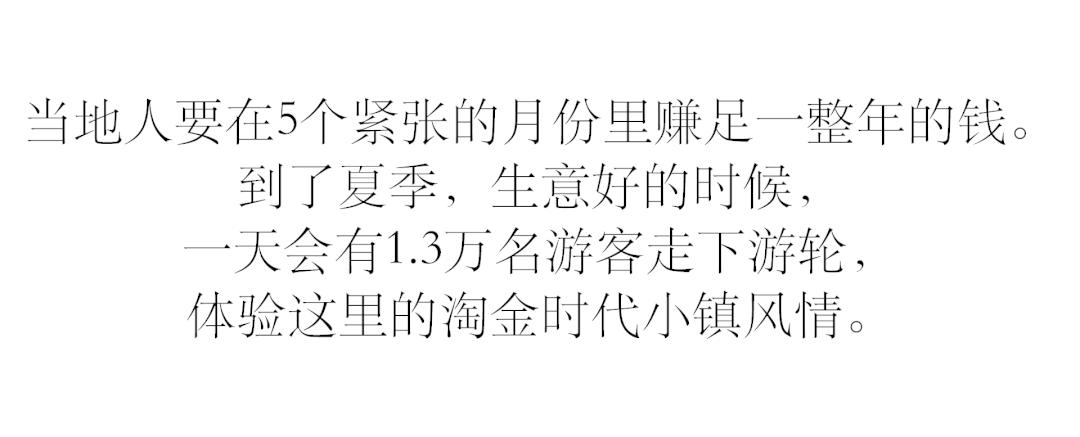
新冠疫情却把繁荣的小镇变成了一座鬼城。2020年,没有一艘游轮在此停靠,2021年的前景也不容乐观。
更糟糕的是,疫情不仅摧毁了小镇经济,也切断了斯卡圭与外界的陆路联系。出镇的唯一通道连接约20英里(约合32公里)外的加拿大边境,但那里已经被封锁了。

一台闲置的吊车停在斯卡圭空旷的游轮主码头。夏季客流量大的时候,这里最多会停靠4艘游轮,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下船涌入小镇的街道。
为了防止大批居民撤离,小镇出台了一套独特的方案。斯卡圭没有像美国其他地区一样,将《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CARES Act)的刺激资金用于市政管理,而是将大部分资金分配给了当地居民。
从2020年6月到12月,每个常住居民无论年龄大小,每月都能领到1000美元补助,条件是他们必须在镇上花掉这笔钱。居民可以用这笔钱还房贷、到镇上的两家杂货店购物、到五金店购买家装用品,或者也可以光顾当地的DVD租赁店。
居民必须提供在镇上消费的收据,才能得到这笔补助。

斯卡圭五金公司是当地的一家商店,居民可以用每人每月1000美元的津贴在店里消费,作为他们留在镇上的奖励。
对克雷马塔镇长和斯卡圭传统委员会(Skagway Traditional Council)主席贾梅·布里克(Jaime Bricker)等小镇官员来说,政策背后的逻辑很简单:他们要让小镇熬过疫情寒冬,直到游客回来为止。
他们还启动了几个项目,包括分发疫苗、检测新冠病毒、为居民支付医疗后送保险,以及扶持镇上的食物赈济处和受到高度评价的学校等。
镇长表示:“1年前,我们的目标是支撑到2021年的旅游季。我们出色完成了任务,再过不久就能熬到2021年旅游季了。”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所以现在,我们得制定一个新的目标。”
他指的是今年2月4日,加拿大政府将禁止游轮驶入其领海的禁令延长到了2022年2月28日,这也意味着斯卡圭2022年夏天的旅游季化为了泡影。

为了让小镇熬过疫情寒冬,斯卡圭传统委员会主席贾梅·布里克等官员想到了向居民分发补助资金,直到游客回来为止。
小镇官员考虑过各种方案,例如他们曾经发起了“挽救斯卡圭”运动,鼓励季节性务工人员回到斯卡圭旅游。克雷马塔镇长说:“现在镇上没有什么人,你可以来这里度过生命中最美好的假期。以往到了夏天,你每周要工作70个小时,现在你能把以前没时间做的事做个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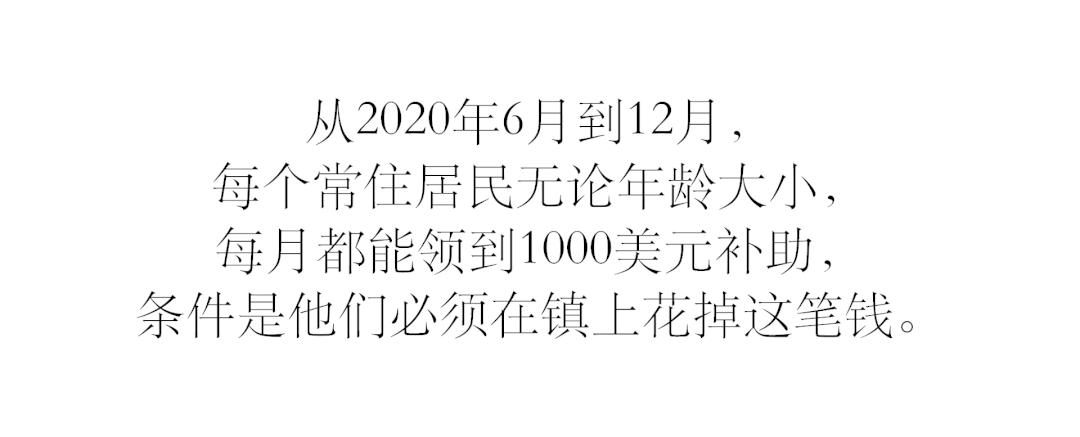
然而,没有人指望这个方案或其他讨论中的方案,能够弥补往年夏季游轮带来的巨大收益。布里克表示:“这里的商店已经习惯了游轮的体量。”

Ocean Raft Alaska公司老板阿什利·考尔的3艘船已经封存了近两年。他原本以为自己会在2020年迎来最繁忙的旅游季。
Ocean Raft Alaska公司老板阿什利·考尔(Ashley Call)就面临着这样的窘境。他说:“对我来说,游客多多益善,而在斯卡圭,大多数做旅游生意的都差不多。只有客流量上去了,我才能重新开工。”他还说,在游轮回来之前,他会一直在建筑工地工作。
为了让小镇撑过2021年,克雷马塔镇长希望政府每项新的经济刺激计划,都能为斯卡圭这样受到重创的小镇提供资金补助。但他认为,抛开怎样再熬过一年的问题,小镇的窘境已经引发了居民对旅游业和斯卡圭未来发展的质疑。
他说:“什么对斯卡圭有利?孩子已经回到了家,你每周却要工作70个小时,这样的生活是健康的吗?还是说,不仅要从经济角度,也要从个人角度来看,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经济会不会让人们的生活更健康?以前很多人都说,他们不会去Broadway逛街,游轮靠岸的时候,他们甚至连邮局也不会去。”
克雷马塔笑道:“在斯卡圭,人们的观点总是截然相反。有人会抱怨不想去Broadway逛街,但也有人喜欢这里的游客。我就很喜欢这里的游客。”
彼得·库亚温斯基(Peter Kujawinski),作家,曾担任美国外交官,与人合著有《Nightfall》、《Edgeland》等5部小说,现居芝加哥。

巴黎
Paris, France
采访对象|名厨阿兰·杜卡斯(Alain Ducasse)、主厨马尔维克·梅迪纳·马托斯(Marvic Medina Matos)
平时,如果想在巴黎享用一顿愉快的经典商务午餐,里昂特色餐厅Aux Lyonnais是人们的首选。
这家小餐馆所在的大楼建于1890年代,距离巴黎证券交易所和《费加罗报》、法新社的办公楼不远。
小餐馆每天都挤满了公司高管、记者、政府官员,他们爱吃传统的里昂菜,在欢笑声中品尝美食。

名厨阿兰·杜卡斯开设在巴黎的里昂特色餐厅Aux Lyonnais转而做起了外卖业务。
如今,Aux Lyonnais鲜红的外墙看起来还是老样子,但餐厅内却很安静。用铁圈箍起的橡木桌子上没有了桌旗、餐具,也没有了球形酒杯。
一部分椅子已经放回了储藏室,锌制吧台擦得锃亮,超大的斜面镜、乳白色的装饰线条、绿色和玫瑰色的花砖也都擦拭得干干净净,等待着巴黎的餐馆可以重新开业的那一刻。

Aux Lyonnais的老板阿兰·杜卡斯(Alain Ducasse)则显得有些失落。
多年来,米其林毫不吝啬地为他的餐厅给予星级评价,富豪与权贵对他在法国和世界各地开设的餐厅趋之若鹜。
在巴黎,杜卡斯名下的餐厅有40%到60%的顾客是游客,其中包括雅典娜广场酒店(Plaza Athénée)以他名字命名的米其林三星餐厅、莫里斯酒店(Le Meurice)内的米其林二星餐厅、塞纳河游船餐厅Ducasse sur Seine、海鲜餐厅Rech、Benoit餐厅、Allard餐厅、Spoon餐厅和Cucina餐厅。

马尔维克·梅迪纳·马托斯(右)正在厨房工作。她为临时改名为Naturaliste的Aux Lyonnais餐馆设计了一份健康的菜单。
新冠疫情颠覆了他的世界,也颠覆了法国美食界。全国各地的餐厅和咖啡馆都关门大吉,复工之日也遥遥无期。和当地许多大厨一样,64岁的杜卡斯也做起了外卖生意(客人可以选择外送服务,也可以到店自取),但他做的可不是普通的外卖。
Aux Lyonnais临时改名为Naturaliste(“自然主义餐厅”),原本用来制备狗鱼可内乐配法式酸奶油小龙虾酱、小牛肝配欧芹和土豆等经典菜品的厨房(可内乐是一道用鱼和肉混合、呈橄榄球形的里昂名菜,译注),变成了他所说的“健康”食品的外卖窗口。新菜品的主要食材是鱼类、大豆、水果、蔬菜,而不含肉、盐、糖或奶制品。
一份开胃菜售价6欧元至9欧元(约合45元至70元人民币),主菜12欧元至14欧元,甜点7欧元。一堵墙边堆放着十几只等待配送的外卖盒(餐馆每天大约要送出100至150份外卖)。
“我喜欢极端,”杜卡斯如是道。

25岁的马尔维克·梅迪纳·马托斯来自秘鲁,她和手下的6名员工通常每天上午9点来到餐厅开始工作。
Naturaliste餐馆25岁的主厨马尔维克·梅迪纳·马托斯(Marvic Medina Matos)来自秘鲁,她与手下的员工一起设计了一份菜单,菜品包括酸橘汁腌鱼配东南瓜、红洋葱和鹰嘴豆泥;甜菜配熏鳗鱼、卷心菜和松子;烤苹果配生姜、栗子糊和焦糖咖啡;以及豆奶巧克力慕斯。他们的目的是设计一份全新的、可以提前制备的菜单。
马托斯和她手下的6名员工通常在上午9点来到餐馆开始工作。Naturaliste餐馆共有11家独立批发供应商,分别负责提供鱼类、谷物、时令水果、蔬菜、鸡蛋等食材,供应商每天或隔天一早就会送货上门。

团队成员穿上白色厨师服,戴上围裙,开始分工合作。一名糕点学徒负责制作开胃菜和酸橘汁腌鱼;另一名年轻的厨师负责准备主菜,用洋葱和胡萝卜烧汤,切叶甜菜,并加入小扁豆;还有一名学徒负责制作甜点,用面粉做酥皮,以及用柠檬和猕猴桃做果酱。
餐点准备得很快。订单一打印出来,马托斯就会大声念出内容,团队成员则齐声回答“好的!”三四分钟后,菜品就制作完毕了。


左图:Naturaliste餐馆的菜单上有酸橘汁腌白鱼、炖鹰嘴豆、南瓜、章鱼、溏心蛋和焦糖果脯。
右图:Naturaliste餐馆精心烹饪的熏鲱鱼蔬菜汤。
每位成员都要负责把菜品装进用甘蔗浆制成的环保盒里。餐具则是用竹子制成的,装在袋子里,上面印有“Naturaliste”的字样。会有一名运营经理将盒子打包,通过巴黎市政府扶持的resto.paris等送餐平台将订单送到客户手中。
就目前而言,外卖生意至少能让杜卡斯手下的员工保住工作,或许还能给餐厅带来一点收益。但在巴黎就餐,关键不仅在于食物本身,同样也在于“社交聚会”,也就是在餐厅一起用餐的经历。
“在法国,6个人一起围在桌边,准备享用一顿丰盛的美食,仪式就开始了,”杜卡斯说。“你们打开一瓶香槟,然后讨论要吃什么。接着开始点菜,食物端上桌后,你们开始点评这几道菜。用餐完毕后,再回顾刚才享用的几道菜。最后,大家一起讨论下周要吃什么。人们希望一边品尝美酒一边社交,看着衣着得体的漂亮女人,而不只是坐在厨房餐桌前看着自己的配偶。”
“天天点外卖的生活不能算生活。”

澳大利亚阿波罗湾
Apollo Bay, Australia
采访对象|中餐馆老板米歇尔·陈(Michelle Chen)、旅行社经理汤姆·黄(Tom Huynh)
新冠疫情爆发前,旅游大巴源源不断地把中国游客接送到阿波罗湾(Apollo Bay),为当地餐厅带来了人气。这座海滨小镇位于澳洲东南维多利亚州150英里(约合243公里)的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沿线,许多行程紧凑的“一日游”旅客往往会选择到镇上观光游览。
游客通常会涌向龙华中餐馆这样的小饭店。这家餐馆面朝大海,入口两侧都有窗户。
高峰时期,这里同时能接待近200名匆忙赶路、但又想品尝家乡菜的顾客。可是现在,到了午餐时间,餐馆里一片黑暗。疫情来袭前刚刚安装在人行道上的大木桌和长椅都已无人问津。

自2020年3月以来,龙华中餐馆大部分时间内都处于歇业状态。在澳大利亚边境关闭之前,这家餐馆主要为中国游客提供服务。
多年前,米歇尔·陈(Michelle Chen)走遍了大洋路,却找不到一家能满足自己“中国胃”的餐馆。于是在2012年,她开办了这家龙华中餐馆。
随着来自中国的“一日游”旅客人数迅速增长,她看到了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餐馆生意也一直不错。但在去年,一切都戛然而止。
2017年,中国反超新西兰,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入境旅游市场。2019年,在以墨尔本为首府的维多利亚州,中国游客一共消费了34亿澳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其后10个海外市场的总和,占所有入境过夜游客消费额的近40%。同年,45%来自中国的过夜游客到访了大洋路沿线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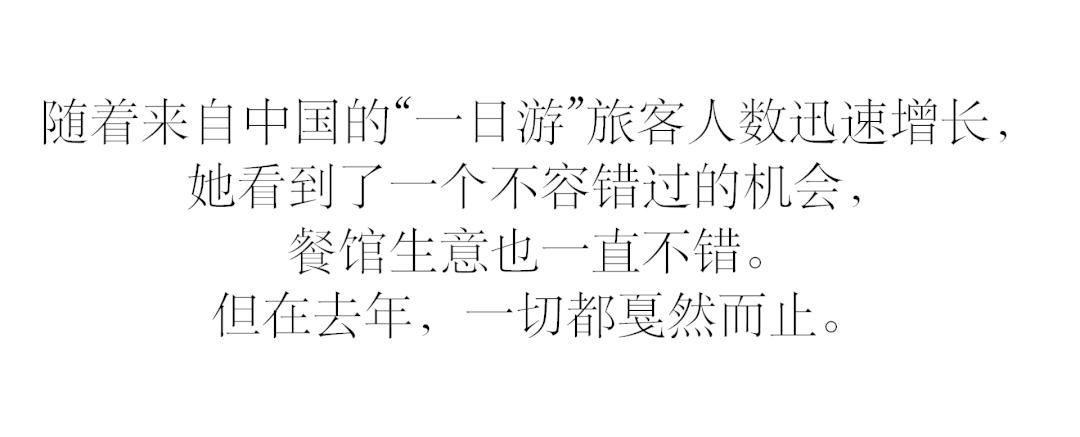
得益于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加上澳洲靠近中国的地理优势,10年来,中国旅客赴澳热情高涨,这也促使维多利亚州的旅游企业和诸如阿波罗湾这样的小型社区顺应潮流,为游客打造个性体验,雇佣会说中文的员工,并把菜单和国家公园内的标识翻译成中文。
但在去年2月1日,澳大利亚禁止了从中国起飞的航班入境,3月又实施了国际旅行禁令,就好像有人一下子切断了旅游从业者的收入来源。
“生意几乎全没了,”米歇尔·陈说。除了圣诞季前后的一小段时间,龙华中餐馆从去年3月开始就一直处于停业状态。

今年2月,澳洲当地游客在平时人头攒动的观景平台上欣赏十二门徒岩。
大洋路的一边是崎岖不平的丛林,另一边则是冲浪圣地。沿着公路继续向前,就是大受欢迎的景点“十二门徒岩”(Twelve Apostles)。这是几座屹立在海中的石灰石群。维多利亚公园(Parks Victoria)商业团队负责人苏·拉德维希(Sue Ladewig)表示,平时这里的游客“摩肩接踵”,特别是在春节这样的旅游旺季,客流量更大,“今年就让我一个人包场了。”
严格的边境关闭措施、封锁禁令和强制隔离政策让澳大利亚有效遏制了新冠疫情,全国2500万人口中,死亡人数为909。不过,澳大利亚或许会一直封锁到2021年末,那些依赖外国游客的企业可能难以为继。
长青旅行社提供普通话服务,来自中国的旅客约占客户总数的一半。旅游旺季期间,他们每周要向大洋路沿线发送16到20辆大巴。长青旅行社总经理汤姆·黄(音,Tom Huynh)表示:“现在哪怕每周能有一个不到10人的‘一日游’旅行团,都算是走运的了。”

墨尔本中央商务区内的一家长青旅行社门店。今年2月,旅行社宣布破产,这家门店也被迫关闭。
汤姆·黄透露,这家于1994年在墨尔本创办的旅行社,已经注销了20来辆一直闲置在车库里的大巴的保险和牌照。今年2月底,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包括他在内的员工都已被解雇。
阿波罗湾面包房(Apollo Bay Bakery)老板娘萨莉·坎农(Sally Cannon)说,旅行禁令生效后,她撤下了店里张贴了多年的招牌扇贝派的中文广告牌。
坎农说:“我们只是觉得,这下完了,这日子还得熬很久吧。”
好在今年2月的一次紧急封锁解除后,游客又开始光顾阿波罗湾(大部分人来自维多利亚州),坎农的生意也有所好转。
扎伊采夫回忆说,他当时“孤注一掷”,想转行做快递员。他拆掉了面包车的后座,用来堆放快递包裹,但收入并不理想。后来,他又试着开展其他业务,比如在去年4月申请了开车接送残障人士的执照,并为此支付了约5000澳元的费用,约合2.5万元人民币。
“猜猜我找到了几份工作?一份也没有,”他说。“我已经尽力了。”

澳大利亚大洋路沿途的十二门徒岩。旅游旺季时,这里的游客“摩肩接踵”。
和澳大利亚许多受疫情影响的生意人或公司员工一样,住在墨尔本的扎伊采夫每两周会从政府那里领取1000澳元的JobKeeper补贴,约合5000元人民币,但这项补助到今年3月底就到期了。
“看样子,我们还没倒下是因为政府给了我们JobKeeper补贴,”扎伊采夫说起像他这样的旅行团业务时表示。“我们都是僵尸企业。”

新加坡樟宜机场
Changi Airport, Singapore
采访对象|高管爱丽丝·廖(Alyss Leow)、机场运营管理主管吴汭刚(Jayson Goh)
一个周四的上午,在新加坡樟宜机场的樟宜贵宾室(Changi Lounge)里,6个人正埋头敲击着笔记本电脑的键盘,他们周围放置了不少豪华座椅。每隔一张椅子上都有一张贴纸,提醒人们“保持安全距离就是保障大家的安全”。
自助茶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服务员送上的羊角面包和咖啡。

今年,新加坡樟宜机场冷冷清清。机场在2019年刚刚启用了一座耗资13亿美元的购物娱乐中心,其中包含一座壮观的室内瀑布。
36岁的爱丽丝·廖(Alyss Leow)是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高管,她花了200美元购买了一张3个月的套票,每隔两三周都会来这间贵宾室办公
"有时候我不想在家办公,这个地方就很合适,”她说。“它能让你的精神得到放松。”
两年前,新加坡樟宜机场的业绩蒸蒸日上。机场刚刚启用了一座耗资13亿美元的购物娱乐中心,其中包含一家影院和一座世界最高的室内瀑布;它已连续7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机场;2019年,这座豪华地标还创下了接待6380万乘客的纪录。
随着疫情在全球不断蔓延,去年樟宜机场的客流量减少了近83%,机场净利润下降36%,降至3.27亿美元左右。机场还中断了第五座航站楼的建设。在2020年1月,共有3.3万架次航班从樟宜机场起飞,而到了今年1月,这一数字下降到了7500架次。

樟宜贵宾室原本用来接待那些飞抵樟宜机场,然后准备搭乘游轮的旅客,现在贵宾室则被改造成了联合办公空间。
为了应对经济放缓,机场决定将重点放在唯一的消费群体——新加坡居民身上。疫情之前,就有许多当地人来机场用餐、购物、学习。为了适应疫情变化,机场推出了豪华露营、迷你卡丁车等项目,并将樟宜贵宾室改造成了联合办公空间。机场还邀请家长带孩子前来参观、过夜。
分析师认为,这些措施大多是权宜之计。在旅游市场恢复之前,机场可以暂时借此渡过难关,但总体收益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善。

航空咨询机构索比航空(Sobie Aviation)常驻新加坡的独立分析师布伦丹·索比(Brendan Sobie)表示:“在市场回暖之前,机场基本处于冬眠状态。对樟宜机场来说,2021年会比2020年更糟。”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樟宜机场完全依赖国际市场,所以会比其他机场更难从疫情中恢复过来。
停运的这段时间,也促使机场重新思考它在后疫情时代中扮演的角色。机场本身一直是旅行目的地,但疫情提供了一个契机,让它开启一项更艰巨的实验:机场能让旅客停留更长的时间吗?

市场回暖之前,新加坡樟宜机场基本处于冬眠状态。
樟宜机场运营管理主管吴汭刚(Jayson Goh)表示,机场高管已经开始思考怎样让渴望旅行的新加坡人“以全新的方式”体验大型购物中心星耀樟宜(Jewel)。
他们推出了“云中豪华露营”项目,正对着著名的室内瀑布,在空旷的广场内搭建了10顶帐篷。但这个活动遭到了许多网友的质疑,尽管帐篷里有大床,但是没有独立卫生间,游客为什么要花上240美元在水泥地上睡一晚呢?
正巧路过帐篷的律师贾森·蔡(Jason Chua)说:“太荒唐了,就好像在围观一群关在笼子里的动物睡觉一样。”
尽管如此,吴汭刚说,为期1个月的露营活动门票在24小时内就销售一空。他认为,这些活动对樟宜机场而言是“一种很好的实验”,以考察那些决定在新加坡东区逗留的外国游客,是否会将这座位于城市东部的机场视为旅游加分项。机场距离樟宜村(Changi Village)很近,樟宜村里有几家度假村和酒店,是周末度假休闲的好去处。
机场贵宾室之一樟宜贵宾室(Changi Lounge)原本用来接待那些飞抵机场、然后准备搭乘游轮的旅客。而现在,机场开始把它作为“安静的工作环境”对外宣传推广。
新加坡国立大学MBA项目主任尼廷·潘加卡(Nitin Pangarkar)表示,虽然机场做了许多努力,但这些措施“并不能完全代替旅客”。他认为:“这只能增加一点增量收入,从长远来看并不会大幅提振业绩。”

疫情爆发前,多姿多彩的樟宜机场令人目不暇接。而如今,航站楼内的自助值机区空无一人。
不少设施专门面向在机场转机、需要逗留数小时的乘客,但在后疫情时代,这些设施难以直接改作他用。吴汭刚说,樟宜机场已经关闭了蝴蝶园和电影院,因为现在游客不想“到处闲逛、消磨时间了”。
周四这天,樟宜机场里只有零星几名乘客准备起飞,有些人穿上了全套防护装备。几个工作人员无聊地玩着手机,等待着永远也等不来的乘客。

美属维尔京群岛圣克罗伊岛
St. Croix, U.S. Virgin Islands
采访对象|马术机构负责人珍妮弗·欧拉(Jennifer Olah)
新冠疫情来袭时,珍妮弗·欧拉(Jennifer Olah)刚刚签下了圣克罗伊岛西端一片两英亩(约合0.8公顷)的牧场,作为她的非营利马术机构在岛上的新家。
“圣克罗伊女牛仔”(Cruzan Cowgirls)马术机构成立于2013年,致力于为岛上的马匹提供救助和康复治疗,让当地年轻人了解这些动物。欧拉招募志愿者来照顾马匹,并依靠外国游客获取收入。游客可以沿着彩虹海滩(Rainbow Beach)骑行,然后穿过雨林,一趟行程约为90分钟。除了小费外,一名游客就能为欧拉带来100美元的收入。而欧拉每周大约可以接待25名游客。

珍妮弗·欧拉是圣克罗伊岛一家非营利马术机构的负责人。疫情之下,她遇到了一连串的烦恼,不仅要担心马料短缺,还要防范小偷行窃。
2020年3月23日,当局颁布了一项“禁足令”,岛上所有非必要企业被迫关闭,游轮也不再停靠当地港口。在一年中本该是最繁忙的旅游季,欧拉的客户渐渐流失殆尽。谈到她的25匹马,她说:“我们在3月份被迫关闭,但马儿还需要有人照顾。我们必须想办法养活自己的家人。”
圣克罗伊岛是美属维尔京群岛的三大岛屿之一,是美国在加勒比海上的领土,主要依靠旅游业与酒店业拉动经济。通常情况下,旅游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0%,但在2020年(不包含12月),美属维尔京群岛的游客数量从2019年的200多万人次下降到了80多万人次,同比减少60%以上。
这意味着岛上失业率翻了一番,偷盗案件频发,许多店铺关门歇业,有的甚至停业10个月之久。“圣克罗伊女牛仔”遇到了一连串的麻烦,不仅要担心马料短缺,还要防范小偷行窃。
欧拉表示:“饲料真的很贵,因为所有饲料都要从岛外运送。”请兽医看病也是如此。由于岛上没有马医,有的马匹生病或需要照料时,欧拉只能请马医从大陆坐飞机过来。如果要为马匹提供良好的医护条件和充足的马料,每匹马每月动辄就需要花费500美元。

这天是工作日,圣克罗伊岛上的一片海滩寂静无人。2020年,美属维尔京群岛的游客数量同比减少了60%以上。
而欧拉的非营利机构没有正式员工,所以没有资格通过美国“薪资保护计划”(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申请贷款。为了渡过难关,她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介绍了自己面临的困境,在网上发起了几次众筹活动。
她说:“我们给过去8年来,每一个在这里骑过马的游客发了短信,请他们捐款或购买礼品券。禁令解除后,他们就可以来马场兑换。”最后,他们筹到了足够的资金,熬过了艰难的3月。
经常光顾的盗贼也让欧拉担忧不已。“几个月前,所有的马料都被偷了。还有一次,我们的发电机不翼而飞。所有的马笼头被偷了两次,还有几个马鞍和鞍垫。有人甚至偷走了几只鸡鸭,上周五,有人偷了3匹马。”(不过后来马匹都找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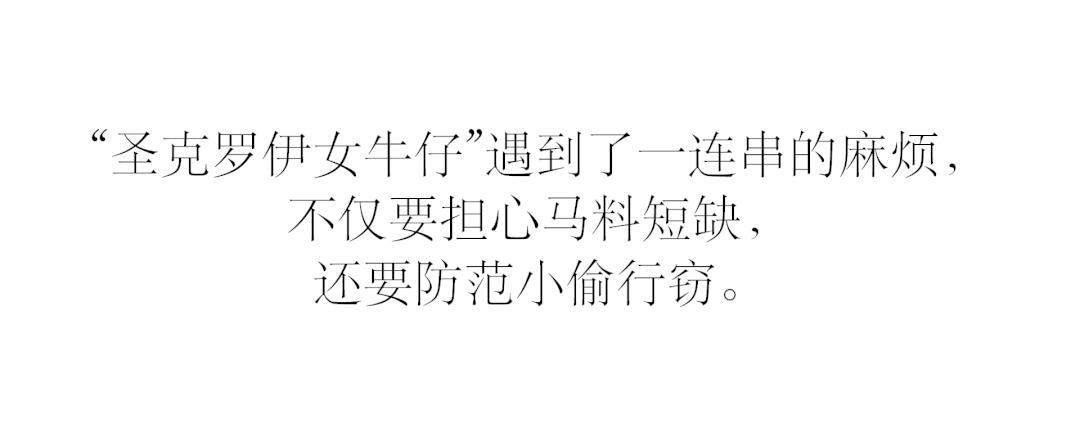
为了省钱,她把喂马的饲料从每周18磅减少到了16磅。她说:“减少10%以后,剩下的饲料就能再多撑一段时间。”
有一阵子她总是失眠,甚至还患上了溃疡。因为压力过大,她一度每周都要去看心理医生。
“我一直在担心,要是挺不过去,这些马儿该怎么办,”欧拉说。“真是太可怕了,我现在还是很害怕,因为不知道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尽管面临种种挑战,欧拉变得更乐观了。她看到旅游业已经有所反弹。小岛重新对外开放,过去几个月里,乘飞机抵达的游客越来越多,岛上一些热门餐厅都需要排队了。

“我一直在担心,要是挺不过去,这些马儿该怎么办,”欧拉说。“真是太可怕了,我现在还是很害怕。”
“我们勉强支撑到了现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她指出,现在又有游客来马场骑马了,只不过人数依旧少于疫情之前。过去马场平均每周接待25名游客,现在则是15名。
欧拉认为:“可能疫苗给了人们一点信心,他们现在可以出门活动了。我们最近接待了很多医务工作者,昨天我还带4个护士骑马走了一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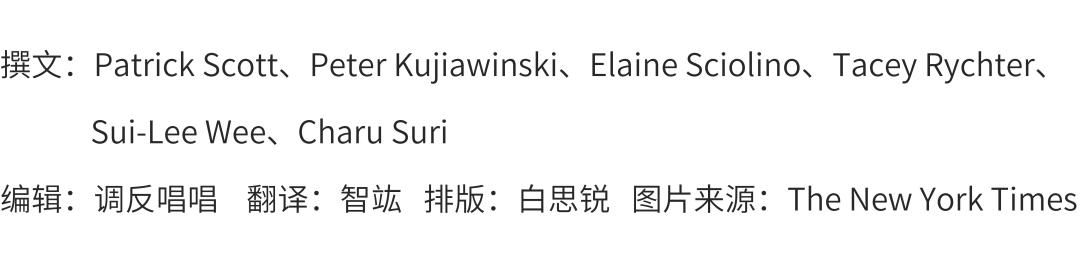
原标题:《在过去的一年里,没有人比旅行从业者更难》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