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为社会而艺术? 社会介入式艺术与人类学的一次圆桌式偶遇
与谈人 / 陆思培(博物馆学学者,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张涵露(策展人,广东时代美术馆)、程新皓(艺术家)、葛宇路(艺术家)
策划+撰稿 / 曾毓坤(人类学者)
社会介入式艺术的定义与反思:地方性知识与全球话语
作为专有名词的社会介入式艺术(socially engaged art)或社会实践艺术(social practice art)发轫自20世纪90年代初当代艺术的“社会转向”。艺术家走出工作室,深入人群和社区,洞察、参与人们的公共空间、日常互动、生活实践和社会意识,乃至以集体创作的方式消解艺术家的身份,以参与和反思的过程代替最终的作品,并生成这一艺术的社区,而非由画廊和美术馆承载、持有和展览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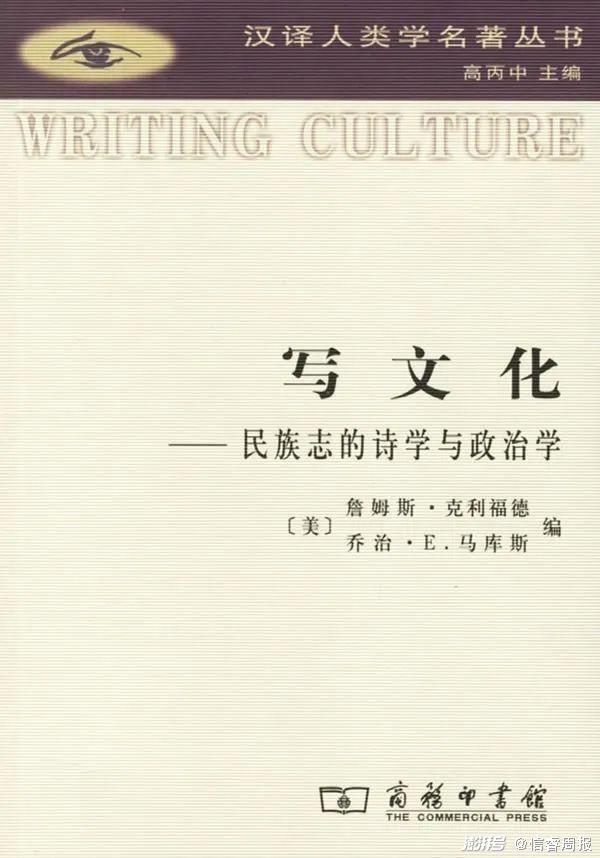
写文化
[美] 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 / 编
商务印书馆 2006
开放的态度和丰富的跨领域性,使得诸多议题、方法和行动都能在社会介入式艺术里找到影子。而在“历史终结”、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的后冷战时代,重塑对公共社会的感知、关注和参与则是社会介入艺术的当代合法性所在。有意思的是,自1986年《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出版后,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人类学明确走出了早期学科想象中的孤岛初民社会,转向当代社会议题,并在“诗意”的呈现形式和“政治”的反思与关怀上日益增进。当代人类学共享了诸多上述议题、方法、行动和论述自身合法性的方式。
但定义什么是社会介入式艺术和定义什么是人类学一样困难,二者也各自伴随着一组家族相似的词汇——社会介入式艺术、社会实践艺术、参与艺术、社区式艺术,人类学、民族志、民族学、社会学。与艺术家和策展人谈论社会介入式艺术的定义,和与人类学家谈论什么是人类学一样,导出的并不是直截了当的定义,而是就某一知识谱系特殊的历史脉络与实践者基于自身立场的反思。
曾毓坤:大家怎么看社会介入式艺术的定义,尤其是其在中国的谱系?
陆思培:创作者需要充分考虑自身的所来所往,创作与语境有关系。“效果”是创作的考虑维度之一,但不是全部,“效果”与“艺术”也不是两极。创作是综合性的过程,往往涉及社会议题、创作者与“对象”的互相融入与表达,重过程而非物质形态的“作品”。其中,艺术发生的方式具体而微,需要个案分析。同时,如果我们真的接受每个人都是实践者、都可进行某种“艺术”的话,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面对自身处境,发明自己的社会介入式艺术。
程新皓:如果回到中国的传统里面,这个问题似乎就没办法来说了,我甚至不愿意用艺术这个概念来讨论。我们可以讨论文人笔墨、丹青这些,但如果要说艺术,其实这里会有一些跳跃。我觉得似乎可以从什么不是社会介入式艺术来说。在我看来,社会介入式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艺术自治性的反叛,社会介入式艺术这个概念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先有相对非社会介入的艺术存在——这种艺术基于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主流。

Artificial Hells
Claire Bishop
Verso Books 2012
当然,如果按照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在《人造地狱》(Artificial Hells:Participatory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中的观点,社会介入式艺术的起点至少是从未来主义和达达主义开始的,其实它也是对一种单纯的现代主义自洽的反叛。按照这条线索梳理下来,其实在每个不同的语境下,社会介入式艺术都会有不同的体现。
对于社会介入式艺术,情景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中的居伊·德波、米歇尔·德·塞托等理论家都讨论过。而在其他知识论域,比如本雅明和阿多诺的论战,也涉及对艺术和政治关系的讨论。艺术是否需要有一个自治域?还是像本雅明所说的,我们其实应该更多地把美学运用于政治,以对抗“政治美学化”的政治?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介入式艺术的体现。
那么在这种语境之下,怎样谈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介入式艺术?如果说官方意识形态已经把艺术定义为某种需要介入社会,并且去影响社会的一种宣传工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的社会介入式艺术一定又会是不同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词语也许不是一个规范实践的概念,而是某种后设的范畴。
张涵露:毕晓普也提到,我们所谓的social turn(社会转向)其实应该是social return(社会回归)。艺术在被封装进与社会区隔的自治域之前,其实是与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我不太喜欢用“社会介入式艺术”这个词的原因,我觉得艺术本来就在社会里面,它需要的是“回到”,而不是“介入”或“睁眼看现实”。
何为“睁眼看”?沿着“为艺术而艺术”这一脉络下来,再加上市场的作用,导致艺术家的生产就是从一个语境真空的地方(工作室)到另一个语境真空的地方(美术馆或画廊),而“睁眼看”就是看到你的语境其实不是真空。
我偏好用“社会实践艺术”一词。如果说艺术在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没有外部性——我们所有人都活在其内部,还要寻找某种不被异化的可能性,那么我觉得在艺术里也只有社会实践,或者说不能被市场化的一种东西是具有这种可能性的。同时,社会实践艺术在西方已经有某种体制化,但在中国好像还没有被体制化,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方面是,我觉得它因此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可能性;坏的方面是,大家对此缺乏讨论,你会发现有关社会实践的讨论隔几年又会回到同样的一两个问题上,没有什么认知进步和理论建树。
语境与体制:突破、反抗与问题化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的《关系美学》因为强调将艺术置于社会关系和在地语境(context)而成为社会介入式艺术的圣典,而注重在地语境自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于20世纪20年代奠定田野调查法以来就已成为人类学方法论的底色。但在地语境既是给当地人的言语和行为赋予意义的土壤,也常常使人类学家的洞察陷入功能主义的桎梏,无法及时抓住在地行动者的创造力和社会的动态[1]。这种方法上的功能主义于70年代被人类学的“实践转向”破解,人类学家追随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和奥特那(Sherry Ortner)的视角,以事件和冲突作为新的民族志单位。

关系美学
[法]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
金城出版社 2013
而更深层次的挑战则是人类学如何面对自身殖民遗产的伦理纠葛。不要说看似中立的纪录式民族志,即便把田野理解为“从他者身上学习”也同样承认了人类学家和受访人之间的距离。而当人类学家从田野撤出,似乎就不可避免地摇身一变、成为在讲台上“贩卖”报道人资料的学者。通过积累报告和论文,学者们也能再次获得田野所需要的资金和时间,重新回到田野,开始下一段“学习”乃至“帮助”——但当回到讲台上又难免成为“收割”。这一循环在放大人类学者和受访人之间的距离之余,更提醒我们其中由学院知识生产体制带来的不平等的斜率。
如果说相比社会介入式艺术,人类学早已发现了社会情境,那么如何面对这一“发现”背后的体制,则是人类学应该向社会介入式艺术好好学习的一课。
葛宇路:能否再具体聊聊,为什么社会介入式艺术在西方会被体制化,但在中国却一直格格不入?
张涵露:有很多因素。一方面,在西方(尤其是欧洲)普遍有公共资金对艺术进行投入,而公共资金投入的要求往往是你的作品要有社会性与公共性。这个时候出现的问题就是,艺术很有可能被工具化。另一方面,当社会实践逐渐进入艺术语汇,也会被逐渐体制化,甚至资本化。美术馆和画廊也会开始注意到它作为新型艺术的价值。我认为,我们的讨论不要脱离中国语境。中国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语境,是一个极度政治化的场域,这对社会实践艺术来说既是挑战也是契机。
曾毓坤:按照毕晓普的梳理,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有官方公共艺术的传统。但这又是体制,当体制僵化成限制时就不再能作为指向公共的情景,而是成了需要去突破的阻力。“85新潮”带动了一批突破这一阻力的艺术,虽然没有明确的社会参与议程,但像“厦门达达”这样的先锋团体明确地批判了美术馆体制,注重实践过程而非成品化的作品。而按照鲁虹在《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1999》中的说法,更加开放的90年代迎来了所谓的“社会学转向”,诸多批判理论,还有一些公共性和政治性的话语进入当代艺术的颜料库,比如政治波普的兴起。但其中的许多作品其实并未很好地消化这些话语背后更复杂、更撕裂的现实,而是很快陷入了西方的市场化语言。如果社会介入式艺术要抓住这种现实,就需要面对多重悖论:一方面有笼罩式的官方公共艺术,另一方面缺乏西方的那种公共资金,此外又有市场化的危险。
陆思培:还是得细分。在西方,我对英国的艺术机制观察比较多。的确,不管是政府资助还是基金会或私人的资助,当这些资助面向美术馆场域里的艺术家或策展人的个人项目时,艺术家和策展人确实会被要求要满足一些特定的功能,或是达到某个具体的目标。但在此基础之上,美术馆、艺术家会和社区去讨论,在国家和资本的框架下,我们怎样才能更有创造性地做社会介入,而不是停留在购买社区服务式的“有这些钱,然后我去做这个事”的阶段。实践者形成了很强的自我反思和纠错机制。
程新皓:关于艺术家和艺术在体制下的能动性,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2]参与、退出和颠覆了2019年的惠特尼双年展。“法证建筑”常年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军警暴力,他们发现惠特尼双年展的主办者——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大股东之一是武器制造商“丛林之地”(Safariland)的创始人沃伦·坎德斯(Warren Kanders)。他的公司生产的催泪弹被美国政府用来驱赶美墨边境的移民、被以色列当局买来袭击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是全球知名产品。于是,“法证建筑”就去追踪坎德斯的公司出品的催泪弹,在各种不同的图像中去寻找催泪弹是怎样被使用的,然后做了一个以催泪弹产品名为名的作品——《三重追击者》(Triple-Chaser)[3]。惠特尼双年展是当代艺术界最重要的体制之一,这一体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邀请艺术家来创作作品,但“法证建筑”在这个体制内用这个作品突破了这一体制,使自己的作品变得格格不入。就像思培刚才说的,体制化之下也存在着能有效反制体制的艺术家和艺术。

采用人工智能辅助手段,“法证建筑”创建了一种算法,以识别“三重追击者”在世界上一些不安定地区的使用。图片来自“法证建筑”官网
葛宇路:社会介入式艺术是行动还是艺术,更像是一种后设的范畴。我觉得具体在里面做作品的艺术家可能并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问题,他只觉得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这样去做,但是最后它具体是艺术还是一次非艺术的行动,取决于观者从哪个角度来看。
刚才程新晧谈到“法证建筑”的作品,让我想到了一种与其相反的,其实是更早存在的形式——这种机构或者说这种规范化的东西,一直在试图把那些反对的声音和行为收编、纳入规范当中。就像现在我们说到的很多身份政治艺术,它本身是作为一种反抗而存在的,但是这种反抗最后会变成它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所在。它需要有这样的反抗以获得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也限制了艺术的反抗,使它最后远离它声称要讨论的问题。
理论、方法与议程:人类学与社会介入式艺术的诸耦合点
人类学在艺术界的逐渐流行有诸多层次,最表面的是人类学理论对艺术批评和策展思路的渗入,如“人类世”一系列概念和相关理论家(罗安清、伊丽莎白·波维内利)的流行,而布鲁诺·拉图尔亲自策展的一系列展览是这类流行的极致。
与之相对的是艺术人类学的发展,从博厄斯对美洲原住民审美和艺术的讨论开始,到阿尔弗雷德·杰尔(Alfred Gell)对艺术品能动性的拓展,“艺术”这一范畴在不断被反思、挑战、情景和实践化。这条发展脉络更紧密地与社会介入式艺术交叉在一起。
当艺术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中被重新发现,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也就在艺术工作中获得了合法性。但在这一基础上,人类学与艺术是否还有别的耦合点?
张涵露:毕晓普也提到了社会实践艺术的两种路径。第一种是伦理至上,比如极端趋向于社会工作的社区艺术。她认为,当社会机构失效或退场时,艺术可以作为补充社会公益的一种方法。第二种其实有点像葛宇路刚才说的,艺术独立于任何价值体系,但并不是回到为艺术而艺术,这种社会实践艺术是通过创造新的语言来将社会矛盾和冲突体现出来。第一种路径对第二种路径的批评是指出后者可能不作为,没有推动什么社会变革,以及不注重伦理。第二种路径对第一种路径的批评则是,前者依旧依附于旧有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框架其实可能已经是比较腐朽的、有问题的社会框架。
毕晓普举的一个例子我也特别喜欢,和难民问题有关,是德国导演克里斯托弗·施林格塞夫(Christoph Schlingensief)2000年的作品《请爱奥地利》(Please Love Austria)。当时奥地利刚选举了反移民的极右翼奥地利自由党上台,施林格塞夫做了这个作品作为回应。他在奥地利市中心放置了几个集装箱,上面写着“外国人滚!”(Foreigners Out!)。集装箱里面是个居住空间,他从奥地利附近的难民营找了几个难民在里面生活。每个星期他都会通过电视直播,邀请维也纳市民投票选出自己最喜欢的难民和最讨厌的难民。

《请爱奥地利》现场,David Baltzer 摄。图片来自克里斯托弗·施林格塞夫个人官网
经过几轮投票,最受人喜欢的难民可以获得现金奖励,甚至可以通过和志愿者结婚拿到公民身份,而票选出来的最令人讨厌的难民则会被驱逐。施林格塞夫本人也住在集装箱里,并一直参与表演,而这些都会被电视直播录下来成为作品的一部分。
毕晓普认为,这件作品更符合第二种社会实践艺术的趋势。这是一个开放的发现过程。施林格塞夫最后发现,政治光谱里有着各种持不同意见的人,有人讨厌这个作品,有人喜欢这个作品。哪怕右翼政党中都有人觉得这个作品好像挺好的,就应该这样做,但也有左翼学生直接冲上去想把集装箱砸了。这些过程都被记录下来,并引发了全世界对欧洲难民危机和政治撕裂问题的讨论。
曾毓坤:这种对发现和揭示的强调也是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和艺术家尼卡·杜布罗夫斯基所承认的双方领域最大的共同点。格雷伯认为,人类学最大的价值是反思且批判地发现不同公共生活的可能性——他尤其强调这种反思不只是自恋地内卷进对自身学科合法性的批判。这有点像刚刚讨论的第一种社会介入式艺术,即便是从内部的艺术合法性突破到外部的伦理合法性,还是有点僵化在合法性内部的讨论中。尼卡认为,突破点在于艺术对个体差异的强调,再由此上升到普遍的人类境遇。这一方面和人类学中博厄斯学派的传统很像,另一方面也很符合施林格塞夫作品的实施过程及其展示的开放性,乃至公共争议。
程新皓:艺术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真正解决公共问题,有时候只是个体的精神胜利。

刘伟伟,“石节子会议日”现场,2017。图片由刘伟伟提供

艺术家程新皓的田野地点——莽人村。图片由程新皓提供
张涵露:我想举一个中国的社会介入式艺术的例子,虽然也是从一种个体的精神胜利出发,但是我觉得它最后朝向的是社会变革。石节子是甘肃的一个贫困山村,这里走出了一位艺术家——靳勒。靳勒一方面扎根当地,鼓励村民进行艺术创作,并带他们出国参加艺术节;另一方面,他也邀请艺术家去石节子做各种所谓的社会介入式项目。有一位叫刘伟伟的艺术家,他去了那里后发现村里只剩下老弱村民,他觉得好像真的什么也做不了,但是这些村民总得活下去,围绕着这个村子的事情还得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所以刘伟伟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从2015年起每年1月3日举行一次村民会议,而且他本人也会到场,以确保村民会议会发生。在村民会议上,大家要讨论村子里发生了什么、缺少什么以及需要做什么。
这些每年在会上被讨论的事是不是真的都会在第二年得以解决,也不一定,因为毕竟艺术家并不是一直都在。但是他在看似很绝望的村子里形成了某种议事决议民主机制,我觉得他是朝向一种开放的可能性的。而且刘伟伟说,这个村子很有可能在哪一天就完全消失了,因为村民真的都是老的、病的。但是他很想看看是这个村子消失得早,还是他刘伟伟死得早,他说他自己活着的每一年都会去确保村民会议发生。
程新皓:我有一个疑问,因为我也曾长期在一个基层村落(做田野),所以我知道开一个大家聚在一起的会和大家真的聚在一起形成一种有效的讨论,二者的差别是非常大的。这种表面上看上去使大家聚在一起、好像在讨论什么事情的会,和它真正讨论了什么事情,最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我会更关心后面的这些东西是否成立。或者说,如果他最后的目的是为了通过会议重新形成某种社区中心、社区决议,我们是否需要打着艺术的旗号去做这件事。由非政府组织(NGO)在那里促成这个过程,我觉得会更有效,但艺术的功能似乎就缺失了。
如果要回答什么是艺术的功能——这可能是一个太私人的回答,但对我来说,一种好的艺术在于它毫无意义,即它不产生任何意义,但是它在那里又不会被任何东西吞掉,它强大到你必须得去看它、承认它在那里。就像我总是在说的纪录片《徒手攀岩》的例子,主角亚历克斯·霍诺德(Alex Honnold)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攀爬大酋长岩。他在不断地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找一种意义,好像是某种超越、某种对自己的挑战。但我觉得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毫无意义,但它又是如此令人震撼。
张涵露:这是很个人化的反应,因为所谓的社会变革最终要落到个体,使个体成为变革的主体。否则的话,历史上类似的灾难太多了。对参与者来说,每年都有一个时间去扮演一个参与民主会议的人的角色,然后他留下了某些回味,这是不是艺术的功能?
曾毓坤:你们说的这种视角差很有意思,很像人类学强调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同样的一次实践对刘伟伟和村民而言是不同的东西,可能都介于艺术和社会进步之间。
而以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作品,其中有好几个人类学与社会介入式艺术的耦合点。有西北山村这样经典的田野情景,里面有社会结构,有文化沉淀,也有特定历史时期下的政治经济学条件——村子因老龄化而凋零。而面对如此的田野,靳勒的项目邀请也要求来访的艺术家有一定的民族志艺术基础,从而能够发现这些社会、文化和问题。
置入情景并运用民族志方法的社会介入式艺术并不少见。这个作品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它还与人类学的议程相耦合——如果我们借用格雷伯的说法,可以把这个议程定为发现并实践另一种政治生活的可能性。
但是,艺术和人类学的分歧往往也在这里。传统的人类学甚少会在田野中做出直接指引调查对象进行民主会议这样的事,人类学家的惯常操作是深描青年劳动力离去、村庄凋零的现状,并真心诚意地相信即使是一群老人也应该有自己潜在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凋零。这种程度的合理化是一种人类学方法上不由自主的功能主义。据格雷伯的观察,这和学院人类学在讲台与田野间反复横跳的知识生产模式有关,二者都不鼓励对社会直接的参与——无论是他者的还是自我的社会。真正面对社会,使“可能性”摆脱话语层面的悬浮,需要的是他所谓的“预演性人类学”(prefigurative anthropology):通过方法和目的的统一,实践可能的生活,暴露出可能的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收获并传播实践的自信与愉悦。[4]
在这个意义上,村民的自信与愉悦非常类似于涵露说的,村民在这个过程中收获的“余味”或者留白,而艺术家的自信与愉悦则有点像新皓提到的快感,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另一面的真实肯定是基层民主决议里的摩擦和不尽如人意,而这种让问题问题化、可感化的过程,正是摆脱方法论功能主义的关键之处。
不过这样说太绝对、太框架,也太前定,不符合艺术家的风格,大家可以再举些例子。



龚豪,《填湖土搭船去欢乐谷》。图片由龚豪提供
葛宇路:一个当代社会介入式艺术的例子是“东湖艺术计划”。组织者之一李巨川一直说,其实艺术并不重要。之所以叫“艺术计划”,是因为媒体的发声渠道、自我组织的可能性都被掐断,而“华侨城侵占东湖湖边公共空间”[5]这件事情却没有办法让更多人知道。
那个时候他对艺术,至少在表述上,没有任何期待了,但他打开了一个开放的结构,这个结构让很多与这项计划的诉求并不是那么相关的“艺术”都进来了。从表面看上去很多艺术作品都不涉及对侵占湖岸线这件事的讨论,但在事实上却从弱者的角度完成了非常有效的抵抗。因为面对的对手非常强大,任何过多涉及事件本身的讨论都容易导致个体的覆灭,所以最后只能让大家去湖边做艺术,亲自去确认正在改变的公共空间这一事实。
比如,有个方案是到湖边折小纸船,然后把船放到湖里漂。这是一个看上去与事件无关的“安全”的艺术表达,但作者作为个体,去现场确认了全部正在发生的事实。于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就有了一个答案。
注 释
[1] 结绳志. 结绳系疫丨错过新冠革命:后见之明与民族志知识[Z/OL]. 2020-08-04;结绳志. 把XX作为XX:方法,地方与有机知识分子[Z/OL]. 2020-10-22.
[2] 对该艺术作品的介绍参见:WEIZMAN E.“法证建筑”:在黑暗认识论的阴影下还原真相[N/OL]. 2019-06-25.
[3] Forensic Architecture. Investigation: Triple-Chaser [EB/OL]. [2021-03-29].
[4] 结绳志. 大学死了吗?人类学与职业管理阶层的兴起[Z/OL]. 2020-10-14.
[5] 姚海鹰. 武汉华侨城东湖开发调查[N]. 时代周报, 2010-03-24[2010-03-29]: B01。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48期)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