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答辩·《走入泰西的旅者》︱晚清外交官的“外交写作”
【编者按】“答辩”是一个围绕历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历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美国斯基德莫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皇甫峥峥与三位年轻学者一同讨论新著《走入泰西的旅者: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本文为第一篇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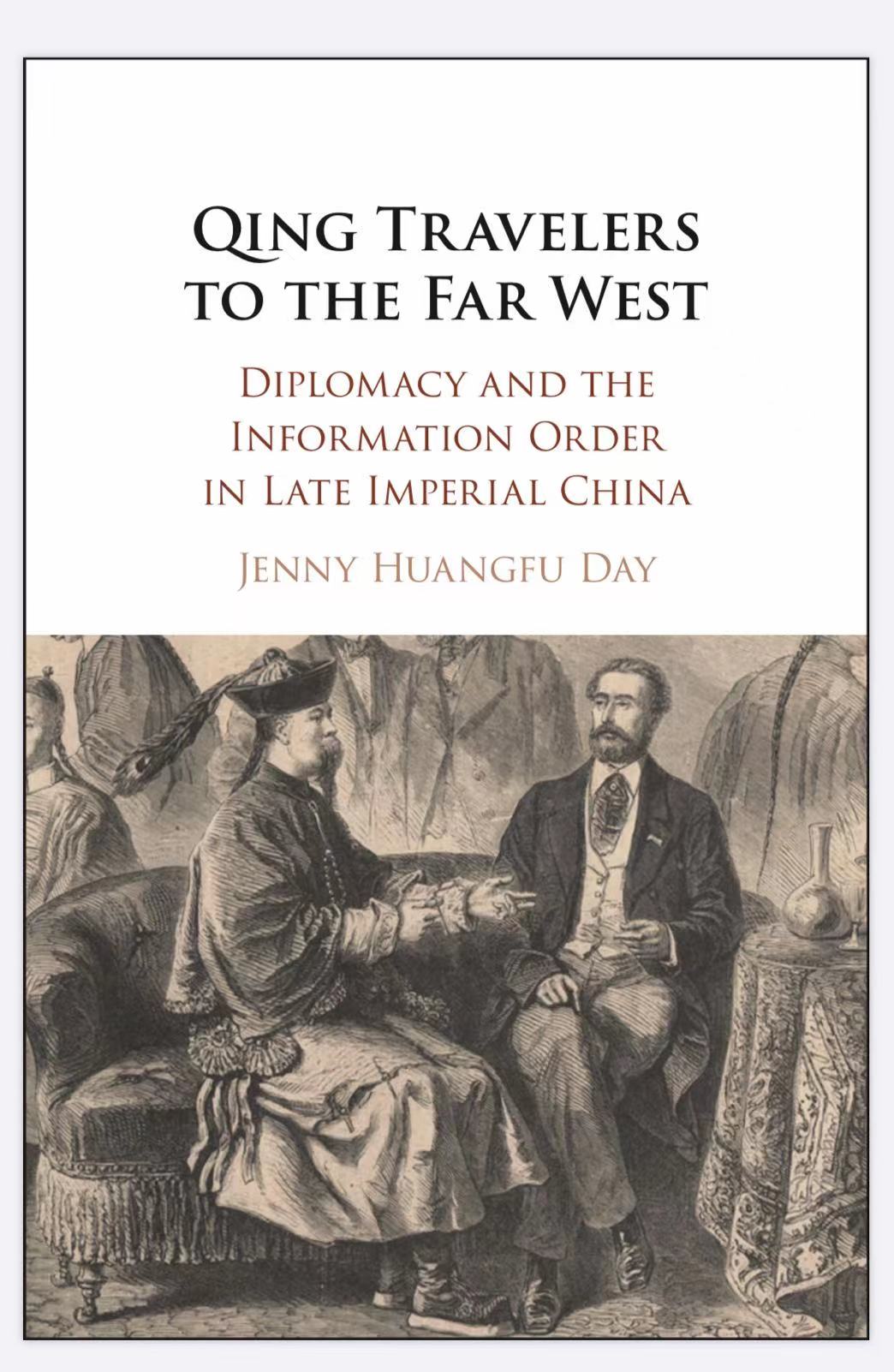
Jenny Huangfu Day, 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中译本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清政府在十九世纪的内忧外患之下,不情愿地进入“国际大家庭”。这国际大家庭并不是一个想当然耳的抽象概念,其成员是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基础的西欧基督教诸国。成员互相派驻公使是进入这一秩序的标志。清政府加入这样的大家庭,也就意味着承认各国平等往来,并且将要放弃朝贡体系,放弃以中国为天朝上国的世界秩序的想象。这对清政府而言是一个艰难的转变。这样的前提下,第一批代表清政府出访的公使团成员,将如何参与这场转变?这批走出中国的清朝官员如何看待西方工业和科技的领先,如何看待西方社会中的道德和秩序,如何理解有别于清廷的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如何向朝廷、向同侪,向士人阶层如何传递他们带回的信息?
皇甫博士的专著尝试跟随1866年至1894年间出访西欧的六位外交官的步伐,透过他们的写作来看这段时间清政府的外交实践和观念转变。他们的外交写作(diplomatic writing,日志、公文、电文等)为当局、同僚和他们作品的读者提供了理解西方世界的一个框架,而他们的表达方式也被自身的受到的教育、训练和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塑造。
正文部分的六章分别介绍了斌椿、志刚、张德彝、郭嵩焘、曾纪泽和薛福成六位外交人员的出访经历及外交写作,各章分别被冠以“旅人”(斌椿)、“大使”(志刚)、“学生”(张德彝)、“学者”(郭嵩焘)、“外交家”(曾纪泽)和“战略家”(薛福成)的标题,不仅体现他们出访时的角色,也反映了公使团/使馆在职能上的变迁。有别于政治史或制度史相对宏大的叙事,皇甫博士从参与者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地还原人物当时的处境,提供了一种更加复杂和细腻的文化史视角。
斌椿是清廷第一位出使欧洲的官员,他是汉军旗出身,通过科举入仕。1866年斌椿接受总理衙门任命,携同文馆学生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回英参观访问时,已有62岁高龄。总理衙门对此次非正式使团明没有明确的使命要求,但仍命斌椿每日记录所见之“山河形状,风俗文化”。斌椿的外交写作主要包括散文笔记和诗文两类,前者在使团返回被后提交给总理衙门,并于1868年先后经家刻及坊刻出版,亦即本章的主要材料之一《乘槎笔记》。他在出使期间及归程创作的大量诗作则被收录在《海国胜游草》和《天外归帆草》两本集子中。由于斌椿是首位出访欧洲的清朝官员,他的日志受到中外多方关注。如何在不冒犯外国读者的同时,不打破朝贡体系中天朝上国的秩序?斌椿的笔记在小心翼翼权衡下达至完美的政治正确,他多着墨於英国的风光、建筑、精巧机械而避谈当地的政治制度及文化。而在他的诗中,使团到访的西欧国家则仍然被视为朝贡国。为何如此?作者认为,斌椿在外交活动中对诗这种文体的采用,是一种中国对待朝贡国的外交实践的延续。作者用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传播仪式观(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来分析,凯瑞认为,传播是信息的传递(communication as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也是社会关系和共同信念的维系(communication as maintenance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shared beliefs, 36页)。通过使用这种在朝贡体系对外交往中常用的文体,斌椿将欧洲君主比作藩属国主,迂回地维系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这样的写作当然无法满足总理衙门收集国外战略信息服务本国的目的。

以斌椿为代表的清朝“外交使团”
第二章的主角是随蒲安臣使团出使欧美的满人官员志刚。作者希望通过他的外交写作来看同僚如何接受志刚带回的信息。1867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任满之后,接受清政府的聘请,代表中国出访欧美。该使团是为即将到来的中英《天津条约》修约之期,向各条约国争取宽容条件的一次游说。相比此前的斌椿使团,蒲安臣使团目的更加明确,使团的外交实践也有了进一步提高。使团在清政府欧美员工的协助下能够进行准确的中英文翻译,也认识到应当为海外华人社群利益发声。
使团此次出使达到了总理衙门的期望,但是并没有遵从避免参与正式活动的命令,而是进行了大量的参观和宫廷社交活动。志刚的私人笔记记载了这些活动,这些笔记并未提交给总理衙门,而是在1877年经过满人武官恒秢之子宜垕编辑整理,坊刻出版为《初使泰西记》。这本笔记揭示出使团更丰富的日程。使团参观美国各类工厂时,志刚对机械和物理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志刚如何看待西方科技和工业的进步?作者指出,志刚深受陆王心学的影响,认为复杂的机械装置应当基于简单易懂的自然法则,他以人类身体类比蒸汽机的运行机制,将冶炼水银的方法追溯至古老的中国道教。作者指出志刚通过设立观念对等物,来将自己的观察赋予意义,将西学通过类比内化为中学,与王阳明心学的认知论相符。志刚对基督教的看法则受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认为基督教无论对中西都是一种祸害。作者认为笔记中记录的与英法传教士的三次辩论,更像是志刚为了表达忠于自己政治职能而进行的文学表演。1890年出版的另一个坊刻版本的《初使泰西纪要》则在1877宜垕編輯的版本之上進行了增刪,尤其是加入了许多欧美宫廷和外交仪式的细节,及志刚不合时宜的个人感情流露。作者认为这些细节紧密与原文相联系,更像是修复了在1877版中被宜垕父子删去的内容。这些内容揭示了使团遵从外国仪式,并且对中国社会种种不满进行批评,新版本也保留了宜垕版中未出现的参观剑桥天文台的经历,挑战着传统中国认为天文现象是对王朝统治者的警示的观念。作者指出,朝廷缺乏系统性的机制,来将公使的见闻转化为外交事务上有益的知识。斌椿和志刚的经历揭示了为何获得有关西方的知识如此困难,因为很多情况下中国的“无知”并不是缺乏信息或者固执地反对了解外国,而是在高度的政治警觉之下,刻意的漠视(“a manufactured indifference exercised with a heightene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第三章的主角张德彝历次随使经历及其笔记呈现出的不仅是外交写作文体和功能的转变,还有公使馆职能和人事任用方面的变迁。他15岁入同文馆学习,但所受的儒学训练相当有限(甚至会把“修齐治平”的顺序搞错)。他不仅是1866年斌椿使团(著有《航海述奇》)和1867年蒲安臣使团的成员(著有《欧美环游记/再述奇》),也是1870年随崇厚使团赴法国为天津教案道歉的使团成员(著有《随使法国记/三述奇》),张德彝第四次出使是1876年随郭嵩焘赴英设立常驻公使馆(著有《随使英俄记/四述奇》),他也是曾纪泽公使馆的随行人员,一生中先后八次随使。他作为同文馆学生期间的外交写作,关注普通人生活的细节(游戏、玩具等),因此呈现出一种迥异于斌椿、志刚或其他同僚的世界主义者的胸襟。这种世界主义精神基于一种对超越文化和政治分歧的人类共性的信任。他早期出使期间对普通人细致的观察和客观的记录,令他意识到所谓“西方”,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整体,中国和西方存在着无数流动着的文化边界。张德彝随崇厚使团赴法道歉时,恰逢普法战争,因此他目睹了战后巴黎街头的满目疮痍,也成了第一个记录巴黎公社的中国人,在他的《随使法国记/三述奇》中,张德彝不顾当时报纸报道及巴黎公社社员自己所采用的语言和意识形态,而用一种天命观的框架,将巴黎公社看作反叛王朝的贫苦农民,对之报以同情。

张德彝
1876年常设公使馆设立之后,逐渐形成一些将外交实践和知识制度化的做法,一方面建立起了从同文馆学生中吸收基层外交人才的机制。张德彝在此前几次使团中积累的经验,令他能够胜任公使馆日常的运作,他的日记也从记录新颖事物,变成了一种外交信息存档,记录所有与公使馆运作和外交事务相关的信息。他的出使笔记《四述奇》在1883年经同文馆和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成为了清廷外交实践实用知识的一部分。但是,外交人员任用的制度缺陷在于,公使馆并不隶属于外交部即总理衙门,而是与之并列,因此公使、领事等高阶外交官来自朝廷指派,缺乏外交知识和历练,对待外交活动态度也非常保守。在保守的儒家官僚眼中,缺乏传统儒学教育,便缺乏一个可靠的框架,来组织、解释和表达外交活动搜集到的信息。
晚清中国的第一个常设驻外公使馆由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主持建立,郭嵩焘是本书讨论的第四位公使。1870年代中期的琉球事件和马嘉理事件令清政府认识到建立驻外公使馆的迫切性,郭嵩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了第一任中国驻外公使。清政府对设立驻外公使缺乏制度性支持,对除了银钱用度有详细限制之外,对公使馆的职能和制度都没有具体规定,公使要自己组织幕僚,成员任用充满了随机性和个人倾向。机构日常运行方面,公使馆的公文往来暴露了缺乏制度协调的弊端。伦敦往来北京的函件单程需要花费约两个月时间,除此之外,由于公使馆不隶属于总理衙门,因此郭嵩焘可以先和英国外交部交涉,再向清廷汇报,而后告知总理衙门,这样的奏报顺序不仅不利于外交,更时常将总理衙门置于尴尬的境地。此外,郭嵩焘缺乏情报安全意识,时常在个人社交中向国外官员透露中国高层政治信息。
郭嵩焘每月上报衙门的第一批日记亦即1877年总理衙门出版的《使西纪程》。在《使西纪程》中,郭嵩焘几乎完全折服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他驻外期间长居伦敦,几乎一面倒地暴露在英国的影响之下,他的日记高度肯定殖民主义的仁德和国际法的公义,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暴力手段(brute instrumentality)。作者指出,郭嵩焘渴求的实际是经历太平天国兵燹之后的中国缺乏的文明和秩序。在他的眼中,英国似乎更加接近儒家的“道”。郭嵩焘不同于张德彝,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家士大夫,在出使英国之前,就已经对清朝的未来感到悲观,认为只有彻底的社会改革才能挽救中国于衰落,回国之后他潜心在湖南推动改革“风俗人心”的礼仪。《使西纪程》的英国中心视角,引起了朝内激烈的批评攻击,及荷兰公使的抗议,书版因此遭到毁禁。而没有载入该书的日记,则透露了更多他对西方政治制度和中国未来的更深刻的思考。他反对独裁和集权统治,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为大众提供了表达意见的渠道,但也忧虑因此带来的社会动荡。郭嵩焘将三代作为文明和制度的理想型,认为秦灭周之后,中国逐渐变得无道,因此逐渐被有道的西方国家超越,面临威胁。郭嵩焘的思想框架受黄宗羲、王夫之等晚明学者的影响,作者指出郭对西方文明的折服,并非抛弃儒学传统,而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框架下对“道”的隐喻的理解。
第五章的主人公是唯一被作者称为外交家的曾纪泽。曾纪泽经李鸿章和郭嵩焘推荐而成为外交官,在1878年被任命为驻英法公使。在他任驻外公使的时代,外交工作变得更加专业高效。一方面,他组织了可靠的公使馆幕府,从同文馆选任经验丰富的外交人才,另一方面,从曾的时代开始,总理衙门和公使出于自我审查和信息安全的考虑,不再以公使日记的形式向清廷汇报日常工作和见闻,而代之以电报消息。虽然1870年上海租界就已经通过电报线路与伦敦相连,但是迟至1884年电线将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与各驻外公使馆相连。曾纪泽在出使之前就与李鸿章交换密电码本,并设计了缩略表达的方法以节约电报费。他也改革了外交公文的呈送流程:先草拟外交文书,再将梗概电传总理衙门,等收到总理衙门电报回复后,便立刻将文书发给所驻国外交部,而文件细节则会以邮件发回北京。为了应付公使馆誊抄大量文书以供公使馆传阅的需要,他在1879年购买了复写机(Eugenio Zuccato’s Papyrograph),为了节省花费,他还亲自试验调制所需的耗材。曾纪泽个人高超的外交能力和对技术的运用推动了驻外使馆的制度化,极大提高了公使馆的工作效率,使得公使馆成为一支解决外交危机的重要力量。在中俄谈判(1880-1881)和中法战争(1884-1885)中,公使馆收集到的信息和据此作出的决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纪泽如何调和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国际秩序上的不同观念?他写给国内官员的信尽量沿用传统观念并在经典和历史中循先例,将中国的处境比作战国时期,自强的终极目的不是加入国际大家庭而是保护王朝的权威。而与英法交流时,他会使用欧洲的观念来解释中国为何不愿放弃传统礼仪和体制。例如他指出公法不外乎“情”“理”,国际法基于刑法,如果两国刑法有别,则会造成观念分歧,朝贡体制符合情理,是将国际法囊括在其中。作者认为这种外交实践类似“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将一种语言中词句的含义从另一种语言的环境中创造出来(meanings of from the guest language were “invented within the local environments of the [host language]”),而使两国的观念“可通约”(commensurable)。此外,凭借高超的语言能力,曾纪泽也成为清朝的对外发言人。他离任前发表在Asiatic Quarterly Review的著名的文章《中国:沉睡与觉醒》,驳斥了当时流行的认为中国行将就木的观点,曾认为中国只是沉睡在过往的荣耀至上,且已经为沉睡付出代价,他预言中国将会和平地站起来(rise),不会对世界造成威胁。并且表达了改善不平等条约和保护海外华侨的愿景。曾纪泽的文章在海外引发了广泛的舆论讨论。曾在西方媒体的发言并不是奉清廷的命令,当时国内官员也很少知道他的文章。作者指出,曾纪泽外交成就的原因,除了卓越的个人能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公使馆地理上的距离,和公使馆与中央政府缺乏整合带来的空间。这使他免于国内的监视。公使馆行政相对独立,善用迅捷的传播工具,这也使他们能够便宜行事。
本书的最后一位主角薛福成和他的幕僚通过出版文集,在报纸、期刊上发表文章,使1890年代外交活动成为联系公众与中央政府与更广大世界的桥梁。薛福成,曾任江苏书局的编辑,宁绍台道台。薛福成在1890至1894年担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但在任满回国的船上不幸染疾暴毙。他文采斐然,有很高的声誉。
薛福成在外交实践上的贡献之一在于将自己外交写作从类型和风格上进行重新组织。他模仿顾炎武《日知录》的风格写作日记,颠覆了出使日记监管和审查的功能,扩大了其政治功能。
薛福成的外交写作反映了他的经世思想和外交谋略。作者指出,1880年代,自强运动的拥护者认同如果西学源自中国,那么主张向西方学习就不成问题。薛福成用一种考据的风格将西学中源进一步发扬,并提升了中国传统中非正统、非儒家学说的地位。例如以战国时期邹衍的大九州说来附会五大洲(欧亚非美澳),《墨子》蕴含物理学,《淮南子》和《吕氏春秋》阐发化学和电学知识,等等。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薛福成将殖民扩张的历史影响看成一种适者生存的自然结果。较高等的种族与较低等的种族接触会自然导致较低种族消失,正如中国曾有狄、戎、羌、蛮等族,如今已不知所踪,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而并无残忍的灭绝。通过将中国和欧洲列强并置,薛完全放弃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评。当西学与传统发生矛盾,他便重新诠释文来调和。他将《左传》中对齐侯的批评“不务德而勤远略”,诠释为“不务德,尽管如此仍勤远略”;他也将君子不言利看作是对孔孟的误读,认为如果是为追求公共的利或者令国家强大的利而引进西方的商业制度,无伤于孔孟之道。出于这些思考,薛福成认为清朝也应效仿欧美,向海外扩张。扩张的办法就是用军事力量来武装领事馆使其成为扩张的前哨,因此谋划向东南亚、澳洲和美洲移民并保护当地华人。他们不仅会带来丰厚的侨汇,一旦王朝有难,海外华侨也将会成为可以指望的对象。
薛福成的经世思想很早就通过出版业问世,他在担任江苏书局编辑和宁绍台道台时就习惯将公牍刊刻出版,他也经常向申报投稿。他的外交写作在1890年代陆续出版,通常先由他的家刻书坊传经楼刻板,再由其他书坊重印,不少文章可以见诸报端。作者指出他的文章启发了一批以古代典籍合理化体制改革的儒家士大夫,为甲午之后的改革家提供了理论框架。
这六位主角逐渐展示了在三十年的跨度中,中国的近代外交实践是如何从无到有,从外交这个窗口接受到的信息又是怎样通过当事人的思维工具和认知框架,通过社会意识形态约束和王朝的审查,被形塑为近代思潮的一部分。这本书并没有具体或宏大的结论,而是展现了细腻、动态、复杂、具体的历史过程。本书副标题的一个关键词是外交,这六位外交官的写作,从经历者的角度展现了晚清的外交是如何从派出公使到建立公使馆,逐渐发挥出近代外交部门的职责,这种改善并不是线性的,因为从人员任用到机构整合,清朝中央政府对公使馆一直缺乏制度支持。偶有成就,和外交官个人的能力和际遇有很大关系。本书副标题另一个关键词是“信息秩序”,一方面指情报传递的顺序,例如曾纪泽奏报外交事务的流程,另一方面,也代表着认知和传达信息的思维框架。徐中约在《中国进入世界大家庭》一书中指出,各国平等交往原则挑战了以中国为天朝上国的朝贡体系,这不仅令异族统治者在汉族臣民面前丧失尊严,也动摇了中国的根本政治和社会制度,即儒家“礼”的观念。因此清朝官员如何向朝廷和同僚描述他们见到的西方文明,不啻于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斌椿政治正确的出使日记,除了是一份合格的思想汇报之外,没有任何信息含量;志刚在见到西方的工厂和机械之时,运用陆王心学的框架,通过设立观念对等物来将西方事物化为中国事物理解;而张德彝是一个反例,尽管能力卓著,外交经验丰富,他始终没有担任高层外交官职位,似乎他的世界主义倾向,正是缺乏儒家训练的体现,是对体制的冒犯。郭嵩焘面对中国相对于西方的落后,用儒家之道的观念来解释,认为三代以后,中国逐渐无道,而西方成了有道的文明国家。曾纪泽虽然坚定维护儒家礼仪,但是在外交实践中却能够采用跨语际实践的办法,将不同文明中的观念变得可以被双方接受。最后,薛福成为了合理化向西方学习的做法,而从中国非儒家的先秦经典中寻找西学中源的证据,他的思想框架在甲午之后更加流行,启发了康有为托古改制的理论。但是,通过外交渠道将有用的西学知识和外交信息整合进现有存信息秩序中的目标,恐怕并不算。这六位是大时代之中知识分子思想变化一个掠影。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出使西欧给他们带来的观念冲击和困惑。作者在处理这六位外交官的个案之时,都对人物的背景、所受的训练以及当时的社会处境有具体的描写,力图将他们的写作放回历史环境中,令读者对其有同情之理解。
此外,作者也对她依赖的材料抱有警惕,通过分析外交写作的编辑、版本、出版与接受情况,本书也涉及到了阅读史的领域,不过,或许是由于史料条件不同,并不是所有外交写作的出版史都得到了详细交代,这使得读者有时要将外交写作当成外交官抽象的思想观念的完整表达,有时又不免思考它是否是当时出版业型塑的产物。当然,作者也意识到文本的作者将他们的文本置于不同的地位,“作为和文人社交的文学表演、作为娱乐大众的畅销产品、作为私人日记的延续,作为呈送总理衙门的报告,作为传播有关国外事物信息的方法”。作者分析六位外交官的外交实践和思想接受史,横跨了外交史、思想史、阅读史等领域,不仅对史料有深入的文本分析,还引入了跨学科理论作为框架,对史料和理论的掌握能力令人钦佩。只有一些小的编辑瑕疵,例如第127页,表头斜体和非斜体应当互换;138页,皇清经世文续编的拼音应该是Huangqing jingshi wen xubian;241页,“海國勝游草”误作“海國胜游草”;当然这些都是无伤大雅的小问题。
柯文在《历史三调》中指出,历史学家与神话制造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话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找出一些个别的特性或模式,当做历史的本质。皇甫博士的这本专著,恰当地呈现了柯文所说的这种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值得对近代外交和思想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