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写字楼里的嘻哈歌手
原创 尹磊 首席人物观 收录于话题#《Z时代商业故事》1个

作者:尹磊
编辑:江岳
2017年以后,所有Rapper都知道,如果上了那个节目,命运就有可能改变。
但说唱的普及,正在把选秀一夜成名的概率不断拉低。对年轻的Rapper来说,选择一份固定的工作,是一个相对聪明的选择。在两条人生轨道并进的未来规划里,职场中的嘻哈歌手,同样向往大厂、期待高薪,并和996的压力尝试和解。
在求职简历里,他们会加上这样一行描述:“我是一个说唱歌手”。
通常,这是一个加分项。他们在公司里正襟危坐、察言观色,然后在周末的舞台上放飞自我。
在都市的昼夜之间,写字楼里的说唱歌手,分饰着两种角色。
01
导演,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Rapper
在一场《中国新说唱》的海选之后,所有来参赛的Rapper在场外等待活动结束,几个导师相继走出来,坐上爱奇艺为他们准备的“保姆车”。最后出来的是吴亦凡,他径直走向自己的法拉利,一脚油门,马达轰鸣声呼啸远去。
有人脱口而出:“一个真正的Rapstar”,现场鸦雀无声,无人反驳。凯桑站在人群里,欲望在一秒钟内迅速变得具体。
嘻哈文化的根源中,有一种迷人的物质化光泽,它具有诱惑力。“不想红”对多数年轻的Rapper来说,是一个谎言;但在说唱事业上All in,则更加荒唐。更多的Rapper,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寻找机会。
凯桑已经是第三次参加《中国新说唱》的选拔,他来自PhoenixGang凤凰社,有稳定的演出渠道,95年的说唱歌手、银川的YoungOG。圈子里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则,2017年《中国有嘻哈》播出那年,是说唱玩家之间的一道分野。早于2017年的Rapper,根红苗正,更配得上YoungOG的称号。

凯桑的制作人咏者,在2019年的节目上被网暴上了热搜,他与福克斯的合作分歧,在爱奇艺的剪辑中被赋予了玄妙的戏剧张力。
凯桑为兄弟解释说:“他被节目组消费了,他本人不是那个样子。”
选秀节目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候,你可能会成为博眼球的牺牲品,对于视频平台来说,“赋予选手人设”是产品包装的一种选择。
平台与歌手维持着一个话语权失衡的关系。
凯桑依然每年报名《中国新说唱》。2020年的导演见面会在西安,他当时还在银川的桥梁设计院工作,为了参加导演见面会,他提前请了一周的假,自费买了往返的机票。
行程临近,设计院突然接到外出勘测的工作,雷打不动的七天到岗,凯桑要迅速做出选择。
和领导对话的开场白冰冷严肃,“你这一去,别人就得把你那份活儿干了,你要知道公司给你钱,你就得给别人干活。”

去西安这件事,对凯桑来说很重要,但对公司,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他的话让你没有办法反驳,你懂吗?”他低下头,点开App,准备取消西安的行程。
领导的态度突然有了松动。新的建议是,找别人协调一下,倒个班。
很多时候,说唱歌手在台上有多能Diss,在公司的领导面前,就有多Peace,一个打工人的桀骜不驯,是有代价的。
如约飞到西安,和前两年报名一样的流程——导演见面会,钻到一个录音棚里、唱自己的作品、讲自己的故事。
导演在现场并不会给出一个明确的反馈。工程师Rapper是凯桑身上的一个亮点,有反差效果,是节目组喜欢的一类。
但漫长的等待后,当节目的预告片都已经释出,凯桑知道他的第三次海选,又以失败告终。
“我自己是被选择的,Get不到他们的选择标准,我不觉得选上的所有人都比我强。”在他所在的银川说唱圈里,去参加节目的有十个人左右,一半去了体育场,两个拿到了链子。没有节目效果的人,在拿链子的60秒,也会被剪辑压缩到惨不忍睹。
创作能力的提升,有时候是在笔头上磨出来的,凯桑需要解决加班的问题。2020年,他离开桥梁设计院,投奔了一家互联网公司,成为了一名数据分析师。
并没有出现传闻中的互联网风气,能支配的时间反倒变充裕了。
2020年凯桑进入了一个创作爆发期,最高产的时候,5天写出4个Demo。新的专辑也开始酝酿,还要配两支MV,这是他目前为止最隆重的一次作品集发布。
其中一支MV已经完成拍摄,取景在银川的岩画公园,没有布景,服装都是自己的。
凯桑在京东上花80块钱买了两个探路蜂,保安巡逻用的那种超强亮度手电筒;还买了一卷透光的塑料彩纸,挡在手电上,能拍出不同颜色的效果。这些是唯一的物料成本。
拍摄当天零下二十多度,是银川最冷的时候。一件短袖外面套一件毛衣,连拍两个晚上,从傍晚拍到凌晨,凯桑他们手舞足蹈,手电筒的强光穿过塑料彩纸,打在他们冻僵的脸上。帮忙拍摄、剪辑的也是同事,给了2000块的辛苦费。
“做音乐这事,完全是用爱发电,不管是拍MV还是录歌、混音、修音,都要花钱,都是工作赚来的。”
在国外的平台上购买一个伴奏的版权,需要500块,而且限制在一万次转发、十万次音频收听以内,超过的另付;录音的棚时费300,混音500,这还是咏者给他的友情价;做单曲封面还要至少300。
一首歌,最起码的成本是1600元。最后把作品发到播放平台上,换来的可能只是十几个评论。
不久前,凯桑刚刚和咏者合作了一首歌,新歌会在咏者的网易云上发布。两人一直是很好的朋友,2019年咏者遭到网暴,凯桑叫上所有朋友,有女朋友的叫上女朋友,让他们给咏者的微博控评,但势单力薄,后来回忆,凯桑说,“咏者和福克斯我都很Respect,但爱奇艺的魔鬼剪辑把咏者给消费了。”
在咏者的评论区里,有个人义愤填膺地评论道:“你们都在说Real,但一个真正Real的人出来的时候,你们却在批评他不Real。”咏者点赞了这条评论。
02
我就服那些80后
“我后来去咏者那录音的时候,我问他还记不记得他转发我的那条评论,他说他忘了。”豆特本来以为两人有惺惺相惜之处,但咏者的回答,让人失落。
咏者被网暴的时候,豆特还是另一个社交圈里的人,后来他第一次见咏者,是凯桑拉着他去录音。那时候豆特的父母逼他考事业编,在银川,进入体制是更舒服的活法,但他没有这个意愿,借口去图书馆学习,背着一书包的“事业单位招聘复习教材”,和凯桑跑到了咏者那。

三室两厅的房子,Muaboss和B·P·E都在里面睡觉,两个人都是有Hitsong(金曲)作品的人,有让人羡慕的粉丝量。传说中的前辈,不枉此行。
意料之中的脏乱,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他本以为这些人都是一副凶神恶煞,比如浑身纹身,满嘴脏话,但等前辈们睡醒,听到他们聊的都是关于“房子在哪买”“怎么找工作”,他觉得这不像一群Rapper会聊的事。
Muaboss跑过来跟凯桑开玩笑,说房间里还睡着派克特(2018新说唱止步六强),豆特脑子还在放空,没反应过来;凯桑信以为真,已经准备去认识一下新朋友。豆特后来说:“真是把我们唬得一愣一愣的。”那天豆特缩在角落里,他本来计划给大家留下一个Hip-hop的印象,但眼前的三个陌生男人,让他最终选择了沉默。
他没有选择银川的事业编,去了北京,远离家人的安排。先找份工作,在一个共青团合作单位做剪辑,要求不高,保证能活下来。
“我本来以为你努力就能适应工作,但在这家公司,我领教了什么叫尔虞我诈。”
一场活动,高强度的加班,豆特三天只睡了五个小时。最后一天结束,和公司里一个前辈吃饭,喝了点酒,价值观迅速拔高,讨论的议题变成了“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深刻的话题,酿成了出乎意料的后果。
“我就记得他说的一句话,他跟我说好人要有大格局,坏人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出卖别人……”前辈的话让豆特肃然起敬,临睡前不忘回味一番。
结果第二天,老前辈和豆特的顶头上司吵了起来,豆特坐在两人旁边,突然老前辈扭过头,盯着他:“豆特在会场上不干活,买了一堆饮料,就为了追公司里的女孩。”
“我人都傻了。”豆特听完脑子嗡的一响,他迅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在公司里的所有记忆。一无所获。
“昨天我们一起聊得那么投缘,他今天就拿我当枪使。我就佩服这些80后,你说他跟我一样都睡了那几个小时,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还有精力玩心机。”
晚上,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好兄弟和自己喜欢的女孩在一起了,而且是早就在一起了。
“我的世界全黑了,你懂我意思吗?”采访中,豆特用手比划着,试图表达那种黑暗的面积。
请了假,他买了次日回银川的机票。回去路上,前面出事故,堵车误了航班,改签到凌晨两点,豆特被霉运包围。
一下飞机,豆特抱住母亲,脑子昏昏沉沉,心里委屈。他第一次在家里抽烟,母亲说:“心情好了就不要抽了。”
在家躺了三天,像治愈一场大病。

晚上9点下班,在北京的7号地铁线上,豆特开始了新歌创作,在家里就酝酿的一个作品。地铁前半程,他安静、专注,维持公共交通上的基本礼仪;后半程,整个车厢的人都走空了,他开始手舞足蹈,车厢里传出“动次打次”的节奏,“7号线坐到后面就没人了,我可以蹦着写。”
写了三天,他把歌发在了网易云上。整个歌曲的制作过程,被做成Vlog,放在了B站。
然而,创作者的伤感是汹涌的,但网民的回应是“骨感”的。
周末下午,在他的合租房里,一个固定的录歌时段。
他轻车熟路地把笔记本电脑、声卡、电容麦挪到两平米的阳台里。电脑放在地上,声卡搁在架子上,然后用麦克风夹紧墙壁的水管,两根连接线卡在阳台和卧室之间的门缝处,中间露出一道细缝。他养的两只猫有时候会去扒那条缝,看里面的人充满好奇。
他一会蹲下来戳电脑,一会站起来凑到麦克风旁边唱几句,他满头大汗,有时候气喘吁吁,在里面已经待了五、六个小时没出来。
猫咪一叫,他就得重录一遍。
03
每天都给领导泡咖啡
和豆特相比,兔子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尽管在采访的最后,两瓶啤酒下肚,豆特和兔子就情投意合地做了决定——合作成立一个新组合,未来的演出计划越说越有眉目,最后聊到了凌晨十二点,各自错过了末班车,才不舍地道别。
这就是兔子所擅长的,他几乎可以和各色人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在采访中,只要你不打断他,他可以一个人说个不停。
从大学毕业,到进入德企,兔子从一个组织各大高校说唱演出的“风云人物”,变成了每天早上给全组人泡咖啡的职场新人。
在北科大,他牵头创办了说唱高校联盟,成员几乎囊括了五道口的所有大学,举办的三次专场,每一张海报的联系人处,留的都是他的微信。
在兔子组织高校联盟的那一年,五道口的高校但凡玩说唱的,多多少少都会知道他这么一号人。
39块钱的门票,办完活动之后,有些学校的团体会找过来抱怨,一次活动下来,自己的学校200块都分不到。
兔子说在活动结束后,他自己几乎就没有收入,“我也不需要有盈利,北京小孩哪有缺钱的,我从上大学到现在,没有体会过缺钱的感受。”他又琢磨了一会,说:“也不是我凡尔赛。我跟他们去谈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也没有谈过因为我辛苦,所以要分到多少钱,从来没谈过。”
2020年12月27日,最后一次专场演出的时候,因为一个流程上的疏漏,导致没有把演出顺序安排好,歌手直接在兔子面前摔了麦克风,然后潇洒地走了。
“面对两三个人的时候,你还能应付一下,面对三四十个人同时问你问题,你怎么办?”活动前的规划没有精确到分钟,就会出乱子。
通过高校联盟,兔子认识了更多人,他在这个圈子里打响了名字,一些酒吧老板也知道了他能做什么。他也学会了怎么在一个活动上独挑大梁。
这些就是他“吃力不讨好”换来的回报。
今年三月,《中国新说唱》在北京的高校海选,全中国的Rapper很多都在,活动结束后,兔子又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主动攒局,把在场的所有Rapper都拉到了五道口的Young Club。
和Rapper以及酒吧老板两头通过气儿,资源互换,全场免单。
那天晚上,他和到场的每一个说唱歌手喝酒,一杯一杯地敬过去,最后断了片。据前台后来描述,喝得迷迷糊糊的,还在到处找垃圾桶,最后问前台要了个垃圾袋,又把垃圾袋套到垃圾桶里,最后才放心吐在了里面。
大家一致认为兔子有很强的环保意识。

在德企工作的两个月里,兔子还没有结束试用期,他的资源目前还没有发挥的空间,办公室里七个组员,无论从资历还是年龄上,都是他的前辈,也都是他的领导,他放低姿态,希望工作能有个Peace的环境。
对他自己身份最好的解释,是在三亚学潜水时,教练跟他说过的一句话:“很多人都想成为一个厉害的人,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成为有趣的人。”
面试这家德国机械类公司时,HR对他简历中最感兴趣的是他的说唱歌手身份,“我在大学就开始玩说唱,这个爱好能让我在人群中凸显出来,说唱这个标签能增加一点个人魅力。”
上班第一天,领导就教了他一个新本事,公司有一套做咖啡的器具,领导让他看自己做一遍。后来,这个活儿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兔子的。花上二十分钟,磨豆子、煮咖啡,每个领导的口味不一样,有多加水的,有加奶的,有加糖的,研发部的七个人,习惯不一,兔子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强调了好几次,说自己不是一个多聪明的人,但在做咖啡这件事上,他的反应力和记忆力发挥超群。
“我也不是特意凑上去做,就是我来了,就顺便做了。其实他们人都很好,买了东西都会一起吃。”兔子也从来不在公司里戴耳机,他觉得领导看到,观感上不好。
和兔子聊得越久,就越觉得他与其他的说唱歌手不同,他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尤其在职场上。
去德国,混进当地的说唱圈,这是兔子理想的未来生活。出国早有计划,只是疫情拖延了时间,“我是向往德国的,甚至包括那边一直被诟病的美食,我也很喜欢,我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练德语,就是想要去德国,去德国就是为了进企业。”
兔子开始苦练Freestyle。
健身为了练肺活量,学两年美声给声音打基础,平时走在街上有意识地听伴奏,学小语种练习咬字……兔子为说唱做了大量的准备,后来他的风格明确为快嘴,技术流。
每一个八拍里,他的歌词密度都要比别的歌手多得多。在他的网易云音乐上,播放量TOP1的是和北科大社团的说唱接力《北科2021 CYPHER》,排在第二的是《为中华之崛起》,白银单曲里还有一首《朱红画卷》,后面两首主旋律的歌,搁在说唱圈子里,得到的第一反应会对作者的动机产生怀疑,而最恶毒的揣测,莫过于,它有“迎合”的嫌疑。
3月的时候,兔子履行了先前饭桌上与豆特的承诺,他在中关村给他们即将成立的组合安排了一个办公室,免费的,他们想了两个很酷的新组合名称,现在陷入了二选一的困扰。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在2021年,开始计划新的时间表,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兔子随时会去德国,豆特正急于沉淀,他读完了《人间失格》,内心苦涩。
04
兄弟,牛
去了天津之后,唐克的说唱之路就被“冷冻”了,他找不到一起玩说唱的朋友,也找不到多少说唱演出,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相声表演,他也从来没去看过。
整个城市给他一种慵懒的氛围,出生在新疆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唐克,从中国的最西边,一个人跑到北京读书,然后就业,从一家明星培训机构离职后,去年把简历投到了天津,依然是教育行业。
在北京的时候,唐克的口头禅是:“骚呀,兄弟”,和刚认识的人说这句话,他会解释一番,他老家那边这话是个褒义词,代表“牛”。
现在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家长群里,他的这句口头禅都是禁语。
每堂课,他负责给主讲老师开场,开场白通常是:“我是你们的唐克老师,今天咱们新一周的课程就要开始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咱们要进入我们的上课状态,唐克老师今天要表扬一下我们作业做得特别好的小朋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表扬榜。”
对于了解唐克说唱歌手身份的人来说,他在课堂上的语调像是一种陌生的人格。他教授的学生主要是9~10岁的孩子,其话术中不断出现的“我们”,是一种亲和的姿态,他在用语言传递一种“像蹲在你身边的一个慈祥的老师”的体验,在民营教育机构,教育不光是一种义务,更多是一种服务。

课堂上每一个家长都有唐克的微信,助教老师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给主讲老师分担课堂以外的工作量和压力。刚上岗的时候,领导让唐克看到家长咨询要第一时间回复,反响速度会计入考核,现在时间久了,回复的监督稍有松动。但唐克的时间还是会被无穷无尽的咨询撕碎。
“我的精力很难从工作上抽离出来,再加上我自己又懒,在这里不到一年,总是感觉提不起劲儿,像是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仅仅是在这里打工。”
大半年的时间里,没有一次商演,所有的表演都是在公司。
“在公司的演出真的演得很傻,他那个设备很垃圾,唱完一首就不想再多唱一句。”演出后,同事们会热情地包围过来,对着唐克说:“哇,你真牛。”
后来公司只要有才艺表演,大家就会想起唐克。

一个数学专业的老师跑过来找唐克,说他们那也有一个Rapper,公司突发奇想,说让两人搞个配合,给公司写首歌,最好能拍个MV。
“毕竟人家都找到我了,我也不好拒绝。我一边受公司压榨,我还得写歌赞美它。”唐克花了半小时就“交了卷”,他总共写了八、九句歌词,“当时我就想,我们是英语学科的,那我就突出一下我们学科的特点吧。”
他套了小青龙一首歌的伴奏,OldSchool的风格,更亲民一些。
“后来那个MV就在我们公司大门口的楼梯间,上头有一个大屏幕,在那上面无限循环,播了一天。但是我没去看,各种教委和组长开会的时候都看到了,然后他们就在群里喊,夸我厉害。”他觉得同事和领导称赞他是应该的,“我花自己的时间给公司写歌 ,他们要是不称赞我,我心里也过不去啊。”
唐克说自己是一个性格反叛的人,有话是不会憋着的,从小学开始,因为一个“良好”的环境,他自小就形成了这个性格,“小学的时候,我妈是学校的数学老师,我哥在学校也能罩着我,我在小学没人敢惹我”。
“但初中就不行了,我初中在石河子上的,我在那边没靠山。”
直到高中毕业,唐克在新疆的石河子待了六年,他最早听到的嘻哈音乐是从吉尔吉斯斯坦传过来的外国说唱,但那里的语言和他的民族语言是相通的。
“那时候我听了那个国家的好多嘻哈音乐,后来听国内的说唱,第一个听的是喀什的,那里距离我住的地方大概两小时的路程,艾热就是那的人。当时我就听艾热他们的歌,就发现喀什说唱太牛X了,然后我就疯狂地循环听。”
高二的时候,唐克和他的同学们决定自己也试试说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声卡,一个电容麦。
“我们学校是半封闭管理,只有周末才能出校门,那时候我们连网购都不会,就在校门口找了一个电脑店,让他帮我们下单,帮我们收货。”几经辗转,唐克他们在一个大冬天的夜里把设备带进了宿舍。
这群高中的孩子创作的第一首歌叫For My Life,歌曲发布在了一个翻唱平台,最后在克州意外地火了,他们不是当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唐克他们的歌是第一个在那里火起来的,克州的一些孩子,有时候会哼他们的这首说唱。
“我们出完这首歌以后贼开心,感觉就是牛X坏了。”
唐克的说唱生涯就此展开,在大学联合组建了自己的说唱社团,后来又在北京的DDC和School酒吧演出。直到2020年的五四青年节那天,他以一个助教老师的身份,加入一家在线教育机构。在求职简历上,唐克习惯在里头加上一句话,“我是一个说唱歌手”。
通常,这是一个加分项。他在课堂上给小宝贝们耐心地授课,察言观色,不冷落任何一个孩子,在任何一个晚上,他的微信都能跳出一个学生家长的咨询,他知道他最好能第一时间反馈对方。
在北京的时候,昼夜交替,他是写字楼里的说唱歌手,而现在,说唱歌手的身份,只有当他在公司的文艺汇演上,才能被大家想起来。
2016年唐克第一次见到黄旭,那时候还没有《中国有嘻哈》,黄旭在圈子里已经非常有名,唐克特别激动,按他的话,就是疯狂地上去套近乎。
他当时自我介绍说,“我真喜欢你,我也是新疆来的,我也是一个Rapper。”
黄旭说:“兄弟,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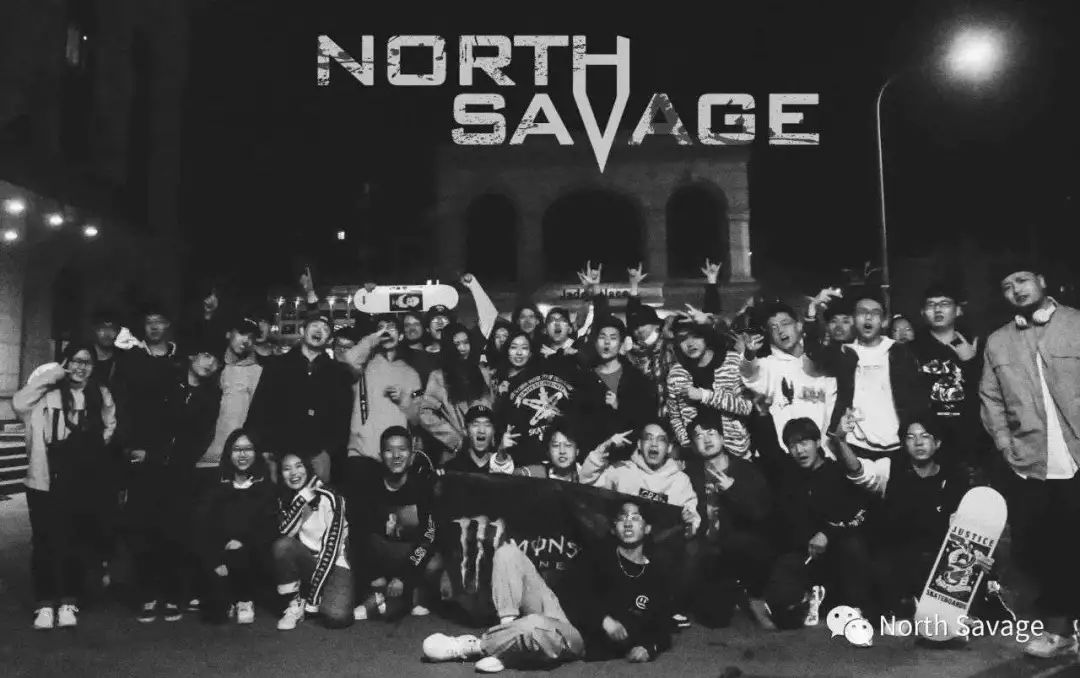
2017年的《中国有嘻哈》上,8强赛,唐克拿着黄旭给他的入场券,还有一条印着黄旭名字和头像的大围巾。
那场比赛上,唐克举着这块围巾,抬着脖子,眼前是吴亦凡、狗哥、岳哥、潘玮柏,以及日后走向中国嘻哈顶流的GAI。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原标题:《写字楼里的嘻哈歌手》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