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读︱谁与谁的对抗?——1812年战争中的族群撕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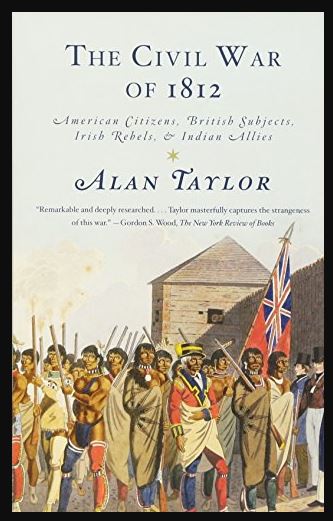
The Civil War of 1812: American Citizens, British Subjects, Irish Rebels, Indian Allies
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冲破警戒线,闯入国会山,迫使正在开会的参众两院休会,议员四下避难。事发之后,不少媒体指出,这是1814年英军纵火焚烧国会后,该建筑第一次被攻占。在此情况下,1812年战争这场近乎被美国人遗忘的冲突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笔者2014年8月刚到美国时,恰逢火焚华盛顿事件200周年纪念日,各大媒体都有所报道。次年游览国会时,观看的介绍影片也提及此事。在主流叙事中,这场战争成功挫败了英国重新控制美国的企图,战后重建的国会与战火中诞生的《星条旗之歌》预示着美国的光辉前景。然而,2017年笔者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堡却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故事。在加拿大人眼中,1812年战争异常重要:由欧洲人、独立战争时期的效忠派及原住民组成的军队抵挡住了美国的入侵,捍卫了加拿大的独立,成为加拿大的立国之始。火焚华盛顿固然不幸,但这不过是对美军焚毁约克的报复而已。
以上从民族国家视角出发的叙事都创造出一组“自我”与“他者”,用以解释1812年战争及它对国家构建的意义,这在强调跨国史的当代学界已显得不合时宜。随着公民权(citizenship)研究的深化,一些学者指出,英国和美国对公民权与臣民的不同理解是导致1812年战争的重要原因,这在英国强征美国水手入伍一事上尤其明显。此外,西部史学者很早便注意到印第安部落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再者,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关于1812年战争的不同态度更是广为人知。在上述研究基础上,阿兰·泰勒又将独立战争时期的效忠派与爱尔兰移民纳入考察,进而认定1812年战争可被称为一场具有四个维度的“内战”(civil war)——效忠派对抗美国人、联邦党人对抗民主共和党人、不同印第安部落拔刀相向、爱尔兰移民对阵英军中的爱尔兰人。
泰勒对1812年战争性质的界定可谓别具一格。在美国史语境下,“内战”一词通常指1861至1865年间南北双方围绕奴隶制问题展开的冲突。不少学者固然注意到独立战争期间爱国者与效忠派之间的对立,但还是不愿将其称为内战。针对印第安部落间冲突以及美国国内党争的研究也是如此。而独立战争后国界已定,爱国者与效忠派分居两侧,更不存在内战一说。但通过使用内战一词,泰勒想强调的是当时历史情境下边界两侧人员的往来以及公民身份的流动性与可变性,这种情况直到1812年战争结束后才渐趋消失。
本书以新任上加拿大总督约翰·格里菲斯·西姆科的赴任旅程开篇,引出独立战争结束后的形势:西姆科在独立战争期间便曾与效忠派并肩作战,战后约三万八千名效忠派定居加拿大,英帝国为他们提供土地、物资援助和低税收等种种优惠条件,既是回报他们的忠诚,更是显示英帝国相对于美国的优越性,以期吸引更多的美国移民。果不其然,1780年代后期至1812年战争前又有数万人前来,主要以中大西洋州的贫穷农民和宗教少数派团体为主。与此同时,英帝国还不时插手美国事务,暗中支持谢斯起义及佛蒙特和肯塔基这两个边疆州的分离运动。再者,意识到先前抛弃盟友的错误的英帝国也注意修复与易洛魁印第安部落的同盟,并推动印第安部落的整合,以遏制美国的向西扩张和可能的北犯,但这些成果随着1794年《杰伊条约》中对美国的让步付诸东流,西姆科决心去职,以免去需将边境堡垒交付美国的耻辱。
此外,英帝国还在帝国范围内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以防止其它殖民地效仿美国要求独立,这其中便包括加拿大和爱尔兰。然而,英帝国官员关于改革方向问题有所分歧,一方呼吁加强控制,另一方则主张扩展权利。在加拿大,新宪法所设置的立法机构与原北美十三殖民地相比更具贵族色彩。殖民地政府强调英国国教相比于福音派在婚姻仪式等方面的独尊地位,注意审查移民的政治倾向,防范美国共和思想的渗透和美国的颠覆活动,对集会和办报多加限制,并警惕法国煽动加拿大法语区居民叛乱,尽管后者更愿意留在英帝国内以防御新教徒占多数的美国。但与此同时,西姆科也下令废除奴隶制。
在爱尔兰,占人口多数的天主教徒并未享受完全的政治权利,美国和法国革命的双重影响及随之而来的爱尔兰独立要求更是使英国忧心不已。1798年3月,英国逮捕了大部分爱尔兰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该举动触发了小规模的起义,进而引来英国更严酷的镇压,至少2万人遇害,另有3千人被流放至普鲁士或西印度群岛做苦役。这导致越来越多爱尔兰人选择移民美国,以改善自身的政治与经济状况。在美国,他们更认同民主共和党人的理念,这遭致联邦党人对他们的蔑视与排斥。联邦党人动用手中权力延长移民归化申请者的最低居住年限,并驱逐具有危险政治思想者,这其中便包括费城民主共和党报纸《曙光报》的编辑、爱尔兰移民威廉·杜安。但这一切都为1800年选举后掌权的民主共和党所推翻,1801年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成立后汹涌而来的爱尔兰移民迅速确立了民主共和党在美国的统治地位。而在国境另一侧的加拿大,占据重要政府机构职位的苏格兰移民也借此排挤爱尔兰裔官员,指控他们与美国来往密切。
介绍完英帝国的形势后,泰勒转而讲述英美两国围绕着逃兵问题的纠纷,这在1807年的“切萨皮克”号事件中尤为明显。该舰在弗吉尼亚州外海被皇家海军军舰袭击并截停,上面有四名海员被认定属于皇家海军逃兵,其中一人被吊死。英国如此行事的根据是英属民身份贯彻终生,移民并不能改变该身份。美国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在共和国体制下,人能通过归化选择公民身份。不少民主共和党人还将被强征和鞭打的水手比作奴隶,抑或是遭受印第安人毁容的白人。而在公民理念分歧外,关于水手的纠纷还与当时拿破仑战争背景下海军对人手的需求及美国商船队的竞争联系在一起。此外,两国陆军的逃兵及他们的追捕者也不时越过美加边境。
这一系列纠纷导致英国与美国在1807年便已走到战争边缘,只是因为英国担心加拿大防务薄弱,又不想从拿破仑战争中分心,美国不愿因战争扩展联邦政府权力而作罢。但由于英国继续截停搜查美国船只,美国国会通过《禁运法》,停止与外国进行商贸往来作为回应,试图迫使依赖美国物资的英国让步。然而,英国不但轻易找到替代性的物资来源,还乐于消除来自美国商船的竞争,加拿大农林业也趁机抢占出口市场。与此同时,美加边境的走私者活跃起来,拥有武装的他们甚至敢于和缉私的民兵组织交火,联邦党人也借机在主要以外贸为生的美国东北部地区重获新生。在此情况下,英国自然不会做出让步,美国国会被迫于1809年3月废除该法案。
但战争还是在1812年来临了,而印第安人和爱尔兰裔扮演了一定角色。1807年后,面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尤其是美国对加拿大的入侵,英国开始重新修好与印第安部落的同盟关系,增加对他们的物资输送。对印第安部落的恐惧成为美国社会同仇敌忾的基础,新当选的国会众议院议长、来自边疆州肯塔基的亨利·克莱便积极主战。为了进一步为战争制造氛围,麦迪逊总统于1812年3月向国会展示英国通过一名爱尔兰移民拉拢联邦党人、进而实现新英格兰地区分离的证据。3个月后,美国正式向英国宣战,每一位联邦党国会议员都投票反对开战,而81%的民主共和党国会议员赞成。
凭借着压倒性的人口优势和对加拿大人立场的判断,美国决心迅速占领加拿大。爱尔兰移民参战情绪尤其高涨,他们看到了为英国在爱尔兰所做所为报仇的机会,以及通过占领加拿大推动包括爱尔兰在内的英帝国解体的可能。美国还认定加拿大的美国和爱尔兰移民将欢迎美国军队的到来。对于那些在英国治下过得不如意、无法实现政治或经济上抱负的人来说,美国的入侵确实提供了新的可能,加拿大法语区居民反对征兵的活动以及部分加拿大人的南逃也给了美国人以错觉。
然而,占加拿大人口大多数的是效忠派及对政治不甚感兴趣的移民,前者对美国充满仇恨,后者则对战事漠不关心。英军的强征补给及人手固然使一部分人心怀不满,进而与入侵的美军合作,但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美军失利及英军的打击促使他们重新选择自己的立场。英军刻意安排的战俘游街示众更坚定了他们的观点。效忠派则成了加拿大地区呼吁抵抗美国入侵的中坚力量,他们将美军士兵描绘成社会渣滓,并称美国将没收私人财产进行重新拍卖与分配。甚至部分爱尔兰移民都加入到英军队伍中,他们的绿色制服尤为显现,英军中出现爱尔兰移民令美军大感意外。爱尔兰人甚至利用美军的这种思维定式伪装成逃兵,出奇不意地袭击美军。
此外,作为加拿大防务的另一条支柱,许多印第安部落也站在英国一边。依靠着他们制造的声势,英国军队在开战之初便不伤一人地攻占了位于密歇根湖与休伦湖交界处的堡垒,打通了印第安部落与加拿大联系与贸易往来的通道。该情况更坚定了印第安部落的站队选择,这在密歇根领地长官威廉·赫尔以保护部落土地完整的承诺诱惑他们保持中立的背景下尤为重要。受此消息影响,赫尔匆匆从加拿大撤军,并在随后面临包括印第安战士和美国移民在内的英军进攻时献出底特律堡投降。此后,仰仗着印第安部落的威慑力,英军得以牵制住人数两倍于己的美军。
但是,对印第安部落的依赖也给英国造成了困扰。相比于谨慎防守的英军,印第安部落更具攻击性。英军无法有效约束印第安部落的作战方式,尤其是屠杀妇女、儿童和战俘的作法,并且也刻意利用印第安人恐吓三心二意的加拿大人,这给了美国舆论以口实。所谓的印第安人对待战俘的暴行成为美军1813年劫掠和焚毁约克及纽瓦克的借口。不过,英国方面也指出,肯塔基人同样采取割人头皮的作战方式,并且残酷对待与印第安人并肩作战的白人战俘,因此美国毫无道德制高点可言。
与此同时,初战失利也给了联邦党人抨击民主共和党宣战决定的理由。此外,为战争热情所煽动的暴民则冲进巴尔的摩一家联邦党报社,打死打伤多人,这更令联邦党人愤怒不已,而民主共和党人则指责联邦党人勾结英国。后方的政治斗争也影响到前线不同党派军官间的关系,民主共和党军官指责联邦党军官畏敌不前,甚至有投降主义思想,而联邦党军官则反感对方的鲁莽冒进。在前线城镇占多数地位的联邦党人则憎恨来自纽约、奥尔巴尼和巴尔的摩的以爱尔兰裔为主的志愿兵,认为他们和后方的暴民是一丘之貉,双方甚至为此大打出手。此外,鉴于加拿大是新英格兰及北纽约州地区农产品重要的出口市场,跨边境的走私开始发展起来。联邦党人既参与该活动,又利用掌握的法庭打压边境执法人员,他们觉得这是对民主共和党人无脑发动的战争的回应。一些边境城市的地方士绅甚至与英国军官把酒言欢,并提供关于美军动向的情报,以换取他们不袭扰城市的保证。美国宪法对于叛国罪的严格界定及证人数量要求导致这些身为美国公民的间谍几乎无法被定罪。1814与1815年之交,联邦党人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开会,呼吁新英格兰各州将税收自用而非上交联邦政府,并要求增加对归化公民担任公职的限制。
面对不利的战事局面,美军一改开战以来不动用印第安战士的作法,利用不同印第安部落间围绕猎场的争夺,组织起野牛溪印第安人作为盟友。这在之后的小规模冲突中收到奇效,也令英军震惊不已。正如美军认为爱尔兰移民都是自己的天然盟友那样,英军将自身视为印第安部落的战争伙伴。然而,印第安部落对加拿大农田的劫掠也疏远了美军原本极力争取的当地居民,将他们送入英军怀抱。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摧毁的第一个村庄正是当年传教士为皈依印第安人所建的。当美军指挥官、爱尔兰移民乔治·麦克卢尔在1813年夏的一次进攻行动中要求本方的印第安人将掠夺的私人财产送还原主时,印第安部落选择离开。而在接下来的冬天,占领部分加拿大地区的美军也不得不通过强征粮食以维持补给,并且不断袭扰附近地区,试图切断英军补给。在此情况下,加拿大人主动向英军提供情报,这进一步招致了美军的愤怒,将他们通通视作美国革命后北逃的效忠派,决心摧毁他们的农场作为惩罚。
而在战线的另一端,围绕着个人忠诚度的争议同样存在。出生于美国的罗杰·谢弗将军不为其同僚所接受,成为丢失约克的替罪羊而被调职。同样出生于美国的乔治·普雷沃斯特将军后来步其后尘,除出生地外,他对法国裔加拿大人的宽厚政策也是原因之一。出生于爱尔兰的议会代表约瑟夫·威尔克斯则被指控与美军勾结,为他们充当向导。威尔克斯无奈逃往美军阵线,并从逃离加拿大的定居者中招募到130多名志愿兵,为美军效力。这些人往往充当美军先锋,劫掠加拿大效忠派。然而,当美军屡战不利时,他们也成为被怀疑的对象,甚至差点被解散。但他们最终还是赢得了美军的信任与称赞,威尔克斯更是在战场上阵亡,为美国媒体所大书特书,而英国媒体则强调杀死他的是一名加拿大人,体现出殖民地对帝国的忠诚。此外,缺乏新的南逃者也导致该部队难以为继。
战俘问题再次凸显公民身份认同在1812年战争中的关键角色。英军对从爱尔兰征召的士兵充满疑虑,担心他们随时可能叛逃,因此通过绞刑威胁和千里迢迢运回英国惩罚俘虏的爱尔兰裔美军士兵及英军逃兵,以儆效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军同时以较差的战俘营条件诱使其他族裔的美军战俘加入英军。而对英军看守的同仇敌忾则让大多数美军战俘放下族裔之见拧成一股绳,共同庆祝7月4日国庆节,重申他们对共和国理念的信仰,尽管这是以他们对黑人战俘的排斥为前提的。在战线另一边,美军也扣押英军战俘作为人质,以防英军以叛国罪处决爱尔兰裔战俘。美军同样引诱英军战俘叛逃,这再次激怒了旨在控制属民流动的英国政府。此外,由于英军战俘数量少于美军,普通美国民众不愿因叛逃英军战俘而减少同胞被交换的机会。1813年11月,70名英军战俘挟持交换战俘的船只,要求留在美国,结果被当地民众强行夺船,扭送回加拿大。这与战前美国民众对英军逃兵的维护形成了鲜明对比,体现出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公民的范围在不断缩小和被框定。
战争的结局进一步强化了不同公民身份间的区隔。随着战事拖延日久、精疲力竭的双方最终坐到谈判桌前。始终将欧洲事务作为第一要务的英国不愿为北美战事花费过多,因此对美国作了不少让步,其中便包括印第安人的权利问题。尽管强征水手一事尚未得到解决,征服加拿大更是遥遥无期,但民主共和党人巧妙地将保障美国独立烘托成战争的主要目的。加上联邦党人在战争期间的可疑行为,民主共和党人在接下来的几次选举中大获全胜。在与印第安人交往中,美国代表也以新近击败英国自许,强调英国的背叛与无力,试图逼迫印第安部落接受美国的土地要求。与此同时,国会也立法禁止外国人与印第安人进行贸易往来,并授权在边境地区修筑一系列堡垒,以进一步孤立印第安部落。英国能聊以自慰的只是两国抵制住了激进爱尔兰人的挑唆,重新言归于好。1837年加拿大爆发内乱,抗议组织者威廉·麦肯齐逃往美国寻求支持,并组织起队伍不时过湖袭扰加拿大,结果被美国政府和舆论一致谴责。加拿大效忠派强调1812年战争将忠诚者与叛徒区分开来,从而得势,开始排斥接纳新近来自美国的移民,不再给予他们土地。英国法庭也裁定,新近移民需经过一系列法庭手续方能归化,而非像之前那样简单地宣誓效忠即可。此外,英国同样逼迫印第安人放弃自己的土地及渔猎的生活方式,接受基督教信仰。
与其他学者笔下的1812年战争相比,本书更多地呈现出战争对具体个人与族群的影响。加拿大人、美国人、印第安人与爱尔兰人内部都因该战争发生撕裂,拔刀相向,原本颇具流动性的公民身份及认同也因战争结局而变得壁垒森严,“自我”与“他者”的区隔越发清晰。尽管如此,这场“内战”的某些方面却在今后的美国史得以延续,尤其是印第安部落间的厮杀,以及不同政党间的斗争。国会山事件发生之后,不少新闻强调美国社会的撕裂程度已经达到1861年内战以来的最高点。但读过此书后会发现,“内战”一直是这个国家的常态。此外,对待移民的不同态度也成了区分两党的重要标志,只不过争议的焦点已经从北境移至南境。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