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镜像生存”中的两性映像——读萨莉·鲁尼《正常人》
《正常人》在文本深处,融合了深刻和“浅俗”。这或许是爱尔兰90后女作家萨莉·鲁尼天才的地方。我们常说雅俗共赏是一个很高标准,但我看,深浅互见,或许更有难度。在这部小说中,你会发现思虑深沉,情感精微的描写观察,又有激情大胆,直露浅白的对话。这显出作家将俗滥主题写出纵深意识的能力,她把两性中悖谬的深刻,全都搁浅在日常的岸礁之上。鲁尼使原本不易觉察的平庸钝感,浮出水面。看似校园男女的“青春书写”,“荷尔蒙叙事”只是表象,相反,作品有化石般的沉积。小说中,寻常、普通、正常与特殊、个性或反常的两套符号系统,不断发生变换游戏。正常人,应是被集体性的期待视野、话语习俗,生产出的符合常规的“符号人”。作家通过情爱与友谊,既延展到原生家庭、阶层差距、亲密关系等核心,又指向精神孤立和孤独存在的生命体验。这本质上沾染了存在主义味道,他人即是地狱,而世界,是恶心的。

这部书或许可有另一别名:《校园秘史》。这秘史本是失语沉默,因为处处都受到压抑。玛丽安就像《红字》里那个大写的A,被“标记”“展示”,又排斥在正常集合之外。她的天才聪颖,玩世不恭与家境优渥,非但没有招致青睐好感,反而成了一种“原罪”。正是才高人愈妒的写照。“差异性生存”成了一个哲学性难题。一旦个体与“大多数”发生偏离,有所不同,就沦为被驱逐的离群之鸟。事实上,如今频发的校园欺凌,本质上都有同样的“发生逻辑”――被侵害者大多是“被异化的少数”,而欺负则看上去没有缘由。
这种不断从正常人里标记不正常的系统环境,是小说感兴趣的考掘。甚至,作家揭示了一种残酷:这个系统还会制裁、鄙视任何同情、尝试靠近“不正常人”的行为。康奈尔本是与玛丽安“同源的人”,如果用结构主义的观念看,他们算是有共同的思维模型。结果,康奈尔迫于周围目光,生生“硬拗”成了正常与合群。他的压抑、表演与言不由衷,造成了行动和精神的严重断裂。他既想与玛丽安保持一种精神密友、灵魂敞视,又要装成符合集体期待的“正常人”。他的痛苦来自患得患失,永远在玛丽安和世界的边缘,寄居着。

康奈尔在校园和床笫之间,反复切换着“双面生活”。小说用大段篇幅和场景,反复写两人性爱,这不应简单视为吸引读者眼球的官能策略。在我看来,它蕴藏一个“性的象征价值”,那就是融合,进入与交换。性与孤独,是互渗的辩证法,越孤独就越渴望融合,过后却发现更加孤独。康奈尔缺乏的是一种男性气概,那种自我决定的意志。他并未邀请玛丽安作为舞伴,参加毕业舞会。这应当视为小说的戏剧性事件,它造成了意义的虚空——让这对男女的关系瞬时变得可疑起来:到底是情侣、床伴还是疑似炮友?
我想借用米兰·昆德拉曾在小说里给出的一种描述,那就是“性友谊”。它是第三种模棱两可的关系处境,它不像密友纯粹,也不如爱人热烈,更不像夫妻履责,他们用身体沟通友谊,看上去“三观不正”。但这种无所谓的轻盈,超出了道德正确。康奈尔是一个“弹性形变”很难恢复的男生,这意味外界可以倾轧他,而他无法抵抗压力。一场看似“负心”的无疾而终,彻底改变了玛丽安,她开始“报复性”生活。《正常人》用一种“对倒”结构,说明康奈尔和玛丽安发生了某种置换。在大学里,玛丽安成了交际名媛,富家千金的身份,受人追捧簇拥。康奈尔反成了蹩脚尴尬的存在,他土气又格格不入,陷入自我放逐的焦虑。

这种翻转难道没有伏笔?其实,小说早就设置了社会阶层分析语境。康奈尔母亲洛兰在玛丽安家当钟点工,这一设计恰恰暗示康奈尔的隐匿焦虑与自卑本源。他和玛丽安的性事,是否有象征性逾越阶层的潜意识?这很可能是故事的一种动力因素。更有趣的是,鲁尼所经营的微妙平衡:玛丽安经济优越,家庭却破碎不堪,充满动荡混乱。康奈尔虽属底层,母亲却能提供心智上的温暖。但两人又有一个联结的共通项——就是父亲缺位。“他对未来无法生出任何真切的焦虑。如果他失业了,玛丽安别的有钱朋友会给他介绍新工作。有钱人会彼此照应,而身为玛丽安最好的朋友和疑似炮友,康奈尔也升级成为有钱人的圈内人:人们会为他举行生日派对,会凭空为他找来轻松的差事。”
这或许融合了通俗小说里“吃软饭”元素,它常是情感误解的“预装炸弹”。当“凤凰男”的自尊被自我刺痛、挤压时,有情人就难成眷属。“玛丽安似乎是一个坦诚直率的人,她会自己把所有流程安排好,他大概顶多只用陪着她坐飞机。”男性角色功能的搁浅与无用,是打破平衡的一个要素。康奈尔或许只能靠聪明和成绩来宣示价值,但这丝毫不能缓解身份意识的焦虑。他能想见玛丽安父母的态度,“他们大概本来也不待见我。他们估计想要你和医生或者律师交往吧”。对于玛丽安而言,康奈尔却有一种“无用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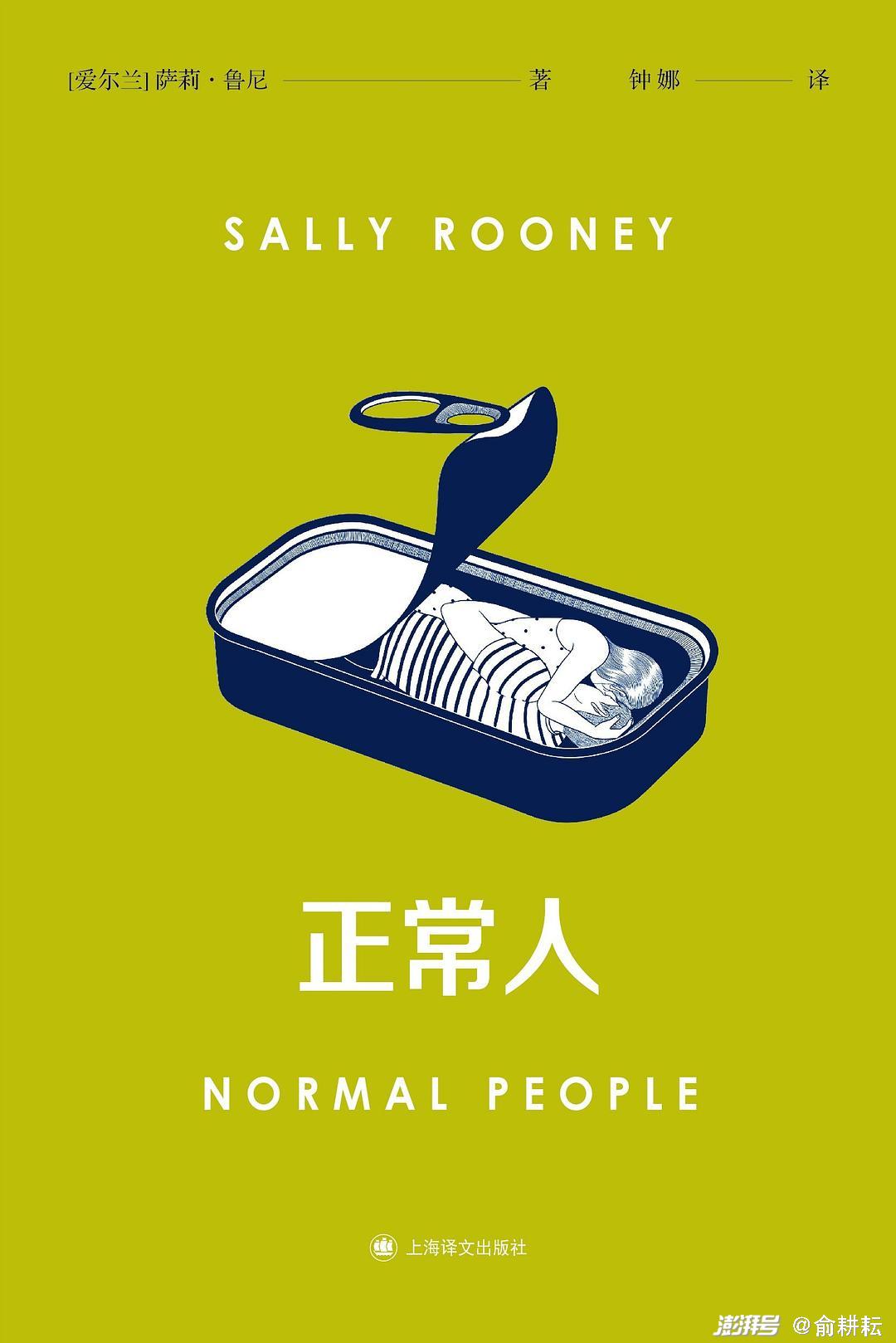
“康奈尔能让她开心。这是他可以带给她的东西,就像金钱或者性。和其他人在一起时她看起来那么独立和疏离,和他在一起时却不一样,她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是唯一一个知道她这一面的人。”密约的共享,是小说从中学到大学延续的漫长游戏。保守秘密,似乎加深了禁忌与亲密。即使玛丽安有众多男友备选,但康奈尔始终是唯一的不可替代。他就是她的“开关”与“阀门”,决定了她的模式状态。但这种亲密又没达到默契合体的境地。当康奈尔付不起房租,想住进玛丽安公寓,又耻于开口,玛丽安却误解了,她没有搭茬。“他还是哭了,既为自己的可悲,居然企图和她同居,也为他们之间结束的关系,无论它具体算什么。”
康奈尔和玛丽安,就像那喀索斯看到水中倒影,却不曾自恋,反而躲闪。“而在她看来,继续喜欢一个永远都不属于自己世界的人很搞笑,像一个他俩才懂的笑话”。康奈尔也将玛丽安视为自我的一部分,而不是他者。玛丽安是他意识存在的确证,一个封闭化的镜像结构,不容许第三者从外部侵入。“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要是佩吉或别人入侵了他和玛丽安之间的私密,这会摧毁他内心的某种东西——他的一部分自我,它似乎还没有名字,他从未试图去辨认它。”康奈尔的女友海伦又意味什么?意味着去除自我负重——那种投射在玛丽安身上的某种自怜。

“海伦给康奈尔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仿佛一只重得难以想象的盖子从他的感情生活上方揭走了,他突然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了。”而我们发现,这些都指向“正常人”的期待,康奈尔在悄然完成自我规训。“作为她的男友为人所知,他得以牢牢扎根于社交圈子里,成为一个能被接受的人,一个具备一定地位的人”。“他发现自己出于某种原因,急于向洛兰展示他这段关系是多么正常”。而这些,是玛丽安无法给予他的位置,效应和身份。从而,小说的主题开始转向“纠正与矫治”。
从这一角度看,鲁尼在故事里安插的虐恋口味儿,绝不仅是臣服/主宰,施虐/受虐的小众性癖,它在本质上是玛丽安创伤性的应激反应。玛丽安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同与反常,仿佛天然之罪,只有被伤害才理所应当。她可以容忍整个世界对自己蔑视,却不能忍受康奈尔对自己也抱有困惑质疑。她的感知模式是奇特的,无论是众人的爱慕追捧,还是轻蔑伤害,都不重要,本质上都没区别。“中学里的男生们试图用残忍和冷落来攻陷她,大学里的男人们试图用性爱和追捧,都是出于同一种目的,为了制服她性格中的某种力量”,“无论她是受人爱戴还是为人不齿,到头来都没什么区别。”
这正是康奈尔与玛丽安的最大分野,它决定了故事的终局——康奈尔渴望在世界中被认可,玛丽安只在乎康奈尔认同。这是一种“方向异位的悲剧”。我们发现作家的二元化编配——那就是“白月光”和“野玫瑰”。前者是海伦,让康奈尔产生归属感、忠诚感,激发他做好人的愿望;后者是玛丽安,让康奈尔觉察出隐匿的野性、创伤,无法融入世界的疏离。
作者:俞耕耘,90年生,文艺评论人,专栏作者,现居西安。微信公众号:书语云中君。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