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杜春媚评《抑郁帝国》|病亦非病?——抑郁症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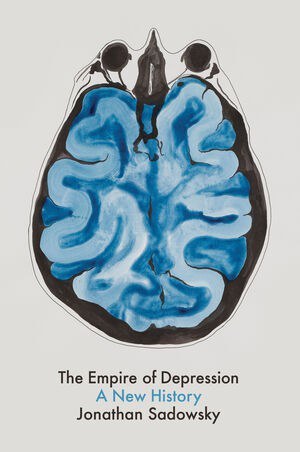
Jonathan Sadowsky, The Empire of Depression: A New History,Polity Press, 2020
很少有疾病如此神通广大,它似乎可以将心灵噬空,让人感到生不如死。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抑郁症(depression)列为全球重大疾病负担之一,到2019年,有超过两亿六千四百万各个年龄段的患者,而自杀也成为十五至二十九岁人群的第二大死因。然而,众多的学术讨论、社会关注以及江湖传说似乎令人愈发迷惑:抑郁,究竟是人生难免的正常情感,还是必须治疗且可以治愈的疾病?是人类普遍的生理性产物,还是与文化密不可分的社会性存在?抑郁医学化,究竟有助于消除社会偏见,还是令人过分依赖药物而忽略了真正的人生问题?医学史家乔纳森·萨多斯基(Jonathan Sadowsky)在其新著《抑郁帝国》(The Empire of Depression: A New History)里,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这些灵魂之问。
如果想从书中获得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那么你会失望;因为至今还没有人可以做出满意的回答。但如果你愿意接受一个不以二元划分的解读方式,那么这本书会向你揭示抑郁的种种维度与复杂面向。书以“帝国”命题有两层含义:一是在西方社会和精神病学中,抑郁自二十世纪后期取代了其他相关语汇与观念,成为解释精神苦恼的一种主导方式;二是尽管不同社会对抑郁情绪的描述有所不同,但抑郁症已经在全球蔓延与传播,成为一种世界性疾病。
在剖析抑郁这个庞大帝国时,作者选取了四个维度贯穿全书:第一、抑郁为历史与文化所形塑,但跨时间和地域的比较既为可能,也有必要。第二、我们不必纠缠于抑郁是生物性、心理性还是社会性的问题,而应将之视为一个综合性的存在。第三、抑郁中存在着现实的不平等政治。第四、专业内部的纷争给抑郁症的社会认知造成了负面影响。
和当今主流医学史的书写一样,这本书中的抑郁史亦是一部西医主导的历史,抑郁的观念也被视为现代西方历史的产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忧郁症”(melancholia)据说是由黑胆汁过多引起的,要通过导泻进行治疗。到了基督教主导的中世纪,忧郁则变成一种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患者的痛苦是否要受到谴责,而治疗方式也类似于刑罚。高举理性火炬的启蒙时代开始偏重抑郁的物质属性,而从“忧郁”到“抑郁”的现代性转向也于十八世纪正式开启。1987年,百忧解(Prozac,即氟西汀)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使用,揭开了当代抑郁症发展史的新篇章;另一抗抑郁药的主要品牌则为制药巨头辉瑞(Pfizer)公司的复苏乐(Zoloft,又名左洛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一种对于抑郁症的新认知已被广泛接受——抑郁症由“化学失衡”(chemical imbalance)造成,与大脑中的神经元传导、激素含量和基因构成等都有关联;因此有一些人更容易患抑郁症,抑郁症也可能遗传。伴随着制药公司的大力宣传,从医界到社会都日益强调抑郁的生物性:既然抑郁症有据可依,那么它的确是一种“真正”的疫病,所以必须进行治疗,甚至终身服药。
“我有药,你有病吗?”是对资本左右疾病与治疗的绝佳讽刺。抑郁似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病征。奥尔德斯·赫胥黎在1932年创作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曾描绘到,未来乌托邦世界里的人类手头常备一种“万能丹”,只要吞下,烦恼立刻烟消云散。可事实上,“百忧解”不但不能解百忧,有时还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和药物成瘾。同时,当商业药物对于医学和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时,过度诊断的危险确实存在。然而萨多斯基也强调,抑郁症患者的剧增不能完全归咎于资本的操纵与裹挟,至少有其他三种可能共存的原因:患者确实在增加;诊断手段和能力增强;以及诊断标准本身发生变化,一些过去不被视为疾病的情绪现在被诊断为抑郁症。同时,抑郁症的医学化可以令很多病人摆脱自责的痛苦,减轻社会耻感,从而易于接纳自己和接受治疗。
尽管绝大多数人都同意严重精神疾患(psychosis)属于疾病范畴,例如精神分裂,然而对于抑郁,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人都难以达成共识。何为正常?何为疾病?谁来界定?在健康与疾病的光谱内,如何划下那条清晰的分界线是一场不会停止的马拉松式拔河。美国精神医学协会编写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是目前西方最为权威的参考指南,其中对于抑郁症有明确的诊断标准:患者必须具备九种症状中的五个以上,包括每天大部分时间心境抑郁、对于几乎所有活动丧失兴趣或愉悦感、失眠或嗜睡、感到无价值或过分内疚等,同时满足症状持续两周以上的条件。
作为精神病诊断标准化的最早努力之一,《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于1952年出炉,2013年的第五版在第四版的基础上历时十年修订完成。但即便是这部由业界最权威人士编写的指南,自出版之日就争议不断。著名精神科专家和心理学家领头公开抨击它将“正常”状况“医学化”,比如丧失亲人后的悲伤状态也被列入抑郁症的范畴,而在上一版手册中则被列为“例外”。更有持极端意见者认为,抑郁诊断根本就不符合真正的医学标准,因为它没有清晰可见的伤口,只有模糊与变动不居的定义;抑郁只是社会和文化的问题。

作者指出,在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抑郁都被视为一个综合的存在;精神疾病从来不止关乎“精神”,向来也关乎身体。将抑郁属生物性、心理性还是社会性的结论视为单一选项,这种排他性思维本来就是新近历史的产物。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man)的研究表明(参看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 Depression, Neurasthenia, and Pain in Modern China),传统东亚文化强调身心的互动与内在关联,认为身体并非只是心理的表征。正是这种兼容身心的观点令神经衰弱这一病症在中国被普遍接受,而在西方却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医学模式和社会模式也并不矛盾,健康、疾病和疗愈从来都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存在,这并不削弱其医学性。
在对抑郁的第三个维度的讨论中,作者瞄准了疫病的政治。历史上不乏用精神病作为标签以惩罚特定人群的例子,例如十九世纪的美国将试图逃离奴隶主暴行的黑奴视为精神病患者(drapetomania,漫游癖),欧洲社会也曾将有色人种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列为精神疾病;政治抵抗被污名为精神障碍,以达到社会控制之目的。乃至早期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还把同性恋列为一种反社会人格的精神病症。讨论作为疫病存在的抑郁症,必须包含对不平等政治的思考。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言,文化的隐喻影响了疾病如何被定义、理解与体验,疫病溢出科学层面的生理学之外,被不同社会演绎,因时空而变换。在精神病的历史中,权力无处不在。
作为疾病存在的抑郁症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除了种族因素之外,阶级、性别和其他社会不公也影响到抑郁症的产生与诊断。为什么全世界绝大多数的社会里,女性抑郁患者都占大多数,得病的概率比男性高一倍?一方面在青春期、怀孕、流产和绝经期间,荷尔蒙的变化会增加女性染病的风险,另一方面女性往往更多地承担了家庭的重担,在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矛盾时面对巨大的身心压力。为什么文化层次低的人常常被认为不会有精神问题,好像精神病是一种“阶级特权”?事实上,得抑郁症的不乏天才,但并非只有天才才会得病,只不过大多数患者没能够在历史上留名而已。
在最后一个维度的讨论中,作者将重点转向对抑郁症治疗手段的纷争上。对于精神病治疗的两大主要手段——药物和心理咨询——的质疑屡见不鲜:药物治疗具有侵入性,是毒药而非解药,乃至可能被滥用并导致上瘾;心理咨询非科学,聊天要是有用的话,凭自己和朋友就可以解决。这些批判藉由专业人士和大众传媒的宣传而广为人知。电影《飞越疯人院》就是最佳例证,其中深入而有力地批判了残忍的治疗方式以及精神病院中的不平等关系,额叶切除手术因此臭名昭著,甚至给整个大众心理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事实上,对于各种治疗手段最为猛烈的攻击,往往来自于心理疾病治疗的不同门派。作为医学史家的作者,梳理了抑郁症治疗领域的内部纷争。在过去百年里,抑郁症的定义与治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九世纪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疗法曾经盛极一时,然而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行为认知疗法占据了主流。前者所代表的心理动力学派强调对内心矛盾的洞察,要求长时段和频繁的治疗;后者则更加契合商业保险制度对于效率的要求,在治疗上注重纠正思想逻辑的扭曲,同时鼓励行为上的改变。
可见,抑郁症的历史不止是一部认知与治疗不断发展的进步史,也伴随着专业内部惨烈的斗争。作者提出,我们不应洗白精神病学中不光彩的历史,它的确给很多人带来过伤害;但是也不应忘记治疗帮助过更多的病人。即便是目前已经十分少见的电击疗法,也非完全无益。绝大部分病人并非被药物麻醉、受到愚弄的幽灵,而是生活确实得到改善的受益者。然而,学理上的相互指摘和对于患者/顾客的不良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对于治疗有限性的放大,再加上对于精神病的传统偏见,令很多人在治疗面前犹豫再三、却步不前。实际上,每种治疗方式可能都只是对某些人群有效,但这并不代表它应该被抛弃。如果抑郁是一个极难驯服的怪物,那么我们需要部署一批武器向它开火,而非固守一个。
今天,中国社会对于围绕抑郁症的诸多批判并不陌生:过度诊断,过度治疗,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将所有问题诉诸药物,人被物化,人生的痛苦被医学化,人类的价值被扁平化。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知识界对于类似的哲学思考耳熟能详。然而,如果说任何理论都是有限与变化的,那么我们在抑郁症的问题上是否可以摒弃非黑即白的态度呢?承认抑郁的不确定性并不等同于其不存在,承认定义的模糊并不代表真伪之间没有区别,承认治疗手段的局限并不是说弊大于利或者根本无效。所谓治标治本的二元论,也许本来就是一个假问题。如果说连断臂求生的外科手术、以毒攻毒的化疗都可以被社会接受的话,为什么在抑郁症求助的问题上,我们要如此望而却步、视为畏途?
人生存有不可避免的烦恼,无论是老病死、伤离别,还是贫困、歧视、战乱、阶层焦虑、政治压迫,或突如其来的非典、新冠。与抑郁共存并非仅是抽象的学理讨论,而是再真实不过的个体当下的痛苦。面对抑郁症,绝无浪漫,必须求助。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